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57 篇文章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外科助手的最後一天
他的舌頭嚐到一絲似苦又甜如化學糖漿的味道,莫名激動的心臟在笨拙地跳動,他匆亂的一生像個跑動的鏡頭下的混沌剪影,突然毫無預警地「砰盪」一聲,從一個霎那跳轉到另一個霎那之間。

見鬼
一切已發生的,都是正確的。如果不正確就不會出現了。

傘
她老是注意到這種極細節的事,然而沒有她的注意,那些細節仍會好好地存在著──她想,自己也是大世界中的一方極小的細節,小到可以被生命忽略。

消失的試衣間
她輕而深地在他匆亂的側臉投注了一眼,流出一抹鬆心的微笑,彷彿這淡淡的一生,從這個微笑開始變得深刻。

花期
愛情過去了,就像心上一塊即將腐化的爛肉,該挖掉的時候,就挖掉吧。

天若有情
顏繪還清楚記得仍是小女孩的庭庭朝他笑的樣子,她的笑臉是六月最燦爛的陽光。

探病
她們一行好幾個去看卞醫師,一個推一個,每個人都縮頭縮腦的笑得很羞

再快一點
年輕人發動機車引擎,轟轟轟,一長聲的呼嘯,機車絕塵衝了出去。

守靈
所幸他們聽不到思想的聲音

兒女們
她腦子亂哄哄的,也不知道心裡是氣,是悲,還是愧?也許只是累,累得她兩邊太陽穴都痛了起來。

山水
不知為何,這讓我想起「蒼蠅王」裡的孩子。

杜鵑
沒有這轟隆搖撼的聲響,天地總顯得過分空寂。

柳仲承
最惡毒的言行有時候便是來自於這種無知的單純,而我卻單純的以為,這只是學期末的一支惱人的插曲,即將淹沒在假期的歡樂氛圍。

玩具
不祥的預感如陰影湧現,讓他愈來愈肯定自己已被惡運糾纏。

浴室
流去的時光是一道傷痕

托缽僧
出世的熱情在轉瞬即逝的一生中看來,就像奉獻了生命的痛苦和恐怖。

外遇
「距離」是愛情在婚姻密室裡的呼吸,不能不小心維繫。

瘋子
生命是不受肉體圍牆監禁的永恆

一個孩子的奇思妙想
他是那麼熱衷地勤於幻想,如此自以為是地在有心編織的幻想中快樂翱翔。

夢見
我夢見你夢見我。你夢見我夢見你。

賊
冷雨打著他已經濕掉的頭髮,蠕動的軀體像不斷緩慢地破碎又重組的黑色波浪。

雨季以後
她厭惡雨季,在每年雨季即將結束的這個時節,她總希望有意外的好運降臨。

歡迎好朋友
他不會用言語表達善意或需求,肢體語言是他經常用來表達意念的方式。

再見阿興
我沒有辦法一再一再地回頭,因為我內心深深明白,只要我再回一次頭,那份不捨就會牢牢地攫住我,讓我永遠也走不開了。

楊宇的一週大事
來不及了,你不想長大,就代表你已經開始長大了。

假作真時
她感到生命的不公,人生的不值,命運的坎坷多舛,然而改變不了的好像只有抱怨和憤怒可以告慰她的痛苦。

相親大作戰
相親不一定會相愛,但有誰說相愛就不能相親呢?

贅
月白星稀,夜涼如水,疏枝濃葉隨風輕擺,空曠的石子路彷彿還留著我輕捷的跫音。我吸著空氣中飄浮的槴子花香,一步步走向陰森恐怖的棚屋。

衙門
也許那不能算是件特別的事,但是對兩個孩子來說,已經夠記得一輩子了。

絲瓜藤蔓下的靜午
我找到那個被我用樹枝做上記號的鳥塚,摘了幾朵絲瓜花放在塚上,蹲在綠蔭下,聽著蜜蜂在花間採蜜的嗡嗡聲,彷彿又看見幼鳥們臨死前的哀鳴。

祭
天的光線慢慢由刺眼轉成暈黃,像灶裡將滅的火焰,餘溫蘊藉,跳動著清寂的光暉。

穗裡
陽光下的她有如一隻鬼魂,陰灰中帶著點透明的質感,彷彿隨時會從人群間蒸發,就好像她平白無故出現在這兒那麼簡單。

我要站著尿尿
豆味家的孩子

我不是太子
動漫風格散文體短小說

Vegetarian Dieter
動漫風格散文體短小說

鬼事
期末考前的深夜,宿舍裡一片燈火通明。那天寢室裡的六個同學裡,只剩下我和阿憲挑燈夜戰。我們的寢室靠近浴室,廁所卻在長廊的另一頭。因為相傳廁所曾經有一位學長喝農藥自殺,所以浴室成了我們半夜小便的地方。是晚,阿憲跟我講起學校的另一則傳聞。他說,你知不知道宿舍門前的地上為什麼畫一朵紅色的大蓮花?

搬家
其中向街的那間房門敞開著,灰沙沙的磁磚地面像鋪了層細雪,朦朦朧朧映著一片青色微光,落地窗沒關嚴,鼠灰色窗帘布裡躲著風,波浪似地起伏著。

玄夜
娟娟牽著兩歲女兒宣宣的手,沿著老舊公寓的樓梯間一級一級往上爬。她們家是頂樓加蓋的違章,整個炎炎夏日都開著冷氣。宣宣怕熱,一熱就長疹子,因此冷氣全天候開著,母女倆幾乎成天都關在屋子裡,很少出門。宣宣抵抗力弱,既怕生又愛哭,出門玩一趟回來十有八九要看醫生吃藥,這兩天宣宣又感冒了,娟娟也跟著被傳染。

狗
他在昏灰的光線中慢慢的、機警的走到窗邊,揭開窗帘往外覷。巷子裡慘白的路燈像把刀似地切進來,詭譎得像一部恐怖片。然後我聽見一片歡快的驚呼,門被新新匆亂地打開,一條黑影跟著飛躍進來,撲在新新身上。

那天
那是一個晴美的黃昏時刻,燦爛的夕照透過斜紋布窗帘滲進來,室內像漾著火光的海底,飄著一絲夏日將盡的鹹腥味。我昏沉沉自睡夢中爬出來,帶著濕粘的汗水和燥渴的舌苔。「是誰拉上窗帘的?」我自言自語起身,嘩一下扯開窗帘,夕陽的金光刺痛我的雙眼,晚風卻靜靜吹著,掀起輕盈的帘腳。

冰紋
有時候她也無法理解,人生為什麼不能照著「對的(也就是她的)規則」前進,她的價值觀為什麼得接受他人的扭曲,在掙扎中求存,如果她不是這麼烈性的反抗命運,從那些不懂得什麼叫做對錯的人集結而成的混亂世界中殺出一條血路,那麼她是不是很快會被淹滅在齷齪、無知的底層?

沼澤
夏季剛剛探頭的那幾天,下了幾場大雨,雲層陰鬱得彷彿要掉下來的天空,黑壓壓地橫跨在人們的頭頂。放學回家的路上,灰沉沉的天地間扁擠著一片光束鉛華、詭色譎彩的黃昏,像爐子裡蘊著的煤,火融融地摻著炭屑。我一個人走在橋上,右手捏著一枝撿來的火箭頭筆蓋,在鉛石拱橋的扶手上假意飛馳。

愛愛
那時,我住在一棟有壁癌和到處霉斑的老舊公寓的四樓,天天和兩個髒得像豬的「臭男生」搶廁所。悲哀的是,我竟然習慣成自然,完全沒有意識到日復一日加諸於生命空白處的,仍是空白。我如何料想得到,只要我再多走一條街,每個月再多貼一點錢,就能擁有雲泥之別的幸福。

外婆
「聽媽說小舅請了個外傭照顧你們,怎麼沒看見?」我一進門便問外婆。「我叫你舅舅帶回去了。你知道嗎?我差點給她悶死,還拿東西丟我呢,你說可不可惡?」外婆心有餘悸地說。「怎麼回事?」 「就那天我叫她幫我洗被單,她笨手笨腳的,把被單洗了個大洞,我唸她幾句,她就不高興了,拿起被單往我頭上罩...

謊言
「媽,我出去一下。」 「你去哪?待會載你去補習呢。」 「去買個東西,馬上回來。」 沈全出門蹬上自行車,往約定的地點去了。半個小時過去,沈全沒有回來,手機也不接。補習班老師打電話來,沈全媽媽只好說:「他感冒了,身體很不舒服,請一天假吧。」 沈全媽媽放下話筒,電話隨即響起來,嚇了她一跳。

以後
那以後,我感覺自己像蜷伏在一個暗繭之中,視線所及都是黑的,雖然可以聽見斷續的悲泣之聲,卻極其模糊難辨。我的思緒無法集中,介於完整和破碎的邊緣,永恆的浮游感,彷彿有太多的一生遵循著某種紛雜的秩序在解構我的信念——這以後,我慢慢的回到了一個孩子的定點,意識到我曾經有過那麼多想望,而它們無時不刻的在形塑我的執念。

擦身
他踉蹌了兩步,緩緩倒下,沉落進無邊的黑暗。時間隨著血液的脈動緩流,他倒在血泊中,像塊被丟棄的髒抹布。陽光依舊,人車冷漠。行道樹招來一陣暖風,微微掀動他額上帶血的一綹髮絲。

單程車票
天黑前,火車在英國南方一個安靜的小鎮過站,我步下車階,走入六月乾淨輕暖的暮色中,月台上寥寥幾個下車的旅客,掮著行李安靜地走向出口。這個小鎮不是預定中的行程,只因為它在晚風的吹拂下,看起來像是個過夜的好地方。站在月台上環視了一遍這座鄉味十足的車站,夕陽泊在眼前的一片茵綠的樹梢之間,...

車禍
許多年前的一個初夏,一個下著大雨的早晨,作家步雲開車去幫一班年齡及文字程度參差不齊的學生上課。她今晨起晚了,慢慢漱洗、弄早餐,等看完一份報紙,才把塗了濃濃一層花生醬的厚片土司配現打的果汁吃完,接著懶懶回房挑選搭配心情的衣服──儘管衣櫥裡清一色的寒色調衣裳,仍花掉了她不少時間考慮。

對話
「聽說村子裡那個沒耳朵的小孩死了?」 「是噢,可憐的孩子,生下來沒耳朵,腦子又不好,父母不要他,還是阿嬤一個人把他帶大的。」 家庭美髮師正在和客人談論那個沒耳朵的孩子。「誰會愛那樣的孩子?長得像隻瘦弱的小老鼠,又動不動就哭。」客人說。「總是個孩子嘛!

耽心
涼爽的秋天剛剛開展它鱗狀的翅膀,使天空看起來更加遙遠,風柔柔地吹落黃葉與枯竭的花瓣,從她身邊掃過一陣韾香。車棚裡零星散置的單車,七橫八豎地攤在眼前,她認得其中一隻黑身硬殼坐墊,剝漆壓肩低車柄的單車。那隻單車她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恐怕比它的主人更清楚它的一顰一笑。

誘
歌聲沉厚的女歌手在台上按著琴鍵,低吟出一首曲風迥異的「Without You」,情致纏綿的尾音勾引起這兒幽焱閑靚的氣氛。她面前挑著一盞紅燏的小燭火,燭火旁插水的單朵玫瑰,似乎正垂頭俯瞰窗外散撒在潔淨天空下的點點燈火。她撥了撥瀏海,露出光潔的前額,右手支頤,左手輕輕撫過燭火,玩弄著游移的焰舌。

廚房的女人
午後,沉悶的陽光漫灑在米色拱形屋頂上,微微暈出的光線懶懶地伸手搭在門前的黑色腳墊上。她倚著門框,愣愣地站著發呆。攔在門前的那一落發黃的陽光,彷彿在那兒老去了似的,寸步也懶得移動。

麻雀與孔雀
麻雀看見孔雀擔負著它的尾羽,替它難過。──泰戈爾 夏日的某一天,一個名叫丁丁的孩子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新球鞋。從很久以前,丁丁就夢想能擁有一雙鞋,就像住在對街的樂樂腳下踩著的白球鞋。樂樂的爸爸是工廠老闆,媽媽曾經是選美小姐,他有穿不完的新衣新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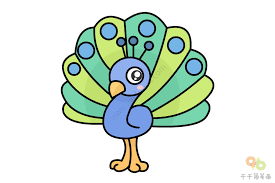
稻草人與飛鳥
我相信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說什麼。我是說,如果真的有人在仔細聽的話。然而事實上,根本沒有幾個人在聽他說話。望著眼前這個長袖輕舞的稻草人,我忽然覺得他是一隻飛鳥,而我們才是那無心無腸的稻草人。

意外
他們從來不打招呼,即使不經意對上了彼此的眼睛,也祇有淡漠地移開。然而,男人沒有移開他的早餐,女人也沒有拿走她的咖啡杯,他們仍然天天相對,仍然天天陌生。

聚會
天空陰沉地板著臉,燠悶的雨灑在台北盆地密集的車陣當中,好不容易等到紅燈擋住車陣,一朵朵閃著雨珠的傘鋪展開來,像一疋華麗氈子上的花斑,在這座繁華的城市裡流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