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我们欢迎人类学学科相关的研究、翻译、书评、访谈、应机田野调查、多媒体创作等,期待共同思考、探讨我们的现实与当下。 Email: tyingknots2020@gmail.com 微信公众号:tying_knots
137 | 思绪在哪里落脚?人类学对于哲学课题的审阅(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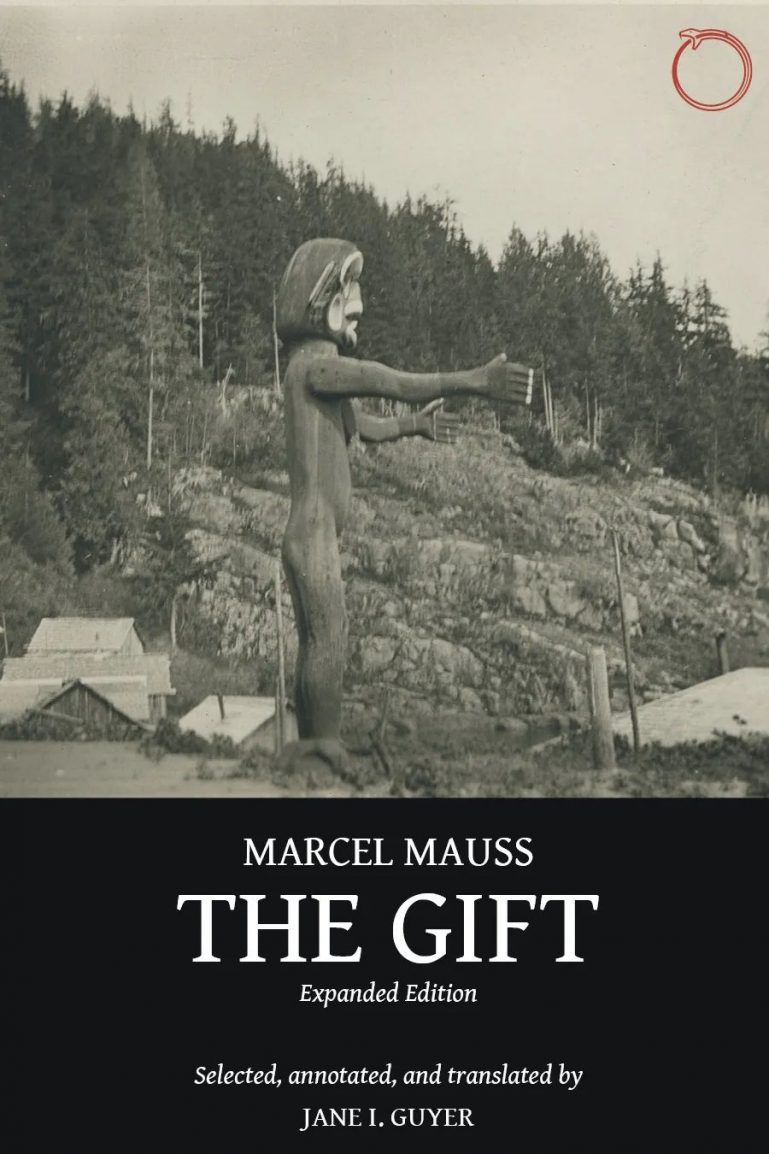
人类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可以无限追溯的渊源,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学科历史,人类学家的思考倚重于哲学的概念与知识传统,而哲学则试图在异域的民族志中寻求西方认识论的启发与替代。然而,壁垒森严的学科分工想象让学者们固守领地,人类学家满足于负责“特殊”的民族志写作,哲学家引述经验只是为了充实“普遍”的分析,二者一面暧昧相望,一面彼此拒绝。
回顾哲学和人类学交织的历史是有必要的。人类学一词早在古希腊哲学已经出现,在哲学受到其他思维范式冲击时,人类学的立场和哲学人类学为人立法的倾向每每是康德、舍勒、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背水或仰攻的阵地。不同于思辨追寻“人是什么”的哲学和神学人类学思辨,近代以来的人类学实践强调通过田野,接触异质的文化,在实践中进行理解、思考和深描。这套语法虽然在20世纪才系统化为人类学的学科,却早已在历史的流转中与哲学家相遇,是卢梭遇上的加勒比人,康德在哥尼斯堡读尽的旅行日记,黑格尔在海地革命里发现的时代精神。而在现代人类学理论奠基的年代,经典的人类学现象、概念与理论也总刺激那个时代最卓越的哲学心灵不断回应和思考。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基于世界范围内民族志材料提出了互渗思维的理论;太平洋的马纳(Mana)概念对20世纪初欧洲现代社会反思启蒙的持续共振;维特根斯坦多次阅读《金枝》,从中获取的灵感启发了他“语言游戏”等一系列后期思想;莫斯的礼物理论不但是最具生命力的人类学辩题,也激发着德里达、马里翁(Jean-Luc Marion)等哲学家的不断回应。
对读哲学与人类学不是去攀附两门学科的亲缘性,更需要的是超越西方中心和学院中心,与在地的行动者一起构筑经验和理论的连续,揭示和理解被压抑和忽视的声音和思考,学习田野里涌现出的伦理和反思:正如作为记者的福柯在伊朗革命时所体察的“灵性革命”,乌鸦族印第安勇士教给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的“基进希望”,正如亚马逊部落启发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对本体论的再聚焦,埃及穆斯林女性的读经运动中马木德(Saba Mahmood)开始了对现代社会自由和伦理观念的反思。无论是丰富对人的境况的学习还是重构对世界的理解,人类学与哲学都需要从典籍转向实践,并在对实践的共同聚焦中重启交流、对话。
哲学人类学是结绳志与哲学社共同策划的系列专题。我们试图通过共同译、校的方式来开启一种共学共读的模式。这是一场去中心化的合作,目的并不是要辩论人类学与哲学的高下之分,而是试图与文章的作者们共同探讨,人类学与哲学在当代如何以新的方式彼此联结、彼此贡献。
本篇为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存在主义人类学家,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D. Jackson)的文章,原文副标题为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Project of Philosophy。本文将critique译为审阅,与其说是以人类学的视角批判哲学,倒不如说是将人类学的视角带入康德批判哲学意义上为思考立法的努力中,看看人类学和民族志可以为哲学做些什么。
思绪在哪落脚、交汇?思想在哪凝聚、诞生?这些过程只发生在学者的书斋之中和课堂上吗?它们的脉络必须只能通过梳理历史和谱系才能叙述吗?它们可不可以就发生在我们的周遭世界之中——现在、这里?杰克逊以反思哲学课题为出发点,引用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以及现象学内生活世界(lifeworld)和人生哲学(lebensphilosophie)等概念,来提议民族志研究方式能够实现思绪本身的政治性和事件性,也就是说它是人类主体间,公共和私人领域间权力关系的表现。文章大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杰克逊认为思绪落脚点是一个社会空间,在其中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摸索前行,所以思绪的萌芽到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主体间交流与分享的过程。有了这个背景铺垫之后,杰克逊主张民族志研究方式的有效性,因为它的假定就是通过沉浸于他人的生命世界中,我们悬置了自身先验的理解,从而使得我们能够站在一个第三视角来判断他人同时自身。第三部分,杰克逊把民族志研究方式从一个方法论提升到了一个思维模式—“旅行想像”。不仅是肉体更多是思想上,杰克逊主张一种持续的“流亡”状态,也就是不避世但是总是站在“别处”思考和判断“这里”的情况。最后,回归到最初的问题——思绪在哪落脚?——杰克逊认为哲学应该舍弃这一假设,即思想以及从它引申出的一系列价值标准拥有启迪和引领人类社会进程的特权。他主张一个实践主义的态度,即思绪本身和人类切身实践密不可分。
原文作者 / Michael Jackson
原文标题 / Where Thought Belongs: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Project of Philosophy
译者 / Michael
校对 / 星原、子皓
旅行的想像 【12】
判断暗示了远行,远行意味着艰辛——连续不断地转变视野,偏离到险峻歧路,而且不停动摇观点。民族志研究的艺术就是把这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Deleuze and Guattari, 1991)转化成好的描述,就是在四海漂泊中寻求益处。
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无家可归是哲学家生活方式中的一件幸事(Arendt, 1971: 199-200)。在他的劝勉篇(Protreptikos)中,他把心智的人生(the life of the mind/bios theoretikos)歌颂为一个陌生人的人生(bios xenikos)。追求求知的人生(the intellectual life)最好在无处,最好什么都不做;对个别情况的纠结和对本地事物的效忠只会阻碍这种追求。在他看来,真正的思考不需要为其服务的工具或是地点,因为“在世界上无论何处当一个人的思维开始运行,他/她会在所有方面被真理的存在所包围” (Aristotle, 1962: 34)。而我赞同汉娜·阿伦特的观点,思绪不能从实际的、物质的和感官的周遭世界中逃离出来,而且我想像她可能也赞同梅洛-庞蒂的观点,哲学不是关于从尘世中抽身,而是关于“侧方位移”(lateral displacement) (1964: 119),这能够使一个人从其他立场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一个人寻求的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之内的“别处”,而不是一个在时空之外的“无处。”对于一个民族志研究者来说,这个别处是一些其他社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些其他时间段。
对于汉娜·阿伦特,“他性”(otherness)有着一个非常切身的含义。作为一个流亡他乡的德国犹太裔学者,她的边缘化身份是被迫的也是自选的。后者的意思是她有意识地从自己作为被遗弃者的身份中找出美德(Arendt, 1944)。具有意识的被遗弃者就像讲故事者、诗人和难民一般,作为陈述式人物(discursive figure)代表了没有被同化、不安和背负怀疑的人。这种疏远可能赋予了被遗弃者一个看到和看穿这个驱逐他/她的社会的能力。
人类学家称之为“局外人价值。”局内人觉得从不同于自身的观点看世界是非常困难的,被遗弃者却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坚守的领地,没有要保护的利益。作为一个访客和滞留者,作为一个总是被推着向前的人,他比会换位思考的好公民更加自由。这不花费他任何东西。在尝试一系列的观点时,他不会丧失任何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因为他已经被标注为游离边缘、失去家国、不可预测。这种被遗弃者的“旅行的想像”意味的不是一个客观的立场(被遗弃者不寻求冷漠或是和他人保持距离),也不是一个移情的立场(被遗弃者对于在他人身上丧失自我没有兴趣);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试图尝试其他身份的方式。结果不是一个对他人世界超脱的认识也不是一种和他人世界观移情式的融合,而是一个换位思考但是不优待任何一个观点的故事。但是它扰乱了任何读到或者听到这故事的人心中确定的事以及对确定性可能存在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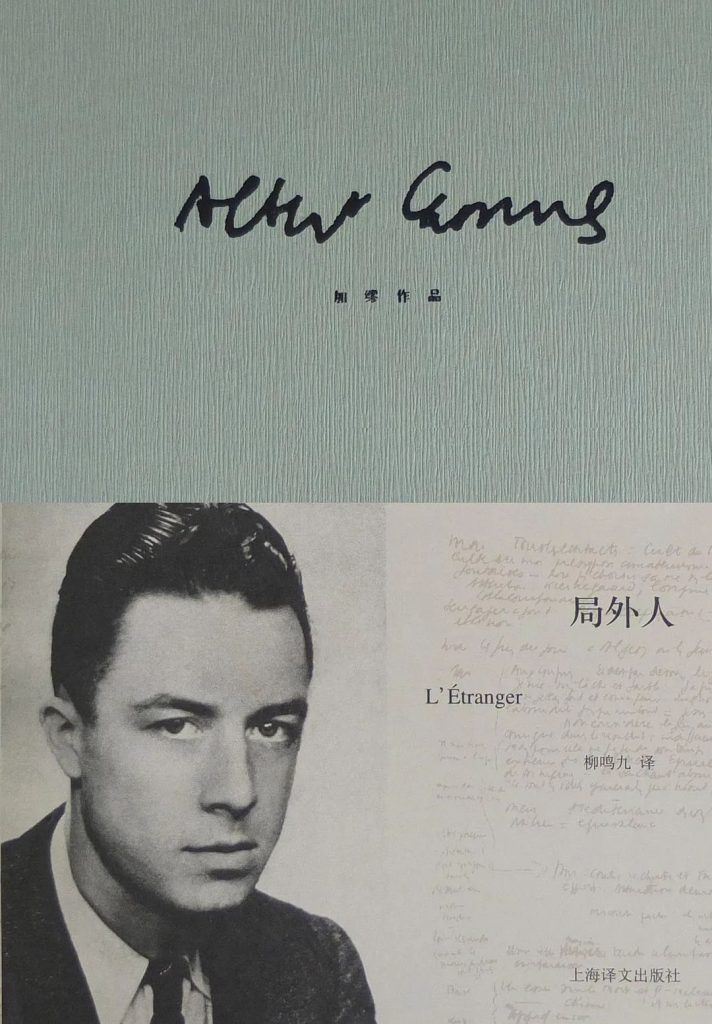
流亡者如乔伊斯(James Joyce)、贝克特(Samuel Beckett)、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阿伦特,所写的作品都具有这样怀疑的、充满创造性的疏远的口吻。所以,加谬(Albert Camus)所称的“清醒的冷漠”(lucid indifference)也是和错位产生的距离感相联系的。这不是从一个享有特权的“无处”看这个世界,也不是和个别人或是群体结盟在他们拥有唯一真相话语权的情感基础上【13】,而是以一种质疑所有号称享有特权的理解的方式,来串联一系列具体的观点。无论他人的观点有多令人憎恶,它代表了对于自我在逻辑上的一个可能性。正因如此,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不同总是受限于我们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被预先决定于某些基因、文化或是道德的本质。
思绪在哪落脚
要让哲学在人类生命世界中扎根,我们就要放弃假设思想理应揭示某个文化、社会和个人的本质,也要停止以一些抽象的伦理或逻辑的理想为标准来评估一个信仰或行为。实际上,这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探索思绪、言语和行为如何和人类利益紧密相连,并以它们为人类福祉产生的结果为标准来衡量它们的价值。正如约翰·杜威观察到的,“思考不是自发的燃烧;它不仅仅发生在‘广泛的原则上。’具体的事物造成和唤起了它,”这包括“一些混乱、困惑或是怀疑”(1991: 12)。这可能是一个历史上的危机或是灾难,如美国内战让奥立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坚持盲目自信会导致暴力、让他发展出一套拓展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从中诞生了实用主义(Menand, 2001: 61)。亦比如纳粹势力占据德国的时期使卡尔·雅斯贝尔斯开始思考: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与其说是理解人类存在意义的方法,倒不如是从其中逃离的捷径。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相比于“规划的整体教条”,那些在可被全面地思考或是轻易地叙述的事物范围的边缘所产生的思绪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加珍贵(Jackson, 2009)【14】。
一些情形下我们的幸福依赖于实际和专门的技能,对此,思绪也同样重要。面临连年的庄稼歉收和挨饿的可能性,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居民的解决之道被我们称为“魔法”,仿佛他们控制世界的技术只是下等的科学和婴儿式的哲学。然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展示的那样,要理解特洛布里恩的花园咒语(garden spells)不是看它们是否符合某些理性、逻辑或是宗教原则,而是要看到它们的实际效果——激励园丁的自信心,使其专注,和帮助他投注全身心到手头上的工作。一个富饶的花园不是咒语的直接结果,但是是一系列劳作的结果,包括仔细准备泥土、种植芋头然后呵护作物。
批判性反思或许也产生于极度贫困、不平等和权力不平衡的情况下。比如说,考虑凯南尔姆·伯里奇(Kenelm Burridge)拜访美拉尼西亚的马纳姆岛(the Melanesian island of Manam)的描述。在拜访期间当地贵族向人类学家揭露了他们的祖传学问,被安置在一本“书”中,但其实是一系列覆盖着灰尘的由龟壳、硬木和石头做成的传统物件。给予这个白人如此的信任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问他为什么使白人如此富有和强大的学问没有被分享出来,而且为什么伯里奇应该随身携带的“信息”,那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信息,没有被交流给他的美拉尼西亚兄弟们。人们在边说边潸然泪下。但是一个莽撞的年轻男子没有咬文嚼字:
你看,你见到的这些物件(祖传的学问)属于我们。它们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而且是我们的仅剩的一切。我们认为白人欺骗了我们。所以我们重新转向了我们的祖先。为什么白人拥有这么多而我们这么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尝试找到它。人类学家的回答呢?“我没有什么可以说,我哑口无言。” (1960: 6)
这样的遭遇暗示着,当人们寻求指引、启发或是建议时,得到的答案内容本身是什么并不总是那么重要,不管是来自一个专家、传统或是典籍。重要的是自由地说出自己烦恼并被聆听的这一过程和行动,因为在诉说或是行动中一个人有效地具象化了他/她的所想所念,而且这本身就改变了一个人对窘困的体验、减轻了负担、恢复了能动性(agency)并且舒缓了他/她的孤单感。简言之,诉说和行动就它们本身而言是有道德上的好处的,不论说了什么或是行动的后果是什么。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思想和它所回应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它所具有的认识论上的特点。让我们以所谓的原住民对生理父系(physiological paternity)的否定为例。这不是在反思原住民们的愚昧无知(或错误想法),而是在反思为什么他们会需要建立的关系不是和个别父亲,而是和他/她的父系原居地。如艾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所说,基督教教义中的基督为童女之子这样的信仰,在脱离了语境后看似没有理性,然而一旦考虑到其实际影响,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在这例子中,肯定基督是上帝之子是一个需求(Leach, 1969: 95)。西方哲学中形而上的偏见不单单导致了欧洲学者在评估或者解释非西方信仰和习俗时只考虑它们是否和客观现实有着逻辑上的连贯性或一致性(在生理父系的上述例子中,生殖方面的生物学“事实”);这偏见甚至促使许多非洲哲学家寻求一些理智层面的至高点来解释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要么发现,相比于崇尚“系统性”和“思索性”的康德思想,他们自己的传统有所欠缺 (Wiredu, 1996: 114),要么他们只关注那些可以和西方圣职人员相类比的本土圣人和仪式专家。在这观点下,只有当非洲开始接近西方对于文明的构想时,非洲才会显得有意思。这种文明构想包括纪念碑式的建筑、一神论的宗教、集权的国家、高端的科技,或是拥有像柏拉图般的哲学家、神圣或深奥的典籍和对于宇宙的深邃认知,比如,被法国民族志学者马赛尔·格里奥尔(Marcel Griaule)认为是归属于西非多贡(Dogon)圣人Ogotemmêli的知识(Van Beek, 1991)。甚至那些批判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哲学家,在主张“传统和非传统,作为理论上可互相替代物,都必须给予法律上的平等和互惠的阐明价值”(Hallen, 1975: 261)的同时,他们也倾向于用“秘密的先贤”(Hallen, 1975: 264; Hallen and Sodipo, 1986: 8-9)来解释“高雅文化“或是“伟大传统”,而非探索普通人在存在方面面临的困境。对我而言,正是这些困境构成了所有思绪生根发芽的土壤。
所以,在任何传统中——美拉尼西亚、非洲、东方或是欧洲——思绪在哪落脚?它不一定在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展现,被孤立于象牙塔中,在拜访图书馆期间显现,蕴含于抽象的言语中,避开“俗”或“大众”文化并且号称拥有普世的真理。它也不需要存在于神话、宇宙学、谚语式的智慧和信仰(巫术、魔法、祖先影响和仪式)中,如维瑞杜(Wiredu)等人所暗示的【15】。哲学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职业,也不是一个发生在被保护区域中的活动。它是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形式,而且就它本身而言,它是我们每日生活中所做、所食和所思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就是尼采(Nietzsche)所主张的,哲学思考和其他有意识的思考一样,是一个“本能活动,”而且每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都是“作者的自白和一种不自觉、无意识的回忆录(1973: 17, 19)。”这是一个福柯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坚持的观点:思绪在我们自身内找到有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不一定是被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思考主体所创造的。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思绪也是类似这样子落脚的——而且可与栖息和构建相比较;这是一种构建活动的模式,一种栖息在这个世界中的方式(1971: 146-51)。对于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思绪属于积极生活(vita activa)——充斥着利益、交流和主体间共享的社会场合。在这里,它以细心、关切、照护、洞察力和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库兰克(Kuranko)人,这些社交技能定义了一个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格(personhood; morgoye)包括了关切他人(gbiliye)和尊重他人(lembé)——认可他人的地位、支付他人应得、为他人的幸福做出贡献。同时,人格在自我约束、控制自我情绪、斟酌言语、考虑大局中实现了升华:
“Morgo kume mir’ la I konto I wo fo la (一个人讲说他所想的任何话;换句话说,先思考再说,以免你脱口而出愚蠢的想法)。”
“I mir’ la koe mi ma, I wo l ke la (你做你想到的事;换句话说,先思考再行动,以免你的行为和意图不符)。”
正如我朋友赛瓦·科罗马(Sewa Koroma)所说:
“当人们说话或做事时,你必须再三思量,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如此行事——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吗?我现在还年轻,但我不得不思考就算酋长(Diang)寿命很长或者我死了,我的孩子正在成长,而且如果我能得到酋长席,孩子可能会对此感兴趣,你是知道的。人们不写历史,他们不把事情写下来。你必须要记住任何事。我们说,‘i tole kina i bimba ko’ (你的耳朵和你祖父的话语一样聪慧)。当我父亲还年轻时,他听长辈讲述发生在很久之前的事情。然后他告诉了我这些故事,我将会把它们告诉我的儿子。它们没有被写下来,但是如果你倾听,你就会知晓这些。它们是你必须思考的事情,你必须用心体会的事情。阿德(Ade,赛瓦的妻子)说,‘你想得太多了’,但是我告诉她有些事情你必须要思考,超越平常的事情,然后你将会知道。”
显然,反思包含了超越自我—从自己祖辈的经验和理解的立场来思考自己周遭处境。这不是寻求一个超越世俗的观点,而是为了识别那些位于日常而自我中心的意识之外半影区的那些因素和势力。但是反思不是关于探索他人心智的灵魂深处,或是达到移情式的理解;倒不如说它注重于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库兰克人拒绝揣测关于他人的经历。一个人被告知,“我不在他们里面”(n’de sa bu ro),或者“我不知道什么在里面”(n’de ma konto lon)。移情式理解不单单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思考,它还被认为是和做一个有高情商或常识(hankilime)的道德高尚的人完全无关。库兰克人的重点不在于和他人一条心,而在于和他人一起行动、工作、吃饭和共处(通常在一种友善的沉默中)。据此,西方人类学家面临的其中一个严峻的挑战是如何获取这样崇尚实际和互动性的技能,在这其中,相比于一个人能和他人友好社交的社会技能,认知他人动机、心态和情绪显得并不是很重要【16】。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他晚年写作中所形容的,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他人——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而是“一种陪伴”,这意味着没有人将会孤独地活着或者死去(2009: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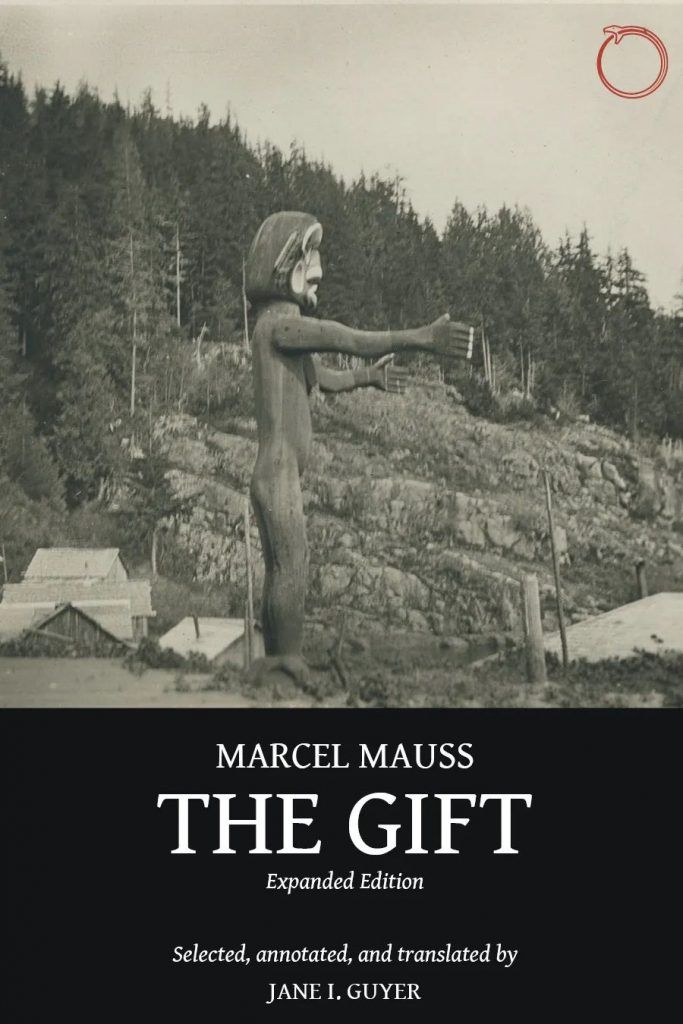
这呼应了毛利人(Maori)的传统价值观。关于莫斯(Mauss)对于塔玛蒂·拉纳皮里(Tamati Ranaipiri)诠释毛利“hau”(风、呼吸、关键本质)的概念的解读,已经有很多注解和批判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莫斯解读中值得回味的价值在于他感知到了毛利人对于努力生存和生命力(mauri ora)的重视,以对抗堕落、衰弱和死亡。“Mauri tu mauri ora, Mauri noho mauri mate”【17】——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神意味着生命,一个失去活力的精神引向死亡。生命是一场在“tupu”(呈现、增长、增强)和“mate”(变弱、减少、死去)两个过程之间永久的较量。有时,它包括了给予他人生命。有时,它需要暴力地夺取生命而且仪式般地将其吸收进自己体内。有时,它要求热情好客并且拥抱外面的世界。有时,它要求封闭和对抗。所以说,“Ko Tu ki te awatea, ko Tahu ki te po”。正因为一切都是按照其增强生命的潜力或者效力来评估,毛利人并不意外地将知识观(maatauranga)建立在“orange”(生命的必要)和“taonga”(文化财富)概念上,意味着知识就仿佛是一块肯定着个体身份的祖辈土地——生命、语言和生计交缠的基质,生者与死者化而为一的环境。求知的所有价值便在于维持包含了文化财富的群体的生息。确实,对于很多毛利人来说,知识是如此得具身化(embodied)以至于它的失去会影响它所归属群体的生命。以怀卡托(Waikato)的玛尼赫拉(Te Uira Manihera)的话来说,当知识离开家之后就会马上消散在他人之间。知识因此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和“繁殖力”。“而且世俗的知识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失去了它的tapu”(King, 1975: 7)。正如我朋友塔瓦伊(Te Pakaka Tawhai)所说的,最要紧的是生命——能够繁衍生息的生命。塔瓦伊的观点中,“古来的诠释”和祖先的智慧(korero tahito)是无价的,不是因为它们有着能够理解人类遇到的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生存困境的法门,而是因为它们是灵活多变而且适应变化的,能够“提供给讲述者一个使它们响应当前问题的能力”(Tawhai, 1996: 14)。
塔瓦伊在1988年去世了。所以我无法问他当“眼下的问题”好像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还是否能够公平对待生命。但是他坚信为了创造一个适合生存的公平的世界,思考是很多方式中的一种。在这种坚持中,我看到了他与汉娜·阿伦特或约翰·杜威这样的其他学者共享的相似点。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不需要我们声称拥有确定性或是真理;它所要求的只是我们反思我们所想所说的后果,并且为这个注定存在贫困和分歧的世界中芸芸众生的福祉做出一点贡献。
注释:
【1】原注:参考 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Heidegger, 1969).
【12】丽莎·简·迪许 (Lisa Jane Disch)在她关于汉娜·阿伦特的判断理念的描述中,创造了“旅行的想像”(the visiting imagination)这一词组来捕捉阿伦特对于旅行(visiting)的理念,旅行是一个从各种观点来塑造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故事的方式,因为这些观点都有意向讲述(自身)的故事;旅行也是一个想像自身作为其他故事中角色如何回应的方式。这种表现方式通过从具体出发走向全面。Lisa Jane Disch, Hannah Arendt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8.
【13】在Minima Ethnographica (1998: 194) 中,我质疑了萨特(Sartre)(1983: 256)、伯格(Berger)(1984: 38)和更晚近的萨伊德(Said)(1994: 44)的观点,即批判性思维必须包含转移个人观点从而使自身贴近或者“见证”庶民或是被压迫的群体,因为这些在权力中心最边缘、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居无定所或是错位的人有着对社会和历史运作真实的洞悉。
【14】唐·希曼写道:“学者不愿直面极端痛苦在意义产生上设置的硬界限,它可以同时摧毁世界和意识。”在他对于拉比夏皮拉(Shapira)在华沙犹太贫民区中笔迹的扣人心弦的诠释中,希曼批判宗教学倾向于“优待陈述上的逻辑连贯性,以至于不顾受难者对于实际效益迫切的忧虑(2008: 466-7)。”
【15】例如参考国际非洲研究所发布的一系列文章,题为非洲思想系统(African Systems of Thought)(Fortes and Dieterlen, 1965)。
【16】这一情况在战后期间戏剧性地凸现了出来。被遣散的军人经常被他们曾经带来严重死伤痛苦的村庄所接纳。接纳的条件并不是他们得经历一系列治疗或者仪式性的赎罪过程,而是他们得做好自己、尊重他人并且为这个群体做出贡献。
【17】字面意思是,“Tu在白天,Tahu在夜晚”。Tu是战争之神,并且他的灵魂(Mauri Tu)掌管着一个会所前面的区域,会所内拜访者会遇到凶神恶煞般的陈列品;tahu(向着光亮)象征着“在一个夜晚亮着灯光的房屋内缓和而安静的接待” (Te Rangi Hiroa, 1966: 373)。
作者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是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世界宗教杰出教授,在塞拉利昂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做过大量民族志研究,关注人类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伦理处境。他也是一位诗人。
译者
Michael,一个关注巴基斯坦边境的学生
Posted in 哲学人类学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28. 哲学人类学 | 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研究与马克思学(下)
129. 你的奥运队可能是个幻象
130. 弗格森 | 今日无产者政治:历史类比中的危险与机遇(上)
131. 弗格森 | 今日无产者政治:历史类比中的危险与机遇(下)
134. 阿富汗人类学书单
135. 运动员为什么要谈政治:赛场内外的行动主义
137. 思绪在哪里落脚?人类学对于哲学课题的审阅(下)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