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E别的女孩致力于呈现一切女性视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儿艺术家的创作,为所有女性主义创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书写 HERstory。 我们相信智识,推崇创造,鼓励质疑,以独立的思考、先锋的态度与多元的性别观点,为每一位别的女孩带来灵感、智慧与勇气。
芭比的进步与《封神》的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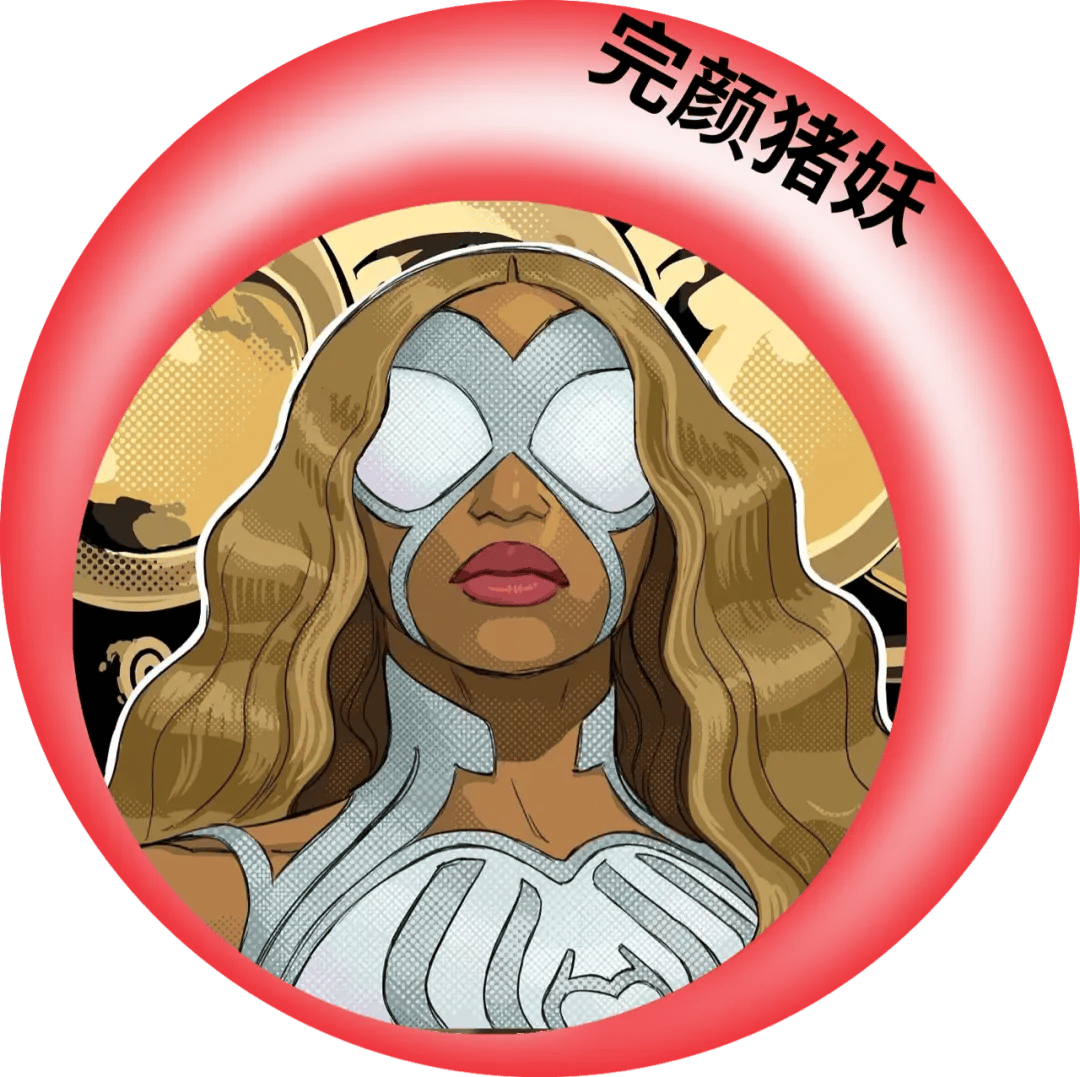
《芭比》上映期间,一部体量更大的国民 IP 兼 “重工业” 电影《封神》也在火热上映。几乎不可避免地,两部电影形成有趣的互文景观:对于父权制这个大他者,前者意图去解构、去揭示,而后者则是在追随、在暗仿,用《芭比》里那句关于父权制的经典台词来说:“当然在坚持贯彻,只是以更隐秘的方式。” 这简直是《封神》整个故事的注解,而来自市场的讨论和反馈,也验证了它的策略对观众所产生的非凡效用。
《芭比》的启蒙之处恰是《封神》退行之处。如何去开启这一观察呢?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两部戏里的 “性别少数派”:芭比乐园里的男人肯,与男人榜里的女人妲己。
显而易见,2023年的妲己已不再也不能是旧脚本中那个蛊惑纣王祸国殃民的妖孽了。任何一个对文化领域稍有敏感度的商业片导演,对旧脚本中红颜祸水的论调和归因方式都不可能不警惕。在这个新的脚本中,妲己与纣王的羁绊,更像是动物报恩的设定,而造成天下大乱的主因和祸害是纣王本人,他才是真正的操纵者,妲己仅仅是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我看到一篇讨论《封神》的文章用了 “阿拉丁” 比喻妲己,相当精辟。这一比喻指出了妲己的工具本质:她仅仅是碰巧遇到了自己命中注定的男人而已。假如她遇到的不是纣王而是许仙,那么她就会是另一个白娘子;假如她遇到的不是纣王而是大雄,那么她就会是另一个哆啦A梦。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少有女性角色出现的故事里,妲己虽不再是 “祸根”,其人格也遭到了严重削弱,被物化为一个 “承担道具功能” 的存在。甚至连 “动物报恩” 式的设定和叙事也未能有足够说服力:在动物、玩具甚至自然元素都能被赋予人格化的叙事界,一个占据不小篇幅的女妖精,反倒只能作为色相与无限血槽供主角和观众消费,很难不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退行。
然而,这样的处理在市场反馈中,却受到了不少的夸赞。微博上赫然挂着 “新版封神妲己不搞宫斗” 的广告宣传,各路营销和不少讨论也对这个新脚本中的妲己设计颇为欣赏,强调其中的进步色彩。在我看来,这简直等于今天的我们居然还在为 “女人无须再裹小脚啦” 倍感骄傲和自豪一样,十足荒诞。这样的 “进步” 对比导演主创对妲己那苍白的工具化粗暴塑造,更像是 “好汉不吃眼前亏” 的自我防御策略,以及对当下性别文化政治正确层面投鼠忌器的反应。
人们一边对新妲己的美貌和姣好体态流露善意,一边对其退居到道具层面的空洞塑造视而不见。新妲己的确卸下了为父权罪孽顶锅的悲催身份,剥离了父权制中更容易遭到诟病的道具属性,但其道具本质并未改变,只是更加不重要了而已。

事实上,与之对应的 “父权” 所处的位置也没有发生改变,它仍是舞台中心的主角,只是被聪明地分化为 “需要割席和打倒的坏父权” 和 “认清形势后理应回归的好父权” 两个阵营。
有趣的是,《芭比》和《封神》都说出了 “你是谁” 这句觉醒之言 ——
芭比:“肯,你要知道,离开了我之后的肯是谁”。
姬昌:“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在旧父权即将崩塌或已经崩塌的语境中,肯和姬发提出了 “做自己” 的命题。在前者那里,这句话意味着权力的颠倒;而在后者那里,反而是权力的再次确认。
在影片前半部分呈现的芭比乐园中,肯并没有强烈的存在感(事实上,在肯的群体中,艾伦则更加缺乏存在感,其后他也被肯与肯相互满足的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排除在外)。芭比们的快乐生活并不需要借由男性构建,而是呈现了上野千鹤子所说的 “女校文化” 状态:
“男人知道的,只是男人世界和与男人在一起时的女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男人、只有女人时的女人的举止,男人们是不知道的。在女人聚集之处,只要有一个男人登场,女人的举止顿时不同,所以,男人终究无从知晓只有女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 上野千鹤子《厌女》
这里实际上已经为肯乐园的形态埋下了伏笔。当肯将 “先进的父权制” 带回芭比世界,带领同性们建造了梦想中的肯乐园之后,在这个新的乐园中,肯展现了其在芭比乐园中未曾展露的形象 —— 用上野老师的话一言以蔽之,“男人只能爱上处于自己指导之下、让自己立于优势的女人”。代表肯的乌托邦梦想的肯乐园,也必须拥有这样的元素:假如男性无法在对方身上建立优越感,使其成为自身展现优越感的工具,那么理想的亲密关系似乎就无法成立。不得不承认,这种关系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相当普遍,以至于《芭比》对这种男性状态的模仿与调侃,几乎成为一种在女性群体中必然引发共鸣的搞笑段子。而肯乐园中也开始流行起男性想要充当女性 “保护者” 的姿态和欲望,其本质同样能在上野《厌女》列举的例子中找到解释: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

可以看出,与芭比乐园的 “女校文化” 恰恰相反的是,那些模仿了父权制的男性,其理想中的乌托邦肯乐园却需要通过女性来确认,比如在女性身上建立优越感,流行起充当 “保护者” 的姿态和欲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芭比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已经能够剥离男人的存在;而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依旧离不开女人的肯定,一旦遭到女性的否定,则面临着男性存在的危机感。
“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今天的女人,已经开始退出男人的脚本。而今天的男人从现实世界里的女人那里逃离后,转去向虚拟空间里的女人 ‘萌情’。今昔无异也。”
—— 上野千鹤子《厌女》
在父权制的世界,男性把女性作为一种资源和介质证明自身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假想的父权制瓦解的社会,男性如何才能脱离女性真正走向自己,就成了一种疑问 —— “做自己” 根本不是芭比乐园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肯乐园的危机。

但肯如何才是真的做自己,《芭比》中并没有真的给出具体答案。甚至可以说,她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是 “离开了芭比之后的肯是谁”。而在《封神》里,姬昌被安排成为一个更加完美无可指摘的父亲形象,姬发则成为骑着马高呼回家的 “亲爹的好儿子” 。在那一刻,“做自己” 跟拥抱一个 “好父权” 已经成为同一件事。
在这里,自我认知的命题被巧妙偷换了概念。“你是谁” 并不是一个探索自我的开始,而是一个回归新父权的话术与伏笔。或者说,父权规训在时代进程中学会了如何利用更现代的话语系统去创造新的话术。这是《芭比》层层套娃里的一环(《活在父权制下,你还会爱我吗?》),是未燃尽的余火、最后撞到的铁壁、见真章的红色药丸,而在《封神》那里,则成了堂而皇之的刻奇、啼笑皆非的 “进步” 和屡试不爽的和稀泥。
比时间更难穿越的,也许就是这个厌女世界的表与里。
— The End —
— 作 者: 完 颜 猪 妖 —
— 编 辑: 赵 四 —
BIE别的女孩致力于呈现一切女性视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儿艺术家创作,为所有女性主义创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书写 HERstory。
我们相信智识,推崇创造,鼓励质疑,以独立的思考、先锋的态度与多元的性别观点,为每一位别的女孩带来灵感、智慧与勇气
公众号/微博/小红书:BIE别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ender cognition, all the way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diversified views on gender.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