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女性主义文艺独立读物。 分享女性共创的电影、文学、社会评论,挖掘历史与文化中被遮蔽的女性群体表达与体验,在批判中激发生命力与创造力。
《封神》:打倒旧爹,另立新爹

正如诸多媒体与学者宣扬,以及绝大多数观众最初看到的那样,《封神》是一部以“弑父”为母题的,近年来罕见的神话史诗。但聪明的你很快会发现,它这里的“弑父”,并非真正精神上的“弑父”,而是一种“打倒旧爹,另立新爹”的“爹味无限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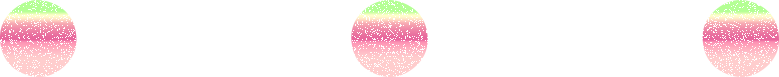

难道子杀生父、子杀养父,还不算“弑父”吗?
为回答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先回到“弑父”的概念上来。“弑父”一说,最早在学术层面由弗洛伊德提出,代表着人子“占有母亲而排斥父亲”的性欲望。自“五四”后,“弑父”的概念被引入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抹消了“恋母”的部分。而学术发展至今,“弑父”在显性的“排斥父亲”之外,更是指向对“父”所代表的,一系列“压抑性权威”的反抗。更确切地说,“弑父”是一种解构,剑指父权制中“上位者”对个体凌辱与漠视的霸权运作结构,并在此过程中寻找人性本体之所在。
如果影片难以触达到这层,它所表达的“反父”“弑父”主题,则无异于虚有其表。有媒体说《封神》借“弑父”情节“对父权祛魅”,但在我看来,该电影中的“弑父”仅是一种刺激眼球的情节设计,深层次维护的仍然是“爱父”的伦理。换言之,电影中对个体的“父”的违逆,却只是推动了父权的承继。

殷寿(纣王)通过杀父兄获得了无上权力,也因此时时忧虑。他同殷郊间就面临着,史传、小说中“天家父子”普遍难以逃过的“帝王猜疑”。
正所谓,“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说的是,晋献公的两个儿子,世子申生顺敬其父,最终被父所冤杀;公子重耳流亡在外,最终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劝刘表长子刘琦离开荆州,援引了这个典故。
实际上,诸葛亮在劝说刘琦出逃时,怀有一种默认,即刘琦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刘表的继承人——殷郊也是如此自我认为。而正是这种父子相继的“默认”足够强大,在登基礼上,殷郊请父亲传位于他,预备“代父祭天”时,才让父亲的猜疑甚嚣尘上。因此,电影中对纣王“猜疑”的批评,不过是在巩固“父子相继”传统的正当性。

再来看《封神》里“逼四质子杀父”的名场面。在这个场景与先前无数的场景中,纣王是无数次向质子旅灌输仇恨,期待他们通过杀父行为,助力自己集权控制。他说:“你们的父亲,抛弃了你们。”
四质子杀父,哪怕动手得最果断的北伯侯之子崇应彪,他的恨意,也从不来自于“父权的压迫”,而是“他抛弃我”。 换言之,激发他杀死父亲的力量,也并不是为“人”的觉醒,而是为“人子”却无法承蒙父爱的痛苦与不甘。杀死父亲后,他也获得了自己最渴望的奖赏——父所赐予的权力。

而在姜文焕不忍心杀害东伯侯时,父亲竟表现出一片爱子之心,主动英勇赴死——父为子之大业英勇牺牲,这同样是父权制下盛行其道的手段。
这时候,我们看向正在百般犹豫的姬发。姬昌对姬发说:“你不是谁的儿子,你是你自己”。假如将区区一句话就当作“弑父”精神的标杆,未免也太过轻易。再次强调:判断“弑父”的标准应是对“父权”的解构与否。姬发从“养父”纣王的影响下挣脱,转向“大义”的,是亲父的玉环和亲父教养出的长兄;是亲父送给他,又被长兄驯养转送的白马。姬发的“做自己”,只是从一个父转投另一个父,其结果是继承了西伯侯的权力与爵位,完成了父权制内部的权力更迭。

因此,无论是“做自己”,还是父亲为了儿子自杀,或是儿子杀死生身父亲、而后取代他的位置,只要父权之父不偏不倚,完成其必有的代际交换,父权制稳稳向前,那么一切的“父子”纷争,都只不过是父权制自身所允许的一种“叛逆空间”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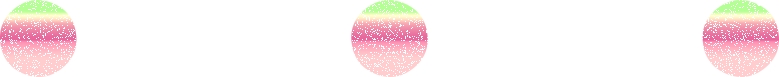

研究中古女性史的郑雅如老师,在她的《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中提到,儒家伦理的一部分底层逻辑在于:父子“天伦”。在这样一种“天伦”下,母亲不是孕育者,而是父亲的妻子。原本是天然的孕育者,通过父系的“礼法教化”,变成“其父以为妻职者,其子皆为母职”。后来,他们发现使继子自然地爱继母太困难了,于是想出了新方法:让母亲消失。
姬昌与雷震子的剧情中,姬昌在野地里捡到了形貌有异的妖怪婴儿,杨戬和哪吒要杀妖孽,姬昌愤声而辩——你怎么知道妖孽不会被教好?而后拿自己的披风裹着,抱着,送上天宫。最后姬昌有难,雷震子学成“正道”,前来“救父”,把他以相同的姿势抱在怀中救走……

这个剧情就是最传统的“母职剥夺”:雷震子哪来的?没人知道,没人在乎。“父”们只需要在地上捡到继承人,并按自己的“教化”思想去培养就行了,甚至“有教无养”,何其安全。由掌权者过剩的自我意识衍生的,在史传中困扰父系家庭千年的生育焦虑、对男性继承人的焦虑,就这样在虚浮的狂想中解决了。
继承焦虑,直指掌权者心中对“自我延伸”的渴望。“自我延伸”不仅通过“母职剥夺”得到缓解,还进一步表现为对“长生不老”追逐和“礼法教化”的正统化。
剧中的纣王,追逐“长生不老”,(怎样追逐长生不老),与父权制下为尊者过剩的自我意识系出同源。另一方面,电影通过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上一代商王死亡的“真相”。这样的情节重心,似乎意图让我们相信,纣王为天下弃的根本原因,乃是违背“礼法”——因为纣王首先违反了父权制的规则,弑父杀兄,所以他不配为“父”,不配充当“礼仪教化”的执行人。

父权制的持久稳固,得益于将男性焦虑衍生出的狂想,不断地“隐蔽”与“文明”化。他们擅长狂想,但又会排斥“显然无妄”的狂想,如对纣王追求“长生不老”及其帝王权力的否定。一种面貌更加“文明”与“得体”的价值系统——“礼法教化”下的父子伦理,以及对“蛮荒时代”的矫正乃至革除,才是电影真正选择的父权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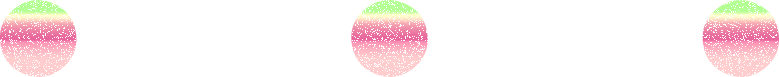

在上野千鹤子老师的《厌女》中,她提出了父权世界对女性的二分法,“圣女”与“娼妓”。再具体点说是:装点其社会地位的“圣女”,与维护其个人尊严的“娼妓”。通过这样的二分法,他们在女性群体中划分等级,设法规训女性,使她们互相蔑视。
《封神》中的姜王后与苏妲己,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本土二分化的结果。很显然,妲己虽是“妖女”,却仍是对男人无害的“妖女”,是其自我意识的延伸,让人十分有“安全感”。电影中,作为“圣女”的姜王后是如此“信任”她的丈夫,以致于她“相信”一个无法直接掌握实权的姬妾会是一切的祸主。她是那样的“孤注一掷”“聪明勇敢”,一心一意地为了她的丈夫与儿子,去诛杀这么一个“祸国妖孽”。


按现代人视角来看,这样的“圣女”与“娼妓”相杀的事件发生在古代似乎是“尊重历史”的,我这里重点想要提示的是,此二分法意识是一种深受近代西方“现代性”及其携带的父权意识形态影响与塑造的结果,而非真实的本土史传,更非传统的古典小说。于是,对比之下,我们能发现一番怪象——史传与古典小说中都无法磨灭的女性力量,当代的中国电影却做到了。
在电影片头中,主创团队打出了故事原型之一:元人所创作的《武王伐纣平话》。在《平话》中,苏妲己陷害姜王后,诬陷她意欲刺杀纣王。在元人的小说中,苏妲己是一个充满刻板印象的“妖孽”,可是,面对这样的妖孽,姜王后却选择,将矛头直指掌握权力的男性:
皇后(姜王后)闻言,心中大怒,不顾其命,乃骂纣王:“信邪佞之言,令我死于目下,贬我入冷宫。无道不仁之君,信谗贪色之主,人神共恶,天地不容,不死在万刃之手,何怒我乎!”
随后,纣王扯住姜王后的衣服与头发,将她推下高楼。死前,姜王后仍痛骂纣王不止。
此外,电影里还出现了“我见犹怜”的典故,却同样使用得“离题千里”。姜王后假装被苏妲己所“魅惑”,一步一步,走入汤池。她抚摸着苏妲己逶迤及地的长发,说出那句“我见犹怜”。随后拔出苏妲己的簪子,意图将她杀死,而紧接着被她反杀。

“我见犹怜”出自《世说新语·贤媛》与其引注的《妒记》。《世说》的版本是:桓温征伐一地后,强取被征伐者李势的妹妹为妾。他的妻子南康长公主知道后,想要领人去杀她。见面后,这个被强取来的女性说:我的国家破灭,所以我沦落到这个境地,这从来不是我的本心。今天你杀了我,这才是我本来想要的结局。
而《妒记》的版本,则是强调了,这个被抢来的女子,对着桓温的正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即她在这样不幸的境地中,仍然保持着冷静,并可以主动诉说出自己的不得已和不由己。而后,这个在传记中被形容为“凶妒”的正妻,“掷刀前抱之”,随即说出了,被《封神》中滥用的那一句: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是什么样的女性情谊,可以让她们在魏晋南北朝那样一种伏尸遍野、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抛弃对于“夫”与“当权者”的重视,抛下被规训出的“夫荣妻贵”的争竞心,乃至“前抱之”,乃至“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反观“现代”电影《封神》里,姜王后在说出“我见犹怜”之后,丝毫不见女性之间的相惜,仅仅是拔出女人的发簪,执行她的精神主人——男性宗主的意志,去杀死另一个女人。我当年读史传时,从这被遮掩的女性故事中获得了多少力量,看《封神》电影,就被那二女相杀的情节冒犯到多少个层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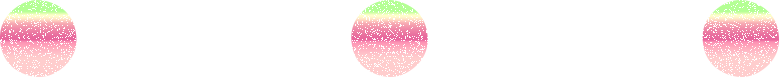

《礼记·曲礼》一篇中写道,臣子劝谏君王三次而君王不听,臣子可以逃走。而儿子劝谏父亲三次,父亲不听,就只能哭泣着跟随父亲。父权制的狡猾在于,他留下了所谓“叛逆”的余地——“逃亡”“哭泣”“做自己”。
然而,这里的“做自己”,是男性的“做自己”,以便他们在推翻旧的父权的基础上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秩序。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被指派的“女性位置”,而没有自然女人。一旦我们代入男性的“做自己”中,与“人子”共情,我们便永远无法逃脱圣女/娼妓的二分法,反成为加固新父权的一分子。终有一日,我们的手段也只剩下“哭泣”与“逃亡”。
然而,女性就连“哭泣”与“逃亡”,也是被历史所抹杀的。正如女性史学家高彦颐老师的《缠足》一书中说道:
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是男性专业史家排挤女性入行的借口。如果不是她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可能还身陷在丛木蔓草之中。
在我们的史册中,有尘埃不能掩埋、强权不能抹消的女性,我们有女诗人、女侯爵、女性最高统治者。她们获得自己声音的过程中,或者智计百出,或者鲜血淋漓。如今深林虽启,蔓草犹未除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片曾为鲜血泼洒的土壤,绝不能再立起新时代的牌坊来。
我引另一位女性史学家伊沛霞作结:
我有证据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所写的这些男人还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

编辑:小狮、阿咸和其他俱乐部姐妹
排版:阿咸、泼泼
Kongfu Girls是全网首个专注于服务女性影迷与艺术爱好者的文化社群。基于对当下流行影视作品的批评,我们致力于同女性观众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能抵御银幕歧视、纠正文化偏⻅的评价体系。
我们提供去中心化的讨论平台,组织写作活动和电子读物,以提高女性影人及其作品的可⻅度、提升女性在 评论界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我们鼓励女性发表自己的声音,分享真实的遭遇,在这里找到情感的共同体。我们要让被动的观看转化为主动的创造。我们要让女性与生俱来的勇气成为立场,要让行动与变革的信心诉诸文字。因为,每位女性读者和观众都是改善我们文化环境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公众号:Kongfu Girls
微博:她们的武术俱乐部
合作邮箱:kongfugirls@163.com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