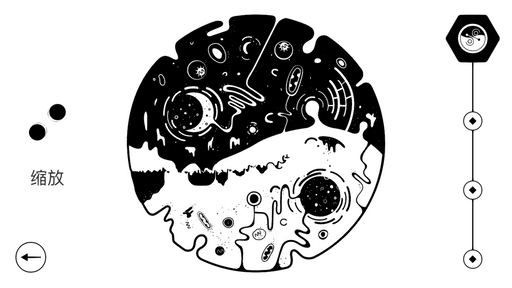
无定形
创客共和国:从数字共享空间到零边际成本社会【译文】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不是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的形象,例如轧钢厂和熔化的钢铁,而是以电子脉冲的形式沿着电路流动的信息中的‘比特’。钢铁制造的机器依然存在着,但它们执行无重的比特的指令。”
———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译者按: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信息和产品流通的成本不断降低,一个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即将到来。作者马里奥 · 卡波(Mario Carpo)则从技术层面出发,设想了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政治与社会的可能性,他认为数字时代实际是一种向传统的回归,数字时代更像是工业革命前的中世纪晚期的城邦时代,那个时候,公社是人们的主要组成方式。数字公社,共享经济的兴起,将人们从摇摇欲坠的工业世界解放出来,新人类将建立自由的创客共和国。该文章的译文原载于公众号:视角杂志
正文
工业世界的技术逻辑是以大规模生产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想象一下传统的印刷机器:任何用来印制的模具(例如雕版、木刻或金属板)都需要花钱,因此一旦有了模具,就应该继续使用它来印刷尽可能多的副本,并抵消它的成本。这就是工业化的标准逻辑:我们制造的复制品越多,每个复制品就越便宜。
然而,数字制造并不是这样运转的。在数字制造的模式中,无论产量增加还是减少,都用不到机械模具。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必要用批量生产来抵消模具成本了。因此,数字制造的每件产品(例如铣削或3D印刷)都是一次性生产的,批量生产对生产成本毫无影响。
正如30年前使用数字激光打印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单位成本打印100个相同的同一页面或100个不同的页面,今天我们同样可以以相同的单位成本3D打印100把相同的椅子,或者100把不同的椅子(尽管在给定的限制范围内有所不同)。数字化大规模定制,或以同样的单位成本大量生产不同的部件,这正是数字制造的普遍技术和经济逻辑,也是所有数字工具的默认使用方式。
此外,由于电子计算的成本在过去40年里一直稳步降低,许多人最近得出结论:基于实际目的,计算的成本将会趋近于零——几乎无限的数据很快将以几乎无成本的方式提供,类似的前提让人们期待一个即将到来的“零边际成本社会”:除了一些需要预付的费用和管理成本(建设和维护一些设施的成本)外,许多商品和服务将会免费。[1]
实际上,在许多基于电力生产和输送的服务中,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社会已经成为了现实:从数据记录、传输到数字制造,以及对电力的消耗。除了建设、维护设备和基础设施的费用外,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力)可以做到零成本发电。鉴于最近智能电网微观管理方面的进展,很容易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为一个由本地的小水电站支撑的网络提供服务的费用,可以轻易转移给当地社区的生产者,他们出于生活环境的考虑,将会自发义务地照管这些设施。
同样在数字制造的微观尺度上,开源运动以及众包数字媒体(包括一些所谓的社交媒体)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大量涌现,这已证明众包协作的零成本商业模式能够与传统上以盈利为目的的产品竞争。正如维基百科、Linux 或火狐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许多人都乐意无偿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从整个社区的集体工作中获益,而不必支付费用。在技术上这是可行的,因为建造、维护和提供这些服务的固定成本很低,从终端用户的角度来讲,这些费用可以忽略不计。
不论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如何,内容(甚至是用户生成的内容)都有成本,即便目前这些成本大多数还是隐藏的、自带的,或者被用户自己承担了。例如,维基百科的智慧并不是群众的智慧:大多数维基百科条目事实上都是由相当传统的学者团体策划的,这些团体之所以可以免费贡献他们的专业知识,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由其他人支付了——通常是大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基百科只是借用了别人的研究投资。(但是它能扩展参与者的边界,这也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对于大多数开源软件来说,培训一个软件工程师或黑客需要时间和金钱——在大多数国家,这种面向未来的投资仍然部分由公共机构承担。
与此同时,计算成本的降低还会带来另一个尚未被发现和计量的关键后果,这也将导致方向完全不同。每笔交易都会有自己的成本,也就是交易成本(完成一笔交易时,交易双方在买卖前后所产生的各种与此交易相关的成本),增加交易批次或者交易数量能够摊销这些固定成本。
如果以数字模式交易,这套逻辑不再适用,每笔交易的固定成本趋于零。既然交易成本不存在,那么交易数量也就无关紧要了。将此与数字制造联系起来,这将催生出一个生产和商业都不受规模影响的经济形态——一个平坦的边际成本社会,一个非规模化的社会。
与此同时,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对价值低廉的物品进行货币化交易,从经济上来说也变得切实可行。这意味着那些没有货币附加条件,直到现在也只能以礼物的形式存在的交易品,可以有效地货币化:营销,购买和以一定价格出售。今天我们可以花钱租一辆共享单车,这种典型的交易直到前不久还只能作为相互帮助,出现在朋友之间(“我可以骑你的自行车吗? 很快就还。”)。
同样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微租赁,它们现在可以被精细化管理。这些交易也是前不久才有了一定的经济意义——虽然每一笔交易的价值都是如此之少,但这些微型交易每一笔都是有价值的。很多类似的微型交易推向市场,已经扰乱了许多长期以来建立的传统市场及其各自的商业模式:例如服务业,而金融业可能是下一个。
简而言之,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平坦的边际成本社会,这与一些人所预测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完全不同:由于计算成本的不断降低,我们正走向一个非规模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社会。对于设计行业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虽然我们知道计算成本正在下降,而且可能趋于零,但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材料成本不会这样变化:钢材或混凝土与太阳能不同,无论我们如何循环利用,建筑材料也供应有限,因此价格一直很高。
设计师需要学会适应这个平坦的边际成本社会,一个规模经济已从生产和交易中消失的社会。这很难,因为它颠覆了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所有基础。虽然零成本模式(数据免费供应,而且取之不竭)可能适用于我们数字生产和交易的方面(不管是信息载体还是能量载体),但它与物质的生产和运输无关。
以上这些都有例可循。在工业大规模生产兴起之前,在自由市场发展之前,在货币经济崛起之前,这些现象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还很兴盛。长期以来,网络自由主义者(推崇互联网自由、反对网络审查的社会思潮)和黑客社区从封建公用土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中获得灵感。在这种模式中,农村土地由集体管理,中世纪的农民在这里工作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契约、协议、义务上的福利。
事实上,“数字共享”(digital commons)这个表达方式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用来指代当今一些数字化驱动的协作工作环境。由于计算成本的下降(以及不久之后,自我生成的电力的出现),这种模式的可行性越来越高。[2]虽然封建公地可能是零成本经济的一个先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模式,但它几乎不涉及制造商的经济。(在制造经济中,产品都是以固定的成本生产的。)
事实上,在封建公地繁荣起来的同时,在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坚固城墙内,一个新的商业经济即将破土而出。在那里,新一代的自由工匠从无到有,他们发明了基于制造业的新社会的规则,并在没有奴隶劳力的情况下,找到了管理和组织手工生产的新方法。
当封建土地不能买卖,只能继承的时候,一些城市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争取并赢得特权、选举权,以此为基础,他们在其城墙内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制度。最先获得的也是最关键的权利是拥有选择艺术、手艺并学习它的自由,然后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的工匠,在城市的行业公会中实践这种手艺。
制造品是独立购买和出售的,但是生产和贸易的方方面面,包括价格,都受到公会的严格管制。另一方面,公会在城市中也拥有大部分政治权力。中世纪晚期的城邦,或者说公社,可以说是创客的共和国。城中的公民身份本身也是公会成员的特权,他们是可以练习艺术或手艺的公民。
从意大利和德国开始,中世纪晚期的公社奠定了许多现代经济甚至精神上的基石:从公司规则下的利润道德(这种道德基于节俭、勤勉和努力工作的伦理),到公司(即以公会为基础)的民主制衡。
把中世纪晚期的城邦(中世纪拉丁文中的堡垒)作为手工业经济的要塞和灯塔,这种观点并没有被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所采纳,直到在卡尔·马克思手里得到最有名的阐释。但追溯工业社会、机械化时代之前手工业文化中的美德与价值,这种倾向对约翰·拉斯金或路易斯·芒福德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很深的影响 [3],如英国艺术与工艺运动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产生受到过约翰·拉斯金的影响),或20世纪20-30年代意大利重新推出中世纪的公会制度,“公社”这个词本身在现代政治思想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到二十世纪的嬉皮士。
欧洲随着新集权国家的兴起,城邦的力量开始萎缩,被公会管辖的中世纪的城墙和城门通常是新巴洛克秩序的第一批受害者:巴洛克式的防御工事是为了领土而战,而不是为了保护城市。不久之后,自由主义思想家特别是亚当·史密斯,认为不管是在城市内外,只要买卖双方达成一致,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以任意价格制造和销售任何事物——简而言之,市场应该从公会规则中解放出来。随后工业革命就来了。在中世纪晚期,市场已经瞄准并迎合了全球市场:各种各样的商品和工业制成品交易横贯欧洲大陆,并远销全球。
但与商业不同的是,手工品生产的逻辑始终与规模经济格格不入:一个手工作坊在生产一个瓶子、十个瓶子,或者一百个瓶子时,单位成本基本相同。因此,手工生产主要是按照订单和规格生产的,而这些产品面向的真实(或虚拟)市场的规模并不重要。与此相反,任何工业组织都有一个可计算的收支平衡点:设备的前期成本能够通过制造和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来抵消。因此,任何一家工厂都需要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工厂越大,只要它的市场也以同样比例增长,工厂能创造的规模经济就越大。工业革命史在地缘政治上的另一面,便是针对所有工业市场规模的永久性争夺:更廉价产品的更大市场。
在某些情况下,欧洲民族国家通过扩大关税同盟,以及在同盟区内强制推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以此填充和抢占市场规模:柏林生产的电器在巴伐利亚州必须能够使用,而且从不来梅市运往康斯坦茨市,每次火车运输穿过城市边界时,都不需要缴税。
对于某些货物或者是商品,殖民地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受浪漫主义运动的文化与思想鼓舞,现代民族国家渴望进步,但是这些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为了平衡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工业化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市场。而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最优的规模则是让每一类工业产品实现规模经济的最大化。
因为手工制造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手工制品的定价就被市场排除在外了;城市制造业的技术前提和社会政治(即公会)都不复存在,手工业城市也就被工业国家所取代了。
我们对这种演变的了解,恰恰源于数字技术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这种趋势的颠覆。和手工业一样,数字制造与规模经济并不匹配;而且如前所述,同样非规模化的逻辑现在也适用于商业。工业大规模生产需要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以创造足够大的市场来实现收支平衡;数字制造不需要这样,因此也可以取消传统上提供法规和保证规模的监管机构,首先是民族国家。
一个边际成本平坦、非规模化的数字社会对于规模并没有任何技术要求:商品销售的市场规模与数字商业无关,因为制造工厂的规模与数字化生产无关。事实上,因为不再需要将生产设施集中在专用、偏远的地方,一些更小巧灵活的技术会更容易融入现有的社区与环境,城镇和村庄可能再次成为生产区域,迟早振兴的城市也会找到合适的政治方式,来发挥其复苏的经济与生产力。
由于在技术与经济的层面上,保证规模的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些政治协会和机构将不得不进行重组,设法更加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社会:有些可能比民族国家小得多,有些规模更大。而匹配大规模工业生产而催生的国家市场也已永远消失了:一亡俱亡。它们属于装配线、煤矿和蒸汽机,它们不会再回来了。
城邦作为数字制造的独立力量,其政治和经济复苏的前景可能显得遥不可及。但现存的少数几个中世纪的城邦似乎都运行良好,即使其中原因往往与上述理由无关:想想伦敦金融城公司,一个仍在运作的公司社区;瑞士联邦,一个直到今天仍由独立企业城市和农村社区组成,以直接民主制运转的联盟;还有一些新成立的城邦,有些是后殖民地国家,例如新加坡;以及一些领土之外不受管制的飞地(免于被国家监管)。
与此同时,让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民族国家消失也显得遥不可及。自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和川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英两国政府基于前所未有的经济保护主义和社会仇外浪潮,采取了严厉措施恢复工业生产、维护民族认同。但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正常框架内,一旦追捧这种政策,人们将要遭受的灾难与集体暴力会一发不可收拾,它会想要、而且可能最先做的就是压制法制,因此需要战争——国家的内战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全面战争。
毕竟现代工业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两场世界大战。期望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和平消亡,这是不合理的。由于技术变革,不再具有成本效益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将会消亡;但与之而来的民族国家不会没有硝烟。
希望有人能够在废墟上幸存,就像古典世界毁灭后的中世纪城市。
[1] 推荐阅读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零边际成本协会: 物联网、分享型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日蚀》一书。(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2]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在何时把中世纪公地作为一个先例,来激励自由软件和开放源码运动的合作精神。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的开创性《大教堂和市集》(印刷于1999年,但自1997年以来在互联网上流传)将中世纪大教堂作为封闭式设计的例子,这与被他视为黑客界典范的市集恰恰相反。雷蒙德还将互联网上知识产权的未来与开拓家园的法律先例有关(通过劳动行为盗用一种普通自然资源,从而导致封闭,也就是说,这与今天“数字共有资源”的意思恰恰相反。参考《大教堂和市集》.1999:76-77)。
书中提到了自然资源的共同所有权,而不是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参考《零边际成本协会》.2014:189-200,202)。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可能是第一个逐字逐句地宣称“互联网是作为公共场所建立起来的”的人,并将中世纪公地与“黑客伦理”和“明天的合作技术”联系起来。
[3]可以参考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威尼斯之石》(1851:53),关于商业共和国放弃其原始的基督教工作伦理,转而成为世袭的贵族;对于路易斯·芒福德来说,尤其是《历史的城市》(1961)第10-12章,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公司的自由发明,以及巴洛克专制主义和新封建地区国家对这些现象的根除。
作者:马里奥 · 卡波(Mario Carpo )
是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的雷纳 · 班汉建筑理论与历史教授。 卡波的研究和出版物集中在建筑理论、文化历史以及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