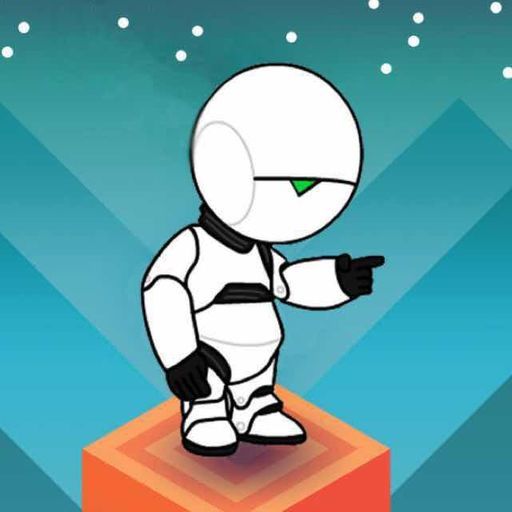
大海里的一滴水。也是咸的。 我们长毛象见:@ziwendong@douchi.space
黃永玉:畫筆下的心境 ——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怡对黄永玉的一篇人物报道
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怡,原始内容的来源(PDF)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九十年代》周刊的第239期。2022年10月李怡去世后,2023年6月黄永玉也去世了。因为非常敬重他们,也感到这篇访谈极有意义,所以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OCR识别+手工校对了它,整理了纯文字版出来,方便更多人阅读。(全文见后,为尊重原文,没有转为简体字)
这篇报道对今天的我们尤其有意义的是,可以看到1989年已经六十几岁的黄永玉在决定旅居香港时,也曾是多么迷茫。明白了他当时的心境,再去看已至暮年的他后来三十几年里的辗转,也能体会到表面的潇洒背后又是怎样的苦心了。
而且这也是他的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不会写到的那部分故事,读过后,也会帮助我们把“序子”的人生拼得更加完整。
黃永玉:畫筆下的心境
李怡
他是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六四以後他含悲帶憤地畫了很多有深刻政治含意的畫。「我爲什麽是這麽一個態度?我今後怎麽辦?」黃永玉談他今天的感觸,也回顧過往……
「六四」前後,去年開始在香港定居的著名畫家黃永玉,在報上發表了好幾張含悲帶憤兼諷罵的畫作。其後,他的感情轉往深沉,以畫他擅長的荷花來寄托他的思緒。一幅「六月之夜」,荷花淌下的竟是晶瑩的血水,他自己說,「我像在畫一個神主牌位。」一幅「雛荷圖」,畫上題字寫他在「電視節目見記者訪問一戴眼鏡小女子,其貌清秀,其言哀側委婉,其勢則萬夫莫當,生命之莊嚴於此可見……」他寫的這個電視鏡頭我已不大記得了,但黃永玉卻一直記着,他說,這個小姑娘對記者說」「我很不安,我怕回到十年二十年前的生活裏去。」她是為此而絕食的,從這小姑娘身上,我們怎麼看到是動亂,是要推翻共產黨的激烈的行動呢?
何日夜而忘之
在這兩幅荷花前,我像見到畫家創作時的悲苦的臉。而另一張「哀郢」,就更令人震撼了,全身紅衣的屈大夫撫地痛傷,狀極感人。畫家畢恭畢敬地把屈原的《哀郢》全文抄下來,我也一個字一個字地重讀這首詩:「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相信《哀郢》必就是畫家在六四後的心境了。
「胡耀邦在世的時候,我正在大陸,屈原這幅畫是當天打下的小稿,但想法、構思、情感都不完整,六四以後,我在香港,把感情放下去,覺得要把整首詩抄下方行,於是完成了這幅畫。」
除了悲戚,這段期間黃永玉的畫作還充滿了憤感與嘲諷,他畫了好幾張鍾馗,但新作的的鍾馗都是不捉鬼的,畫題用廣東話寫着:「人哋(人家)罷工我罷捉,捉點小鬼算什麼,而家(現在)大鬼追返我,從來未見鬼咁(這麽)惡?」黃永玉說,「我年年畫鍾馗,但現在覺得無聊,發生了這樣的大事,你捉點貪污之類來開開刀,有什麼意思?鍾馗是捉鬼專業人士,現在連鍾馗也饒不了,大鬼追起鍾馗來了,以前我畫鍾馗都提一把大刀,現在他的刀是一把小刀。」
另一幅「天生一個張之洞」,是黃永玉知道他的好友黃苗子安全離開中國、前往澳洲之後畫的,在這幅畫里寫滿了打油詩,黃永玉信筆寫來,邊寫邊塗邊改……。像這一類的漫畫型的國畫,這段期間他畫了很多。
我特別註意那幅「愛護國家財產,不能打破水缸」的畫,這幅畫取材自司馬光打破水缸救人的陳年故事,卻反其意而用之,古代司馬光為了救人而打破水缸,現代中國卻為了愛護國家財產,任由人在水缸中淹死,畫家在這個階段對現實的體味反諷,真能發人深思。
四六年,初臨香江
在旭和道黃永玉的家中,一邊看他的畫一邊聽他談他和香港的緣源。
他說他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四六年,那時抗戰剛勝利,香港人跡稀少,他來這兒找工作一直沒找到,於是就去了福建,在南安國光中學教書教了半年,然後到上海了。
上海正值「反肌餓、反内戰」學生運動輿起,民主進步的浪潮洶湧,二十三歲的進步青年黃永玉,一下子就投身到全國木刻協會的活動中去了,木刻協會當時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所領導的,通過木刻活動,配合學運反國民黨,爭取民主。參加木刻協會的青年木刻家都很窮,往往三天才吃一頓飯。開一個展覽會,開完以後大家說,我們去吃一頓西餐吧。那時的俄國大餐是八毛錢一頓,吃完後,大家說下一屆明年展覽以後再來吃吧,後來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呆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受國民黨的政治追害,是沒有飯吃。
黃永玉形容自己當時雖不是共產黨,但自己以為是共產黨,以為自己很了不起,而且認為自己若被敵人抓走是不會投降的,刻傳單時,窗子都用毯子釘起來。「後來有些地下黨的人告訴我,你不釘毯子,人家還不知道,你釘了毯子等於叫特務來抓你。」黃永玉嘲笑着自己年輕時的「左得可愛」。
國共和談破裂,上海的左派報刊一家家封了,無法謀生,黃永玉就應另一個畫家張正宇的邀請,去合灣編一本畫冊,每月所得的酬勞只夠吃飯。最後,張正宇發現屯積起來準備印畫冊的紙,因為漲價,如果不印的話比印出來還值錢,所以就不印了。就在這時候,黃永玉接到通知,國民黨會來抓他,於是他立刻坐車到基隆再乘船來香港。他說,在國民黨治下,他被當作共產黨,在共產黨治下,他也一度被當作國民黨,其實他什麼也不是。
「左得可愛」
一九四八年初夏,黃永玉又來了香港,住在荔枝角九華徑,那時,進步的文化人南來香港,沒有家管的人多住砵蘭街勞工子弟學校,有家眷的就住繙譯家樓適夷在九華徑的住處。
黃永玉起初給大公報寫稿,後來新晚報辦起來他就在新晚報拿薪水,每月拿港幣一百五十元,另外他又在黃墅主編的《長城畫報》拿一百五十元。後來他給長城影片公司寫劇本,寫了一部《兒女經》,是石慧的第一部戲。「我沒有用我的名字,」黃永玉說,「那時我認為自己很左,很神秘,不能用真名,所以用了一個筆名『黃笛』,認為自己應該隱姓埋名,以利工作。」他用自我調侃的語調講他青年時代的事。
更「左得可愛」的是,五十年代香港大學有一位能講中文的英國文學教授會找黃永玉,告訴他哈佛大學有一批中國的民間年畫,沒有人懂,想聘請黃永玉去哈佛工作。黃永玉認為這是對他的政治立場的考驗,他回答說,「第一我不懂英文,第二現在抗美援朝,我們要打美國鬼子,我到你那兒工作乾什麼?」那位老先生客氣地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囉。」現在想來,黃永玉覺得當時的想法真太簡單,而且左得不得了,「其實不去也不要罵人嘛!」他說。
回歸祖國
在香港從事左派文化工作,乾得好好的,為什麼囘大陸去?是什麼時候囘去的呢?
一九五三年。黃永玉說,那時候,他認為若再不囘去他在藝術上就沒有出路了。
有兩個人寫信勸他囘去,使他下了決心。
一個是雕塑家鄭可,他曾在法國十多年,戰後在香港的工廠當經理,很有事業基礎,但在一九五一年囘大陸去了。另一個人就是著名作家沈從文,沈從文寫給黃永玉的信實際上在訴苦,但同時又說,我在受苦,這不要緊,我們擺脫自己來看中國共產黨,看新社會,真是從來沒有過的,這麼講工作效率,這麼廉潔,這麽樸素,這麼好。他還說,他手邊有幾十萬件文物,值得他投身進去研究。
沈從文是黃永玉的表叔,他在北平易手前夕寫信給黃永玉還說自己准備含笑上絞架的,現在他給黃永玉寫來這樣的信,擺脫自己去看問題,黃永玉想,那一定是很客觀的了。
囘北京以後,就到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因為看過許多黃永玉的木刻、畫作,以為他是五十多歲,見到他說,怎麼這麼小呀,方二十八歲,給你當個講師吧。沈從文為此很感抱歡,他認為應該給黃永玉當個教授、副教授的。黃永玉卻說,當講師對我來說已經太好了,我怎麼能當講師呢?
一頭栽到新中國的藝術工作中,黃永玉非常積極地工作,刻了有名的「高爾基像」。
兩年後,就有人叫他入黨了。入了黨沒有呢?黃永玉說,他寫了入黨申請書,可是人家看了就覺得好笑。他的入黨申請書上說,他以前一直跟黨做工作,刻木刻,為黨的事業有許多建樹,「我怎麼不是共產黨員呢?我早就應該是了。」寫這樣的一封信,「簡值是笑話!」於是,入黨也入不成了。再過了一兩年,夏衍跟美院的黨組織說,黃永玉為什麼還沒有入黨,黨的副書記告訴黃永玉,「我聽了正磨拳擦掌地准備入黨,結果反右了,這個黨委副書記做了右派,於是入黨的事又泡湯了。」黃永玉這麼說。
反右,那是一九五七年。回大陸四年後,黃永玉想入黨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大躍進時要交心,問過我的入黨動機。那時我有新的認識,不再認為自己早就應該是共產黨員了。我坦白說,我的動機是,我入了黨就不受欺負了。我感到生活很可怕,入了黨我會有安全感。」黃永玉這麼說當然就受到批評了:你以為共產黨是欺負人的嗎?你入黨是要欺負別人而不被人欺負嗎?黃永玉連忙解釋說,「不是這意思,我入黨就心里感到安全,不怕了。平常我真是很害怕的。」
當然,這種想法黃永玉現在也否定了,因為那時候他看到每次開會時大家都看着黨員講話,於是他感到黨員都是罵人的,可一點也不知道黨員在支部開會時也照樣挨駡。
大風何其威嚴
五三年囘國,首先是肅反,然後是胡風事件、反右,一連串的運動,似乎都沒有觸及這個自由主義的畫家,直到文革方出事,是什麼原因?
黃永玉近年被他的好友問到這問題時說,「你們太傻,我狡猾。」另外,他認為歷次逃過大難的原因一是機緣,二是對他從海外囘歸的照顧。怎麼狡猾呢?黃永玉說,比如反右已開始露出苗頭了,開會時卻還是叫大家對黨提意見,黃永玉就說,我很有意見,早就要講了,我們美術學院的樹,很多讓蟲咬了,為什麽我們不用點消毒藥水把它灌一灌,把樹保護起來?講完以後他就帶學生封森林去畫畫了,因此他既沒有機會「放毒」,也沒有挨批。
文革前的幾個政治運動,黃永玉都沒事,但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也心煩,因為要跟着去開會。實在受不了,只好老是說謊,說不舒服,裝病,其實在家里看書。所以一有運動,他就在家里讀書,而且是有系統地讀,一個階段讀一批大書,關於自然科學的、地質學的、動物學的,什麼都讀,他說,「現在你要我講地質學,動物學,我真可以給人上課的。」然後就是畫畫,畫一些他自己在大小會上交代、批判過的畫。
到文革,他就逃不過了,挨過打,游過街,關在屋子里挨鬥,下乾校種稻子三年,各種苦頭都吃過,各種凌辱都受過,然後大家都沒事了,他還有事——就是黑畫事件,黃永玉被列為榜首,他的一幅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貓頭鷹」,被江青指為「別有用心」,在一次「黑畫展覽」中,排在第一位,後來人稱黃永玉為「黑狀元」。
「黑畫展覽」已到文革末期。毛澤東對此有批示,並因此而使四人幫饒過黃永玉。毛的批示說:墨畫的怎麼能不黑呢?大潑墨嘛!對我來講,貓頭鷹就是一隻眼睛開一隻眼睛閉的。這個畫家懂得這情況。
對文革際遇的好與壞,黃永玉表示,「真是很難說」。比如文革開始時,因為他寫動物寓言,被揭發批鬥,當然是壞事。但如果不批鬥他,他就會參加一個戰鬥隊,「那就完了」。又比如說,江青批他的貓頭鷹是「黑畫」,說不定還是他的運氣,因為如果反過來江青喜歡上他的畫,他會怎麼樣?他會很高興,有機會畫畫了,會感到安全了,孩子也不倒霉了。如果江青要他去當個文化部副部長,他也只好去做,而最後恐怕還是會被江青刷下來,因為他這個人講人情,對人總是狠不下心來。
「一次吃飯時,廖承志問我,你說說看你怎麼跟四人幫鬥爭?」黃永玉說,「我說我還敢眼他們鬥爭,我頂多不求饒就是了。廖承志說,不求饒也不簡單,我說那就太起碼了。」
我想起他的那幅大畫「大風歌」,畫上的題字是,「世人多詛咒牆頭之草而不敢深究草搖擺之因由根源大風,大風何其威嚴若是。」這幅畫里面也有一株不倒的荷花。但是,充滿人性的黃永玉在這畫里表達的不是不該詛咒墻頭草,而是更應該敢於去詛咒何其威嚴的大風。
「風真的太大了,沒有辦法,」黃永玉感概地搖着頭,「李怡,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毛堂大畫:只想快點完成
四人幫垮台後,黃永玉被選中去畫「毛主席紀念堂」的大畫。當時很多人都想畫,而黃永玉自己說他其實是不想畫的。一天晚上,要各個畫家出稿子。有的畫梅花,有的畫松樹,黃永玉就在長長的一張紙上,畫一條弧缐,表達地球,然後是長江,黃河。「我的想法是更觀念一點,結果政治局常委選上它了。」
你自己喜不喜歡這幅畫呢?
「九米高,二十七米長的一幅畫,畫了一年。開始時是喜歡的,畫到後來就累了,只希望它快點畫完。」黃永玉說,「因為每禮拜二要送中央審查,一下子哪一個領導講一個意見,就要從頭來改。自己畫畫,自己做主人哪有這個問題?所以弄到後來就疲沓了,倒胃口了,完全沒有創作的快感。」
接着,黃永玉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大畫完成後,一個報館的記者去訪間他,問他「這麼大一張畫,你畫的時候心里想什麼?」黃說:「我沒想什麼,想趕快把它畫完。」記者問,「你再想想看,你有激情沒有?你的激情的落腳點在什麼地方?」黃說:「落腳點就是色彩,筆觸,就是把它畫完。」記者說:「不,不,你再想想看……」黃說:「你不要問我啦,你要我說我心里想毛主席是不是?根本沒這個事,我一邊想他一邊還能畫畫嗎?」
說到這裡,黃永玉就說,三十年來,他也必須跟着叫「毛主席萬歲」,但每叫一次都臉紅,實在是不好意思。他想,何必呢?其實不這麼做多好呢!人不能這麼簡單嘛,怎麼能滿足於人民這種簡單地叫你萬歲口號呢?
「我原來以為他們都是很懂馬列的,而馬列之深奧又是我一輩子學不會的,因此他們說一句我信一句。後來才知道他們其實都不太懂,也不讀馬列。我以為他們很有東西,原來他們不行,沒有東西。這一覺悟,使我對很多事都注意起來了。很多人說一個藝術家早就把許多事情看清楚了,還說我怎麼先知先覺,其實沒這個事,也不可能。我實際上懂一點政治是很晚的事。」
殺了人,性質就改變了
去年重囘香港定居,黃永玉並沒有放棄他在北京的家。他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在北京的住處,還有許多畫,自己的,其他名畫家的,這麼多年積的錢還買了一屋子的古董。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動,他都有所參與,今年四月,他還去北京開全國政協會議,回來就發生「六四」事件。於是畫家以悲情的心情,不停地畫畫。為什麼要畫這些有那麼深沉的政治含意的畫?
「人從是非觀念出發,作出判斷,往往只是一剎那,因為是非是太清楚太簡單了。」黃永玉說,「若仔細琢磨自己的利盆,那就不是一剎那間可以決定的了,要想好幾天,往往也下不了決心去做。」
作為一個政協委員,跟中共的一些領導人又有蠻好的關係,三十多年活躍於中國的文化圈子中,黃永玉為什麼在「六四」以後就因為這一剎那的是非觀念而畫出這些畫來呢?
「晚上我常常問自己,」黃永玉說,「這麽突如其來的一件事,我為什麼是這麼一個態度?憑政治嗅覺?憑政治傾向?我想不是。從我的一生來看,我好像不是把政治放在前頭的。三十多年好歹我也在大陸生活了,同一些領導人的關係也不錯,大陸的人對我也很好。我想我的出發點就是情感和良心。」
黃永玉談到四、五月間他在大陸時對學生游行有兩種看法,一是不要緊,學生游行沒什麼關係,另一是覺得學生這麼搞來搞去,搞到戈爾巴喬夫來了也還在閙,這麼做不好。對一些問題,比如貪污、腐化,他說他也討厭,但可以慢慢改正,現在已比四人幫的時候好多了,只是還不夠好。因此,黃永玉自承並不完全站在學生一邊,對一些老一輩的領導人,他還是尊敬的。
但是,殺了人了!黃永玉說他的腦子里就發生了「性質的改變」。對中國的老一輩領導人,過去是終身都交給他們的,前前後後的情感都交給這個政權的。文革時與這些領導人一起受苦,常比作與他們是同命鳥。七八年前黃永玉去美國,有人叫他留下來,他說,「我們做朋友也不能是朋友窮了就不做朋友了,我跟鄧胡趙這些領導人是同命鳥,是共過患難的,好不容易才把局面弄成這樣,我怎能不囘去呢?」
「良人者,終身所託者也,今若此。」「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黃永玉曾向中共政權寄託終身,今天卻有了「終身之憂」。
「殺了人了,殺了人間題就多了。現在我要怎麼去揣度你呢?你是怎麼一囘事了?如果我是李鵬,不但可以不殺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把吾爾開希那幾句話對付過去。很普通的話嘛,你生什麼氣呢?如果周總理、葉劍英、陳毅活着,這三個老人家會這樣乾嗎?當然不會。」
外國不願去,祖國不想回
「六四」對黃永玉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他今後會在哪里生活呢?
「殺了人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黃永玉說。
他現在是香港居民,但如果要到外國去,那麼到許多國家都是可以的,事實上也有好幾個國家邀他去。「但是,的的確確,我要問我自己:我為什麼要去呢?我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土地、人民,我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呢?在外國,我的精神生活不行,物質生活也不行,誰認識你?我怎麼辦呢?我已六十多歲,還能像年輕人那樣拼,那樣去適應嗎?」
像過去一年那樣,以香港為居留地,卻常回大陸,以大陸作自己活動的舞台,行不行呢?黃永玉說:「我現在囘去,見到每一個朋友都那麼害怕,那麼緊張,我囘去乾什麼呢?正如《哀郢》所說,老百姓這麽苦,祖國遺麼可愛,但我怎麼囘去呢?外國我不願意去,祖國我不想囘,吾將為赴?」
所以,黃永玉決定留在香港等,等七年,看九七年之前中國有沒有轉機。
說到這里,我們二人都沉默了。我不知再問他一些什麼,他也不知道還要談些什麼,我們都為那句「吾將焉赴」而靜默起來。


***
黃永玉生於一九二四年,是湘西鳳凰縣土家族人,早年以木刻版畫著名,其後則作多種當試,而以國畫及漫畫獨具風格。一九八六年以繪畫藝術成就而獲意大利政府頒授「騎士勵章」。除繪畫外,黃永玉又常作詩和散文,詩集《曾經有過那種時候》獲一九八三年「優秀新詩獎」一等獎,近日出版有雜文集《吳世茫論壇》。黃永玉嗜烟斗,養狗,看書,聽音樂,繪事中更常有自娛而不供發表的諷世之作。黃健談風趣,博學多聞,與他聊天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九十年代》月刊 1989年 第239期
一点补充信息:
会查到这篇文章,起初是因为我在香港电台1997年拍摄的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中,看到了那副他在1989年胡耀邦去世时创作于故乡的《哀郢》。当时印象很深,却发现这幅作品在网上几乎看不到,只有李怡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黄永玉的回忆文里曾经提及。后来在我找到的另一篇李怡的文章中,也看到他再次提到这幅作品,并说起曾在《九十年代》周刊上刊出过。
于是我这才去找了最初刊发这副作品的《九十年代》过刊。很幸运地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是开放查阅电子版的,而且居然不仅有这幅作品,李怡还写了一篇这么有深度的人物报道!隔了三十多年后来读,依然让人十分唏嘘,也非常值得更多人阅读。PDF版肯定不利于传播和检索,所以就冒昧整理了文字版,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文字版里恐怕仍然有些错字漏字,还请各位见谅并指正。
黄永玉的相关纪录片也可以在YouTube看到: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