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我们欢迎人类学学科相关的研究、翻译、书评、访谈、应机田野调查、多媒体创作等,期待共同思考、探讨我们的现实与当下。 Email: tyingknots2020@gmail.com 微信公众号:tying_knots
244|“更勇敢一些”:“典型性”与“交叉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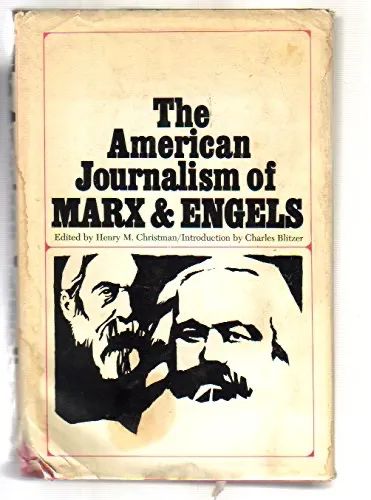
人类学学者项飚曾提到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原生态的、原初状的民族志写作。而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文本,和非虚构写作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比如大量文献资料的搜集、观察与访谈等。那么做过田野就能写非虚构了吗?何为非虚构里的伦理或问题意识?人类学家和非虚构写作者相互可以学到什么?有人类学感的非虚构写作可以是怎样的?这样的笔下,“我”是谁?“他人”是谁?“公共”在哪里?这一写作/知识生产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促成了与《小鸟文学》一起合作的这期Corona。
–
本篇推送围绕本次Corona的讨论部分。嘉宾集中讨论了人类学中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区分,并尝试为“如何使研究更具典型性”提供了一些可操作路径;此外,也提及了“交叉验证”在新闻领域和田野调查中的运用与困境,如何在坚持求真的同时符合伦理,这值得深思。
–
第一篇 纪录一列所有人的列车:非虚构如何写社会 | Corona x 小鸟文学 1
–
第二篇 拯救田野的非虚构?| Corona x 小鸟文学 2
–
Corona是一个起源于疫情期间的公共讨论平台。底色是人类学,但疫情的复杂性很快溢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读书会也逐渐转化为议题导向的半公共讨论平台,以期实践呼应应急性议题而非拘泥于静态理论的知识-行动联结。疫情和疫情次生社会现象之外,Corona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别与LGBT、美国黑命攸关运动、基建、诗歌、他者、全球灾难政治等,也力图对紧急议题做出反应,如就20年洪水策划的鄱阳湖批判历史地理学和大坝与水利政治的讨论和今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阅读。有意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后台留言。此前书单见石墨文档: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2WHbleK9gN20TXDCvteG13708Jw6hBsAE-kNHL_q9w/edit?usp=sharing
–
以往笔记可以在上述书单中找到,整理后的文章可于结绳志Corona专栏里找见。有意加入本次讨论请直接按照海报上的链接加入,意图长期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活动尾声联系主持的同学们。
主讲 / 伊险峰 杨樱 周雨霏 林叶
主持 / 张亮亮
客座编辑 / 木子
代表性、典型性、普遍性
孙博文:
各位老师、学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的孙博文,目前在读人类学博士。现在也在巴基斯坦做田野调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关于非虚构和人类学联动的一个讨论。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做任何有关的访谈也好,还是田野调查的素材收集也好,当最后素材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研究范式后,如何能让人不去质疑它的典型性或代表性呢?之前有看过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王宁教授关于个案研究——“代表性还是典型性?”的探讨,但更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我不知道在座各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杨樱:
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有人问我们,张医生和王医生能否代表沈阳人,代表工人阶级吧,确实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凭什么他们可以代表。我感觉在创作这本书时,跟你们的学术路径是恰好相反的。因为我们是先有这两个人,然后从他们身上的个性化遭遇, 去解析背后的普适性的社会问题。我并没有把他们两个作为代表,我只是在解释的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本书,其实它是一个由点及面的问题。刚刚那位孙博文同学的问题好像与我的创作经历相反,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群体的时候,如何才能选择一个合适的个体去代表这个整体,以确保准确性,我好像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确没有从普遍性里面抓出特殊性问题,从来没有过这个考虑。
周雨霏:
我觉得刚刚杨樱老师提到的像是非虚构写作和人类学学术之间的差别,但我觉得仅就人类学而言,其实很多方法跟杨樱老师使用的方法是很像的。我们研究初期在写研究计划时其实也无法写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之后就直接去田野了,开始找人时可能找到几个关键的人物,你就跟他们混在一起,接着你就开始慢慢要抽离出一些面,一些更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提的问题的核心在这里,我在田野里只经历过跟这么几个人的互动,然后我现在需要做出关于这个村、这个厂、这个学校的结论,要做出一个更抽象层面、理论层面的概括,这是一个难点。
从这个层面来说,这确实是非虚构不太需要去回应的问题,这位同学提到的其实我们很多课程与文章也有讨论,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人类学真的没有一个标准或规范,实际上很看你自己的良心。你做田野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多去找一些反例,多去找一些并不支持你第一印象的东西,直到那个论点真的是你自己都无法反驳,最后在写的时候也尽可能把你发现的反例写出来,尽量去把它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然后你再说我得出了一个小小的结论,真的没有那么理直气壮的典型性存在。还有一点,有学者说民族志就是关于特殊的(the particular),认为民族志全都是关于具体微小的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写的就是这些芝麻蒜皮的事,但我们恰恰可以用这些最生活或最鲜活的小例子去挑动一个已经看起来非常完整的大的理论,可能你挑动了一点点,这篇文章就已经成功了。

伊险峰:
我觉得像《桑切斯的孩子们》,这本书写的就是墨西哥城经济崛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张医生王医生也有点像,你说桑切斯他们一家有代表意义吗?毫无疑问,它就是代表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你说是不是代表了墨西哥城整个全部的变化?我觉得倒也未必。纽约客的作者凯瑟琳·布曾写过一本《美好时代的背后》,是关于印度贫民窟的纪实文学。她挑的那几个人物,你说他们就能代表孟买贫民窟里人的生活吗?我觉得可以代表。从非虚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她写的内容无懈可击,至少在孟买贫民窟这一点上写的是客观又公正。孟买一定也会有一些质疑她的人是吧,尤其是“您把我们孟买写成这样”,“把我们印度写成这个样子”,但就是说你质疑的话,我对自己笔下所有的信息的处理都是问心无愧的,或者说我在写作伦理上无懈可击,这个叙事就是成立的。
林叶:
杨樱老师刚才说代表性和普遍性其实是两件事,我特别同意,不管是学科内还是学科外。代表性问题提出的背后,是一套特定的逻辑。像杨老师刚才说的,张医生和王医生所在的沈阳、工人阶级和时代变迁,他们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让我来概括,就叫人类的普遍处境,在很多民族志作品里都可以看到。比如我当时做“拆迁”田野调查时,我面对的质疑非常多,各个地方的情形不同,政策、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尤其是我写的拆迁户都属于蛮底层的,最后几乎得不到什么。那么立刻就会有人质问你“那些拆迁过后拿到千百万的人,也是你的对象吗?”因此我的研究也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没有代表性的。但是我觉得自己那篇非虚构《“废墟”上的日子》里呈现出来的“钉子户废墟上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普遍状态,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的无房者身上看到,比如在项飙作序的《扫地出门》那本民族志中,写美国的中下层无房者的居处,那么我们中国的拆迁户并不是说同样可以被划归到美国那类社会问题中,但是这些人在日常生活里,其实面对的是一个相似的暂时性的处境。
我自己觉得大量民族志处理的就是这样普遍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各地的人和事物是可以对话和联系的。它不可以被归纳,不应该被归纳,也不应该被追问代表性的问题。换句话讲,我觉得恰是因为好的非虚构作品,有意义的民族志作品,甚至包括一些虚构性写作,它有真实的出处和处理,它处理的是人类的普遍处境,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打动读者。
我作为读者,作者写的那些事让我觉得我也会遇到,这个作品是跟我有关系的,要不然你代表性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另外刚才说典型性的问题,我认为在人类学里我们还是承认典型性的。刚才伊老师讲的特别好,我今天本来还想拿《桑切斯的孩子》出来举例,它里面讲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人类学、社会学里面的典型,它是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这个不是代表性,而是典型性。再比如说很有名的民族志《努尔人》里的豹皮酋长,讲到如何处理部落纠纷的长老。那么像我自己做基层纠纷的研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又一个经典的民族志里的形象,对后面所有的研究者都是有启发的,这种典型性是可以承认的。包括张医生和王医生也完全构成了一种典型性,就是典型的人物,其背后也有普遍的人类处境或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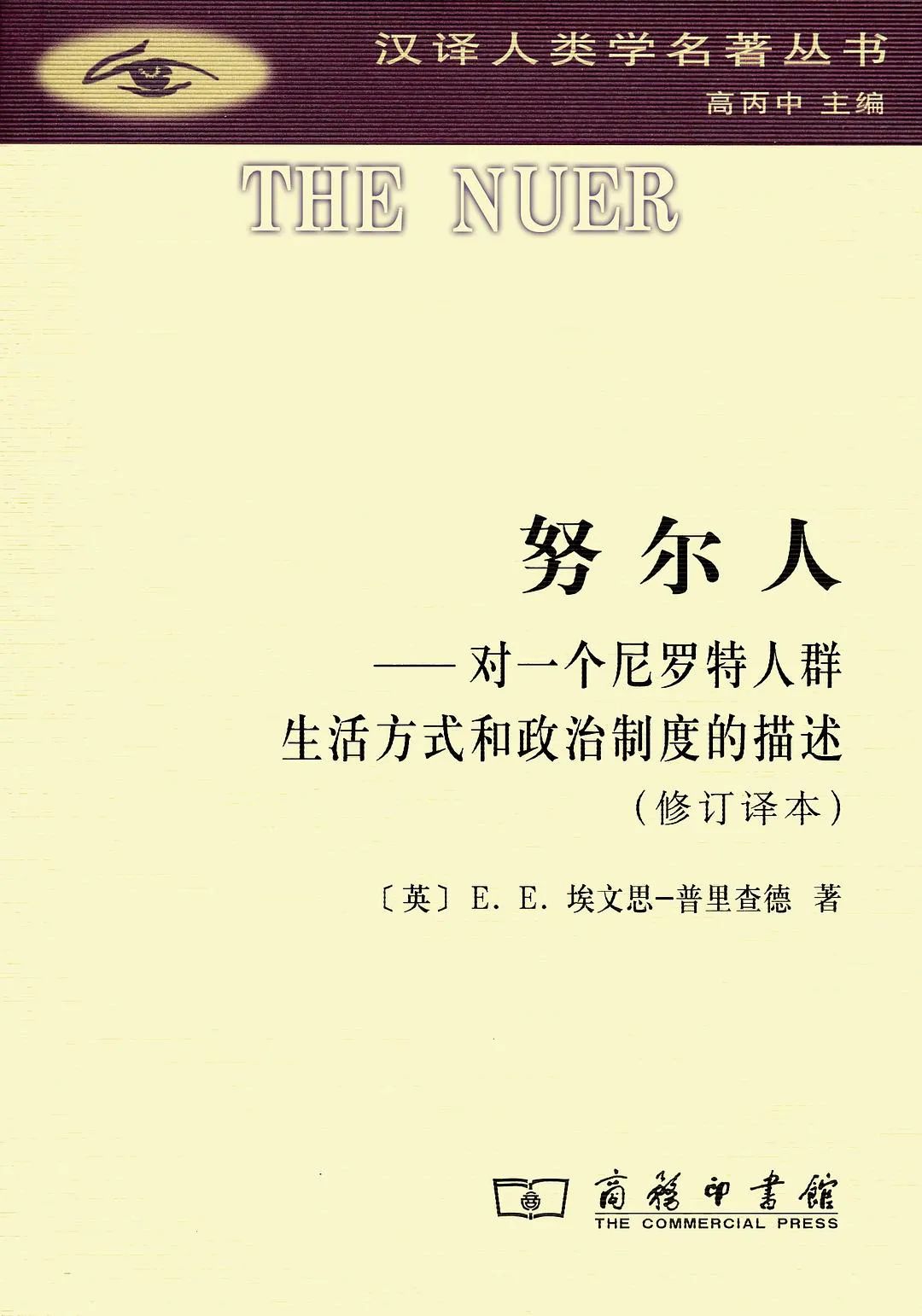
我也提供一个从学术编辑视角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首先你要认可自己所有的研究——你现在写出来想要去发表,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在平台上还是纸版——都是阶段性的。在你的智识上,以及在你所观察的社会过程上,这都是阶段性的,所以确实不需要有特别大的心理包袱。另外一个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同行和已经有的这种学术伦理的讨论时,解决方法我觉得特别简单。首先你自己作为作者,你可以先于未来的批评者,在你文章的那些不起眼的、但是正式的脚注里,陈述自己研究和观察的局限性。
其次,在我们清楚和不断反思发现自身的研究其实存在各种问题时,我们试图解决的学术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表述当中提出的学术问题,我们叫“克制”,或者是审慎地看我是不是能回答那个问题。因为往往会带来质疑的部分原因是你提的问题特别大。比如你只观察了小城市某个群体里一部分人的生活片段,可是你非要去回答一个更加笼罩性的问题。这样是在给自己找事,但是大多数的文章其实都在给自己找事。所以我自己作为学术编辑,我会常常跟我的作者讨论,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缩小。我觉得有时候一旦把问题缩小,当它变得相对具体一些时,往往是可以被解决的,或者说也可以还原那个研究本要处理的一个阶段性问题。
文化的用途与田野的责任
曾毓坤:
我觉得大家都说得特别好,林叶,包括前面雨霏讲的基于特殊性的民族志逻辑,在学术脉络中,就是人类学的新康德主义。面对现代社会强势的基于归纳演绎的逻辑实证主义时,人类学则是强调诠释而就讲因小见大的学科。强调人类的意义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从而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到了格尔茨讲“深描”时,强调看似一样的物理行为(如眨眼)背后的不同意涵(如暗示 vs 下意识的生理反应)。细致地分辨特殊的处境是意义世界的重要研究方法。
不过今天为了讨论,我决定策略性地站在人类学“黑”的一端。我先讨论一下前面提到的《桑切斯的孩子》。本书虽然在民族志写作上评价很高,但其实在学界是非常具有争议的。因为作者刘易斯用以解释桑切斯一家(和他研究的其他贫困社群)的框架是所谓的“贫穷文化”(culture of poverty)。刘易斯认为文化是有代际传递性的稳定价值体系,其所形塑的文化习惯反过来又会造成进一步的贫穷。这样一来,虽然刘易斯揭示了贫穷社群的文化层面,但这样的写法反倒容易让人觉得贫穷是”罪有应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学理上,贫穷文化有循环论证之嫌,且容易让社会结构的批判失焦,并容易忽视底层的能动性,好似把贫穷社群完全封装在一个他们无法逃脱的牢笼。有意思的是,《识字的用途》就将文化作为社会批判的起点,而非答案,从而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性文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其实打开了阅读《张医生和王医生》很有意思的两个方向,“小型军阀”这样的“东北性”是理解东北的钥匙,还是进一步展开结构性批判的起点。

赖立里:
我先从前面天伊提到的伦理问题说起,我觉得和代表性一定是有关系的。首先比如像美国为代表的IRB(伦理审查委员会),美国的人类学界自身是很反感的。大家不是说不重视伦理,而是说 IRB太机械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笑话。我写博士论文,要填 proposal开题的时候,被要求在田野之前必须得到IRB的批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写,我的老师们没有教过。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个模板,是医学院的模板,然后按那个模板的口吻把我要做的研究写了一下。结果IRB的人看完以后非常生气,觉得我这项研究非常差。为什么?因为我完全按照医学的标准把对象当成了一个物,当成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对象。我同学看了告诉我,你这个不对,得把措辞重新改一下,不能把他们当成实验动物或者受试者。我又改了一次,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还不错。
IRB的目的是什么?是免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他并不是真的要去保护对方的伦理;他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将来不会被起诉,不会遭到麻烦,是自保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很多人类学家不喜欢IRB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做田野不是去探清私密的事,不是为了探听某个人的隐私,我们研究的是公共的东西。如果对方有一些隐私,他不会告诉你,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偷听,一定要去把很私密的东西问出来呢?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伦理。我们关心的事情不是他的个人生活,我们关心的是呈现在公共生活的部分。刚才杨樱老师说得非常好,他们先找到了张医生和王医生,然后越分析越宽广,他们这一代人是深陷在历史、深陷在社会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间接地回答了刚才代表性与否的问题。
典型性就是很好的一个转折,因为代表性背后是关于“科学意义”上“大家都是统一个体”这样的说法。问题是人不是统一的个体,这也是人类学有魅力的地方。我特别赞成大家都在说人类学和非虚构是梦幻联动,我真的觉得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刚才提出来的,不一定非要去掉理论才是非虚构,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求真:田野中交叉验证的困境
曾毓坤:
我去年当了一段时间记者,刚刚伊老师很诚恳地提到你们没有学术标准,但我觉得新闻行业还是有一套关于信息的标准和追求,值得人类学学习。比如交叉验证的问题,田野研究及写作中会有许多单一信源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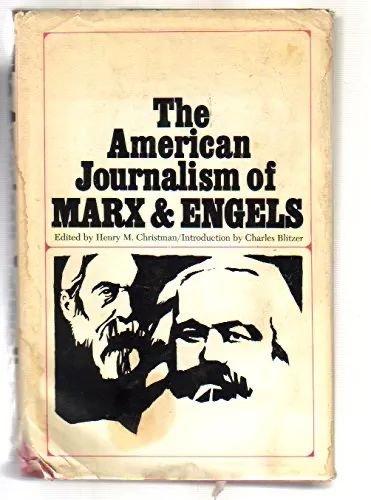
纪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重要媒体《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媒体实践的《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马克思的记者生涯要长于他的社科学者生涯,莫斯也常年给左翼媒体写合作社的报道。许多最重要的社科理论家都是一线的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学术和媒体实践往往相得益彰。
好的新闻重视交叉验证,这背后并不是说新闻从业者“求真”的道义感就比其他知识生产更强,而是因为处在“十目所视”的公共关注下,关键事实的清晰准确与否是公共讨论责任重大的基础。而在IRB的要求下,学术机制内的田野信息采写,很可能只是5到10年后才公开,不到一打人会读的几百页论文里的一个脚注,身份是匿名的,地点是模糊的,其实就不太存在质询交叉信源的问题。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是爱丽丝·戈夫曼的《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这本书后面遭到非常多质疑,比如说指责她的论述带有夸张和过度渲染的成分,包括贫穷社区里特别戏剧性的场景。这其实有点像前面伊险峰老师提到的三联主笔的那种操作,但最终这个事情成了一个无头案,因为戈夫曼很遵从田野伦理,她为保护研究对象的匿名性将田野研究材料保存三年之后全部销毁了。在伦理之外,如果缺乏交叉验证的意识,田野方法也存在依仗非验证信息的情况:问到的不如看到的,然后看到的不如偷听到的。许多偷听到的东西会特别有启发性,但这个东西怎么进行交叉验证,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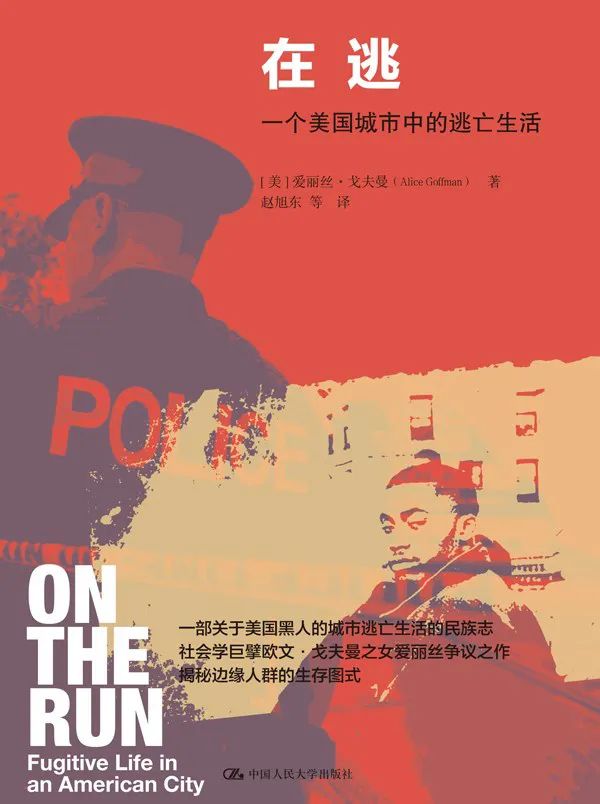
然后另一个极端情况是当研究面对的是两个及以上有强利益冲突的群体。田野工作者可能会出现与一个群体非常熟悉,而与另一群体相对疏远的情况。所以有同学提到“自然发生交叉验证”,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但这一点我比较质疑,自然状态下更容易出现的信源完全基于报道人的亲近程度。如果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呆的时间久可能反倒会加深“偏见”。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学史中有很多。当然,我绝对不是说人类学没有办法做很好的交叉验证,而是要准备好这一方面的方法意识和相应的投入。
赖立里:
我刚刚听到毓坤说人类学没有交叉验证,这个和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人类学当然不会只是做一两个人,它的对象始终还是一个群体。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你如何去分析它,如何去呈现它。刚才有同学说所谓的自然而然就是你在那待得久了,哪怕你的切入点是这两个人,但是你越做、你肯定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其他的人,他们这些人会自动地把更多人带进来了。我不知道这个“交叉验证”是不是说你看到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然后从各个角度去看它都无懈可击。可问题在于你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不断变化的事物,不断变化的社会,很可能人类学家自己的参与就是一个在造成它改变的因素,你的写作,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有经历过的——做完田野后有些东西你发现对方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是你再去分析他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时候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事实?我觉得这样去纠结这个事实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还是要承认写作无论如何肯定是有所谓的主客观问题。你一定要去追求所谓的不存在的、彻底的客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illusion。当回到写作上来,写作者自身参与且生产这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袁丁:
各位好,我是袁丁。刚刚毓坤提到了互证的事,我想加两句。我自己在教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那么在田野调查方法里面,一般我们会强调三角互证,三角互证就是指从数据、物质资料以及田野观察这三个方面来把你的资料进行一个互相的认证。毓坤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可以说要去进行互证是比较困难,我可以承认。但是如果你说人类学的调查方法里不去强调这个点,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合适。
杨樱:
交叉认证真的是我觉得更接近新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新闻里面会提出?因为很多新闻,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非虚构写作,即便在欧美也不是很长时间。他们其实是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当然作为一个题材一直有,广义的非虚构那就更宽泛了,从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但是新闻上的交叉认证其实相当于那些独立事件,比如凶杀案,那些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有,因为你无法只相信一个人,所以要用很多方式,无论是文献、其他人的引证,还是与其他事件的时间交叉,基本上跟刑侦差不多了,你从新闻提供的这种真实性来说的确有交叉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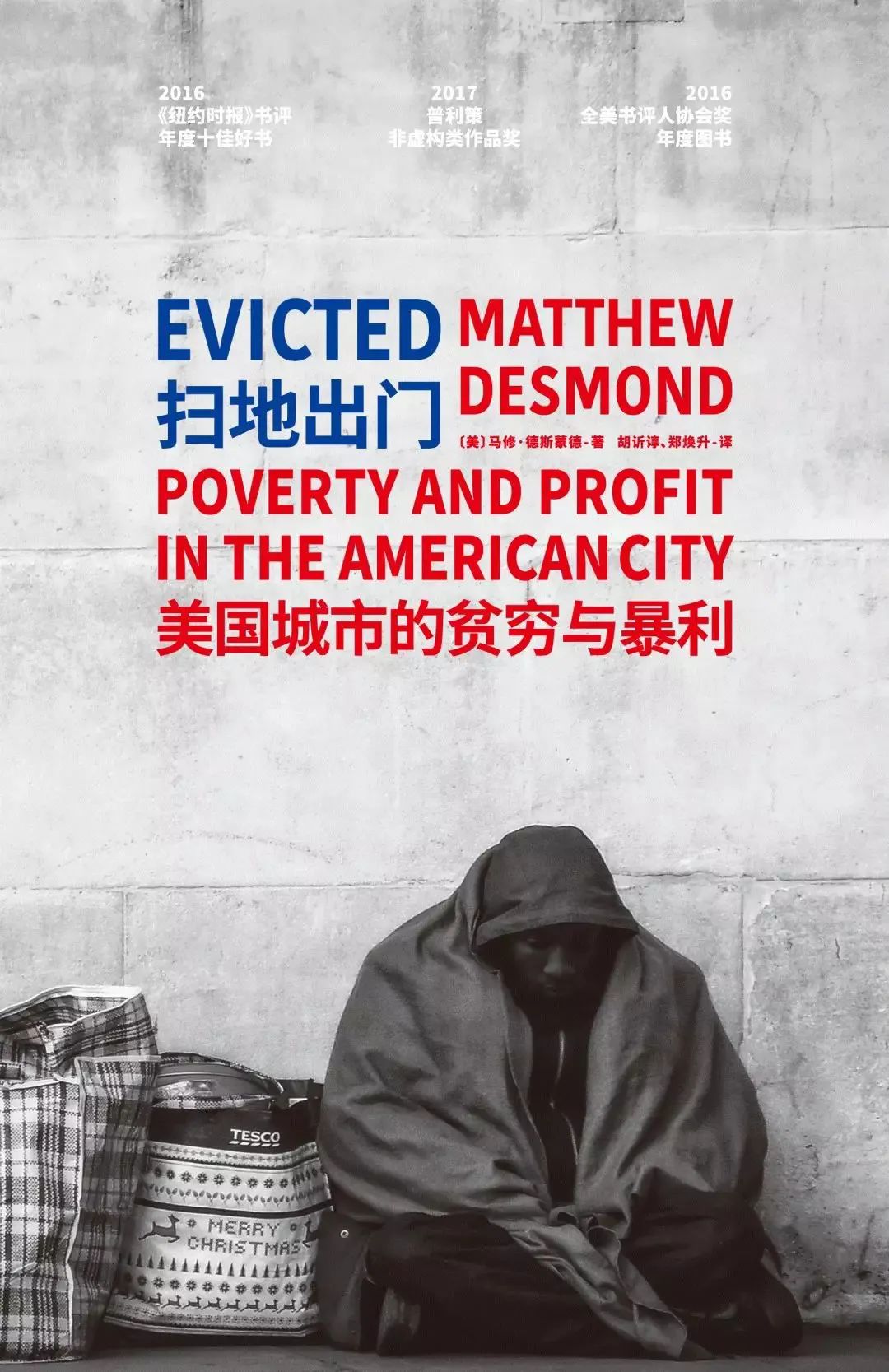
伊险峰:
其实大家的目的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对公众负责任的角度,怎么能尽可能地去接近真实?我觉得这有点像以赛亚·柏林他们喜欢提的,你说这个内容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事实本身,其实很难立得住脚,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去接近,尽可能地去把过程中我们的方法、程序,手段都做到相对正确。不管是人类学还是非虚构写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我对自己所处行业的伦理道德是了解的,我对做的这件事于自己的意义和于公众的利益都是有深刻认识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达到的时候,我就应该往前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假如刘易斯不写《桑切斯的孩子们》,人类学界是不是就缺少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还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太多了,包括像张医生与王医生,我觉得谁都可以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你看《桑切斯的孩子们》,书中一家那几个孩子跟刘易斯也纠结了大半生,刚开始生气,后来也选择了原谅。我觉得从人类文化这个角度来说,摸索是有一些成本的,大家应该更勇敢一些吧。因为我看我们媒体界或者说非虚构界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太多人爱惜自己,他觉得写这个东西不够完美,写那个东西也不够完美,结果就是浪费了各种各样的素材。因为他自己也不学习嘛,因为我们这行当还不如人类学有学术积累,做学术的这种能力,大家最后是属于做什么也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大胆往前做一些事,而不是让自己处于一种纠结的状态。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更勇敢一些”:“典型性”与“交叉验证”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