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我们欢迎人类学学科相关的研究、翻译、书评、访谈、应机田野调查、多媒体创作等,期待共同思考、探讨我们的现实与当下。 Email: tyingknots2020@gmail.com 微信公众号:tying_knots
217 | 阿布-卢戈德 | 女性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下)

近些年来,性别议题在全球各地均得到广泛关注。就人类学视角而言,女性主义民族志的理论化、实践化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本文分享的是莉拉·阿布-卢戈德(Lila Abu-Lughod)于1988年2月29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具体探讨了在当时语境下,“女性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这个问题。虽然距离如今已有三十余载,但其中涉及的“客观”与“主观”二分法、民族志书写与理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等议题,不仅在当时颇具争议,在全球联系日益加深、学科不断交叉、科技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更是值得继续探究。
阿布-卢戈德教授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她因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性别和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表达和媒体方面的工作而被广泛认可。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阿布-卢戈德在埃及与来自Awlad’Ali部落的贝都因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半,为她的民族志《遮蔽的情感:贝都因社会中的荣誉和诗歌》(Veiled Sentiments)和《书写妇女的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奠定了基础。她曾在访谈中提到,“我最初选择与她们一起工作,是出于对沙漠生活的浪漫迷恋,但当我到了那里,一切都变了。我参与她们的世界,试图理解她们的世界,并且传达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世界,特别是通过她们的诗歌和故事。我与她们保持了近30年的联系,有种共同成长和变老的奇妙感觉。” 她还撰写或编辑了许多性别、媒体相关作品,包括《重塑女性:中东的女性主义和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自9.11事件和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来,阿布-卢戈德教授也一直致力于从民族志、性别、经济、政治等多重视角,打破对于阿拉伯社会的偏见,呈现这一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面貌。
上篇内容参看《阿布-卢戈德 |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拓展阅读:
原文作者 / 莉拉·阿布-卢戈德(Lila Abu-Lughod)
原文出处 / 《妇女与表演:女性主义理论杂志》(Women and Performa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
原文发布时间 / 1990年
译者 / 王玮祎
校对 / 王菁、马景超
编录 / 王菁
04. 女性主义人类学走到哪里了?
鉴于我刚才所概述的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中对客观性的讨论趋势,人们也许会期待一种融合,也会期待丰富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作品的出现。但这些却还没有发生。那么,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都去哪儿了?如玛丽莲·史翠山(Marilyn Strathern)所说,面对应和研究对象构建什么关系的问题,女性主义者和人类学家各自采取了不同方式,而女性主义人类学家是否陷入了这种紧张关系之中呢?【14】《写文化》一书中并没有发现她们的身影,而克里福德承认这种缺失“急待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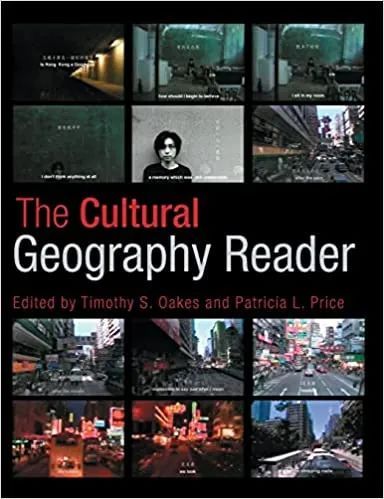
对于这一运动排除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现象,克利福德的借口是没有人参与了文本创新。【15】文本创新与内容和理论的转变之间的区分虽然存疑,但若是我们确信这种区别的存在,那么或许得承认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可能对这一轮新的形式实验确实没有什么贡献。可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因由。我们甚至不需要问那些有关个人、机构、赞助人和任期的基本问题,只要转向女性主义议程本身即可。
我想在这里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另一个是在肯定专业价值的过程中学术与政治的纠缠。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开展了振奋人心的工作,可以说,她们更关注政治意义(而不是文学)上的表达。她们的研究议程致力于两点:一,确保女性的生活在描述社会的文本中有所体现;二,在我们对社会如何运作的描述中,她们也致力于确保女性的经历和性别本身得以理论化。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与其他学科里的同行一样,正试图使女性和性别政治成为可见的、合法的、甚至是核心的研究领域。【16】这样的研究议程可能会鼓励形式上的保守主义;但我们需要说服我们的同事,将性别纳入考虑的人类学不仅会是好的人类学,而且会是更好的人类学。
若上述议程能够行得通,如果我们摒弃了男性偏见、性别盲点,或不再陷入西方关于自然和文化关系的假设,特别是生物本质主义,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问题在于,这种认识论的立场是不稳定的——我们要基于何种立场才能获得这种更好的观点?
那些文本主义者共享的前提是后现代主义,即映照外在现实的科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思考和谈论事物的一种个别且特殊的方式。一些女性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都回避了这一观点,担心这可能会颠覆他们在学术界内外的政治议程。她们怀疑这种论点,担心这意味着相对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南希·哈佐克(Nancy Hartsock)也表达了这种怀疑:为什么当黑人、被殖民者和妇女等被统治者或边缘化人群开始拥有发言权、并要求得到发言权时,却会被白人男性告知,没有人可能成为有权威的发言者或主体?【17】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批判,但我们也必须知道,最终带来的可能反而会是客观性神话的终结,以及总是助长这种神话的等级化的二元论。对女性主义人类学家来说,下一步应该认真思考这些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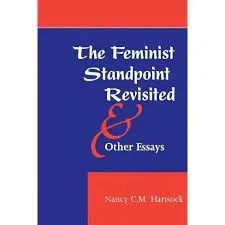
施加在女性人类学家身上的政治问题,也可能使她们无法追求文本的创新。在这点上,拉比诺(Rabinow)对元批判议程和实验性民族志的怀疑,以及对民族志的定位被限制在学术而非殖民政治中的论点令人耳目一新。拉比诺直接指出,实验很大程度上受终身教职制度(tenure)推动。此外,我想进一步补充,我们还需要考虑女性和专业主义之间存在的问题,以把握为什么女性主义人类学家没有争取进行新的形式实验。
毕竟,与克利福德对这一问题的声称相悖【18】,“女性已经形成了非传统形式的写作”。克利福德只是忽略了她们,忽略了少数专业的人类学家,如劳拉·博汉南(Laura Bohannan)、让·布里格斯(Jean L. Briggs)和卡拉·珀韦(Karla Poewe)。她们在民族志写作中已经尝试了新的形式,并实验了一个完整的代替性方向——“女性传统”。【19】在这里,我指的是通常由人类学家的 “未经训练的 ”妻子所写的优秀而流行的民族志,如伊丽莎白·沃诺克·费尔纳(Elizabeth Warnock Fernea)的《谢赫的客人》(Guests of the Sheik)、卢蕙馨(Margery Wolf)的《林家》(The House of Lim)和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的《妮萨》(Nisa)。【20】
这些女性人类学家使用了不同的惯例(经常关注个人——她们的陈述、日常活动和关注的问题,以及她们的人际关系),对研究对象的立场更加开放(将她们定位为参与者,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对她们的权威或全知全能不那么确信,并且,与标准民族志的专业作家相比,她们的作品面向了略微不同的却更广泛的受众。在她们的叙述中,也触及了通常在该地区的人类学叙述中讨论的主题,但这些主题往往出现在人们的生活情景中。通常,她们对女性视角的关注导致了对社会形式的意义和重要性完全不同的解读,例如,性隔离和父系家庭。
那么,为什么这些作为文本创新者的女性们被忽视了?检视《写文化》本身,可能就会找出部分的答案。目前,民族志写作的实验和批评的支持者们都借用了哲学和文学研究等精英学科,来打破平淡无奇的人类学叙述。他们没有通过更平凡的资源来打破常规,如日常的经验或他们的研究对象实际所使用的话语。他们拒绝社会科学的修辞,不是为了用普通的语言去描述,而是为了一种充斥着行话的高深话语。(这种行话的翻弄)使得一位编辑部的读者被激怒了,还写了一首嘲讽行话的诗,玩弄了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如比喻、惊叹、转喻、煽情、现象学、感叹、认识论、指示语、生动叙述(tropes, thaumasmus, metonymy, pathopoeia, phenomenology, ecphonesis, epistemology, deictics, and hypotyposis)——这首诗被讽刺地作为一种召唤列入该书的序言。【21】在写文化运动中,有一种比日常人类学(ordinary anthropology)更排他的超专业主义。
因此,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女性传统”的问题在于,它并不“专业”,而且没有声望,而且可能只能由不确定自己地位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勉强地进行推广和探索。当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在主张自己的专业性时,可能不得不将自己与这些女性区分开来,甚至与向大众读者传播的愿望保持距离。向大众靠近的努力破坏了专业地位,正如发生在玛格丽特·米德身上的事所展现的那样。但在这里,也许他们应该对专业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因为批评人类学家妻子的作品是非专业的指控本身,便隐含了一种等级制度。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论述“客观性”的部分提出了质疑。因为在这里,第一个术语中的“专业”是与有价值的男性气质相关的词,而“非专业”是与无价值的女性气质相关的词:专业/非专业,客观/主观,抽象/具体,理论/描述,引用或与文献相关/基于个人观察。

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女性主义者就已经抨击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本身是一种破坏性的排他做法。专业主义的做法不仅对女性不利,而且与一种固定的操作模式相关。如多萝西·史密斯所说,这与统治和管理的机器相关。【22】然而,无论这些批评多么尖锐,都没有动摇“专业性”的权力,也没有改变这种等级制度;那么,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认为这类民族志实验的风险太高也很合理。如果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在认识论问题上没有像克利福德他们那样努力,也没有在形式上做很多尝试,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建立自己的信誉,获得认可,并推进他们在学界和政治上的目标。
这些都是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在这些人类学辩论中没有那么活跃的原因。但她们在女性主义关于“客观性”或女性主义理论的其他问题的辩论中也没有什么存在感。同样,我们必须问为什么。
首先,人类学家经常被女性主义者降格为提供人类起源和可能性的信息库。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常常被问及女性是否一直、并且在任何地方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是否存在过母系社会,世界上是否存在着性平等的社会。我们或多或少愿意提供这些信息,但感到不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向我们寻求的可能是错误的东西,由于人类学也正在将女性纳入记录,我们也在想,鉴于我们的理论之前错过了很多东西,那么我们拥有的关于他者的知识到底有多可信。女性主义人类学中最好的研究就是重塑社会生活的理论和分析的类别。所以我们谨慎地回应说,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人类学中对地位和平等的定义,以及重新考虑人类学中通常理解社会生活的二分法——公共/私人,符号/物质,生产/再生产等等。可是,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明确答案,所以我们的听众变得更局限于学科之内;我们的研究也更多面向着其他人类学家。【23】
另一个人类学家在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很难谈论“女人”。当来自各种学科的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客观性”或其他以前被认为是普遍的、不被注意的品质实际上是男性气质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广阔的可供探索的空间,可以去想象一个女人或女性主义的方向。【24】到处都有女性主义者开始问:那么一个女人的大学会是什么样?一种女人的政治秩序?女人的写作?女性主义社会学?一套女性主义的方法?【25】一种以女性中心的科学?
在这里,作为人类学家,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坚持的问题是:哪个女人?什么样的女性气质?我倒是可以谈谈我阅读女性主义理论的经验,以及分裂的状态。在阅读里奇有关强制性异性恋的文章、麦金农关于自我意识(以女性主义方法为名出现)的文章,以及爱莲·西苏关于女性性爱文本的文章时,我心中的那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感觉十分振奋,尤其是在读到“我-女人,要在语言中……把法律炸毁”这句尤甚。【26】
这一部分的我,在读到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关于基于照护和联系而不是权利和自主的道德观念时,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关于母职思考的概念,或者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关于结合了手、心和脑的高级科学的建议时,都感觉到了自己的魅力,并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欣慰。然而,我心中的那个人类学者,那位文化差异的专业识别者,那位与埃及贝都因妇女生活在一起的田野调查者(按照我们的标准,她们似乎并不女性化),以及那位进入人类学这个学科、期望能解答我关于自己在两个世界(我的美国母亲和我的巴勒斯坦父亲)之间成长的个人经历意味着什么的人,正强烈地抵制着女性主义中的这些主张。在每个所谓“女人”的方向中,我都看到了极为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女性气质的含义,就像在激进女权主义者列出的那张针对妇女的罪行清单中,面纱、裹脚、阴蒂切除和娑提被等同于强奸、色情和细高跟鞋,我看到的是一个因没有结合实际情况而不可接受的失败。你们在说哪些女性,哪种女性气质?致力于文化差异和谨慎的经验主义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面对这些只能是消极的。
当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女性主义民族志”的问题,以及它可能是什么时,我向这些文献寻求了帮助,并尝试了许多想法,但最终我不得不决定拒绝它们。因为我对民族志有一个不同的设想,我以它的名义撰写了资金申请书。这个设想是作为一个女性民族志学者,去倾听其他女性的声音。我在女性写作的文学研究中,寻求了能肯定我模糊想法的论证,即以一种非支配性的方式写作,写日常经验,写女性对其社会和生活的看法,写与他者息息相关的个体们,关注特殊性并避免泛化,以关照和依存而非保持距离的方式写作,去参与其中不是把自己摘除。
我面临着两种关于女性写作的争论,一种是英美式的,一种是法国式的,两者对女性写作的看法并不一致。【27】然后,问题又开始出现在作家内部,因为女性作家开始抗议她们不是“女性作家”。伊莲·肖华特作为女性写作中“她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最主要支持者之一,为了证实她们确实是女性作家,——提到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她40岁生日聚会上的一句调侃。【28】当有人试图通过说她看起来不像她的年龄来赞美她时,她反驳说:“这就是40岁的样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的意思就是,无论女性作家写了什么,都是女性的写作。她们之所以否认自己是女性作家,是因为女性写作被贬低了。我们需要对抗的正是这种贬低。但是,如果要问女性写作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然后,对法国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写作并不必然局限于女性,甚至大多数不是由女性实现的,因为很多女性作家只是在模仿男性。她们的写作也被定义为来自身体、液态、前意识、符号学(意指在语言和意识的符号化之前)或压抑的写作。对法国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写作”应当颠覆男性的语言、逻辑和连贯性,因此必须是一种诗。尽管这很吸引人,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如果她还想写民族志——关于其他人的生活的书,而不是来自她身体的诗歌——那么法国女性主义学者的提议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似乎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明智的尝试。
如果不去借鉴西方文化中有关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似乎很难界定 “不同声音的民族志”,或者在民族志写作中女性的、甚至是女性主义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民族志的这一危机,与当代女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危机十分相似。这种危机被称为“差异的危机”,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学界都经历过。
简单来说,事情是这样的——女性开始大声疾呼,并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任何关于女性的定义提出异议:“这不包括我和我的经验。你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反对这种全体主义,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也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其结果就是,在最近的每一篇女性主义文章中,都出现了关于黑人和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女性的仪式般的套话,以及此类说法只出现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身上的套话,也出现了关于女性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女性这一类别、关于象征主义、关于殖民话语等等的文章。【29】正如桑德拉·哈定所说,危机就在于“一旦单数的女性被解构为复数的女人,社会性别被认为没有固定的所指,女性主义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就会消解,而体现的也是一种自然化或本质化的发声者的声音”。【30】她补充说,这并没有使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身份而消亡,但现在女性主义圈子里讨论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出一种建立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的团结、联盟或亲缘的政治”。有些人,比如唐娜·哈拉维,把女性主义的这种危机看作是一种现代后工业资本主义新世界秩序下的积极发展。【31】
而我认为,在女性主义和人类学发展转折的这一关键时刻,对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机会。
05. 女性主义民族志中的融合
为了理解这一转折点的性质,我们必须退一步看。观察作为学术实践的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这两个学科,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不平等世界中,两者分别产生于这一世界所依赖的两个根本的且政治的差异系统:种族和性别。两者都植根于、并试图处理历史上构成“自我/他者”区分的问题,但是从差异结构中的不同位置,来处理这一问题的。
人类学的话语,源于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探索和殖民化,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话语。人类学把自己主要定义为对他者的研究,这意味着人类学的“自我”并不构成问题。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西方文明对“自我”的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对野蛮或原始的他者的对抗和描绘构建起来的。【32】即使当人类学处于危机之中,甚至当这种危机的焦点正是“自我/他者”的问题时,就像反思人类学和新兴民族志一样,往往仍然不会去质疑那一条鸿沟本身的存在。民族志学者现在担心的不是“自我”和“他者”之间产生区别的历史,而是如何去跨越这条鸿沟进行沟通,如何与他者对话。人类学依旧假定,确实存在着一个“他者”,并由此推断出也存在一个与之不同(在不同这一点上不构成问题)的“自我”。如果要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就要研究人类学、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构建西方“自我”上的关系。【33】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话语是从我们社会中另一个巨大的差异系统的对立面开始的——性别。正如西蒙·德·波伏娃在很久以前就指出的,至少在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女性一直是男性自我的另一面。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女性主义者不能对有着自我/他者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权力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这种差异系统是有等级的,也是关于权力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也许这个差异系统本身就构成了性别歧视,因此必须被理解和拆解。
第二,尽管女性主义试图将那些被构建为“他者”的人转变为“自我”,也就是将客体变为主体,但紧随这一尝试而来的危机(也就是我刚才讨论的多重差异的危机),既显示出了创造“自我”这一事业中固有的暴力,也展现了再次思考身份认同问题的必要性。女性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女性身份只是我们身份认同中的一个部分。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自我支离破碎的基础上工作,我们不得不作为不同的自我一起工作,而这些自我只是部分地交汇。
那么,这种自我身份对人类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我不想争辩说,因为女性知道什么是他者,所以她们可以对那些在另一个差异系统中的他者产生某种特殊的同情。我想就女性主义民族志学者的定位提出一个更结构性的论点。尽管,任何试图在民族志写作中定义一种女性声音的做法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但关于女性主义民族志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如果它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由女性为女性写的民族志(即使位于焦点的女性大多来自其他文化,而执笔的女性大多是西方女性。这些西方女性想了解性别意味着什么,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生产出女性的境遇——这仍然是世界的不平等结构和人类学的结构),一些重要的转变将会发生。通过假设同一性中也存在差异、自我的认同是多重的,以及他者也可能是部分的自我,我们的工作就可能会超越固化的“自我/他者”或“主体/客体”划分的僵局。
然而,这一点让新兴民族志学者感到不安。说得更明白和具体些,想象一位女性田野工作者,她不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对自己所处的境遇、自己的行动以及她所写作的社区中人们的互动中,保持性别的意识。在了解他们的情况时,通过逐渐明确相似和差异的过程,她也在了解她自己。最重要的是,她对掌握他者的境遇抱有政治上的兴趣,因为她和他们往往都认识到互相只有有限的亲属关系和责任。【34】
女性主义民族志能够为人类学做出的贡献,是去动摇人类学作为一个“自我”研究“他者”的学科的界限。这一界限也正在从另一个方面被动摇——从本地人那里。我指的是本土人类学家的崛起,尤其是“halfies”——介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人,他们的成长、父母一方或受到的学术训练来自西方,而他们文化的源头、家庭的起源、父母的另一方或他们身份的某些部分在他们正在工作的田野中有所体现。【35】
这些人类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自我是多重的,而在这基础上,他们的实践也以富有成效的方式打破了自我和他者、主体和客体的界限。他们的痛苦不在于如何跨越鸿沟进行交流,而在于如何将这样的经验理论化。他们在所居住的许多世界之间来回移动,这种移动是在一个复杂的、由历史和政治决定的世界中的往复运动。当阿帕杜莱提出,从来就没有“本地人”这种东西的时候,他是在说,与我们西方人不同,那些人没有被困在思想的模式和特定的场所里。【36】而当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说,东方不是一个地方,他也是在暗示同样的事情。东方和西方之间(想象的)分界线的建立,以及对新定义的他者的支配是同时进行的,整个过程都是创造一个独立的“自我”的方式。女性主义者知道这种二元划分对女性来说是多么负面和被动。在女性主义和halfie的民族志中,通过与他者对立来创造自我的做法被禁止了,因此,自我的多重性和他者的多重性、重叠和互动都不能被忽视。
鉴于此,在我看来,女性主义民族志和halfie民族志都是可以撼动人类学本身范式的实践。它们向我们展示,我们始终是我们所研究的事物的一部分,我们始终与研究对象保持着有限的关系。人类学中的经典假设是,我们站在外面:大多数新的民族志都未能打破这个神话。现在可能到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颠覆这个假设的时候了。对民族志写作本身的反思,在人类学内部创造了空间,而这种努力则基于所有知识和表象都是情境的和有倾向性的认识。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危机为女性主义人类学,提供了更多关注性别和女性跨文化工作的受众。女性主义民族志,是试图描写在其他地方和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民族志,也是探索工作、婚姻、母性、性向、教育、诗歌、电视、贫穷或疾病对其他女性意味着什么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可以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一种方法,通过在地感受到的异同,来取代对对于女性经验的单数预设。
女性主义民族志也可以明析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认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的想法只是一种伪装。这个世界使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走到了一起。在这个世界里,我能够在电脑上写下这篇演讲稿,回答贝都因女孩关于她们在广播肥皂剧中听到的电脑的问题,而电脑生产则取决于东南亚拿着低薪的女性在跨国电子厂中长时间的组装。因此,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女性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现在正是我们探索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时候了。
阿布-卢戈德教授对本文的介绍
这是我于1988年2月29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内容略有修改。演讲是学者们经常进行的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尽管有缺点,我仍决定将这篇演讲原样保留。自从发表了这篇演讲,我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关于女性主义者们和halfies的共同点,和她们对于人类学有何启示,我在《反文化的书写》(Writing Against Culture)一文中进行了更多讨论,收录于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编辑的《介入:当下人类学》(Interventions: Anthropology of the Present;校注——此书后来出版时题为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我感谢 NEH(国家人文基金会) 的研究经费,使我能够于1987-88学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研究,也包括为这次演讲所做得准备。我受益于性别研讨会的讨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我也感谢凯西·鲁兹(Cathy Lutz)的评论,以及康妮·萨顿(Connie Sutton)和苏珊·斯利奥莫维奇(Susan Slyomovics)鼓励我将这篇演讲以更永久的方式发表出来。
译者介绍
王玮祎,古镇人,在日本读人类学,爱好小鸟和野生三色堇
校者介绍
王菁,喜欢没有(以及看起来没有)脊椎的海洋生物,人类学视角的跨学科研究和公共对话
马景超,哲学系博士在读,现居美国费城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208. 我们留给未来的过去正如何过去
209. 海鲜女的码头江湖
210.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211. 孝道、国耻与性劳动:中日女性与劳力贩卖的法律史一瞥
212.疫情至此,选择生命还是经济?抑或反思这一提问本身(上)
214.疫情至此,选择生命还是经济?抑或反思这一提问本身(下)
215.代理人背后的普通人战争|从俄乌what about叙利亚
217.阿布-卢戈德 | 女性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下)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