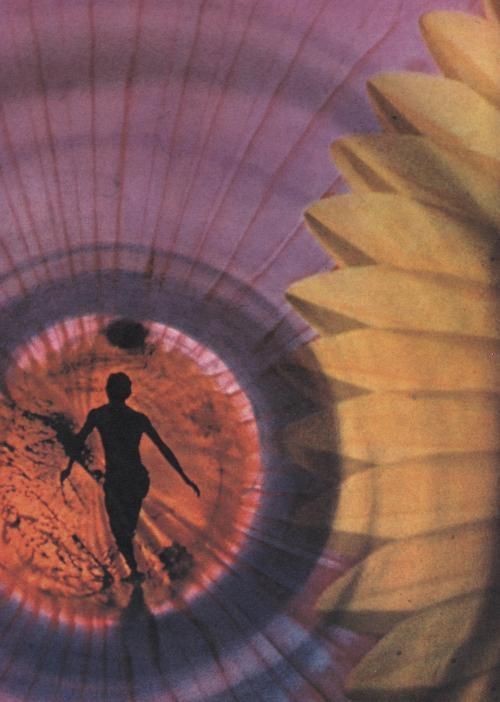
突然了解游戏的奥,为什么我不能把写作当游戏?慢慢扩及人生。
默爾索身上一種關於無所謂的美學:人生如戲,我不參與
厨川白村說,文藝的表現需由象徵。
這足以使我想起一個人。加繆。他的文字,全然是他所說的“愛與節制”。
我常把作家的文字比做一張精神的面孔。加繆是第一眼看上去冷而疏離的人,甚至讓你感到不自在,因為你不得不歷經深思才能領會他的神情。當你對這張面孔凝視的越深,卻越覺得熱切而感動。你開始覺察,他那張冷靜的臉,彷彿是以生命的熱情去刻畫的。當然,這並不好懂。
加繆常用精密的佈設去描繪一個簡單的人物。如同卡利古拉說“我是个简单的人,这点你们永远无法明白。”直到重讀局外人,我猜測加繆對“簡單”有所偏好,默爾索即是一個簡單的人。“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他拒绝说谎,他是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他“真实的表达着自己”“有什么就说什么”“头脑简单到没有什么心思来遮掩什么,谋划着获取什么”,从而他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真的是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的“局外人”。
局外人,明明是那麼乾淨的一個故事,節制的表達,卻令我止不住地心潮澎湃。我意識到,我就是默爾索,我想成為默爾索,我曾光榮的成為過默爾索,如同他被死刑判決的那一刻(當我真正意識到靈魂判官無處不在,我便對昔日好友說,你們都是想當上帝的人)。
荒谬的世界只能接纳一种美学论证。-加繆。
我想從默爾索的人格結構開始講起,其中可以總覽的一個動人特徵:他是個無所謂的人。需要明確:無所謂不代表放棄。無所謂是一種美學。
佩索阿說: “一个人能够获取的最高自律,是无所谓地对待自己,相信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不过是房子和花园,命运规定了一个人必须在此度过一生。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梦幻和内心欲望,应当有一种伟大主宰无所谓的随意傲慢”。
對默爾索的批評大多在於他没有理想,沒有信仰,沒有激情,沒有規劃,隨波逐流。以及他對一切事物顯得“無動於衷”(這是無所謂的表徵),他在母親的葬禮上不掉淚,次日就與女友做愛,只因太陽晃眼就殺了人。他當家暴者的朋友,他懶於為自己辯護,甚至有時想握握法官的手,和獄卒擁抱一下。我在豆瓣上見到有人評論默爾索沒有人性,只有“動物性”,原因是他的心情太容易被天氣影響,被慾望勾引,卻對人類社會所建立起的整套文明體系免疫。
這實在是令人忍俊不禁。一個沒有習得荒謬的人是荒謬的。多麼荒謬。
很顯然,加繆是在用否定法描繪這個人物,悄悄的否定信仰—反英雄,否定喬裝打扮的社會—煽動人遂著“合理”的方向處世,否定作假——刻奇,否定價值——命名價值的是強大的秩序與權威,否定情感——那些被定義為正當的,高尚的,合法的情感。否定死刑——比卑鄙的罪犯更可惡,法律是以良心的名義幹卑鄙的勾當。
米德提出了“主我”和“客我”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了"performance principal",他认为今天的个人不是在实践人的真正存在,而是在实践被规范的、设定的功能。
默爾索就站在這被規範,被設定功能的局外,他要有什麼所謂呢?他像他自己,而不像被規範的人,當人們以角色生活充當完整存在,以功能關係窮盡情誼的真諦。默爾索早已剝離了所有幻覺。“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
正是由於身處被設置的局外,默爾索與他接觸的人事總保有距離感。布莱希特曾强调演员表演上要突出自我和角色的距离感。有这种距离感人性的狡诈才可能露出马脚。 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距离感呢。我想他也许意识到,人每时每刻都在一种戏剧性里表演。要从这种戏剧性里超脱特别难,思想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演员。为了分辨无数混乱的真假难辨的界限,确定自己几分真诚几分虚荣几分自欺欺人几分是故意编造的幻梦,就必须跳脱出自身。 塑造这种距离感。有益的距离应当是深情冷眼。加繆在書中塑造的默爾索“距離感”是渾然天生,在此我覺得這也許是為了突出寫作效果。在真實的情境下,這份距離感,若非時刻的反思狀態(反思类似于冷漠的反刍,剜骨。)與超常的智識是很難擁有的。——加繆寫的是一個天生的局外人。而我這裡闡述的是如何成為一個局外人。
默爾索的無所謂具體化為一個最可愛的品質:絕不演戲作假。因为有所谓才有必要演戏作假。這就決定了默爾索的古怪。他不與這個作假且不承認自己作假的世界合污。加繆也說社会需要的是那些会在母亲丧礼上哭泣的人。
人生如戲,我不參與。好比昆德拉筆下那個真正生活在別處的人⋯⋯我是說,戲劇。捷克大混亂時代,“他背弃了历史以及它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背弃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完全把精力集中在自己上,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中和他的书本中”。
無論是被女友問及愛不愛她(可以結婚,卻不能說愛),還是被自己的律師要求克制天生的情感,表演出陪審庭希望看到的那種“悲愴”(無所謂的人是做不到的)抑或面對牧師時的憎厭和暴怒,無一例外,默爾索幾乎是油鹽不進地保守著自己內心的真實,而丝毫不顾虑后果,这就是加谬说的“头脑简单”。最後,人們把他完全撇開,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处决了他的靈魂。默爾索顯示出了一個人面對荒謬時的赤裸無助“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但经过考虑,我又没有什么要说了。”
那麼如此無所謂的默爾索究竟是不是一個無情之人呢。默爾索在監獄中與日回憶自己塵世生活的細節,自己的住宅,海風,市野,瑪麗的眼睛,他说,“人即使只活一天,就可以在监狱里待一百年而不会难过”我想,這份對生活巨大的眷戀,我是難以企及的。加繆自己也說,默爾索本人絕不麻木,他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情。
再談局外人開篇第一句話“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按照我們習以為常的情理,都會立即感到某種幾近反叛的冷酷。而薩特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這一句話的語氣儼然是一個孩子的口吻。“媽媽”而非”母親““媽媽”在法語中是個十分親暱的稱呼,“媽媽”一詞,足以體現默爾索的傷懷。回歸到加繆的寫作筆法“愛與節制”,既然默爾索是一個萬萬不作假的人,那麼他便坦率言行,絕不渲染喪母之痛,他反對的正是絲毫的誇飾。後文默爾索內心獨白“你們誰都沒有權利哭她。”更是體現了默爾索與加繆相近的死亡觀與人生觀。比審判更噁心的是拯救。监狱牧师多次想要拯救他的灵魂时,默尔索肯定地告诉这个荒诞的世界:个人的灵魂从来与他人无关,他人无权过问、无权审判、无权怜悯。死亡亦是如此。加繆說“用来判我们刑的,永远不是我们自己认定的那个罪名。我还可以做出其他十个可能的结论。”
加繆承認,《局外人》的調性是故意的。通過日常事件讓人物自然而然的來到唯一的大問題面前。面臨那個沈重的時刻——與壓倒你的荒謬相對峙的時刻。人是徹底的無助。加繆的人道主義即是理解這種無助。
局外人的文尾最打動我:“為了善始善終,功德圓滿,為了不感到自己屬於異類,我期待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
這是無所謂美學的高超之處,也是加繆對人們面對荒誕的回覆——接受荒誕並反抗它。
“世界是荒谬的,不明不白,不伦不类。”
“对于这种荒谬的状态,关键是要在其中生活。 ”
“荒诞启发了我:没有未来嘛,从此这就成为我极大自由的依据。”
--阿尔贝·加缪”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