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失联人权律师常玮平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绿4岛
常玮平:祝福重庆大学90校庆
常玮平:祝福重庆大学90校庆
原创 常玮平 绿4岛 2019-10-12
今天重庆大学90年校庆。按理,我应该毫无障碍的喊一声:母校生日快乐,但我是那种不太习惯过分亲昵的人呢。作为一座即将百年的名校,她当然值得我喊一声母校,只是我对她的感情,又不是这一个经常被滥用的词能涵盖。90年里,我们只有4年的交集,那么多学生,其实大家并不熟,但在重庆的那些年,确实深刻的改变了我。这么重要的节日,我没去现场,但也努力的回想了一下与重大的一些点滴,希望聊可作为一种祝福,至少别添堵就行。

上大学之前,我惟一去过一次的大城市就是宝鸡了。03年的高考,数学很变态。不过大家都觉得难,这时候填志愿就是拼胆量了。那时的我,也没什么胆量,只想着无论如何终于脱离苦海,好坏报个念念得了。可能大家都这心态,那年那些好一些的一本反倒没人报。
嘉陵江发源在宝鸡。暑假很长,我还找了一本地图,想象着河流的走向和山城的模样。等到开学在即,终于坐上了去重庆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要绕道成都,25个小时。第一次坐火车,很新奇,也不觉得累,到了,办好手续,躺到宿舍的床板上,才感到床在晃动,耳朵里全是哐嘡哐嘡的铁轨声。
我爸把我安顿好就要走,我送他到南门,没再迈步,看着他远去,哭得稀里哗啦。他也没回头。今年夏天,暑期西南游,我带他重新走过重大南门,还想起当时的场景。人类真是残忍的物种。不管有多痛,都能做到分离。古文学里,生离和死别,是差不多相称的一类事情。现在交通便捷了,但对那时第一次离家远行的我,那种撕裂感,铭记终身。
然而,在此之后,这种真的,而不是过家家式的分离的积极一面,逐渐显露出来。陕西也是高校资源丰富地区。在省内上学的同学,更便利,更容易适应,但也失去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做生存训练和接触当地风土人情的机会。重庆对我这个从来没出过远门,一直被照顾、被安排的大宝宝的重塑,大抵是在这一刻,按下开始键。
办完入学碰到的第一件事却是我差点儿被退学。
报道完后,是送到部队军训一个月。我们被分配的部队,跟西南政法大学一墙之隔。但分配之前,要先体检。我的首次体检结果乙肝阳性。复检后等结果,足足三天,宿舍里就我一个人。这三天我很不淡定啊。按当时的说法,如果确诊是阳性,是要退学的。很多年后,我因为做了一些反歧视的案子,知道这种检测本身就是违法,退学更是错误,开玩笑说,如果当时真复检阳性,起而维权,说不定早就成为成名,其后的人生轨迹也将被改写,不至于窝行摸索这么多年。
后来当然是伪阳性,又去了部队。在部队又是另一番感受,最后的训练项目里还有实弹射击。篇幅所限,此处暂不讲了。后来我发现很多学校的军训就是在自家操场走正步,我对重大的这种强悍的作风,还是很佩服的。

这也是重大给我一贯的感受,什么事就是来真的,而不是装样子。有一年我过年路过西安,去同学的学校,晚上到点儿要熄灯、断网,要关宿舍门、校门,遇到当时气焰正盛的反r游x,学校直接就封校了,白天都禁止出入。这是我在重大永远都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住的7舍,就在重大南门口,24小时,永远开着,车水马龙,早晚都坐着一些永远在打牌的“棒棒”,宿舍从来不熄灯,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封校之说。那时我才觉得大学还是有不同。有的真的是把你当作一个人,一个大学生来看待,有的还是高中那种思维,像在看管一些动物。印象深刻的是,有时候晚上,整个宿舍区突然就“疯”了,跟狂欢节一样,但更像是泼水节,各个楼宇之间,相互叫嚣着,呼喊着,歌唱着,但也都控制在一个不太出格的范围。人年少时,总会做一些离经叛道、莫名其妙的事情,重大是给了学生充分自由和尊重的,当然也换回了大家的克制。我每每想到那些为数不多狂欢的夜晚,觉得即便大学只是提供了四年的床位,什么都不管,那也是值得的。她至少不强迫,不矫饰那些无聊无趣的东西给你,任你自由选择、独立判断。
我们所在的专业,材料化学,又是材料,又是化学,听起来很酷很跨学科,其实很容易哪个都只学个皮毛。我们有些无机材料的实验,比如混泥土的凝固时间和强度测定,是在B区的材料学院,那是合并的原重庆建筑学院的实验室,实习时去的企业,也是生产钛白粉的,而这个专业本来的设计方向,是有机高分子材料。我只记得钱力老师说起他用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做的一个复合材料桥梁,却从来没有见过。毕业论文,是在罗志勇老师自己博士阶段的课题方向上,做了一种高铁酸盐的电池材料,坦率来讲,也没什么创见。不过我也不是一个对学术很有兴趣的人,直到现在连跟理科都完全断了关系,这个当时稍显尴尬的专业也就无所谓了,毕竟不管谁上大学,也都只是为了谈恋爱啊。前年,毕业十年聚会,大体上,除了做游戏,或像我做律师之外,都还在这个行业。而学院已经搬到了虎溪。环境当然更好,水平又更上一个台阶。那时我们班的勾茜女士,也已经在学院任教。
我不是突然弃理从文,除了本专业,我选修了很多其他课程。我选修过摄影。用的是正片拍摄,底片洗出来就能放在放映机上投影的那种,而不是负片的反色。我现在用手机再潦草,也拍不出构图太烂的照片,大抵也受益于此。还选修过日语、法语,基本忘光了。去旁听过会计专业的课程,旁边经常坐一个叫刘小萍的江浙女生,她教了我很多星座知识,所以当然也没学到什么会计,后来也再没有见过她。但这些学习的过程,还是强化了兴趣,增加了了解,为毕业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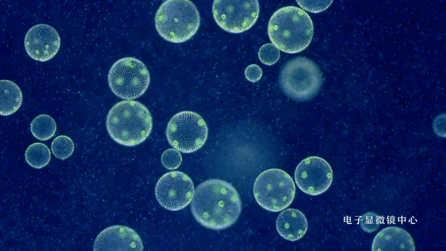
那时候重大的领导,也都不错。有一次,去打篮球,迎面来一个人,笑着跟我打招呼,看起来是去打网球的。我想这人好奇怪啊,没事献殷勤,走出去几步想起来,这不是校长李晓红嘛。还有一次,重大搞了个“五月的花朵”合唱,我就记得校长走上前台宣布开幕,然后又跑回他自己参赛的队伍里开始唱起歌来,角色无缝切换,很有亲和力。毕业时,学位授予大会,校党委的欧可平书记,几千名毕业生的学士帽上的流苏一个一个的拨一遍,那真是个体力活,而且不拒绝任何一个合影要求。就我们这些总之残留了等级制余毒的人来讲,一个副部级学校的一把手,以那么和蔼、谦卑的姿态出现,还是很感动。
重大或者重庆给我最大的感受,当然还是山城的烟火人间。我总觉得这个城市,有一种独特的情调,如笼罩于其上的两江水雾和无法挥之而去的火锅气味,和这个城市浑然一体。刚开始还是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汤菜、烧白、酱肉包子、小面,偶尔各种小炒,对我们这种在北方长期各种面食的人来说,非常过瘾,偶尔也去外面吃饭,南门外的三娃串串,牛肉刀削都记忆深刻。有一次胡贵超生日,我们去C区旁边吃片片鱼,从上午一直吃到下午,一个人好像是11块钱,我真不知道那个老板怎么赚钱。等到毕业季,那就是寻衅滋事式的找人吃饭,各种火锅。我开始胖,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时候。而且,重庆这个地方还好在,多少年后,你在回去,那个味道还在。它顽强的占领了你的胃和灵魂,从此再也无法远遁。我总觉得,不管一个人厌食还是厌世,去趟重庆那种地方每天到了饭店,全城都沸腾起来的地方,都能得到根治。

这次重大校庆,看报道,任正非先生捐了100台钢琴。我校这么多年,一直以任总作为知名校友头牌,似乎不太受任总领情。重庆大学的A区是其老巢,B区是合并的原重庆建筑学院,任正非似毕业于此。现在中美贸易战,华为夹缝中生存,非常难受。国家不幸诗家幸,任总对这个合并出来的后妈,看起来终于有了感情。
说起来惭愧,作为特别不知名的校友中的一员,我也曾以另类的方式,热爱过母校。重庆打黑正炽之时,重大聘请了重庆市检察院幺宁检察官做硕士研究生导师。陈忠林教授做重大法学院院长,延揽幺宁不奇怪,但我很好奇幺宁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到底开了什么课,发表了什么论文,于是向重大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大答复说,幺宁没开课,也没发论文。母校这么诚实,我再深究都觉得不好意思,也就此点到为止。

前一段去成都,见到胜明。我们是高中同学,在重大又是校友。火锅吃到12点,意犹未尽,又去卡拉ok,只是因为他吹牛说,他现在会美声唱法,还看戴玉强的音乐会。我说你什么时候搞得这么有情操,他说在重大读博士期间认识了个从小学唱歌的高人。
张爱玲说,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我觉得大学的价值,大抵是在人化学活性最高的三五年里,有那么一个去处,提供相应的便利和提携,让你可以自由的学习和结识,产生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在重庆,我的青春会在哪里消耗。但至少在重大的岁月,有太多美好,没太多遗憾,现在想起来,依然心怦怦跳。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重大的创校先贤们的教导: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
重大,生日快乐!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