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掩盖真理,尤甚于谎言。
我从未朝她伸出过一次援手
我母亲是个脾气很急的人,现在年纪大了收敛很多,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告诉她新学期要交多少学费,她“嘭”地把手里的碗砸向饭桌,朝我大声吼叫:“上什么上,交不上学费就干脆别上!”然后开始大声斥责我父亲的斑斑劣迹,说的话大约是很难听的,那时的我年纪太小,分辨不出哪些是可以诛心的话,只记得爷爷奶奶也不敢跟她发火,只是小声地说着大过年的一家人不要吵得这么难看,这一类无关痛痒的话。这些话激起我母亲更大的怒火,她一向埋怨两位老人对自己儿子的不堪视而不见,那是一个混乱的除夕夜,很多细节都消失了,唯一记得的是被那种恐慌的情绪笼罩的无助。
我的童年很多这样记忆,失控、激烈、深刻但模糊的争吵。我父亲是一个农村非常典型的败家子,他暴躁、浪荡、自私,他们的婚姻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两个人争吵了太多也太长时间了,以至于我至今对婚姻和家庭都没有任何美好的想象。
直到在我大约十二岁那一年,我母亲吞了安眠药。当然,她没有从这样决绝的选择中得到解脱,死有时候是很容易但又很难的事,我叫了当时邻居家的叔叔帮忙,把她送到了医院。几个月后,她拿起一把水果刀,割掉了另一个女人的头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人会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解释其中的原委。年底她回了老家,除夕前一个漆黑寒冷的深夜,她突然不见了。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深夜,我飞快地奔跑在乡间的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到了离我家最近的姨妈家里,哭着问她有没有见到我的妈妈。
没有。她无端蒸发在了那个黑夜里,而我除了姨妈家,不知道在茫茫黑暗中还能去哪儿找她。我家旁边有一口池塘,回家经过它的时候我盯着黝黑的水面,认真思考她走进去的可能性有多大,甚至在脑子里描摹出了她要以怎样的节奏和步伐走进水里才能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那种恐惧甚至不来源于死亡,而是一种未知,我母亲不知道去了哪儿,她抛弃我去了别的地方吗?还是真的去了那片水里。但第二天她就回来了,神情平静,告诉我她当晚连夜去了外婆家。那时候去外婆家只能步行,至少一个半小时。
她再也没跟我提过那一晚的事情,没说过为什么要去外婆家,没说过那么黑,那么阴冷的冬夜,她跋涉了多久才回到自己的来处,也没说过为什么那个晚上突然就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必须要走,哪怕前方是黑暗和冰冷。
那一年过后她变了很多,情绪里激烈的部分好像都释放完了,她变得不在乎很多事情,婚姻、家庭或者生活本身。她开始跟我父亲分开生活,自己做过很多工作,保姆、进厂打工或者在家务农。她常跟我说生活过得去就好,妈妈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开开心心最重要了,生活总是能过下去的。
可是我连这一点也没做到。我情绪和精神状态最糟糕的那一段日子曾经在电话里怪罪她,威胁她,在生活里拒绝她,驱赶她,那时候我家庭受害者的身份被无限放大,她成了我的原罪之一。那时候我从不跟父亲联系,她也只是被允许生活在离我一定距离的地方,我们住在一起,但我一整天也跟她说不了几句话。她被再次卷进一场因为家庭和血缘维系起来的悲剧,她的女儿濒临崩溃,连带着把她也拖进深渊,而因为这是她的女儿,她无法也没想过要拒绝这种迁怒和裹挟。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触怒我,被再次逐出我的生活。
这一切都成了很遥远的过去。如今她和我父亲都年过半百了,兜兜转转还是生活在一起,两个人默契地不再提及那些伤害。她开始刻意地在电话里跟我说起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详细到隔壁家今年高粱的收成好不好,但很少跟我提婚姻和工作,她隐约能知道我不喜欢说这些,每次跟这些话题擦边,结尾还要补上一句:“妈妈不是要求你怎么样,只是让你考虑一下。”
她只有小学文化,大约不会懂我那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我不知道她从多少细节里积攒下经验,知道我的很多选择大概会跟其他年轻人不一样,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被我曾经歇斯底里的生命危险吓到再也不敢给我一点点压力。她那么小心谨慎,生怕把我逼到她无能为力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家庭有一种深深的厌恶,对一切讴歌父母无私的形式嗤之以鼻,这大概来自一种近乎中二的原生家庭受害者思想。但我却在过了25岁后开始对母亲产生了迟来的依恋,并开始有意培养这种依恋。我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从小就比旁人安静,朋友不多,亲密的更少。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太单薄了,这些年我从重庆到昆明,再辗转到北京,似乎随时可以抛下一个城市奔向下一个,轻易地在陌生的环境里落地,又轻易地连根拔起。人在无从得到社会关系满足的时候便自然地转向自己的来处,我渴望与母亲建立起浓厚的亲昵的关系。这么说有些无耻,在一切社会关系和自身都无可挽救自我的时候,我才终于向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伸了手,只是因为我知道她不会拒绝我。
母亲当然不会知道我这些百转千回的心思,她的回应只是来自为人母的本能,以及对衰老带来的脆弱的抵抗。市场上有很多关于亲子关系的书,从各种角度切入来告知人们怎样认识,以及怎样有技巧地处理这种所有动物都必须面临的关系,但谁也没有信心拿到高分。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被动卷入这样的关系,就像很多人在对抗父母时的嘶吼:“不是我愿意被你们生下来的。”生命始于不自主,但她确实以一种本能在接纳我的一切,她似乎也意识到这个世界在逐渐离她而去,而我,她的女儿,成了她与这个世界唯一可靠的联结。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些我也不堪回首的过去里,我妈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她其实很胆小,晚上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那她当年是以什么样绝望的心情吞下那些药片,举起那把闪着寒光的水果刀,踏上那条漆黑的归家路的呢?在那个所有人都站在她的对立面指责她对我爷爷奶奶不够好,丈夫和孩子以不同形式抛弃她的那些年,她是不是真的想过舍弃这让她痛苦的全部,回到她来的地方,而她又还能回得去吗?
在看科尔姆托宾的短篇小说集《母与子》时,这些问题疯狂地朝我涌来。托宾真擅长描写亲子之间微妙的关系,互相不理解的母子,小心翼翼照顾着抑郁症儿子的母亲,死去的母亲,被苦闷的生活逼走的母亲。书中最后一篇《长冬》太动人了,我差点丢脸地在工位上哭出来。在那个因为不被丈夫和儿子理解愤而出走的母亲身上,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影子。米盖尔体会到的那种尖锐的愧疚感铺天盖地砸向了我,在那些被生活和家庭的重压逼迫到无法喘息的日子,她辗转难眠的长夜里,有没有想过要舍下这沉重的一切,出走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原里。
或许我的母亲也曾经朝某个方向求助过,曾经希望我哪怕能有一次跟她站在一起,即使是以沉默的姿态。她失望了多少次,才不得不从愤怒走向和解。
但我从未朝她伸出过一次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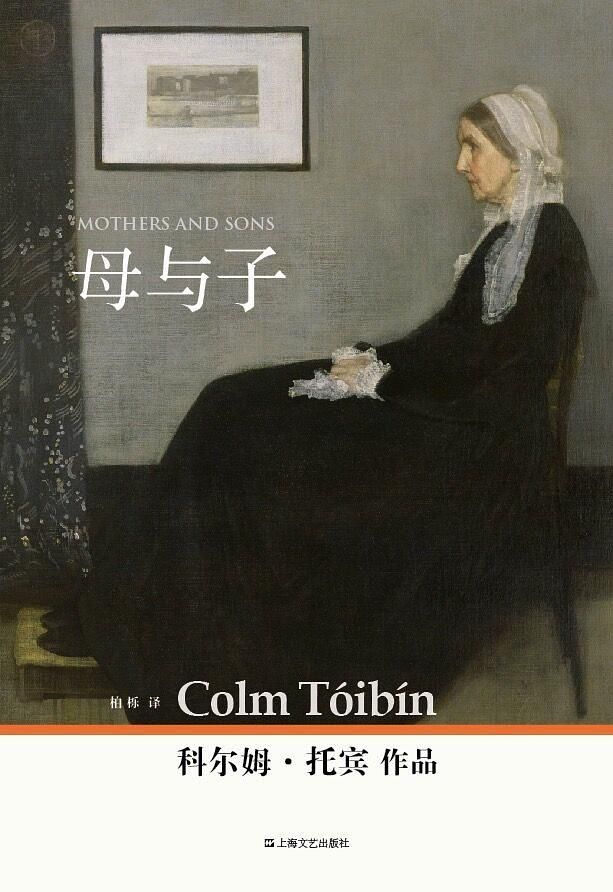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