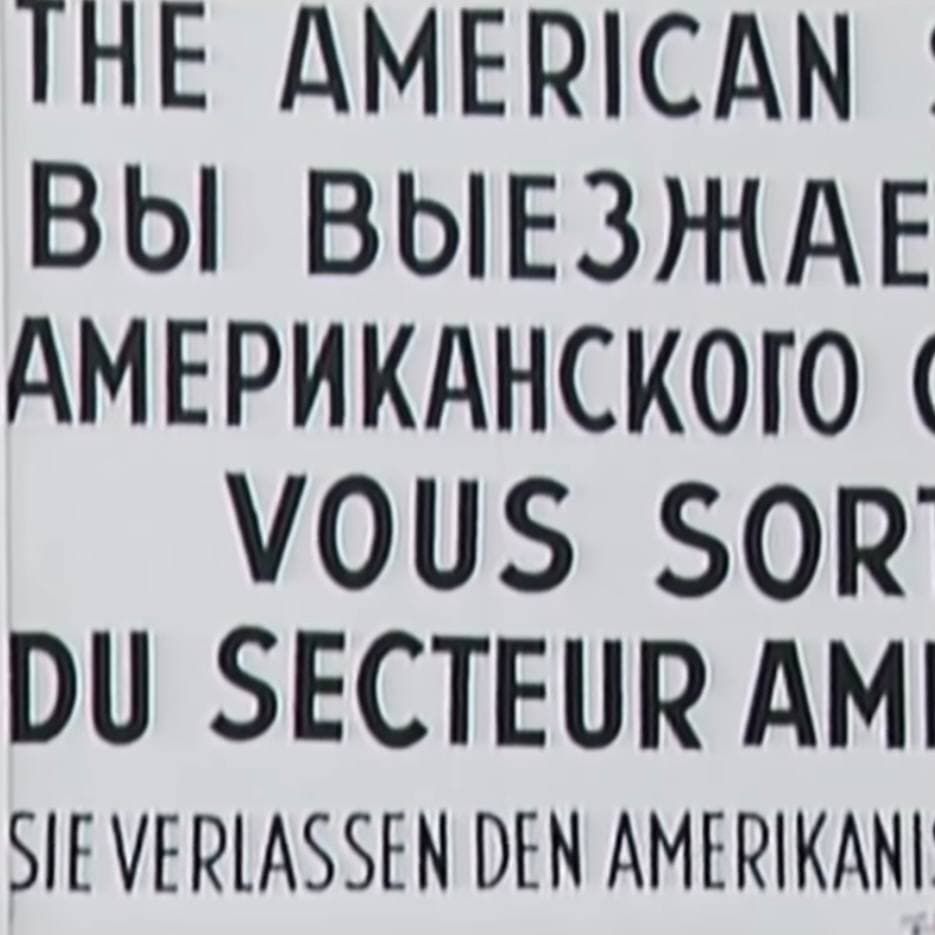
是为记
“后现代”的前现代性
作者按:本文希望把一些相对零散的想法整理成篇,当然这些想法都和同一个主题相关、或至少遥相呼应。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既包括不少读书笔记性质的引用,也包括一些全凭作者大胆发挥而产生的内容,欢迎各位批评指教,又或能博君一笑亦未可知。最后,为方便日后检索资料,我列出了文中部分引用内容的来源,附在末尾以供参考。
一
瘟疫、萧条、饥荒、战争,在发生的一切都显得太符合古典主义政治现实的时代,谈论“后现代”的前现代性似乎的确有些不合时宜。可是又有什么更合适的时间呢?毕竟在现代性未完成的意义上来看,post-modernity这个词处在和pandemic这个词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它们都是太古典、因而太现代的概念,当然,唯独却和“在现代之后”毫不相干。说它们古典,是因为概念本身对认识的要求处于古典水平,而说它们现代,则是因为它们确确实实地具有一种当下感(即使不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也可以找到相应的本体论的当下),而且正是这种当下感才让古典在现代性中真正地完成。或者换句话说,“太古典、因而太现代”的意义是,正如本体论是在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才开始完成的一样,认识论的完成也许也需要一次大转向,而在此之前,认识论就会一直是不完备的。
可能有朋友已经发现了,上面这段论述中的“古典/现代”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宗教/启蒙”描述的似乎是同一组东西,按照我的理解,前者应该算是对后者的一次有些简单粗暴的扩充,不太优雅,不过应该挺好用,有些时候概念的威力正是表现为它涵盖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可以简单谈谈“后现代”。它是个非常模糊、表意含混不清的词,不同人拿它有不同的用法,从语言哲学、解构主义到难以评价的艺术作品和卖弄词藻的艺术批评,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本文使用的加上双引号的“后现代”,指的是这个词在它的字面意义上所能指的各种含义。所有这些含义,或至少其中一大部分,在我看来具有同一种自欺欺人的特征,它代表了一种虚妄,似乎通过声称某些人和(或)某些东西处在现代之后,现代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样,似乎通过这种命名法就能靠规避核心问题而解决问题本身一样。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当然挺好,但是没有这种如果。
“后现代”从字面意义上看代表了一种非常直观的虚妄,这种虚妄首先是人对自我的欺骗。在此之外也有必要谈谈另一种,语言表达的虚妄。语言是真实的吗?一个人不管对自己再怎样真诚,他能表达出真实吗?陆机自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描述的当然不仅仅是自谦性质的文字贫乏,更是指向认识论的问题 — — 亚里士多德的“不可言说的”,到底该怎么说,到底该怎样用语言表达?康德是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至少看上去短暂地)解决过这个问题的人,阿多诺[1]从因果性概念入手阐述康德的第三组二律背反(自由和必然),指出自由的概念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甚至是他全部哲学的核心,理性批判的澄明意图和形而上学的拯救意图构成了康德的出发点,这种矛盾也正是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的动机(Motiv)。那么康德是怎么处理这种矛盾的呢?他说只要我们严格分清自由和必然分属于自在之物和现象世界,则即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由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也能够从它们的二律背反中摆脱出来。他摆脱了,我们没有。邓晓芒[2]说:“日常理性和科学主义力图把自由还原为自然或必然,还原为可由认识来加以固定的对象,这种倾向将导致人成为非人。自由其实正在于努力突破这种思想禁锢而向未知的领域超升,凡成为已知的,就有成为自由的束缚的可能。”在现代性语境里,这种源于日常理性和科学主义(或者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名词,“工具理性”)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无可避免的,无论是否希望拥抱它,总要接受,因为在这里的接受与否的问题上人类实在是没有做出其他选择的余地。不过可以往好处想,自由作为我们时代的人学的根基,离不开我们时代的“人”,因此或许到不再有“人”的时候,自由和必然就会不再矛盾。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语言表达的真实性。设想一种情景,随着算法进步、算力提升,机器对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远超常人的水平,在那时不同语言之间还会有区别吗?会有的。翻译算法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机器可以让一种语言变成(或用黑格尔的动词,entwickeln)另一种语言,任何翻译过程都不是让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按照流行的生成语法或语言解构的理论,不同语言都只是通向同一种“内在”的特定方式。我举一个可能有些强调私人体验的例子,万叶集里有一句「船乗りせむと月待てば潮もかなひぬ」,我在读时想到的是马拉美的几行诗:
Solitude, récif, étoile
A n’importe ce qui valut
Le blanc souci de notre toile.
两种场景的确很不一样,额田王在熟田津咏歌,马拉美在宴会祝酒,可是通向船、月、潮这些“内在”的却是同一条路,远征前的船队在浪潮里静候月升,而马拉美的小帆船和潮涌相触,泛起的白色泡沫里也一定有等了很久的月亮倒影(tu le sais, écume, mais y baves)。至于船上坐的是宾客还是征夫又有什么影响呢?
不过我其实不同意上面这种“通向同一种内在”的解释,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罗马,在语言的层面上,任何能构建这个“罗马”的理论却注定必须是已经远离了“罗马”本身的。设想一下,如果是康德遇到我们时代的机器翻译的问题,那他就很有可能会选择在这里停下(“分属于自在之物和现象世界”)。或者把这里的人换成维特根斯坦,如果做不到把这个部分从体系中隔离开,那他的体系就不可能开始。在这里可以继续推论,语言其实正是谈论主体间性的绝佳主题。赋予符号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主体的客体化,而符号本身、以及符号被传播后的意义回归(参考生物学意义上的转录和翻译),也是事实上的客体的主体化。主体间性,即使在最基础最通泛的层面上来看,也是根植于语言的。
对某种先验的“罗马”的依赖使得人们可能遇到这个相当讽刺的问题:是不是语言哲学、乃至全部哲学都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似乎也无从反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欧洲有一些议员提出要在法律中取消“种族”这个词,即使是说所有人不分种族一律平等也不行,因为即使只是写下Rasse这个词就已经构成了对种族(Rasse)这件事的承认。熟悉朱迪斯·巴特勒的朋友不难发现,这种通过否认“种族”来消除种族主义的行为模式在她的体系里是有贴切的位置的。她说以否认男性霸权为方法的女性主义实质上是承认了男性霸权的“自然”存在,巴特勒[3]认为,该做的事情是揭示这种霸权的不自然,亦即其偶然的权力的本质。仅就性别问题而言,我是认同巴特勒分析的思路的,不过这里的问题在后面,“种族”也可以被揭示为类似的不自然的、偶然的权力的本质吗?很自然的思路是当然可以。但吊诡的地方也在这里,如果要承认“不自然”,首先要承认的是先验的“自然”,而一旦承认先验“自然”,其实也就承认了关于“种族”的权力叙述,这种叙述却是可以表现为必然的。宗教提出的问题,启蒙没有答案。
第二个例子,汉娜·阿伦特[4]有个富有争议性的说法,“平庸恶”,不妨说说她选择的banality这个词本身,作为一个比较喜欢阿伦特的人,这是她少数我愿意提出强烈批评的地方。阿伦特自称非哲学家,而是政治实践者,这让人尊重,但也成了她一些理论问题的来源。康德讲Willensfreiheit,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设”,那么整个超验逻辑的构建就会失去意义,KrV(纯粹理性批判)从一开始就写不下去。阿伦特继承康德哲学(这也让人尊重),因此也在自己的体系中强调自由选择的位置。回到提出的语境,她讲艾希曼的banality表现在他无非就是靠一些clichés思考,其“深度”和其恶行“不成正比”,考察阿伦特这里的想法,其实是指,艾希曼事实上没有做出“自由选择”、而是遵循恶的环境选择了恶的行为 — — 这是平庸和恶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这种关联方式是忽略了一些哲学基础而只注重实践政治的(也可以理解),有能(在时代限制的条件下)理解并挑战这里的哲学基础的天分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康德都没做到(当然他也未必想做)。人的自由选择何以可能?只能等待尼采式的Übermensch吗?还是说原来康德只是做了个太美好的假设?应用康德当然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不去一一分析并尝试解决当然也非常合情合理,可是阿伦特在这里的做法在我看来是有些“不负责任”的,首先是因为问题处在非常核心的位置,其次是因为banality的概括给了一种明明很妥协但看上去却很完善的答案,虚假答案。就好像自由选择成为某种特权,又或者它根本不成立。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能成为对阿伦特自己体系的致命反驳。
二
如果在自欺欺人的虚妄之外,人们只剩下真诚的语言表达的虚妄可以选择,那么还有其他合乎理性的解决办法吗?有的,其中一种尝试是现象学。作为所有现代哲学的一种基础的现象学不是要问虚伪/自欺到底有没有在人心的深层结构中占据着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或是它问为什么/如何/会怎样的问题,而是要揭示这种不可缺少性和遮蔽性。非常可惜的是,现象学为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而使用的方法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如果说康德的动机(Motiv)在于批判和拯救的矛盾,那么胡塞尔[5]的动机就可以说是面对永恒哲学的危机感。他说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被哲学坚信的一种普遍方法,一种发展为实证主义的科学的期待着鼎盛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种朝向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 et universalis)的方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遇到了明确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哲学本身成了问题,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形式成了问题。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形式的疑问如今早已成为共识,但尽管有这种共识,从胡塞尔到他的直接和间接的传人们也还是没能给出令人们彼此信服的解决方法。哈贝马斯评论胡塞尔的方法,认为探讨意向(Intention)而非意义的做法其实正是先验哲学命题的经验转向,他关注卢曼对胡塞尔的继承和发展,说卢曼的理论是“对一种传统的创造性延续”。这个传统深受现代欧洲自我理解的影响,而它本身又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或然模式。这种或然模式,在现代性语境中、或者说在2020年看来,也许该说其实是一种必然。
齐泽克[6]说真正的激进不是要改变一切现有体制,而是要改变现有认识的体系,例如在市场和政府究竟该哪个多哪个少的话题上,真正的激进当然不是全市场也不是全政府,而是跳出市场和政府的认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哲学的危机感其实正是激进哲学的源始动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近几十年来一直炙手可热的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概念,和前者其实是可以遥相呼应的。不过在这里需要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才能算是范式转移,它最初被用来描述科学史上的突破性理论进展,后来被借用到诸多其他领域,而在挪用的过程中这个词常常难免被误解。简单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是一种范式转移,而从策梅洛-弗兰克尔集合论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就当然不算,因为前一组改变了理论认识的层次,而后一组没有。库恩本人想来猜到了自己的这个概念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反复声明不喜欢它被跨领域使用,他的确没有过虑,如今在很多场景中常见的是如“从象征主义到后现代艺术也是一种范式转移”一般的可笑用法。“后现代”究竟转移了什么“范式”呢?从理论认识的层面来看,它明明仍停留在古典的自我欺骗的阶段。
言归正传,关于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危机,哈巴马斯[7]做过很多哲学史的梳理,他着力于分析并批判“现代性”自诞生以来所遇到过的种种困难和错误,事实上就是一部按自己的体系书写了一部黑格尔以降的哲学史,在这条线上,他对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的论述很精彩。不过哈贝马斯虽然很少在精准的批判上吝惜笔墨,但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时常显得有些单薄 — — 甚至空置。当然不能怪他,哪有那么好办。现代性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确证是黑格尔就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而这规范和确证的依据 — — 主体性的原则或是自我意识,却是自黑格尔以来一直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说也许现在到了不得不重新回到黑格尔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当然也是黑格尔的同代人,我们所有人都是。
黑格尔的十字路口,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有很多方向都已经有人试过。其中一条属于尼采分支的支线是德里达的普遍文本概念和德里达的美国继承者们的泛文学化的解构方法的理论。哈贝马斯[8]提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德里达的解构其实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这问题正是尼采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发现、海德格尔想从主体哲学中以一种非主体的方式克服的问题,阿多诺想靠否定性的破解行为重拾哲学对理性的信念,而德里达则认为这种不断进行的自我否定依然沉溺于辩证法理性的极乐世界。德里达也不满足于海德格尔,因为后者还陶醉于形而上学对源始(此在)的狂热之中。可是德里达提出了什么方法呢?对哈贝马斯来说,借由语义学方法和对先验主体的迷思的解构,哲学思想不再有解决问题的义务、转而转变为文学批评,德里达的这个过程不仅仅让哲学失去其“第一性”,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其创造性和积极性。而对于德里达的美国继承者们的文学批评方法,哈贝马斯的评价简洁有力:抽离了审美的经验内涵的形而上学批判是不会有判断力的。这个判断力,如果要解释,应该就是康德在写完纯粹理性批判后意识到的不得不继续批判的那个判断力。其实也可以继续说下去,哈贝马斯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回答吗?在黑格尔、尼采和胡塞尔之后,如何兼顾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呢?康德的思路当然已经不合时宜,可是黑格尔和之后真的有解决了的方法吗?哈贝马斯自己对主体哲学的发展在于他的交往理论,在于主体间性可能可以替代或构筑某种先验主体,在于实践生活中的公共空间的构建可能可以实现对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的真正理解。可是如果不可以呢?比如,如果主体哲学的消亡最终不是由形而上学思辨引发、而却来自技术对主体的无可避免的消解呢?
哈贝马斯一向积极参与实践政治,他是欧盟的坚定支持者,今年十月发表的文章[9]继续呼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如果一个超主权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同盟能在欧洲实现,如果至少在欧洲一部分国家可以以类似公民的身份完成某种“国家的国家”的意义上的立宪,如果康德的世界宪法[10]哪怕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获得认可,那这些无疑就将是哈贝马斯毕生追求的实践生活中的理想公共空间的构建的最真实的表现。可是这些没有发生。如果说他在哲学体系上只是方法保守的话,那在实践政治中就是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了。我读到过一篇评论Philosoph der Ausgrenzung — Habermas’ linker Politstempel[11],此文相当精准地抓到了一个很能消解哈贝马斯的魅力的点,der zwanglose Zwang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是不矛盾的(在哈贝马斯体系中),也可以是矛盾的,如果要考查其中的矛盾成分,它和哈贝马斯体系在构建方法上的整体的保守其实脱离不了关系。
哲学离不开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离不开实践政治,这既是哲学的悲剧,也是其魅力所在。如何应对呢?本雅明提出了一个政治美学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灵光(Aura)闪现,于是出现了通向弥赛亚时间的时刻。这是太美好太天真的虚妄,是一种非常真诚的自欺欺人。注意在这里,本雅明是超越了古典的自我欺骗的层次了的,他非常真诚 — — 可是他也同样在自欺欺人。这意味着前文所述的两种虚妄在此达成了某种统一,如果要为这种统一了的虚妄命名,那么不妨借用本雅明的主题,作为唯一真实的历史的弥赛亚。关于本雅明的认识论,沃林[12]的概括非常精彩,他说理念作为一种包含了对自身的乌托邦式寓言的存在,在真实转型为可能性的边界确立了自身。于是最初的(伊甸园)语言才得以可能,真实的历史也才得以呈现 — — 经由理念和理念的寓言。上世纪20年代的卢卡奇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思维与存在、应然与实然的二律背反,由康德完美表达,经黑格尔得到纯粹思辨的扬弃,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中才第一次真正得以克服。卢卡奇的这种构建模式和本雅明的认识论其实是暗相吻合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历史”是自在的、不可知的,那么揭示“真实的历史”的方法就是破除这种(让人们远离伊甸的)名为“历史”的遮蔽了可能性的“直观性神话” — — 依靠无产阶级。不难猜测这正是本雅明后期转向卢卡奇的部分原因。题外话,他们两套体系的出发点和结论都完全不同,模式上的相似性只表现在构建体系的方法上,然而这种方法本身或许才是二人留下的体系中真正的精髓。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颠覆性的技术在他们的时代还只是若隐若现,现代性问题在原理上就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任何真正的回答都必须首先消除这个问题本身。在当代,无论是“弥赛亚时间”还是作为“同一的主客体”的被历史选择的无产阶级,抑或是某些如“无产阶级弥赛亚”或“资本社会主义”的拼接物,显然都已不再适用。唯独编纂的方法本身依旧熠熠生辉。
顺便考察一下本雅明最著名的概念Aura,我喜欢“灵光”的翻译。本雅明[13]早年给它的明确定义是„einmalige Erscheinung einer Ferne, so nah sie sein mag“,一种远方(无论它有多近)的显现。这种灵光由die Einmaligkeit und die in sich getragenen Geschichte eines Kunstwerks构成,不理解这种独一无二的瞬时性和艺术作品自我承载的历史是什么也没关系,继续读,他的结论也很明确:
„Was im Zeitalter d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des Kunstwerks verkümmert, das ist seine Aura.“
在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它的灵光“枯萎”了,或者用我喜欢的表达,灵光消散了。什么消散了?比较公认的对这种理解的形象表达是里尔克的一首小诗Spaziergang:
Schon ist mein Blick am Hügel, dem besonnten,
dem Wege, den ich kaum begann, voran.
So faßt uns das, was wir nicht fassen konnten,
voller Erscheinung, aus der Ferne an —
und wandelt uns, auch wenn wirs nicht erreichen,
in jenes, das wir, kaum es ahnend, sind;
ein Zeichen weht, erwidernd unserm Zeichen …
Wir aber spüren nur den Gegenwind.
而本雅明[14]在此之后则是用波德莱尔解释的,用的是《恶之花》里一节讲他的Correspondances的诗:
La Nature est un temple où de vivants piliers Laissent parfois sortir de confuses paroles ;
L’homme y passe à travers des forêts de symboles Qui l’observent avec des regards familiers.
人穿行于象征之林、那些熟悉的眼光注视着他。波德莱尔对这种现象的洞见正呼应了本雅明对灵光显现的方式的想象:人与人/自然/艺术作品间的互相注视。这种注视的效果是什么呢?在政治美学化的过程中,来自弥赛亚时间的“熟悉的眼光”是能给人温暖的。自欺欺人是虚妄,语言表达也是虚妄,但对真实的感觉却可以是真实的,这就是作为唯一真实的历史的弥赛亚。之后他又引用波德莱尔《恶之花》里的一节:
Je t’adore à l’égal de la voûte nocturne,
Ô vase de tristesse, ô grande taciturne,
Et t’aime d’autant plus, belle, que tu me fuis,
Et que tu me parais, ornement de mes nuits,
Plus ironiquement accumuler les lieues
Qui séparent mes bras des immensités bleues.
或许本雅明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种真实究竟是什么样的真实,belle, que tu me fuis,想来肯定也会是他的慨叹。
三
关于弥赛亚时间,或其他在某种意义上比较类似的表达,比如文艺复兴,有一个可能因为太直观反倒常常被忽略的特性:它首先是一个时刻,然后无论是过去的(传说中的)发生还是未来的(幻想中的)再现,都必然被嵌套在一个时间的概念之中,简单说,它离不开对时间的认识。其实本文标题在这里也有一点小恶作剧,“后”和“前”当然也离不开时间观念。
胡塞尔[15]对时间这个概念的分解尝试大概算一种精致的失败。失败的原因用非常概括的说法来表达就是他不懂物理,他说“事物在其各个显现的流动中构造自己,这些显现本身是作为在原初印象的河流中的内在统一而被构造起来的,并且必然是一个接一个地构造起来的”,于是这种延续和延续的延续就区分开来。比如内在声音的意识,作为延续的出发点的、作为本原的内意识就“不可能具有内在的时间性”,而作为延续的延续的出发点的、关于内在声音的“当下化意识”(它在相应变化了的意义上是“关于对声音的内意识的当下化意识”)则是一个内在客体,从属于内在的时间性。这样绕一大圈的好处是现象学方法得以再次合理,即使是在面对时间这个注定要寻求延续和寻求Vor-zugleich的概念时。但就其物理意义而言,这种“显现的内在统一”更像是对没有观测能力的情景的臆想,当然有可能对,但也非常有可能错得离谱。就现象学方法而言,胡塞尔认为自己靠把超越性还原到内在性中就完成了彻底的主体性。但列维纳斯[16]不同意这样的方法,他要将内在性和超越性完全隔开,但却既不能澄清超越性如何显现或给予,也不能合理地解释二者的关系,为了说明超越性如何给予自我或主体,或者说,如何在内在性的世界中具体显现,他却不得不乞灵于Épiphanie。这样,现象学费尽周折才貌似剥离开了的神的位置,通过这次显圣,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问题之中。
在继续主线问题前先回头看看更早的历史。古希腊末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事实上超越了个别或普遍的自我意识,甚至也超越了对自我意识的怀疑和简单否定,成为一种异化,正是这种异化直接开启了基督教的时代。“上帝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上帝是人的自我意识产物,但是一旦产生出来,它就凌驾于自我意识之上,取消和否定了自我意识。否定的自我意识导致了自我意识本身的否定。”这段是邓晓芒[17]介绍新柏拉图主义用的原话。在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罗马反对者之后的罗马时代,这种异化是开创性的。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在近代、甚至当代,这个上帝真的已经死了吗?当然在尼采之后基督教的上帝慢慢不再存在了,可是上帝真的死了吗?很多风靡一时的后现代哲学,本质上难道不也是“因信称义”吗?
于是说到无神论的话题,其实真正的无神论者少之又少,又或者在哲学史的意义上来看,真正的无神论对人的要求过高。所谓“世俗化”其实是个很投机取巧的词,在后世(如果有的话)看来可能会有种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的感觉。关于某某为何不是无神论的疑问,跳过那些很好理解的,简单说一下现象学。上帝死后哲学史遍地废墟,胡塞尔的野心是重建仿形而上学的罗马帝国,他意识到超越性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不管怎样总是会有个上帝的位置,那是起点和终点。而既然上帝死后这位置的空缺带来问题重重,胡塞尔就想,能不能让这个位置消失、或至少被转移到体系内。当然消失是做不到的,于是他论证了一个似乎包罗万象的主体,然后讲内在性中的超越性,似乎就把超越性还原到内在之中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现象学论述离不开现象本身,“内在”是不完备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实现完备,神的阴影就会同时降临。以上如果用现代性语境里的话语来概述:上帝死了的代价是人也必须跟着死去 — — 而这个过程的完成却必须伴随着现代性的完成。
这里就已经回到主线了,现代性如何完成?也许需要的是认识论的完成。为此不得不考察“先验”的范畴。它其实是和人的认识水平分不开的,也因此受限于技术发展的水平,用马克思式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的本质性的作用。可以举个例子,阿伦特[18]说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是有(先置的)条件的,其中有些是先验的有些是政治的,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她的政治学论述。她也顺便提到一个可能的未来场景,如果人类移民火星,那么火星上的所有这些条件就都变成人造的了,但至少人还是在符合条件地生活 — — 好像这样就不会与她在地球上的论述产生决定性冲突了一样。其实不是的,所谓先验为什么不能也是人造的呢?如果需要火星场景才能方便设想一种全部由人造的pre-context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不妨再多做一些幻想:未来人类技术高度发达,在星际漫游,寻找适合做生命实验的行星,如果其中有一批人选择跨越时间的维度,来到(我们的意义上的)很久以前的地球创造呢?在原始人的印象里当然不会有“来自未来”而只有“创世泰坦”,或者随便你叫什么名字,不影响在这里提出的哲学问题:这里真的有先验吗?举这样的幻想场景为例意在提示所谓“先验”的概念蕴含在其本身的矛盾,而不是说我真的相信某种玄学创世论,不过以防万一简要的“逻辑”辩护还是要做一下。根据线性时间观和因果逻辑当然可以说如果没有原始人那也不会有掌握未来科技的人,因此似乎上述场景自相矛盾,其实不是的,在这里矛盾的是时间观念和逻辑本身,或者换句话说,有人能提出这样的质疑这件事本身已经在逻辑上证明了未来科技的可能性,既然在当下可以有认识,那么在过去和未来也都可以有。此外,非线性的时间的可能或不可能在当下属于先验语境,不代表它就一直属于先验语境,这里和“先验”这个概念本身的矛盾在结构上是相似的。顺便提一下胡塞尔处理时间意识的方法,在以上矛盾的意义上来看,其实就是在(徒劳地)掩盖问题,超越怎么能被还原呢?只能去超越以前的超越。
“超越以前的超越”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诘屈甚至荒诞,可以举很多例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有很多赞誉,从音乐史的角度看,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超越了古典交响乐的形式框架,而从艺术批评的角度看,贝九却是呼应了、而非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主题。这一点不影响贝九在当代的评价,因为即使今天人们也能在其中听到呼应当代主题的内容,可以很直接地想到两种解释,要么是启蒙尚未完成因此主题相通,要么是贝九在跟随时代“进化”、不停自我超越,严谨一些的说法是,这两种可能性可以并存,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可能性:超越也是相对的,把它“还原到内在”的努力因此就像是刻舟求剑。设想一个或许有些可怕的情景,如果有一天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也丧失了那种被今天的我们称为超越性的东西呢?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理解贝九了呢?那当然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人的终结,可是我们今天的意义在那时还重要吗?
继续音乐史的话题。巴迪欧[19]谈瓦格纳,首先指出瓦格纳身后有许多冲突的场景,包括波德莱尔式的,也包括马拉美式的竞争者,海德格尔-尼采式的“必然”的决裂者和阿多诺式的超越者,其次说瓦格纳之后有很多合理不合理的爱好者,一个例子,当代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理论的两个旗手,齐泽克和巴迪欧自己,都是瓦格纳音乐的听众。须知瓦格纳在自己的时代明明正是没落帝国昔日余晖的绝佳代表,为什么在当代却能同时吸引这两位风格迥异的“极端左派”呢?因为瓦格纳的意义在于,他之于音乐正如黑格尔之于形而上学:完成了所有可以完成的,留下了所有可以留下的。阿多诺[20]比较瓦格纳和贝克特,说前者的音乐里只有一种虚假的等待,而不是《等待戈多》里那种现代意义的等待,因为瓦格纳的音乐需要太一(l’un)的主宰,那些不协和音程只是推迟、而不是阻绝了终点的完成。整体性,这是后世对瓦格纳最常见的批评方向,他的音乐被称为原法西斯主义,或辩证法的理性的黑格尔式的,这些都是巴迪欧不同意的方向。举个例子,后人在瓦格纳的音乐中见到了几乎无处不在的肆意展现的色情和性欲,如果参考美术史上的全面的欲望指引的历史 — — 所有作品都(可以)是色情作品。那么瓦格纳对音乐的一个意义是,他让音乐也这样色情化了。齐泽克用拉康解释瓦格纳表达和隐藏的这种性欲,似乎也呼应了一个讨论瓦格纳的主题:transition,非连续性和连续性。通常认为瓦格纳把非连续性淹没在了连续性之中,巴迪欧觉得正相反,他说瓦格纳的非连续性太激进,以至于开创了新的关系模式。而transition用本雅明的语言来说就是政治美学化的过程中闪现的通往弥赛亚时间的点,在此意义上“非连续性淹没在连续性之中”就是个荒谬的命题,因为在弥赛亚之外没有历史,在非连续性之外也没有连续性。当然从超越本雅明的角度来看,既然弥赛亚是绝望寓言,那么瓦格纳的音乐就也通向同一种绝望。换一个角度来说,人们无法抵抗色情的原因正是色情即是生存本身,而生存(存在的欲望)又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所以巴塔耶谈禁忌时选择死亡和爱欲这两个主题是非常敏感的,它们直接关乎生存这一唯一的禁忌。
四
面对禁忌,除了在福柯式的规训中遵从它之外,人们也有渴望突破它的经验。巴塔耶让对死亡(作为生存的对立的死亡)的渴望成为回归某种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的渴望,他说对僭越的恐惧不依赖于设置禁律而依赖于对被禁止的事情的充分了解和体验,广义地看,这种禁忌掩盖的正是某种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这也是神圣性的想象之所在。死之所以成为生的禁忌,在巴塔耶看来是源于生的自主权的冲动,随之而来的是主体性对权威的抵制和对自身解放的追求,对于禁忌的情况,首先是恶心,然后是对恶心的克服,接下来就是陶醉了,生死之间的陶醉。还是哈贝马斯说得好,巴塔耶的哲学史意义是在尼采之后开始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的路线,而他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揭露了“理性的他者”如何被可计算可操纵可利用的世界所驱逐和排斥,不过这个体系最终还是无力克服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内在悖论,对此巴塔耶本人非常清楚,也非常乐意摆出一副就让它去吧的姿态。在当代,谈巴塔耶的意义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于对“反形而上学”的反思,正如“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是过去的话题一样,“形而上学如何不可能”也早已成为过去的话题,于是又谈到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其中一条途径正是历史(或者用其他的什么名词)对形而上学的扬弃。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弗洛姆的朋友圈爆款级别的精神分析学概念“逃避自由”其实正和这种巴塔耶意义上的“主体性对权威的抵制和对自身解放的追求”遥相呼应。弗洛姆[21]区分了freedom from和freedom to这两种类型的自由,认为前者的自由作为对打破禁忌的渴望的呼应是有破坏性的,除非能在此过程中通过某种神奇的手段(按我的理解,比如魔术)添加足够的创造性,这就是作为对与他人的“真正联结”的呼唤的后者的自由。于是在这一来一去之间,弗洛姆就把自己限制在了甚至会令巴塔耶哑然失笑的局促的理论空间之中 — — 巴塔耶在空中花园里建假山池塘,弗洛姆则要来这个池塘里放一个充气式浴缸去养鱼。
擅长、或至少是有意识地尝试打破这种空中花园的哲学家当然也有不少,齐泽克有些时候算得上。2020年对身处2020年当下的所有人来说都显得有些非同寻常,在疫情正盛的时候,齐泽克也写过一些应时更新的文章[22]。不过就体系而言他的思路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依旧很好理解,当常态不再,除了哲学家之外的大多数普通公众也发现了常态本身的荒谬之处,所谓“自然”的理念原来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面对这一从哲学史扩张到了全部历史、也因此而变得急迫的难题,齐泽克指出对人本身的意义的疑问成为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事情。这种对认识论的大转向的需求呼唤一种哲学史的扩张。然后我再补充一点,Covid-19本身并不是促成了这种哲学史扩张的决定性事件,可以说它是标志是催化,但决定这种扩张的仍然是现代性语境中的现代性本身,另外也要明确corona时代当然也不(一定)会迎来问题的解决,消除人的意义的不是生存危机、也不是形而上学沉思,而(可能)是技术。最后这点其实正是哈贝马斯的担忧,齐泽克大概也认同,他不喜欢的是哈贝马斯在这里的逃避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不过话说回来,齐泽克当然也没什么好办法,我相信他自己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继续思考这种扩张之前,有必要插入一些同样非常应时的讨论。对敏感的观察者来说,“常态”的荒谬之处其实并不需要一次全球大瘟疫才能凸显,而另一方面,对生活在带有非常古典的认识模式的现代经验中的很多其他人来说,常态就是唯一真实,正如应许之地之于神的选民。2020年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细节,其中一个是,在近四年的川普任期之后,仍然还有许多人会对川普的出现、乃至其存在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惊讶,这种惊讶令人匪夷所思。100年前的美国总统哈定在1920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脱颖而出赢得了各方的妥协,并随后大败当时竞选副总统的罗斯福,那时一战刚结束,哈定的核心口号就叫Return to Normalcy,按理说来,人们实在没道理对这些年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感到陌生,顺便一提,哈定的另一个主题正是America First。他于1923年在任内病故,他的副手柯立芝继任后则做到了1929年,直到大萧条,他们带领美国走完了最后的Normalcy,作为一种幻觉的虚妄的常态。当然在corona时代,普通人感到被从“常态”剥离并不需要经济和政治的宏大叙事,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lockdown体验里,因为越少接触意味着越少风险,所以见面这件事本身就显现为某种同时对双方(主体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主体)生效的暴力体验。于是被这种体验剥离了正常感的人或许就会因此想到,是不是见面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而之前只是没有表现?精神科医生斎藤環在今年的采访[23]中说「会うことが呼び起こすうれしさと憂鬱さ、それらを併せ持つ、両義的な意味としての暴力です」,见面所带来的高兴和忧郁都是暴力所在。而今年顺势大火的热门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也正是在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没有这种见面的暴力的外在世界的意义上取得了空前成功。
可是如动森一样的电子游戏毕竟不是能给人真实感觉的真实,它并不能带给人们常态,或者换句话说,即使是动森的无暴力的外在世界所代表的那种例外状态,其实也只是一种无“常态”的常规。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这是魏玛时代的宪法用语,意思就是指国家的紧急状态,和法国第一次corona lockdown时马克龙说“我们处于战争之中”基本一个意思。关于这个词,本雅明[24]做过非常精确的描述:
„Die Tradition der Unterdrückten belehrt uns darüber, daß der ›Ausnahmezustand‹, in dem wir leben, die Regel ist.“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例外状态”乃是一种常规。
于是在不得不面对这种常规的意义上回到哲学史的扩张。在谈论世界图像时,海德格尔[25]说Weltbild der Neuzeit和neuzeitliches Weltbild这两个说法讲的是同一回事,因为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中被寻求和发现的,这个事实区分了有世界图像的时代和过往的所有时代。区分Weltbild der Neuzeit和neuzeitliches Weltbild这两个说法也因此成为了理解海德格尔的一个角度。在谈论现代性的时候,neue Zeit总是非常自然地成为moderne Zeit(黑格尔),但如果注意到海德格尔的事实的诠释学方法(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那么neu和modern之间是未必可以直接划等号的。海德格尔让这个等式重新成立的方法是,把Zeit(时间)这个概念延伸,这样现代性就亦是一种世界图像。与此同时,因为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所以现代性又总是现在存在的,像本雅明说的Jetztzeit。哈贝马斯说的现代性是未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人的此在(Dasein)是未完成的、所以Weltbild就仍然是现代性的。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要想完成现代性,必要的前提就是超越“此在”的人,也就是超越现代性。“现代性”这个概念本身的危机当然不在于故弄玄虚的“后现代”,可是也不在于某种“难道原来是当下感造成了现代性与之前时代的差异的错觉”的“禅意发现”,“现代性”的危机从来都只是现代性本身。如果说“后现代”的错误源于迷恋某种当下的正题,那么“禅意发现”的错误就源于迷恋这种当下的反题,它们都是“当下感”的理念工具。而这种当下的合题则正是现代性的危机所在。
而克服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或至少其中一种可能性,也许就在于前文数次提到的技术的发展。举一个不难想到的例子,随着算法进步、算力提升,机器终于实现了被今天的我们称为“强人工智能”的东西,然后其中一种应用场景是这样的:出于某种原因,机器通过某些方法制作了一个功能特化的强大算法,姑且叫它“AI康德”,它可以还原康德的所有想法,在所有场景下它都能和康德做出同样的判断,那么这个“AI康德”和已经故去的、已经走向了作为生存的唯一禁忌的死亡的康德又有什么区别呢?“AI康德”是自在之物还是现象世界?它和它自己二律背反吗?我们还有禁忌吗?齐泽克呼唤对人的意义的再思考,在最近的采访[26]中,他把自己以前的东西拿出来说了一下然后放下了这个老问题:”what does it mean to be free dignified human being, to re-define ourselves”,这种re-define恐怕会比现在的每个人能想到的都要更具颠覆性。Das ist echter Paradigmenwechsel hier. 当然齐泽克也有太多过早停下的地方,止步于此最多只能面对老问题,是没法解决老问题更没法提出新问题的。比如采访前半段里提到的sexual fantasy的概念,即使在今天的技术的认识水平来看,这也远非fundamental的Schema,在他说的re-define发生后或发生的过程中,曾经超验的Schema很可能是会经验化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飞起,因为古典的骄阳过后确确实实地迎来了现代的黄昏,而在这黄昏之中,人们还能提出问题吗?比如,黄昏之后还是黄昏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前提是作为一种超验的Schema的“昼夜交替”真实发生,而在现代性语境里,矛盾之处也正在于此,一旦超验的Schema真实发生,它就会立刻被经验化 — — 而经验化了的朝阳还是朝阳吗?于是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性的完成。
当然在瘟疫、萧条、饥荒和战争的时代里奢谈现代性的完成的确不合时宜,可是不然要等到什么时候谈呢?鲍德里亚在1992年的文章[27]里说通过人工手段把环境里的病菌都消除而创造出的无菌的清洁世界和实现这种世界的完美技术都是“致命的”,“人的灭亡正是从病菌的灭亡开始”,因为仅仅一个“非理性的病菌”就把人的常规生活打乱了,把这个透明的宇宙打乱了,用他最出名的概念来说,现实在此消失(disparition)了,不过却没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幸运的是鲍德里亚已经体验了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人的非常完整的一生,在十几年前已经走向了自己的生存禁忌,而与此同时,2020年的人类还远远没有见到决定性的突破技术,不然我们就有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场景,不知道是什么的人向不知道是什么的身体(body)提问:“AI鲍德里亚,现在你后悔了吗?也许你真的需要一些针对非理性的病菌的有效抗体(antibody)?”
2020年11月23日
参考资料:
[1]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
[2] 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 — —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
[3]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4]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I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63/02/16/eichmann-in-jerusalem-i
[5]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6] 齐泽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
[7]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8] 哈贝马斯,论哲学和文学的文类差别
[9] Jürgen Habermas, 30 Jahre danach: Die zweite Chance
https://www.blaetter.de/ausgabe/2020/september/30-jahre-danach-die-zweite-chance
[10] 康德,论永久和平
[11] Alexander Grau, Philosoph der Ausgrenzung — Habermas’ linker Politstempel
https://www.cicero.de/kultur/philosoph-jurgen-habermas-die-linke-cdu-angela-merkel/plus
[12] 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
[13] Walter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14] Walter Benjamin, 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
[15]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16] 吴增定,现象学中的内在与超越: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批评
[17] 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
[18]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19] 阿兰·巴迪欧,瓦格纳五讲
[20]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21] 弗洛姆,逃避自由
[22] Slavoj Žižek, The will not to know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the-will-not-to-know/
[23] 斎藤環さん、コロナで誰もが気付いた「会うことは暴力」
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N6D0R3YN6CUCVL02P.html
[24] Walter Benjami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25] 海德格尔,林中路
[26] Slavoj Žižek Interview | Oxford Political Re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V2vt1g_Jc
[27] Jean Baudrillard, Transparenz des Bösen: Ein Essay über extreme Phänomen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