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無中誕生︰探索文學邊界。香港文學館經營網上發表平台「虛詞」、實體紙本月刊《無形》。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由一群香港作家及學者組成,並設立香港文學生活館。常與大學、藝術單位合作,策劃各種文藝活動及展覽。 linktr.ee/houseofhklit
在香港談詩,我們談的其實是甚麼?——《詩》影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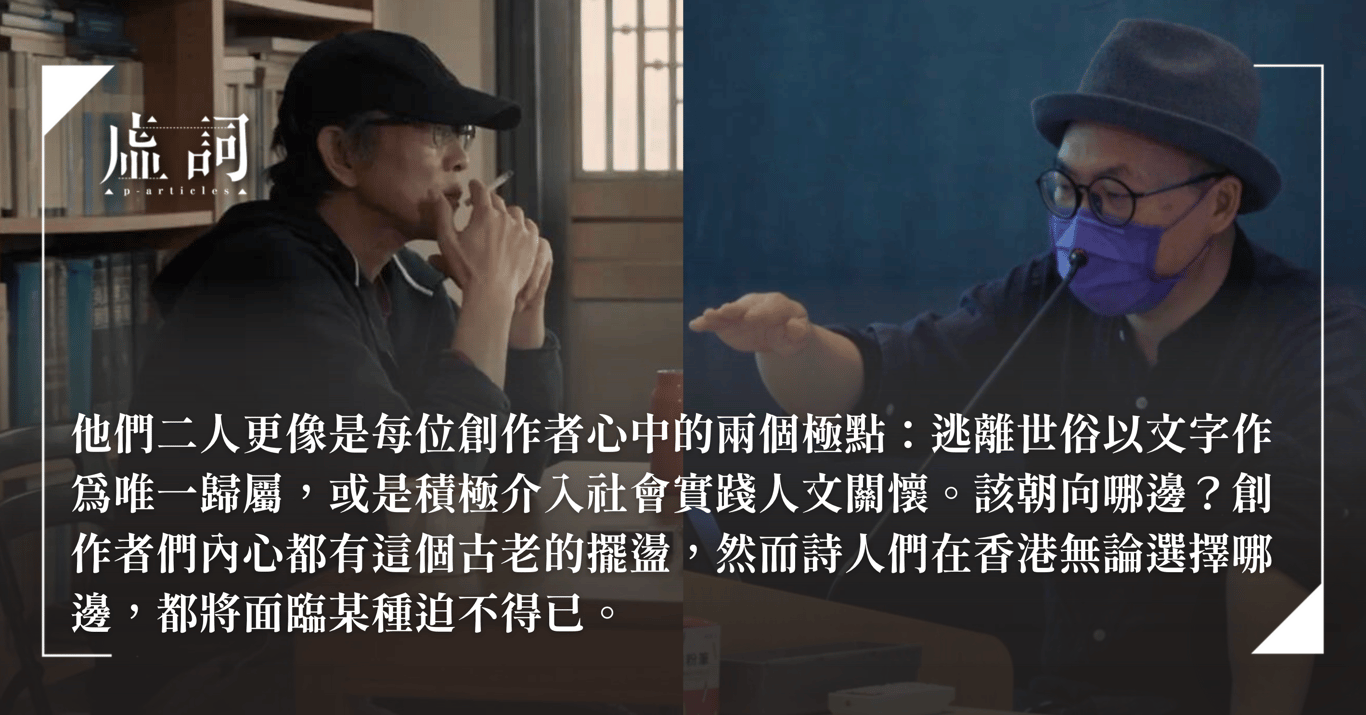
文|張欣怡
午後,一列小火車試探地向前發動,或許莽莽撞向牆壁,又或許引起一些注意。紀錄片《詩》裡最富詩意的隱喻,來自幾分童稚——詩人廖偉棠害羞的兒子Marcus,對正在拍攝的爸爸感到好奇,以車代人率先發出探問。這列被笑言為「超現實」的玩具火車,其實也在導演許鞍華手裡,輕輕推向觀眾。
火車承載的問題是:假如在香港談詩,我們談的其實是甚麼?問題聽起來很玄,實際上電影內容很大一部分更像是詩人日常vlog,觀眾跟詩人黃燦然去補褲子,跟詩人廖偉棠去上課。沒有甚麼虛筆。大眾眼裡虛幻飄渺的詩,老老實實地被攤平在大屏幕上。
詩人與尋詩者
從文字駛向影像,此類媒介轉換的文學紀錄片絕非新鮮事,光是近幾年,在台灣就有「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台灣男子葉石濤》等電影,在中國則有賈樟柯執導的《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前述的紀錄片多圍繞單一詩人、作家,或是並置幾位詩人、作家,從而建立影像結構。而《詩》卻是「三文治結構」,即開首的香港一眾前輩級詩人們約十分鐘的短訪片段,與結尾訪年輕詩人黃潤宇及導演許鞍華的片段,夾著最大篇幅的中段——拍攝兩位詩人黃燦然與廖偉棠的生活日常。如此近乎斷裂的結構,開啟了追尋的視角。而許鞍華在《詩》裡高度介入的拍攝手法,可說是直接且誠實地敞露:我也不懂,所以給你們看我怎麼找答案。詩性虛幻,就把它捋成尋覓的過程。於是,觀眾在《詩》裡時時看見她與詩人們對坐而談。她會冷不防向詩人黃燦然的觀點提出挑戰,又會在廖偉棠的講座結束後興沖沖地提問。除了導演,許鞍華還擔當了尋詩者的身分。
尋詩者有其開拓的空間,因尚未抵達意味著可被鬆動的距離。電影裡偶爾嵌入「詩意」片段——城市裡的碎片影像,如高樓間平行的天空、夜色暖燈裡的西服裁縫等(這部分是許鞍華的拿手好戲,空鏡有情),搭配詩人誦讀作品以及音樂人江逸天的配樂。這些詩作文本的再現,都是許鞍華以電影語言抵達「香港詩」的嘗試。過程中甚至不把作者本人視為解讀的權威,她在訪談裡分享自己曾為如何演繹黃燦然的詩作〈戀愛中的女人〉,而跟他爭辯,「我唔同佢拗,我唔會知。」(我不跟他爭辯的話,我不會知道。)(1)
詩人們表面上是被探問、發掘的對象,實際上,許鞍華與詩人們互為主體地呈現了詩在我城的切面。
在迫不得已之間
那麼回到那個問題,假如在香港談詩,我們談的其實是甚麼?
先定立錨點。電影之初,安排詩人西西、鄧阿藍、飲江、也斯、馬若與淮遠現身,或分享對詩的想法,或誦讀詩作,折疊時空地為觀眾鋪下一條歷史軌道。依循前輩們的錨點,觀眾也許會得出香港本土詩的風格——生活化、容納廣東話、都市感等特色作為答案。但電影顯然無意在此煞停。
繼續推進,便看到同樣從詩出發,走向卻截然不同的黃燦然與廖偉棠。他們二人更像是每位創作者心中的兩個極點:逃離世俗以文字作為唯一歸屬,或是積極介入社會實踐人文關懷。該朝向哪邊?創作者們內心都有這個古老的擺盪,然而詩人們在香港無論選擇哪邊,都將面臨某種迫不得已。
譬如迫不得已的「經濟流亡」,黃燦然此形容一出即惹得電影院哄堂大笑。笑聲過後卻無法反駁,我城裡的詩人必然屈於金融中心、商業大樓的陰霾底下。如黃燦然所言,詩人「本身精神很高,但他的身體是很世俗。」(2)買新褲子要錢,飽餐一頓牛排也要錢。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香港裡,潛心煉詩的選擇會遭俗世加速磨蝕,因而走向避世一途。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的香港,避世的取態未必討喜。但戲裡黃燦然談詩的真誠始終讓人敬服,與其說他是脫離社會,倒不如說他脫離的是現下的社會。這是一種強大的信念——他的詩是要活在他死後的,可以說,這近乎漢娜·鄂蘭形容班雅明那種,對自己身處時代的「生疏」(inexperience)。
廖偉棠面臨的,則是畫面模糊的迫不得已。畫面指的是電影中保衛皇后碼頭的片段,以及更多。影像當然本是清晰可見的,放到觀眾眼裡時,卻光影散亂,只餘聲囂可傳遞。這是近幾年香港人心照不宣的迫不得已。廖偉棠把責任看得重,擔當父親擔當老師擔當知識分子擔當詩人,即使疫情期間,日子仍然過得自律且緊湊。他是積極介入社會的詩人典範,從前他把自己放在現場,到了台灣授課,仍然絮絮講解策蘭及布萊希特(作為他詩課的學生,我可以親證他講述兩位詩人時,總是說得肉緊。)而一個連詩集也會被下架的城市,注定要讓這樣煮雨焚風的詩人揪心又疲憊,如同那些模糊影像裡的吶喊。
但是,迫不得已,就是電影反覆在城裡尋詩的答案嗎?
《詩》的亮光最後灑在黃潤宇和許鞍華身上。無論是黃潤宇提及把詩寄給獄中人的眼淚,抑或許鞍華明知題材小眾,仍想把紀錄片拍出來的心念,恰恰是「詩」的力量。在迫不得已之間生發。那就像是,《生命之詩》裡美子拾起地上熟爛甜杏的瞬間。超越現實的瞬間。
(1) https://youtu.be/SX1c1o7FVkI?si=-aW65lpoHSckEsZz
(2)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30709/1688840510358/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窮一生的詩-許鞍華與黃燦然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