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想你同情又挑釁:《地厚天高》與《藍天白雲》(上)
香港的年輕人還有甚麼出路?《地厚天高》與《藍天白雲》雖然類型不同,但同樣回流露出年輕一代的灰暗展望。兩齣電影中的主人翁似乎都要走進牢獄,象徵同代人的目前困境,生活在壓抑與暴烈之間迴蕩的情感氛圍之中。

《地厚天高》的導演林子穎和《藍天白雲》的導演張經緯描寫人物時都嘗試引起觀眾對該人物的「同情」,但叙事上分別用上「補白」與「留白」兩種進路。有趣的是,兩位創作者使用的手法總會引起一些觀眾困惑和不滿,似乎也在他們有意識的藝術取捨之中。藉著這些取捨,這兩齣電影能給觀眾帶來甚麼?
《藍天白雲》的問題:爸爸我想殺咗你
《藍天白雲》被一些評論者指為人物單薄丶劇情不完整,導演在叙事中刻意的「留白」是一種結構上的闕漏,使主要角色的關鍵行動沒頭沒尾地出現,欠缺說服力,更遑論引起共鳴。這樣的情節主要有三個:女主角Connie決定殺害父母的觸發點不明;為何其好友Eric那麼討厭自己的家,在母親面前說出「寧願坐牢也不想回家」的話;女警Angela在的士上突然情緒失控摑打患上老年失智症的父親,心底裡甚至恨得想殺死他,但劇情並沒有對她的恨意作出清晰交代。
若說「留白」是為了引起觀眾參與,讓他們自行想像劇本沒表明的事情,就Connie的殺人動機這一點是比較容易為人接受的,因為編劇用了比重較大的篇幅去描寫Connie家裡的處境,以及其父親是多麼自私、可惡的人,使觀眾對她產生同情。但她的具體殺人動機是甚麼?為何連同受父親壓迫的母親也殺害?Eric曾經問她其父親有沒有試過「打她的主意」,對此觀眾也得不到答案。這種雖無法理解也可以想像的空隙不大,就如一幅拼圖所缺的零丁數塊。可以說,導演期望牽動觀察的情緒,以替補其認知上的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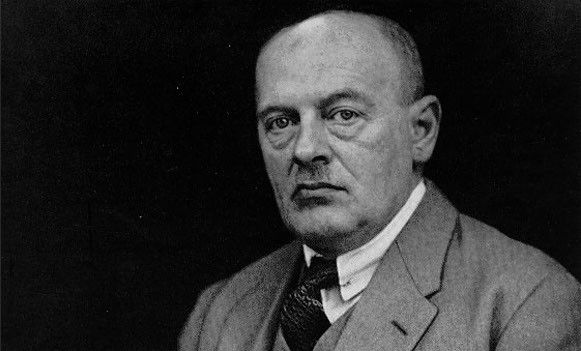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對「共通感受」(Sympathie/ Shared feeling)的現象學分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藍天白雲》裡的情感操作。舍勒把「共通感受」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直接的共同感受(das unmittelbare Mitgefühl/ Community of feeling),例如幾個受欺淩的學生一起感受到委屈;第二類是真正的同情(das Mitgefühl/ Fellow feeling),例如一個學生見證其他同學長期遭受欺淩,因其痛苦而自己也感到痛苦。這種情感的基礎是對受苦者的理解,但雙方的感受是類似而非相同。
第三類是「情緒感染」(Gefühlsansteckung/ Emotional contagion),例如一個學生遇到一眾同學興奮地欺淩一個同學,受到其氛圍影響,不禁也興奮起來。這種情感是情緒先於理解的,因此也是危險的,例如魅力非凡的獨裁領袖可藉此操縱狂熱的群眾。第四類是「真正的移情」或「情感認同」(die echte Einfühlung/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是「情緒感染」的極致,個體間的界限漸漸消弭。
當中最重要的看來是第二類「共通感受」,即基於理解的同情,有意識地分享到別人的感受。在電影的解讀中,我們可以分別處理創作者、角色和觀眾相互之間多個層面的共通感受。

如何讓人同情兇手
Connie為何要殺死自己的父母?其中一個解讀是,一次偶發事件觸發了她要毁滅自己家庭的動機:Connie的父親把援交對象帶回家,不只親熱,還要把她留在家晚飯,而這援交對象正是校內的欺淩者,更是受教師信任的女班長。父親是家裡的欺淩者,沒有保護女兒的母親同時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女班長則是校內虛偽的欺淩者,而這個「欺淩者聯盟」同檯吃飯的景象徹底地顯示出「家庭親情」的虛假,令Connie忍無可忍。
或許其他觀眾有其他的想法,但導演引起觀眾這種參與意欲的方法,是引起「同情」。戲中對Connie受欺淩的苦況以及對其父親的負面描寫,在認知上給予了觀眾部份的基礎,但最重要的一記「情感的跳躍」,是在社工辦公室的一場,當社工告知Connie父親其女兒涉嫌偷東西之後,Connie父親生氣得把皮帶抽出來要攻擊社工--就像當他發現Eric藏在女兒的衣櫥之後的反應--這時Connie突然跳上桌子,向父親像野獸一般叫喊。導演嘗試讓演員梁雍婷用這種撕心裂肺的反應,把一種無以名狀的忿恨和痛苦直接傳達予觀眾。這種引起同情的方法比較傾向第三類的「情緒感染」,以情緒替補認知上的空白。
在《藍天白雲》的結尾,作供過後的Connie失聲痛哭,Angela也感觸落淚,這是角色之間的「共通感受」。不難理解,Angela傷感的基礎來自錄口供的過程中對對方苦況的理解。另一方面,她會否也是感懷身世,因為Connie對其家庭的憎恨讓她聯想到自己對父親的負面情感?
問題正在於,在電影中有關Angela的背景被刻意省略,劇情僅向觀眾提示其父親在患上失智症前或許做過傷害妻子和女兒的事情,但觀眾也只能猜猜而已,而且這猜想是從她在車上摑打父親的行為反向進行的,那麼她恨惡父親的理由,觀眾其實無法認知,難以同情這個角色(類似情況也出現在Eric身上)。因為認知上的空白太大,觀眾難以對角色生出同情心,反而感到突兀--「我怎麼想像她的經歷和心態呢?提供充分的情節和人物描寫不是創作者的責任麼?」

張經緯說過他有意師法伊朗導演Abbas Kiarostami提倡的「未竟之戲」(An Unfinished Cinema),邀請觀眾介入。《藍天白雲》也令人想起奧地利Michael Haneke的《第七大陸》(The Seventh Continent)和波蘭導演Krzysztof Kieślowski的《殺人短片》(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前者講述一個看來準備去旅遊的中產家庭最後全家自殺,後者則講一名青年隨機殺死了一個的士司機,最後接受死刑。這兩個故事裡,自殺/殺人的具體動機都是隱晦不明的;叙事上的大量留白正是漢尼卡的慣常風格(他的觀眾在中途離場也非新鮮事),而《殺人短片》中的兇手不是冷血或發瘋,他的經歷得到其辯護律師的同情,這一點亦跟《藍天白雲》相像。
當然,電影大師會用「留白」手法,不等如「留白」的就是大師。這種手法作為對觀眾參與的邀請總是冒險的,因為觀眾總有拒絕的可能。即使觀眾進場時懷著一顆開放的心,他們能否「進入」電影打開的缺口往往受一些外部因素影響,例如創作者所處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語境,以及觀眾自己的背景是否能提供充足資源讓他們在留白的空間有所發揮。
(待續...)
[原載於2018年2月11日《星期日明報》]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