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文詩人🌀 @字縛雜誌 Founder 書評外的話👉 https://liker.social/@MaryVentura
書評•評書|賈平凹的《極花》與性感腳鏈
賈平凹從來不是我喜歡的作家類型,他的《廢都》在我腦海中也永遠只會是那個高中時代青澀卻略帶禁果味道的談資,但讀了《極花》及其後記以後,我的態度改變了——我覺得賈平凹是一位不錯的作家,他的虛構創作將這樣一個沈重、滅絕人性的人口販賣故事以受害者的角度展現,其真實感有時候甚至會讓人覺得作者是一名女性。而他在後記中開頭講述的《極花》其實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結合書中情節細想,不寒而慄且更加令人心碎。
鐵鍊拴著的李瑩事件後,很多人對賈平凹這本書後記中作者表現出來對拐賣婦女的態度嗤之以鼻,覺得這樣的一個光棍村子以不把女人當人只當作是生育工具的地方斷香火就斷吧,滅族就滅吧,其實,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也不無道理,只是從《極花》小說本身和《極花》後記這兩個部分來看,賈平凹似乎是兩個人:前者,賈平凹是極棒的作家,他醞釀了很多年的這個發生在自己老鄉身上的真實的故事經過他的修飾和敘述,成為了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後者,在《後記》中道出這個真實故事的賈平凹成了一個需要迎合審查,站在一個不作為的國家的角度說話才能過審的小心翼翼的詭辯者。這,正是嚴歌苓再也不願意做的吧。誰又能確定賈平凹不是呢?
《極花》中女性的絕望
讀《極花》,作為女性,痛得無法呼吸。有些文字我會閉上眼,彷彿眼前的黑暗能抹掉剛才看到的文字的暴力一樣。徒勞。
看不见窑门窑窗,而似乎是窑门旁春节贴的对联已经破了一角,在风里一起一落,像一只鸟,永远在那里扇翅膀。那就是老老爷家。
《極花》的英文書名如下👇

因為被拐賣的女人叫胡蝶。她被困在窯洞裡,看到對聯永遠在那裡扇翅膀是揮之不去的一個畫面。我也住過窯洞,那時候小,還很新奇,後來再去窯洞裡也總還是有趣得很。但是讀了被困的胡蝶的話,感覺到她的無助,渾身顫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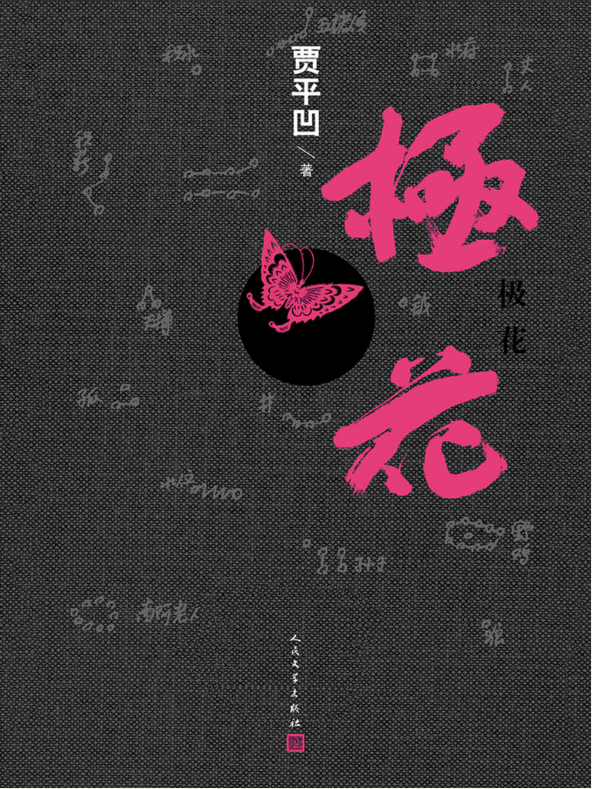
中文書封我非常喜歡,黑中透著藍的底色,好像是那無盡的天,胡蝶每每看著天,卻走不出那四方的地。封面上四散著星座的圖案和名稱。那些是老老爺給胡蝶畫的「星座圖」。老老爺給胡蝶扔了一個紙團,胡蝶以為是逃跑的路線圖,打開一看卻是封面上這樣的「星座圖」。成天坐在那兒看天的老老爺也沒有幫助她。看著中文書封,就好像看著胡蝶將那揉成一團的紙慢慢展開所經歷的失望。一隻像窗花一樣的胡蝶在「極花」二字旁邊扇翅膀⋯⋯
被拐賣來之後立即進行「婚禮」,胡蝶趁亂跳窗逃跑,卻被幾乎都來「喝喜酒」的村漢們抓了回來,衣服扒光,當場猥褻毆打。後來,胡蝶就被制伏了。再後來,胡蝶腳上拴上了鐵鍊,窯洞外臥著看管她的狗。再再後來,胡蝶被「丈夫」五花大綁起來強姦了。
《極花》中的人格解體
上述👆這些敘述的文字非常難讀,是任何一個人可怕和難以想像的噩夢。在胡蝶遭受村里人的集體暴力和丈夫的強姦的時候,她在極端情形下經歷了心理學意義上的人格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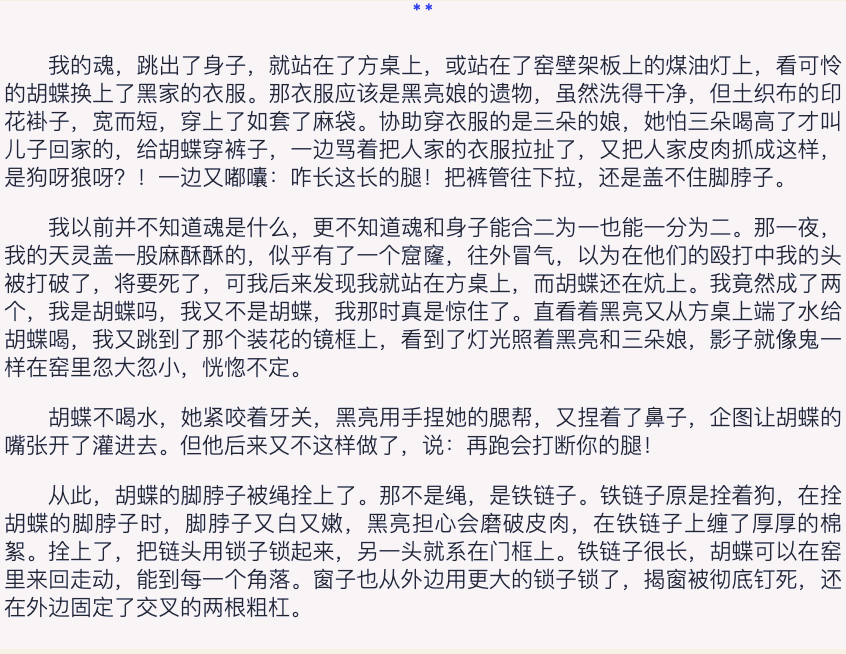
這種在經歷極端暴力或trauma的時候,大腦出於自救機制將人的mind從暴力現實中抽離出來的過程,在之後的人生中會重現,叫做人格解體。賈平凹不一定知道這個現象在心理學上的分析,但是,他一定聽過旁人敘述這個感覺,就像是靈魂出竅。在這樣的人格解體片段中,胡蝶的魂在👆上面,如同上帝視角,以第三人稱開始敘述。之後,胡蝶在日常生活中也屢屢經歷人格解體。不得不說,賈平凹將這樣的經歷寫得真切。
《極花》中現實的絕望
在故事的將近末尾,胡蝶經過一番打鬥被解救出來了。書中來解救胡蝶的是她母親和派出所的民警,賈平凹在《後記》中說道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去解救女兒的是他自己的老鄉。老鄉這麼多年為了找女兒只能撿垃圾維生,終於將女兒解救回家。可是,跟故事裡一樣,被解救出來的時候,胡蝶已經有了孩子——兔子。有了孩子的被拐賣婦女會獲得一些自由,因為她們的孩子就是人質,往往在她們單獨行動的時候不能跟著,這樣,即便想跑,也不會跑太遠,最終還是回來。
其實,我覺得本來已經足夠悲傷、絕望的故事了,沒想到,結尾被解救出來以後的部分讓人陷入更加無底洞般的絕望——
胡蝶被拐賣後獲得民警解救的事蹟被當地電視台翻來覆去歌頌,胡蝶受不了來自外界的指指點點,無法出門,而來自家裡人的責怪更像是一把把尖刀,扎在胡蝶心上。是啊,唯有來自你深愛的家人的傷害才能從根本上將你連根拔起,那一刻,以至於那以後的每一刻,你便是一顆浮萍,一隻蒲公英,隨著風落在哪裡算哪裡⋯⋯你不再有家了。
在故事裡,回來的胡蝶被親弟弟責怪——
“弟弟还在说:姐,你怎么就能被拐卖?!我连老家也无法回去了,就给弟弟发脾气:怎么就不能被拐卖?我愿意被拐卖的,我故意被拐卖的!弟弟说:真丢人!你丢人了也让我丢人!我就和弟弟打了一架,打过了我就病了,在床上躺了三天,耳朵就从此有了嗡嗡声,那声全是在哭。”
走在街上被小女孩的媽媽指點,說如果小女孩將來不聽話就會像她一樣被拐賣。我覺得自己好像就是胡蝶,因為我對這種指責受害人的文化太過熟悉。你心痛、撕裂的傷只不過希望最後一次得到父母親人的舔舐,然而,從來沒有過第一次,何談最後一次。沒有人詢問過胡蝶受到的傷害,沒有一個字的詢問。更可悲的是,胡蝶的被拐賣就是因為她心心念念要掙大錢,養母親;而在受到全村男人的暴力群毆和猥褻姦污時,胡蝶想著的是母親可能愁白的頭髮,生在中國的女孩子,有太多太早就失去了自己,只有父母,唯有父母,而父母也唯有父母。胡蝶經歷著非人的虐待,像是被鐵鍊鎖著的李瑩,可是胡蝶心裡擔憂著父母,責怪著是自己讓父母操心。
在這樣層層吃人的文化下,生為孩童往往經歷的是一種collective般的侵害,文化沁入肌理,一定讓孱弱的受害者一遍遍地責怪自己,是自己讓父母擔心了。我現在升為人母,終於可以有自己深愛的孩子,告訴他我選擇你出生就會為你擔心一輩子,但所有的擔心都不是你的責任,而是為人父母的必經之路。
故事的最後,胡蝶選擇回到被拐賣的村子裡,去跟自己的孩子和拐賣自己的丈夫團聚了。賈平凹說,老鄉身上的真實的故事也是這樣,女兒選擇給父母留下一張字條,回到那個曾經如地獄般盼著被解救的村子去了,不僅僅因為孩子在那裡,更因為解救出來後,她的絕望成了現實,父母想要讓她嫁到遠處一個並不認識的男人那裡,離家遠遠的,別人不知道她的過去。
故事和現實中一切的一切都透著前現代社會黑洞般的絕望,更令人深感無力的是,你我都深切地知道,那絕望就在不遠處。
胡蝶坐在回村子的火車上,她腳上戴著老老爺給村里每個人的祈福繩繩。同座位的女孩對胡蝶說,「你的彩色腳鏈好性感啊!」我不知道胡蝶的心是怎樣地滴血。
看完書,我自己也用繩繩編了一個腳鏈,不是彩色的,倒是把自己一個Tory Burch的手鍊剪斷做的。這個剪斷的手鍊是Tory Burch的一個基金手鍊產品,每買一個手鍊都會為幫助女性出一分力,是老公給我的禮物,另一面寫著「擁抱野心」,鑲著一顆小水鑽。我把它們一個編成了手鍊,一個編成了腳鏈。編的時候,腦海中一直想著胡蝶,想著當她坐在自己選擇的再次去往被拐賣地點的車上,聽到腳上的鏈子被稱作「性感」時心裡的感受⋯⋯無形之中我似乎越來越理解自己的遠走,也越來越近似絕望地看著曾經那個小女孩,你得不到的愛永遠都不會得到,你長大了,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也只有自己再去愛那個小女孩了。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