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世界是否变好已不重要

被关在笼子里已超过50天了。不时有外地朋友来问我:你什么时候解放?又或是在宽慰之余说一句:祝愿你早日解封。
说实话,这个就不指望了。
我当然知道他们都是一番好意,但如果你也像我一样,3月24日封小区时只说是两天,此后经历了各种说辞的变卦之后,就会明白,这种希望不过是虚幻的一厢情愿。它和你的所作所为没多大关系,无法寄望,那像是一个冷淡的神灵,即便对虔诚的祈祷也无动于衷。归根到底,这对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来说是有伤自尊的。
希望确实是个好东西,但那有个前提:我们自己能掌控那个希望。一个飘忽不定、完全不受我们左右的念想并不是希望,而更接近于“运气”。在随机的风险之下生活,所谓“希望”就像是蝼蚁竭尽全力想着下一次能否免于被大象踩死。
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突发奇想,如果你仔细看看周围,或许也会发现,在空前严厉的管控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大彻大悟。如果你努力的一切,瞬间就能面目全非、房子随意被闯入破坏、即便亿万身家也最终都不是你的,那努力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及时行乐。
人们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地基下巨浪翻腾,而就算这场海啸退潮,它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曾写过,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发现,他们的生活不堪一击:
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和其他身体疾病,迅速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前,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

当然,大部分人会熬过来。上海迟早会解封,街市恢复熙熙攘攘的景象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没有疑问。这座城市遭受过更大的破坏,就算死一半人,也还是会重生,问题只是要花多久、有多少人能熬下来、熬下来的是不是自己而已。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那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所熟知的生活,以及那种生活所奠基的安全感,已经被摧毁了。有人和我说:“很多时候,历史一个轻轻的拐弯,对于很多人就是漫长的一辈子。光明终将到来,但是黑夜已经埋葬了很多人的一生。”她说得对。
这两年来,欧美也常有人抱怨“疫情使我们的视野变得狭小”(“the pandemic has narrowed our horizons”),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疫情都在推动某种内部化转向:它减少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压缩了个体的活动与交流空间,进而大幅增加了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人们的生活视野被迫由外转向内在,不安全感与风险规避倾向也随之与日俱增。
借用刘子健对宋代社会文化转向的论述,我们可能正目睹“中国转向内在”(China turns inward)。对秉持这种新精神的人们来说,早些年那种在“致富光荣”口号下获取外在物质的冲动,甚至在尚未得到之前,就已转化为一种成熟的冷漠,一种置身事外的犬儒。
当你看着台上那些煞有介事的忙碌,洞察到其荒诞性,很难克制住不发笑。“人生就是一篇荒唐的故事,由白痴讲述,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那是一出悲剧,一场表演,遗憾的是,我们所有人为了这场演出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我们,也没办法退出。
人民已经疲惫了。就像橡皮筋一样,在被剧烈拉伸折腾得久了,弹性就没了。看多了,就很难再惊奇了,遑论感动。如果你认真问问年轻人,会发现在他们貌似顺从的外表下,真实的想法是:随便,你高兴就好,我根本不在乎。

准确地说,这样的心态在疫情之前就出现了,只是那往往仅见于那些敏感的心灵,他们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提前捕捉到了那种异化带来的空虚,那正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人们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哲学式的精神困扰,被视为一种全新的疾病——“空心病”。
也许要不了多久,大家长们就会发现,真正头痛的问题并不是人们的抵抗,而是其全盘热情低下——以前他们害怕人们的积极,很快将担忧其消极。
有一位公务员朋友说,他也理解很多人的苦闷、不满,那行啊,“期望有更多不满的、有自信有素质的人,愿意投身公共服务领域”,怕的倒是疫情过后,“人们对公共领域的热情和关心也烟消云散了”。实际上,都不用等到疫情结束,现在人们的这种热情就已经在大幅衰减了。
从这一意义上,这段封控所推动的社会心态变动,是任何公共知识分子都无法做到的:让更多人转向自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公共政治。在公信力崩塌之后,一种立足于自身的质疑精神登场了:对于官方的宏大话语,先怀疑,除非后续能证实。
前些天,有位读者私信给我说:“经此一疫,这世界是否变好已不重要,尊重自己的想法而不被愚弄就好。”他说出了很多人的想法:那种对外界、对未来不断进步的信心已遭重创,也并不在意了,转而坚守自己内心。既然正因为抱有希望才痛苦,那么干脆完全撇开,也就无欲则刚了。
有朋友说,她现在只想着怎么让孩子顺利出去并留下来,“我也就安心做最后一代了。那句‘我就是最后一代’,真是让我心里难受。这是最后的牵挂,让人舍了,可不就可以随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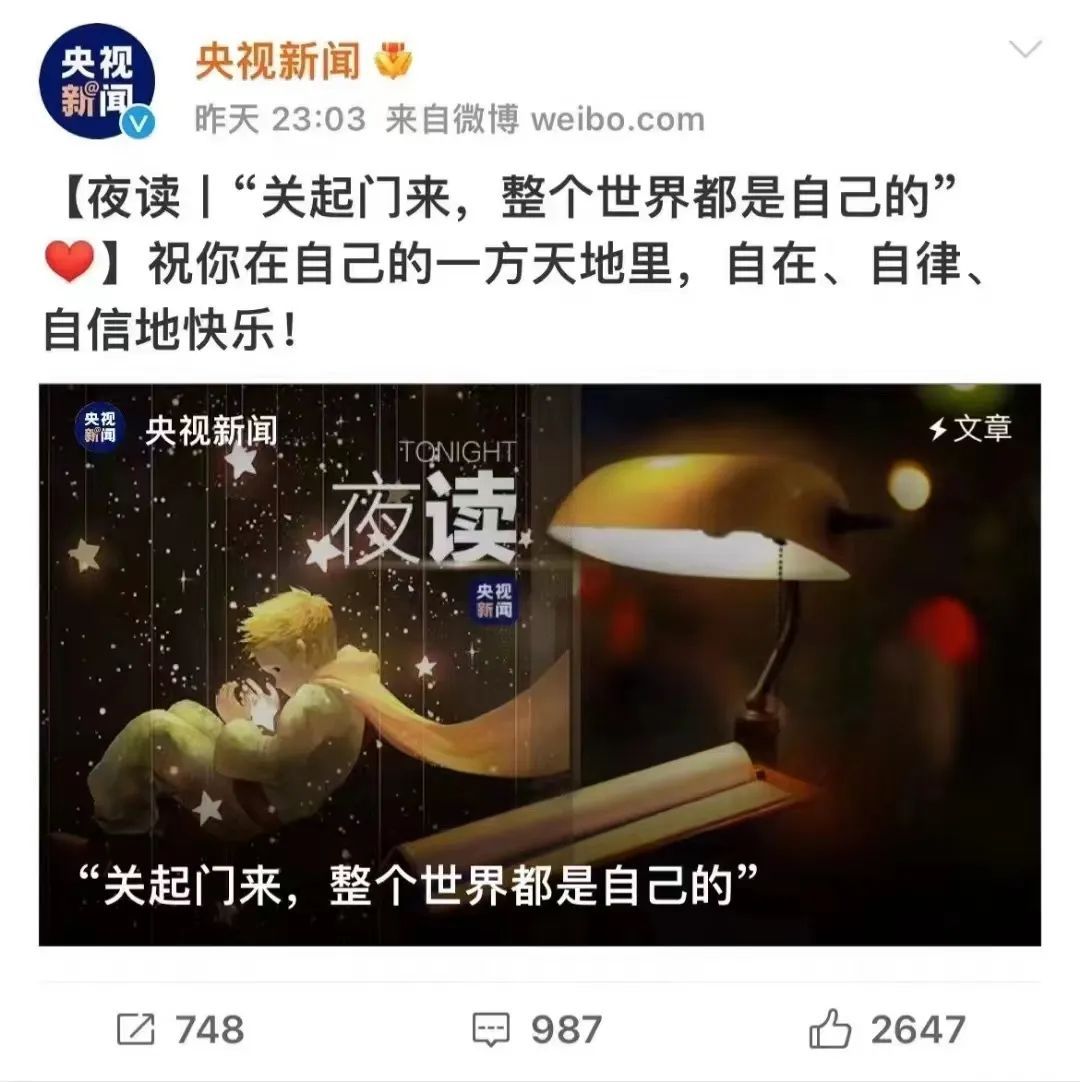
但是等等,这会让我们反过来在无意中成为共谋吗?当你看到央媒都说“祝你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自在、自律、自信地快乐”时,可能本能地怀疑这是不是塞壬的歌声。那种“关起门来,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的说法,更像是我们当下大环境的隐喻,而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处境——在现实中,你随时可能被破门而入。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服务于控制的“岁月静好”假象与坚守内心的自尊,看起来只有一线之隔。在此,重要的或许不是全然摒弃外界,更不是切断与外部的联结,而是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看清现实,看清自己究竟是谁。
现在已经到了捍卫自己价值观的时候了。不止一次,我听到有人说,原本关系很好的亲友都吵翻了,有时甚至也没说什么激烈的,忽然就被拉黑了。现在的状况,那些曾坚信国内做法的人或许尤为挫败,既不能说服他人,又不愿被人说服,毕竟颠覆自己的元认知是一件痛苦的事。那种拉黑看似是攻击性的,但本质上却可能是防御性的——然而,这种防御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动摇了。
如果这能带来内省,那也意味着一次大规模的“自启蒙”: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最终取决于你最不能舍弃什么。那并不只是在“断舍离”的清单上打勾,还意味着被迫转向对自我的全新认识:人生一世,我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仍然可以心怀希望,但这希望要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任何外部力量上,因为它们都是靠不住的。抛开那些不必要的牵挂,我们应当在这短短数十年的人生中,尽可能地追寻生命的可能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雪莉·杰克逊在她的小说中曾说:“没有任何一个活的机体能够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长久地保持健全理智。有人认为,就连云雀和蝈蝈也会做梦。”是这样,蝼蚁也许不关心这世界会不会变好,但在活着的短暂时光中,它也会做梦。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