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实修·转化
546 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靈|杨小凯
野兽按:《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是杨小凯回忆录,讲述文革时期他在长沙坐牢时认识的二十多个人物的故事。1994年出版,1997年、2016年再版。英译本名为《囹圄中的精灵》(英语:The Captive Spirit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内容和中文版差距较大。多数章节曾以《狱中回忆》为名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连载。
余杰在书评《在暴风驟雨中,有青草生长的声音》里写道: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中共高干家庭。“文革”爆发后,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和“狗崽子”。一九六八年,二十岁的杨曦光写出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此文震動全國,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于是,杨小凯被毛泽东“钦点”抓进监狱,一年多之后,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此案更是连累其父亲被监禁,其母亲不堪羞辱上吊自杀,两个妹妹四处流浪,可以说是因言获罪、家破人亡。
十年暗无天日的冤狱,会毁掉一个庸人,也可能成就一名先知。杨小凯此后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成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奬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跟这段顿挫苦痛的人生履历不无关系。而最让我感到“拍案惊奇”的是,杨小凯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狱中回忆录《牛鬼蛇神录》。在出狱时,他對自己說:“不管將來發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爲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政论家胡平高度评价此书说:“《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杨小凯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他们确实是颠覆中共暴政的身体力行者
陈独秀说过,监狱是研究室,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成不了一流的思想家。聪明绝顶的杨曦光遇到文革风暴,不能上大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卻將监狱当作一所另类的大学。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他发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地下世界,结识了一批比他更彻底地反抗中共暴政及其意识形态的先知先觉。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全民“道路以目”的“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那个“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尽管必须承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狱卒的羞辱和折磨,以及防不胜防的告密者,但杨曦光与志同道合的狱友們逐渐形成一个小团体,他找到了政治学、经济学、数学、英语、建筑学等各门学科的老师,长沙郊外的建新农场的师资力量竟然不亚于北大、清华。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劳改大队,可谓藏龙卧虎、群贤毕至。
这本回忆录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第一手材料。杨曦光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的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他们以共产党暴政的掘墓人自居,求仁得仁、死得其所。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属于劳动党,有的属于民主党,有的属于反共救国军。劳动党倾向学习苏联体制;民主党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有几十个人是反共救国军成员,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集团”多少都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大饥荒使很多人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杨曦光书中的这些信息,改写了此前人们对大饥荒时代社会状况的误读:过去,许多人认为,大饥荒时代的中国人如同待宰的羔羊,即便被活活饿死也不愿或不敢挺身反抗。其实,不是没有反抗者,而是反抗者都遭到了关押或屠杀。
一般而言,监狱是一个遵循丛林法则、你死我活的世界。但是,在政治犯群体中,杨曦光卻感受到思想同道相濡以沫的温暖与幸福。在这本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等反抗者的友谊。他们彼此坦率地交换思想,在无边的黑暗中撞击出闪亮的火花。连贯全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而相关问题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但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利用那些大好机会取得一些进展?”杨曦光的答案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以前有社会地位的人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进牢里以及杀掉。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两三百年的寿命。它是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
所以,这些大都被处以死刑的先知先觉的反抗,如同飞蛾扑火、蝼蚁撼樹。更可悲的是,因为被虐杀,他们的思想未能成熟和成型,未能广泛传播并成为解冻的“催化剂”,他们是历史学家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幸运的是,有了杨曦光的记载,这些人物终于在书页中复活并且熠熠生辉,正如杨曦光所说:“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給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所有的中国人都崇拜毛泽东吗?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急剧左转,毛泽东的幽灵附着在习近平身上,小型文革,亮剑舞刀,风雨欲来。毛派分子在此背景下疯狂鼓吹毛当年如何深受民众爱戴,企图重新制造对毛的偶像崇拜。
然而,正如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指出的那样,即便在毛时代,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崇拜毛泽东,在各阶层人士中,都有很大比例的人对毛深恶痛绝。以杨曦光本人而论,他直截了当地说:“整个中国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得生灵涂炭。每次我看到毛泽东的像,就像看到一个杀人魔王的像。他那大而高的额头在我眼中成了妖怪的特征,他的脸色充满着一股杀气,显得十分阴暗而凶狠。”这与八十年代刘晓波形容毛是“混世魔王”不谋而合。
杨曦光在狱中结识了不少因为毫不掩饰地反对毛泽东而被判处死刑的囚徒。其中,作为民主党首领的粟异邦,虽然是一名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体制的批判卻超越了那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一名亲眼目睹粟异邦被杀害的场面的囚犯,如此对杨曦光描述当时的场景: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警察將其扑倒在地,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還没有停止。有个警察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還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支枪刺插入他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让在场的人全身发麻,等不到大会宣布结束,他就已经死在血泊之中。
早在文革初期,杨曦光就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残民以逞的暴君,周恩来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奸相。在许多人都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顶礼膜拜的时候,他就看透了暴君与奸相合作演出的这场丑恶的“二人转”。杨曦光并未经历一个对毛崇拜然后崇拜破灭的过程,從一开始起,他就看透了毛并不坚守任何主义而只是追求权力的真面目,毛是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朱元璋那样的暴君的“升级版”,毛和毛的政策其实并不得人心。在劳改营的观察,印证了杨曦光的想法:“那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仇恨心情大概是非常普遍的。看看劳改队那么多因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判七八上十年刑的人就知道这种仇恨心情的普遍性了。”
痛恨毛的暴政的人士,遍布中国的各个阶层。杨曦光的难友中,有个名叫萧民生的解放军营长,收听台湾的自由中国广播,將其中揭露毛的邪恶的内容向部下传播,结果被捕。在劳改农场出工的时候,又见缝插针地散发手写的反毛传单,结果被判死刑。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上台,又有一批新的囚犯被塞进劳改营。杨曦光发现,有几个老实农民,是因为在毛泽东死的那天公开表示高兴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其中,有个农民一听到毛泽东死的消息就高兴得跳起来,大呼:“毛爹爹死了,这下我们会有饱饭吃。”可见,即便在迷狂的文革时代,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從理性、從直觉等各个方面出发,突破了官方炮制的毛泽东崇拜。
在地狱最底层,人性之光依然在闪烁
《牛鬼蛇神录》既是杨曦光心灵成长的轨迹,也是催人泪下并让人肃然起敬的“反抗者列传”。既然洞悉了地狱最底层的幽暗与隐秘,一步步地走向光明的信仰的杨曦光,用一种冷静、简洁、朴素的文笔,描写了那些他爱过的灵魂,那些被监禁、被凌辱、被虐杀的伟大的同胞。
必须有人讲出他们的故事。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讲述了十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她认为,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以萨克•迪内森为例,阐释了故事是如何拯救生活的:“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阿伦特发掘出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
在我看来,《牛鬼蛇神录》是一本比《黑暗时代的人们》更加优秀的書。《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某些人物,并非黑暗中的萤火虫,如布莱希特,后来成了为黑暗唱颂歌的夜莺,阿伦特似乎对诗人有特别的偏爱与谅解;而《牛鬼蛇神录》中那些发光的生命,大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扎根于大地,更有来自山川雨露的钟灵毓秀。比如,有一个名叫卢瞎子的囚犯,是被共产党剥夺了财产的小企业主,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而奋起抗争,结果被关进监狱。多年以后,杨曦光回忆说:“是他的命运告诉我共产党人对私人企业家的迫害和歧视以及对财产的侵犯是何等残暴无理。在卢瞎子看来,他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权利是如此自然、合法而合理,而共产党的理想和整个意识形态卻与如此自然合理的事不相容。好多年后,我还会想起卢瞎子那握有公理和正义的自信心,我变得越来越喜爱他这份自信。”也许正是这位难友的自信,讓杨曦光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后,始终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传统,并使之成为对抗现实中的极权主义的源头活水。
还有一位名叫李安祥的难友,三十多岁,信天主教已经二十多年。教堂被关闭后,他在自己家供奉上帝,還去亲朋好友家传播上帝的声音,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判刑十年。杨曦光写道:“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杨曦光第一次看到李安祥祷告的时候,還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后来,他发现,李安祥每天争着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每个星期天都会洗地,一点点地用抹布擦洗地面。杨曦光不禁感叹说:“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没有敬意,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二十多年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杨曦光受洗成为基督徒,也许是当年上帝使用李安祥在他心中种下的那颗种籽终于破土而出。
在尘土乃至粪土中,你仍然可以活得像珍珠和钻石那么高贵、那么纯洁。让我们祝愿那些在黑暗时代经历过、爱过、死去的人们获得良心上的安宁,就象斯温伯恩的诗所写的那样:“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甚至疲倦的河流也是如此,曲折而安然地流入大海。”
刘瑜:在黑暗中消失之前——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词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作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我总觉得更残忍的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倒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我们,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祥、张九龙, 因家破人亡而反抗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像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上世纪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本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革命的血雨腥风席卷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清醒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你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杰出的思想者被赶尽杀绝。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像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追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之猥琐的必然性,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细细簌簌成长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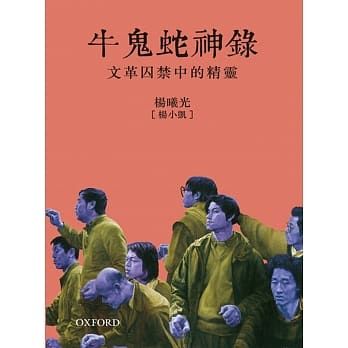
楊曦光(楊小凱,1948–2004),1988 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他的論文見於各著名的經濟學雜誌。著有《專業化和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等專著。
1966 年他中學年代迎來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 年下半年起,楊小凱已開始嚴肅思考文革,並寫出了當時屬大逆不道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因此被關進了黑暗的監牢十年。
本書初版於一九九四年,論者說「關於文革的回憶錄,《牛鬼蛇神錄》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這個詞不夠,更確切的詞是盪氣迴腸。」
本書的主題是:「秘密結社組黨的反對派運動在中國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甚麼作用?」相關的問題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在文革中曾經非常活躍,但為甚麼他們不可能利用那種大好機會取得一些進展?」敏感的讀者還可以找出更多這樣的主題,這些互相衝突的概念之所以能融合在一本書中是因為作者楊曦光本人就充滿着矛盾。他出身於高幹家庭,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周圍的朋友親戚在文革中全是保守派,因此他對共產黨保守派非常瞭解,特別對那些聯動精英有深切的同情,但同時他又是個極端的造反派。他坐牢時與國民黨精英人物,造反派,保守派精英人物,受蘇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和受美式教育的精英人物以及一般下層人物都有很好的關係。這就是此書複雜而多樣化的原因。
此書中每章是關於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中一個或兩個犯人的故事,他們中有地下反對黨的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容許的自由經濟活動的企業家,有扒手、強盜,有各式各樣的不同政見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國民黨時代的高官貴人。
這裏並沒有很多楊曦光本人的故事,但從楊曦光的眼睛,讀者會看到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形形色色的精靈是如何重新鑄造了楊曦光的靈魂。由於楊曦光獨特的政治理解能力和他的敏感,通過他的眼睛,讀者將接觸到當時中國政治犯一些獨特而深刻的方面。
目錄
xvii 自序
1 「中國向何處去?」
11 左家塘看首所
21 羅 鋼
35 盧瞎子
45 張九龍
63 向土匪
75 「紅色怒火一兵」
87 粟異邦
99 「聯動分子」
125 聖人君子
143 「舵手」
161 建新農場
179 逃跑犯
195 賓師傅
209 余總工程師
223 劉震宇
233 復舊和斬草除根
245 宋導演
257 黃文哲
267 黃眼鏡
281 勞動黨員
301 演說家
321 何老師
345 王師傅和盧師弟
363 王醫生
377 「反革命組織犯」
391 來自解放軍的囚犯
397 出監隊
413 後紀
自序
自從一九九〇年本書部分篇章發表以來,收到不少來自讀者的反饋。每年來美國開會,碰到朋友, 總會提起這個連載。令我掃興的是,即使遇到經濟學同行,不一定會提起我在JPE或AER發表的得意的經濟學文章,卻一定會提到這個連載。特別是碰到太太們,甚至會說他們收到刊物時最先讀的文章就是這個連載(可能是故意講給我聽的)。但是我特別要謝謝對這個連載文章的批評。因為刊物編者對這個連載的組織中的問題,讀者對此連載的性質有不少疑問。我在此作一個解釋,也算是後補的「前言」。我是於一九八五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論文時開始寫這本書的。書的中文名就叫《牛鬼蛇神錄》,英文版也是由我和蘇珊‧秦同時寫出,英文名叫Captive Spirits,直譯應當是《囚禁中的精靈》或《囹圄中的精靈》。 中文是於一九八八年完成,英文於一九九一年完成。《囹圄中的精靈》交過出版社後,他們將其當作學術著作, 請匿名審稿人審稿,匿名審稿人對書稿的評價出人意外地高,因此出版社的學術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接受此稿。《牛鬼蛇神錄》分篇發表時,編者未徵我同意就將題目改為《獄中回憶》。但是《獄中回憶》已與《牛鬼蛇神錄》有不少差別。首先《獄中回憶》把與政治犯無關的有關刑事犯的故事都刪掉了。《牛鬼蛇神錄》共二十八章,但《獄中回憶》大概少於二十章。編輯從未告訴我刪節的原則,但看起來留下的都是政治犯的故事。有點對刑事犯不公平。其實我覺得一些小偷、扒手、性犯罪的故事蠻精彩動人的。我雖曾是政治犯,但卻對刑事犯沒有什麼偏見。有些章次本身也被刪節一些內容。英文編輯開始也說書稿篇幅太長,是否可以砍掉一些章節,看到匿名審稿人熱情洋溢的審稿報告,她再不提刪節的事了。
讀者的實質性批評最精彩的是作者「無非是處處美化造反派」。我曾有一條規矩,從不答覆別人的批評,除非批評者非常有理由地要我回答。我想這個批評者看完整本書後,自己會回答他的批評的。另一條精彩的實質性批評是「此書無主題」,「不能成書」(這是一位英文版讀者的批評)。我被這個批評弄得難過了一陣。忍不住打破規矩,回答一下。無主題本來當然不是壞事,凡書就強調主題,這本是過時的老套。但此書是提出了非常多並不一定有答案的問題(也是種主題吧?)。如果讀者像我一樣多愁善感,一定會發現這一類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政治辭典中的「革命」與「反革命」?在中國的司法實踐和在朝、在野的政治意識形態中「革命」和「反革命」究竟意味著什麼。書中幾個被殺害的反革命組織頭頭的政治意識形態有很多西方政治學中的「革命」內容。而書中後半部中描寫的一九七二年的復舊,有很多西方政治學中的「反革命」內容。作為一個反革命政治犯的楊曦光其實是因為他的革命思想而坐牢,但在一九七二年復舊的氣氛感染下,他又真正變得十分「反革命」了。這個「革命」與「反革命」主題混雜著「歷史誤會」,「政治誤會」,曾經是一些以行為主義哲學為背景的文學作品中最令人神往的主題。這就是為什麼贊助內容麼這本書的最早被考慮的書名是《革命和反革命》。當然這兩個詞的涵意在中共官方的辭典中又是另一種莫名其妙、趣味無窮的定義。而這種官方定義有著血腥味的司法意義。
另一個書中的主題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秩序和公正的衝突,反政治迫害和動盪的衝突。在這些衝突中,保守主義的價值和造反的價值都有非常令人信服的支持。保守派精英的代表是程德明,保守派一般群眾的代表是毛火兵,造反派精英的代表當然就是楊曦光,造反派一般群眾的代表是向遠義和另一位扒手。下半部中還有代表支持保守派的農民的人物。從所有這些意識形態敵對的人物,你看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們有時十分可笑(例如造反派扒手為了壓倒保守派,半夜起來在保守派的花上撒尿),但他們的思想並不是發瘋。程德明和楊曦光的思想是當時很有深度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思想。在此書後部分,共產黨保守派復舊的可愛(秩序加理性)和可恨(政治迫害加歧視)更從一個個血淋淋活生生的犯人的故事中展現出來。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迫害的造反派再一次被煽動起來鬧平反更是突現了兩種互相衝突但同時存在的價值的意義。
當然連貫全書最重要的問題是:「祕密結社組黨的反對派運動在中國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麼作用。」相關的問題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在文革中曾經非常活躍,但為什麼他們不可能利用那種大好機會取得一些進展?」這個主題一直要到此書的最後兩三章接觸到勞改隊中可能的政治犯秘密結社問題時才會被挑明,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至少可以從這些真實的故事理解,那時祕密政治結社的社會背景、動機、意識形態和活動方式。這其中尤其是意識形態,不但學者難以瞭解,就是坐牢時天天與「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的人在一起的人,如果沒有敏感的理解能力和極好的人際關係,也不可能得到此書中有關地下反對派意識形態的信息。書中關於劉鳳祥和勞動黨的故事可以將分散的章節連成一體。
敏感的讀者可以找出上十個這樣的主題,這些互相衝突的概念之所以能融合在一本書中,是因為楊曦光本人就是個充滿著矛盾的人物。他出身於一個高幹家庭,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周圍的朋友親戚在文革中全是保守派,因此他對共產黨保守派非常瞭解,特別對那些聯動精英有深切的同情和瞭解。但同時他又是個極端的造反派,對保守派敵視,對被迫害和被歧視的下層人物認同,甚至與扒手共伍。他坐牢時與國民黨精英人物、造反派,保守派精英人物,受蘇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和受美式教育的精英人物以及一般下層人物都有很好的關係。這是此書多樣化的一個條件。
我們已決定將英文的《囹圄中的精靈》和中文的《牛鬼蛇神錄》分成兩本獨立的書(它們互相有相當大差別),這兩本書正式面世時,讀者將從連貫的閱讀中瞭解它的複雜和多樣化的主題。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1「中國向何處去?」
歐美的漢學家大多知道中國文化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於一九六八年被譯成英文,在美國一些名牌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裏,我發現過三個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是「鋼三一九『奪軍權』一兵」,有的署名是「紅造會『奪軍權』八.一二小分隊」,有的署名是「省無聯」。* 但我碰見的幾位漢學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長沙一中的一位學生楊曦光。廣州王希哲的著名的大字報《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及劉國凱的文章《文化革命簡析》*** 都自稱受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影響。這兩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較而言,劉國凱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國向何處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卻是最早形成全國甚至世界性影響的。
《中國向何處去?》目前被歐美漢學家視為中國大陸內第一篇公開批判共產黨的特權高薪階級,主張徹底改變這種體制的文章。不少漢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和楊曦光作了不少研究,有的人認為《中國向何處去?》是用無政府主義思想批判共產黨體制。還有些漢學家對楊曦光的「平等派」思想極有興趣,但卻對二十年後的楊曦光(他改名為楊小凱)的「自由派」政治觀點和「保守派」經濟觀點不以為然。其實,作為楊曦光本人,我覺得很多漢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和長沙「省無聯」的其他文件所作的研究與一九六○年代末的 楊曦光這個活生生的人有相當的距離。
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家 Jonathan Unger 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為了研究《中國向何處去?》成文的背景和楊曦光當時思想的形成過程,專門找我座談過幾次。這些座談的內容對於此書的讀者瞭解作者及書中故事的背景會極有幫助,所以我將這些座談的內容摘錄在本書的第一章中,作為全書的導引。這些座談中,漢學家們感興趣的一個題外問題是:極端激進的主張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中國大陸的特權制度的楊曦光是怎樣在二十年後變成一個思想相當保守的(特別是經濟學思想完全與 Milton Friedman 認同)楊小凱。當時楊小凱已得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得到導師的極高評價。這份好奇心自然是與三個楊曦光(楊小凱)的巨大反差有關。一九六八年的楊曦光穿着當時時髦的紅衛兵服裝(褪色的舊軍裝),神態天真單純,另一個形象是他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後被當局投入監獄和勞改隊後穿着破舊的勞改棉襖,褲子和衣背上都印着黃色的油漆大字「勞改」,頭髮被剃得光光的。第三個形象是他在以保守著稱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被授予博士學位時頭戴博士帽,身着莊重的黑色博士袍,胸前佩戴着博士學位繡紋的樣子。很多知道楊曦光傳奇經歷的人都在三個形象的反差上感到迷惑,不敢相信楊曦光和楊小凱是同一個人。很多不知內情但卻知道楊曦光和楊小凱兩個人的人,絕不會接受他倆是同一個人的「假說」。
顯然,這本書正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而解釋人們的疑慮的,是那些中國大陸的「古拉格群島」將楊曦光改造成楊小凱。儘管不少漢學家喜歡楊曦光甚於楊小凱,但這本書中講述的那些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精靈」怎樣促成了這個魔術般的變換故事一定是讀者神往的。
楊曦光生於一九四八年秋。他父母當時都是共產黨從延安派到東北去接收日本人軍備的幹部。楊曦光生下來時正是國共兩黨內戰,中共產黨從劣勢轉為優勢的時候。共產黨在東北打了一個小勝仗,於是這位男孩被取名小凱。楊曦光是他上學以後的學名。他一九七八年從勞改隊刑滿釋放後找不到工作,大家都知道楊曦光是寫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爸爸勸他改名字。中國人講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於是大家認為重新啟用他的乳名小凱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從那以後,楊曦光這個人就在中國消失了,而楊小凱卻在中國內外慢慢通過他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被人知道。
楊曦光生長在一個一九四年革命後暴發的共產黨新貴家庭。從小生活環境優越,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受到共產黨極深影響。從小學到中學,他關於中國現代史的知識充滿了對共產黨征服國民黨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崇拜,他看的小說,看的「革命回憶錄」中都充滿着這種對用革命暴力改朝換代的迷信。
但共產黨這個「扭秧歌」王朝內部的不斷搖擺和動亂自一九五七年後開始給楊曦光的家庭帶來災難。首先是他哥哥和舅舅被劃為右派,接着他父親於一九五九年因為反對大躍進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農村去勞動。楊曦光屬於思想成熟較早的人,入學前,父親就請人在家裏教他《論語》,小學二年級時他就能讀大部頭小說。一九六二年正是他開始養成閱讀成人的報紙 的習慣時,中共又發生了一次政策的大搖擺。楊曦光的父親被當時的黨中央宣佈徹底平反。楊曦光在「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復舊氣氛中考取了當時的全國重點中學長沙一中。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那些「右」的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一九六二年復舊的氣氛中如魚得水。一九六四年政治風向改變,突出政治、階級路線又佔了上風,但楊曦光因為高幹的家庭背景,仍是激進路線的受益者,所以又受到左的路線影響,開始在日記中批評自己一九六二年的右的思想傾向。但他父母尤其是他母親對那股「左」風一直持一種批評態度,也總是用她的觀點盡力影響兒子。
文化革命一開始,楊曦光就捲入了長沙一中反對工作組的活動。楊曦光的父母被當時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並由省委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曦光受到工作組迫害並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紅衛兵歧視。他自然而然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由出身不好的同學組成的造反派,與支持當局的保守的紅衛兵對抗。一九六六年底,他積極參與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動,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個跨部門的準政黨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軍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數造反派組織打成反革命時,楊曦光被軍方關押了一個多月。
他出獄後在北京等地串聯,接觸到一些批判共產黨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的「新思潮」。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學生和北京批判血統論的中學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楊曦光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對共產黨當局表達的強烈不滿,開始重新思考文革爆發的原因等問題。楊曦光家裏有個保姆,文革前看上去似乎對他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參加了保姆的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幹們剝削了他們。楊曦光夜裏與保姆深談過幾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黨幹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黨的專橫早已是懷恨在心。他發覺這種社會矛盾並不能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綫鬥爭」的理論來解釋。楊曦光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瞭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與共產黨幹部發生激烈衝突的真正原因。
他讀了不少馬克思的書,也在湖南農村進行了一些社會調查,特別是調查了當時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運動和臨時工、合同工組成工會式組織提出經濟要求的運動。他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純馬克思語言)人民。中國的政體與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所以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體。這就是《中國向何處去?》中的主要觀點。
當時類似的思潮在武漢、上海、山東、北京的學生中 都出現了。當局一直認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會贏得對人們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導的權力。想不到長沙的一位中學生和其他學生竟想獨立於政府的意識形態,自己找尋 理論。中共的上層首腦特別是康生、毛澤東對這股造反派中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潮非常害怕,因此特別召開了一次會議,取締當時湖南激進造反派的聯合組織「省無聯」,並點名批判了楊曦光、張玉綱、周國輝等學生中的思想家和領袖人物。全國很多官方和當時群眾組織的報紙都將《中國向何處去?》作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這就是為甚麼一張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發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傳單造成全國性影響的原因。
《中國向何處去?》一九六八年通過香港傳到海外, 美國的「新左派」十分喜歡其中的觀點,於是各種英文版本的《中國向何處去?》和其他「省無聯」的文件在 美國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楊曦光父親那一輩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的子女與楊關係十分密切。他們文革中都是保守的紅衛兵。迫害出身不好的人很積極,但卻不造父母的反,是可愛的堅定的保爹保媽派。
楊曦光周圍的幹部子弟朋友沒有一個參加造反派的。他的經歷也許相當特別,但是他在山東和廣州的朋友中卻有高幹子弟參加造反派的例子。他們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內受實權派迫害的高幹,文革一開始就被當權派批鬥。他們的父輩都是那種三代以上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幹部,而他們自己都是學習成績很好、極聰明的學生。但總的而言,高幹子女參加造反派的實在是鳳毛鱗角。但正因為楊曦光與創建「老紅衛兵」的保守派(後來的「聯動」)有很多私人關係,他是屬於那種對保守派觀點 極為瞭解,並與他們有很多私人關係的造反派。
楊曦光在文革中的政治傾向部分可以用他的家庭背景來解釋,因為文革中大多數右派和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楊曦光批判特權階級的思想與其父輩的政治傾向應沒有甚麼關係。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出身社會上層的青年人由於本身地位未穩,形成與家庭高地位的對照,因而兩代人的利益衝突在社會上層家庭內特別激烈。這種假說可用來解釋歷史上上層家庭內的有些年青人為甚麼特別激進。
另一方面楊曦光從小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在自己被當局迫害時,希望找一種理論來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馬列正統理論基礎上合法化,而馬克思關於民主主義的觀點及反特權反迫害的觀點,自然成為他的思想武器。但一九七○年代初楊曦光在監牢裏徹底放棄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而成為一個極力反對革命民主主義,支持現代民主政體的人。此書中並沒有很多楊曦光本人的故事,但從楊曦光的眼睛,讀者會看到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形形色色的精靈是如何重新鑄造了楊曦光的靈魂。此書中每章是關於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中一個或兩個犯人的故事,他們中有地下反對黨的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容許的自由經濟活動的企業家,有扒手、強盜,有各式各樣的不同政見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國民黨時代的高官貴人。楊曦光於一九六九年底被判處十年徒刑,罪名主要是寫《中國向何處去?》。判刑前他在看守所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判刑後他去了洞庭湖中一個湖洲上的建新農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反刑事犯罪)運動中他又在長沙的模範監獄呆了八個月。之後他回到建新農場直至刑滿。所以此書涵蓋了中國古拉格群島的三大系統:看守所、勞改隊、監獄。由於楊曦光獨特的政治理解能力和他的敏感,通過他的眼睛,讀者將接觸到當時中國政治犯一些獨特而深刻的方面。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