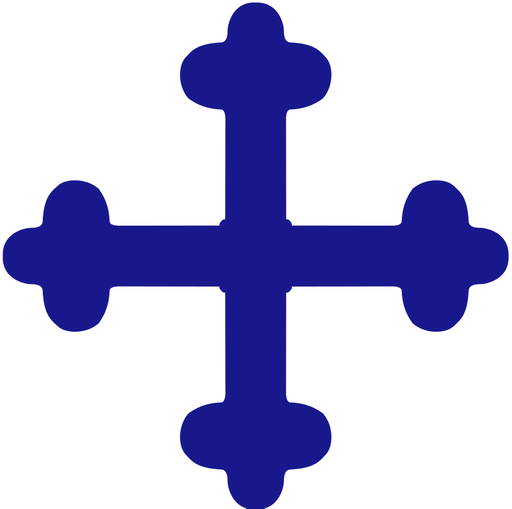
撰稿人 關注國際政治與政治理論。
语境的语境:波考克的《德行、商业和历史》
本文首发于豆瓣,有一定修改。
(一)
在抽象和简化的层面上,波考克、斯金纳、邓恩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可被称作“语境主义”。他们的政治思想史(或曰“政治话语史”)理路非常强调以下两点。其一是文献诞生时的话语环境。其二是话语的历史脉络的考察。这种方法势必一方面要求历史学家掌握语言学/语言哲学的方法,另一方面成几何层次的提高了搜集、阅读历史文献的要求。历史学家所处理的不再单纯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诞生于过去、存在于当下的孤立文本。他必须尽可能搜集一切书面的文字材料,重建文献诞生前后整个政治话语的结构与传承,并把相关文本放入这个结构中加以考察。换言之,语境主义的写作也为读者提出了一些挑战,他将不得不跟随作者的脚步,进入历史背景下政治话语的拟构中。但这种“阅读”的能力,也建立在相当层次的阅读与积累上。
由于这些能力缺乏的缘故,我没有完全(合乎语境的)把握波考克在本论文集中所论述的内容。但可以相对保险地讲,作为巴特菲尔德(《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的作者)的弟子,波考克在本论文集中努力沿着乃师解构所谓辉格党史学的路径前进,拒绝承认17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是洛克为代表的“占有性个人主义”(麦克弗森语)高歌猛进,打败古代世界思想的史诗。毋宁说,在波考克看来,除以占有-权利的法学话语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谱系之外,以自由-德行的古典话语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谱系也同样保持了相当的活力。两者作为有力的对手,维系着持续的、并非不重要的对话。这场对话带来的挑战,迫使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先驱——不管称之为辉格党人、自由主义者还是苏格兰启蒙主义者——为已经诞生、正在巩固的新秩序辩护,从而也间接型塑了近代自由主义观念的若干特征。也只有在这种“对话”的语境下,当代读者才能对彼时的政治话语——从美国独立,下到法国大革命——有更切题的了解。
在波考克看来,以共和主义德性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强调不动产有助于公民独立的独立性质。这种独立凝聚在刀剑在身、地产在乡的公民-战士形象中。公民德性对自治共同体有着根本重要性。共和主义者也借着公民-战士的形象,反对英格兰革命后随着公债体系不断巩固的“辉格党霸权”以及“金钱利益”,将其斥责为滋生依附性的“腐败。”不动产代表的是稳定、独立,从而也是自由。而“信用”则是飘忽不定、投机的代表。至于公共信用更是造就一批(辉格党寡头)的食利者分子,就像他们中的代表分子沃尔波尔一样,将自己和政府的沉浮绑定在一起,从而不再是自治共同体的一份子。受到启蒙影响的大学者们,从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再到亚当·斯密,都感到有必要为辉格党党治下的新秩序辩护,以对抗“德行”的话语。他们因此发展起了一套精密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理论。指出“教养”和“文明”,这两个几乎无人反对的好东西,是随着商业的扩展而逐渐萌发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劳动分工,使人变得更加丰富、儒雅、有能力。文学和艺术得到发展,生活同时也更自由。劳动分工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所有人依赖所有人,从而使得古典德行和古典共和国变得不可能。不过,谁又说古典公民是必不可少的呢?古典的公民-战士,是野蛮、粗鄙好斗的原始人,不依赖于奴隶制和暴力,他们的德行便无处安放。相比之下,“现代社会”更富裕,也更文明。从精神到物质上的进步一日千里。由此,苏格兰启蒙者宣布,这场古今之争,以“当代”全面胜利而告终。当然,爱德蒙·伯克是个有趣的例外。他认为商业和专业化并不能离开教士和骑士奠定的基础存在。繁荣造就的知识分子阶层与“金钱利益”,却有可能反过来造教士和骑士的反。“高贵风尚”没有成为商业发展的朋友,反倒成为后者的敌人。这种看法在海峡两岸的启蒙精神中并不占据多数。被旧大陆驱逐的共和主义幽灵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在英国发育不良的共和精神,在美国开花结果。独立的北美殖民地,既无法接受议会君主制,也没有建立不列颠辉格党寡头议会制的条件与历史。他们选择成为共和国,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中铸造了双面的品格。美国的开国者认识到:洛克和休谟很重要;加图也很重要。人民主权如果写进宪法;“枪炮在身”的有产公民就要写进第二修正案。在每一个汉密尔顿对面,都等着一个杰斐逊。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勾勒出波考克此书中营造出的复杂(如果不是暧昧)图景。现代早期的思想、话语、党派有着高度的流动性。在波考克笔下,前一阵时期还是辉格党的激进分子,到了下个时期就成了托利党反动派。共和主义者和詹姆斯二世拥戴分子同仇敌忾,自治市选民和乡绅一起反对伦敦的钱商。就连什么是“辉格党”的含义都一直在变化。而他们的死对头托利党也不遑多让。在18世纪早期托利党还指的是保卫旧君主制的顽固分子。等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托利分子“这个词却被拿来形容辉格党秩序的顽固守卫者!这副思想画面毫无疑问是纯粹英国的。也正是在英语国家的历史中,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取得了最丰富的成果。不列颠人拒绝严格的抽象、拒绝脱离习俗和先例以及历史已经达成的成就而谈论抽象权利。只有当他们被迫反击后者的时候,才将自己的论说不情愿的体系化和理论化。休谟反对“古代宪法”的缘由是共和派将古代英格兰描写为共和化的封建天堂,他指出英国人的自由很大程度是1688年革命后的产物。伯克对法国革命者的同路人(从而也是英国共和派)普莱斯的驳斥,造就了《法国革命论》。脱离了英国语境,不管是共和派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会遭到扭曲。英国共和派不是雅各宾分子,尽管他们可能是雅各宾派的同路人。他们精神上更像是美国各州的保守农民。英国的保守派也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或威廉·德·迈斯特。尽管保守主义者在必要的时候会支持“反动”统治,但他们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丘吉尔和撒切尔。
(二)
如果我们反过来“语境地“考察波考克的写作本身,就不得不提到上世纪中叶以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的“共和主义复兴。” 这股潮流不仅包括汉娜·阿伦特和菲利普·佩蒂特在内相对纯粹的政治学者。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本人也是所谓共和主义新罗马流派的代表人物。共和主义复兴与波考克等人强调共和主义谱系、弱化洛克等“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是观之,以语境为对象的写作,本身就处在、或者型塑了语境。这在我们的阅读中展现出某种奇特的嵌套关系。作为辉格党历史的挑战者的“共和主义修正派”与这一修正大加批评的美国施特劳斯学派之间的争论,本身就能够单写一部学术史。将波考克的著作放在当代共和主义话语史的脉络中解读,大概也会有超越文本之外的收获。
这提示我们,历史的著作同时也是当代的在场,德行与商业之争并没有就此划上休止符。世界各地本土派、民粹派的诉求与经济自由主义者对此的恐慌与嘲弄,何尝没有几百年前争论的影子?共和的德行也许封闭、狭隘,抗拒融合,坚守身份政治,从而不能见容于崇拜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护教学。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最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是开明专制的恭维者。他们有幸见证绝对主义君主的和平与效率,却高傲地无视共和派的警告:僭主从来不是自由和财产可靠的朋友。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