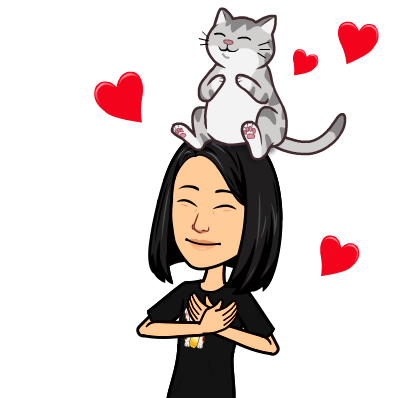
荷兰语学习者
【译文】与现实世界失联:当代顶级球员的生活
原题:Het contact met de wereld verloren
作者:Simon Kuper
来源:De Groene Amsterdammer

6月11日参加欧洲杯的年轻球员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人类学家的儿子并采访足球运动员将近三十年。我尝试着书写球员的职业民族志:忘掉他们的“明星”身份,像观察太平洋岛屿上的部落一样观察他们。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对待金钱?他们关注什么?如何看待世界?
今天,大多数顶级球员都是在社会之外长大。青少年时,他们进入了职业俱乐部学校。这使他们与前几代的顶级球员有本质的不同。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出生于充满阴谋论的庇隆主义阿根廷下层家庭,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ijff)来自荷兰战后婴儿潮的加尔文主义家庭,而莱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则是家庭和巴塞罗那足球学校的产物。对孟菲斯·德佩(Memphis Depay)这类在清贫家庭长大的球员来说,PSV埃因霍温俱乐部学校可能是成长中最稳定的因素。
许多球员来自贫穷或弱小的国家——想想比利时的伊登·哈扎德(Eden Hazard)和罗梅卢·卢卡库(Romelu Lukaku),又或者荷兰的蒂姆·克鲁尔(Tim Krul)和内森·阿克(Nathan Aké)——并在青少年时移民到国际大都会。作为职业球员,他们在机场贵宾室比在城市街道上更自在。即使是住在家里的球员,陪伴他们长大的也常常是外国队友和教练:法国的凯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从 16 岁起就成为职业球员,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和英语。
足球学校变得越来越专业,许多学校聘请中小学教师,单独给青年球员授课。在有些俱乐部,球员只有先完成学业才能参加比赛。巴塞罗那俱乐部学校里,一半的青年球员会去上大学。2014年,世界冠军德国队的24名球员中有55%有高中毕业文凭,比例略高于德国平均水平。中场球员约书亚·基米希(Joshua Kimmich)的高中毕业成绩为1.7(评分标准从1到6,1为最高分),他敢解雇经纪人,自己经营自己。球员中出现了自治的新趋势:姆巴佩也不雇用经纪人,而是雇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这一代欧洲球员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尽管现代球员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充足的闲暇时间,但他们不断被灌输只考虑足球。高薪鼓励偏执和幼稚。从青春期开始,球员就被随行人员、家人和俱乐部保护起来,让他专注于工作。财务顾问负责处理金钱收支——但他们常常因为能说会道或者亲戚关系被选中,而不是因为有才能。如果问一个球员“你在哪里纳税,纳了多少税”,他通常一无所知。
天才球员如果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也会被淘汰。最好的例子是意大利人马里奥·巴洛特利(Mario Balotelli):他是 2012 年欧洲杯意大利队的明星,现在效力于末流球队蒙扎(Monza)。尽管他才30 岁,但已经失去了加入国家队的资格。他的荷兰-意大利经纪人米诺·拉伊奥拉(Mino Raiola)告诉我,巴洛特利有时在赛场上表现不佳是因为在谈恋爱:“有意无意地,巴洛特利不让足球成为他生活的核心。” 所以总有一些其他问题会影响他的表现。根据拉伊奥拉的说法,成功的球员——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保罗·博格巴(Paul Pogba)和帕维尔·内德维德(Pavel Nedvĕd)——不会受这些影响。
我向拉伊奥拉解释说,也许一些有天赋的球员不想成为顶级球员。为什么非要成为顶级球员?他们也可以在稍小的俱乐部赚几百万美元,又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嗯,没错,”拉伊奥拉回答,“因此我最近经常问球员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踢球?你的动力是什么?”“他们怎么回答?”
“大多数人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让他们回家之后好好想想,我说:‘想想看’。”
你很少听到球员在赛场外的消息。与流行歌星或网红不同,他们不会推出有争议的个人品牌来赚钱。他们接受媒体培训,学会应该怎么说话:“我们为这次失败感到难过,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下周还有另一场比赛。” 这些回答听起来很蠢,尽管球员本人并不蠢。
职业球员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欧洲杯每场比赛前,都有球员在更衣室厕所里呕吐。有些球员因为压力而腹泻。有时球队只能等压力过大的球员准备好了才能上场。很少职业像足球运动员这样压力巨大,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国际媒体谴责。
在比赛后,球员会从网站和报纸上看有关自己的数据。前英格兰前锋加里·莱因克尔(Gary Lineker)现在是 BBC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说所有球员都会看这些数据,“即使他们说自己没有。”
许多球员关注社交媒体对他们的评论。一条讨厌的推文可能会毁了他们一天的心情,或者让他们一直心绪难平。比如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对阿森纳中场、瑞士队队长格拉尼特·扎卡(Granit Xhaka)说:“希望你的女儿得癌症。”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仅2020 年 12 月,他在 Twitter上就收到了1374条带有侮辱性、种族主义或威胁性的消息。
和其他人一样,顶级球员也会焦虑。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知道如何将恐惧化为动力。如果无法应对恐惧或者完全不会恐惧,有才华的球员也会在层层选拔中被淘汰,比如在国家青年队(17岁以下)选拔时。美国钢琴家查尔斯罗森说得很对:“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他们都会怯场,但业余表现出来而专业隐藏起来。”
被选拔踢欧洲杯的球员从小就看着竞争对手们陆续被淘汰,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能力获胜。没有人会因为裙带关系或者上学的地方被选拔进国家队。尽管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荷兰国家队教练弗兰克·德波尔(Frank de Boer)也没有选择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卡尔文·斯滕斯(Calvin Stengs)。当你为国家队效力时,你的队友不会太在意你的肤色、俱乐部、性取向,甚至社交能力,只要你表现出色。利利安·图拉姆(Lilian Thuram)是代表法国队参赛场次最多的人,他在球员生涯结束后成为一名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他说:“我从未在赛场上遇到过种族主义者。也许他们存在,但我没见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种族主义者通常不在乎其他人。但在足球中,我们必须分享。踢球时不会有种族歧视,因为我们根据非常具体的表现来评判球员。”
一个认为自己是精英的成功者,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傲慢和蔑视。顶级球员往往会乱说话,因为他们能比教练更好地诠释比赛。他们觉得普通人是几十年来从事无聊平庸工作的畸形胖子,普通人从事的行业几乎没有质量要求。
顶级运动员不明白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许多普通人的职业巅峰是升职、获得上司表扬、与同事出海旅行,甚至是退休的时刻。难怪成功的足球运动员都会尽可能地寻找让肾上腺素激增的新方法:比如约翰·克鲁伊夫雄心勃勃投资商业,或者迭戈·马拉多纳滥用可卡因和酒精。
顶级球员的错觉是竞争比生死更重要。大型比赛淘汰阶段一球致胜的方式在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的,一球告负亦然。你和队友们一起回到更衣室,疲惫到不能喝水,精神快要崩溃。在足球生涯结束之后,你再也无法与他人共同经历这种强烈的情感。
我采访过的大多数球员都很友好、很有教养。有亲切的约翰尼·雷普(Johnny Rep)和天生的心理学家弗兰克·里杰卡尔德(Frank Rijkaard),也有比如像法国前锋尼古拉斯·阿内尔卡(Nicolas Anelka)这样似乎患有人格障碍的人。但在面对普通人时,球员总不能压抑自己的不屑。
很多球员认为足球场外有一群很糟糕的人,他们趴在训练场的围栏上偷看或者辱骂球员。一名球员在和妻子、孩子去餐厅吃饭,会不得不与旁人合影15 次,甚至无法与家人说话或吃东西。我最近写了一本关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书,为俱乐部工作的一名心理学家告诉我,足球运动员有被“非人化”的风险。她说:“人们把球员视为超人。如果你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就会变得很糟糕。”但这不取决于球员自己,是球迷把球员非人化。
像姆巴佩这样的明星——他想成为一个明智的、有思想的年轻人——过着奢侈的囚犯生活。“粉丝给了你无限的爱,”他说,“但有时太过了,他们可能不尊重你的亲密关系。我不抱希望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我认为,稍微尊重一点个人的私生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姆巴佩只要出现在街上,就会被人群包围。他说:“你需要一个团队来帮你走出人群。”他曾感叹,如果他未来的孩子问起他青年时的冒险经历时,他只能回答:“我没有。”
21 世纪的球员最讨厌的可能是手机摄像头。他们一直担心被人拍下不雅照片或视频,或者在餐厅的私人交谈被传到社交媒体上。因此,和他们一起出去玩的人不得不交出手机。一些球员只能坐在夜总会包厢里俯瞰舞池,去洗手间也得带上俱乐部的警卫。
著名球员的社交圈往往局限在家人、儿时伙伴和少数几个队友之间,因为他们明白: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点什么。人们喜欢拿前荷兰中场球员韦斯利·斯内德(Wesley Sneijder)和电视人约兰特·卡布·范卡斯伯格(Yolanthe Cabau van Kasbergen)这样的名人夫妇开玩笑,尤其是在他们最终分手时。但名人更容易理解名人,因为他们都像是笼子里的金丝雀。他们的恐惧和怀疑往往是合理的,围绕他们的人常常是为了钱或者借用他们的名气。因此,球员也常常反过来利用其他人,把他人当做性对象或者免费勤杂工。顶级球员要买机票或手机,自然有人会去处理。他们很少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一位前经纪人告诉我,球员将一切都外包给跑腿的人,除了足球、性和偶尔购物。据他说,大多数球员缺乏同理心,他们在一个竞争激烈、多疑、男性化的世界中长大,不这样就会被淘汰。
过去三十年,不断上涨的工资让球员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对球员来说,金钱最主要的作用不是支付。如果你赚了一千万欧元但不能出门,你花不掉多少。金钱在一支足球队中代表着非物质的东西:它是衡量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韦斯利·斯内德曾经在国家队训练营问当时维特斯阿纳姆足球俱乐部(Vitesse Arnhem)的门将皮特·维尔特休森(Piet Velthuizen)收入是多少。“四十万欧元”,维尔特休森自豪地回答。对于一家省级俱乐部的年轻守门员来说,这代表着很高的收入和地位。斯内德据此估算出维尔特休森在国际米兰的收入将提升十倍。克鲁伊夫在 1997 年就已经解释过:“钱代表了升值的程度。所以这与你赚到多少无关,这关系到你的等级地位。”如果俱乐部用姜饼来支付薪水,只要一名球员能得到比另一名球员多的姜饼,大多数球员就能接受这种支付方式。
顶级球员的收入足以支付一整个随行团队。年轻球员与外国俱乐部签约时,他们通常会租一栋别墅,与经纪人、理疗师、女朋友、家长、助手以及一些有经济往来的朋友住在一起。从人类学上看,这是一种新的家庭形式。
结婚后,球员进入了不同的人生阶段:从黄色法拉利到黑色揽胜。但是球员与普通人的婚姻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一位巴塞罗那的前银行家说,一名经纪人为巴萨新球员开设了三个银行账户:球员和妻子的联名账户、固定成本账户和球员本人瞒着妻子开的账户。
女足运动员的生活方式与男足不同。2017年,列克·马滕斯(Lieke Martens)为荷兰队赢得了欧洲杯,并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同时她也在巴塞罗那俱乐部女队踢球。5 月,她的球队赢得了欧洲女子冠军杯。但她每年只能回家探亲几次,也买不起能住全家人的大别墅。马滕斯说:“男足球员可以带上全家人,可以带上任何他们想带的人,住在自己建的别墅里。但女足球员不行。我仍然时不时地想家。”目前,顶级男足球员的收入是顶级女足球员的50倍,但这种差异正在缩小。随着女足球员地位上升,她们也会成为明星。
许多球员会雇佣各种工作人员,他们成为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障碍。今天,一个关键球员像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他自己付钱雇佣经纪人、社交媒体经理、私人理疗师和造型师等。
因此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我曾经认为顶级球员和其他行业的高技能工人一样与雇主关系冷漠,就像大多数外科医生、银行家或大学教授。他们希望为一个能够保证职业满意度、高收入和认可度的组织工作。如果目前所在的俱乐部提供不了,他们就会去下一个俱乐部。他们的想法与球迷不同。他们对俱乐部队徽、教练或队友无感。
现在我认为球员与球队的关系比我之前认为的更商业化:顶级球员就像是雇佣兵。他们在某个俱乐部或国家队聚在一起,共同开展一个短期项目,比如欧洲杯,就像演员们一起拍电影。他们每天为球队工作大约三小时,同时他们也为赞助商、慈善机构和个人品牌工作。
有时,俱乐部会抱怨很难与球员本人沟通。豪尔赫·巴尔达诺 (Jorge Valdano) 在 2010 年担任皇马技术总监时抱怨道:“25 年前,俱乐部和球员可以直接联系。那时一切都很简单。球员是俱乐部的雇员,他们拥有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尽义务。今天,俱乐部和球员之间隔了许多层。尽管你仍然需要与球员本人打交道,但很多时候是与球员的父亲、经纪人、通讯主管、女朋友打交道。”
现在的教练必须说服球员,而不是指挥球员。恩斯特·哈佩尔(Ernst Happel 奥地利著名球员和教练)、里努斯·米歇尔斯(Rinus Michels 荷兰著名球员和教练)这类沙发上的“将军”已经绝迹。任何“男子气概”型的教练——他们试图违背球员意志来“激励”球员——在今天总会输掉比赛,最终被解雇。现代教练已经不再幻想自己可以主宰流动、跨国、超级富有、不可替代的球员。大多数球员也非常自负,雇佣了强大的经纪人和新闻监督者。在人才驱动的行业中,人才具有主导优势。
球员们力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让这一代球员在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激进。最近,许多球员已经打破了不谈政治的戒律。2020年黑人同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中,连续几个月欧洲球队在开球前都单膝跪地。5月欧冠决赛时,曼城和切尔西队都是如此。2019 年 11 月,传统上不关心政治的荷兰国家队也由乔治尼奥·维纳尔杜姆(Georginio Wijnaldum)和弗兰基·德容(Frenkie de Jong)发表了反对种族主义的集体声明。在疫情期间,以英格兰国脚、利物浦队长乔丹·亨德森(Jordan Henderson)为首的英格兰球员也为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机构捐助了巨额款项。年轻的英格兰前锋马库斯·拉什福德(Marcus Rashford)在小时候常常吃不饱,他在成名后发起一项运动,游说英国政府在暑假期间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校餐。
社会激进主义与千万富翁格格不入。聪明的足球运动员清楚这种矛盾。他们既为自己的薪水感到自豪,又同时感到内疚。对马拉多纳和罗马里奥(Romário 现在是国民议会的左翼参议员)这类在贫民窟中长大并以政治激进分子自称的球员来说尤其如此。
这种内疚感有时也会导致自毁行为。一些足球运动员非常随意地把财富分给其他人。现任曼城总经理的费兰·索里亚诺(Ferran Soriano)写道:“有些球员既会花数十万欧购买他们不会使用的汽车,也会在路边见到乞丐就给五百欧。” 这表达了球员们的愿望:他们希望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