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途愉快
信|To Judy
Hi,Judy,春天好呀,尽管最近的天气不那么春天,但不久后一切又会好起来。大概是在一年前稍晚些的时候,我闯入了你的领地,就像这封信,出现地唐突、不合时宜更有甚是冒犯,实在是抱歉,你可以就此打住,不再看下去。
那时的你为一段关系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也使我重新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后来也曾写下诗信。我明白你的边界和我们当初的约定,一切因我的错误所致,我坦诚地接受。
拉康说一封信总会抵达它的目的地,这次,我想试着让这封,在犹豫中写了很久的信,抵达那个理应被你眼睛审视的空间。
先说起那个晚上吧,一年前的那个时间静止的晚上,4月30日,是你生日,我被你的眼睛捕获、占据、否定。
或许是因为曾经失败的感情,那时的我试图将自己浸泡在一种麻木的真空里。在你面前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像一种笨拙而滑稽的表演,并试图自作聪明地回避一些问题。你戳穿了我那个虚伪的中立表面,用你的眼睛,坦诚的眼睛。
在后湖,你留下眼泪的那个片段里,我惊慌了,失去了身体,也没有了灵魂,变成了从你眼睛中投射出的一个傀儡,在你费了好大力气才用真诚树立起的幕布上。我太糟糕了。你的眼睛就像半支耳机中的那条 黑色的路,明明向我诉说着一切直达内心的可能,在路的尽头是你所有的真挚与温柔,而我,在这份美好前,竟空洞到不知所措。坦诚或真诚,是我相信并迷恋的品质,我也向来用它们标榜自己,真是羞愧。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个雨夜的漫步与交谈梦幻到不像是真的,但我总是能在回忆里通过它们来确证我的存在。在那些时刻,不再有真空。回忆一直都在发生,那双眼睛总是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去年夏天,在秦岭沿着山脊线前进的那个夏日午后。远离地表的燥热,云海从身旁流经,急剧变化的阴影,如同时空在我眼前流淌,我前所未有地置身于流动带来的恐慌中,那并非我所迷恋的,出现在村上春树小说里附着疏离感的流动,并非我过去课后独自一人乘坐公交穿越城市时的流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花生漫画,查理·布朗和他的伙伴们生活在一个永恒失败的世界里,也正因如此,它是反成人的,充满了温暖和可爱,唯一的遗憾或许就是失败的必然性中也包括了所有人的爱而不得。我常常以查理·布朗自比,那个世界也映照了我性格里的某些部分。
长久以来我似乎都是一个什么都抓不住的人,在散漫的天性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某种自诩为态度的任性里对评价体系和权威秩序不屑,我清楚地明白这些行为的代价,但就是这样,我不善于处理自己情感,面对自己就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回想起你也说过类似的话),更何况是以一种系统化的姿态面对所谓的外在世界呢?天性里的敏感和脆弱,是那时我想向你掩盖的东西,我也曾因它们受到创伤。
秦岭的夜,在被海拔三千米的烈风不断击打的帐篷里,我又看到了你那双眼睛,帐篷外的世界瞬息变幻,所有人行色匆匆,你的眼睛是那么宁静。
回忆是一种回溯性的建构吧,其中难免又附着了我自欺欺人的想象(如果这冒犯到你,还望见谅),但它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夏天结束后的冬天,以及又一个春天。
后来,当我不知从哪里读到何其芳的诗句,“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你可以目不转移看着我的眼睛。”顿时觉得,我所有的记忆和文字都显得可笑。是啊,黑夜可以遮断一切,但无法遮断那双可以逼视灵魂的眼睛,它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
我究竟为何而恐慌呢?认识自己真的好难,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去做什么,种种,确定性是什么?想到滨口龙介在《偶然与想象》里让角色说出,只有做自己才能“在某个瞬间和某个人 产生奇迹般的共鸣和共勉”。我只是知道,那些没有“做自己”的时刻里产生的遗憾都是一种惩罚,我接受生命的惩罚。
在《史努比:花生大电影》的最后,查理·布朗终于鼓起勇气和喜欢的红发女孩说话,红发女孩对他说,“你拥有我欣赏的一切品质。”他们成为了笔友,那一刻我好羡慕他,世界仿佛,不再残缺了。
我没有那么好的品质,还善于搞砸一切,不配拥有查理的结果,但你的真挚和美好值得一切赞美,谢谢你照亮过我的那片空洞的真空。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还是要说,很抱歉这封信的不合时宜,希望你原谅它和我的唐突。你积累起的坚固、安全的堡垒,如果我又失足踏入其中,望Judy见谅。诚惶诚恐地写下这些笨拙的文字,仰慕与爱意,皆诚发自心。
最后,祝我们不再害怕。
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小雷
20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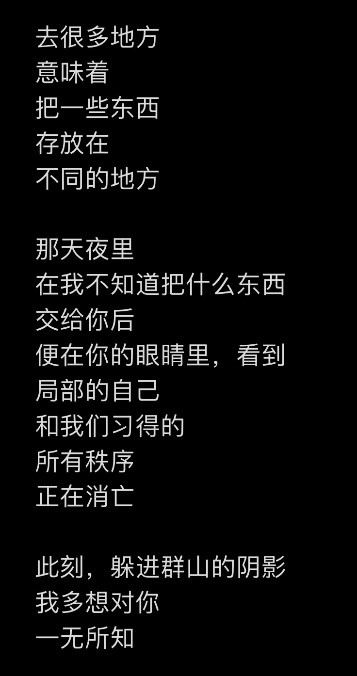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