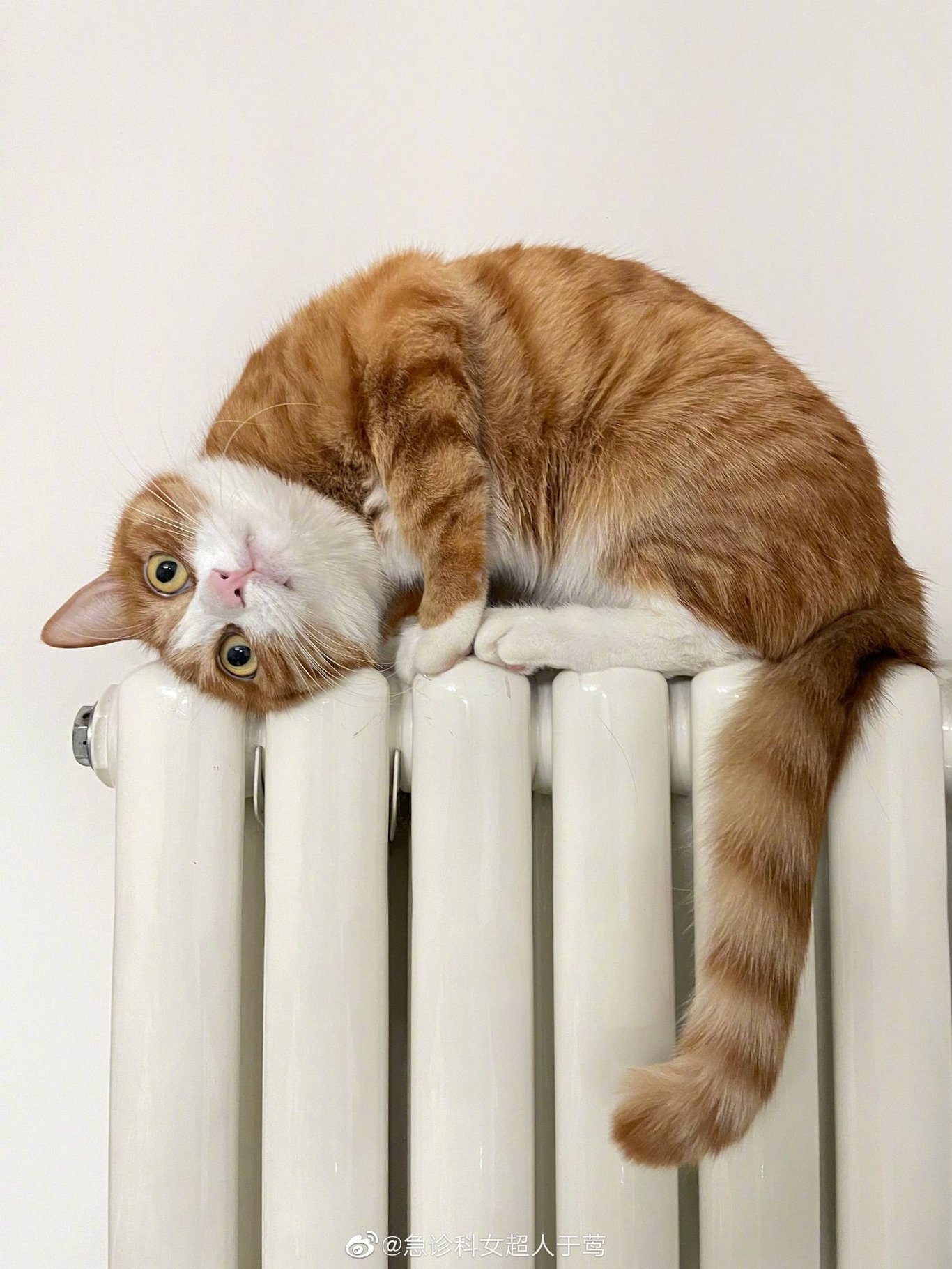
没事写点脑洞,爱说瞎话,不用在意。@cherylmia2013@liker.social
无解的孝道
这是一个悲伤而无解的故事。
我同事的一个病人,中国人,女性,才刚刚40岁。
要知道,在医院里,一个40岁的人,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她的诊断,是癌症末期,下一步的治疗计划,是临终关怀。
而她一直没有告诉她的父母。
关于她的生活的具体细节我知道的不多,因为我们很少讨论除去clinical需求以外的信息,这是我们工作伦理的一部分。
我只晓得她几年前独自移民到了这里,最初的病历记录是独居,后来又加上了父母从国内来看她,与她同住,拿的是旅游签证。
她在确诊之前,曾在唐人街打工,据说做了很短一阵就辞职了,因为老板不给工钱。具体是怎么回事,她不愿说。因为英文不太好,加上身体每况愈下,便没有再工作,申请了政府的补助金。
确诊癌症晚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她对我同事提起她最大的难处和焦虑,是不知道如何告诉父母。以前她曾经生过一次大病,那个时候,她的父母表现得非常焦虑,所以这一次,她不想说也不敢说。
我的同事和主治医生还有护士长都做了很多工作,跟她一起开了会,讲诉利弊和将来会发生的各种情况给她听。她欣然同意了各种治疗和还有社会服务,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她不许医疗和服务人员上门,也不许任何人打电话给她的父母。
她身体很虚弱,可是她愿意花钱打车去机构。
其实她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了,尽管医疗开销政府会cover很大部分,但是药物还有特殊的营养食物也都是很大的支出。
打车又很贵。
对了,他父母完全不讲英文。
她说:“有什么好说的呢,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吧。”
作为医院,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毕竟她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你说,她为什么这么坚决不让父母知道呢?她已经处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了,她需要安慰,需要关心。”我的白人同事这样问我。
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我甚至可以给她开一堂课,但是终究我也只能说:“文化背景的原因。”
又或者说,这是一种常见的一个家庭中纠缠不清的共生关系。
我全方位的入侵你的生活,你也要全方位的为我的喜怒哀乐负责。
我们是一个讲究集体主义的国家,如同《巨婴国》中所述,我们从小承受了无数来自父母的付出,而这一切都是要还的。
这个病人,还不起了。
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相比关心和安慰,她需要的只是少一点负罪感和愧疚。
她得了癌症,她快要死了,她对不起她的父母。
这就是她真实的想法。
想比病痛,来自父母的焦虑更可怕,无法解决父母焦虑的无力感更可怕。
她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逃避,一直到最后的那一天。
说到此处,想起一个华人实习生,她是生了孩子之后重新走上社会的,我们主管闲聊时问她孩子谁带。
她说自己的父母在。
白人主管笑言,那他们一定很开心吧。
那个华人实习生很勉强的笑了笑,“他们或许内心很乐意。但是他们会让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favor,我以后一定要还的。”
她看了看我,像是我一定会懂。
我报以一笑,点了点头。
还是说回这个病人吧。
她已经出院了,社区的临终关怀接手接下来的事情。
我知道临终关怀的同事,会把她照顾的很好,可是止痛药并没有办法治疗心理的痛。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
她说,她想要带父母回国,然后在国内度过最后的时光。
她的父母完全不会英文,所以她必须送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为止。
这也不是不可以,主治医生问她回国以后的医疗安排,药在哪里拿,有没有冰箱,有没有人可以给她打点滴。
答案是,回国以后要经过各种隔离,加起来将近两个月。或许是翻译的问题,我的同时对我说是quarantine hospital,而这个quarantine hospital居然没有医生。
“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她很快就会去世的。”我的同事说,“她需要止痛药物,需要缓解症状的药物,需要能最大限度帮她延长生命的药物!”
可是这个病人还是要回去。
我们帮她想了许多办法,她坚持要回去。
她说她必须在死之前把父母安排好,绝对不能把他们扔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这是一个无解的悲剧。
而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