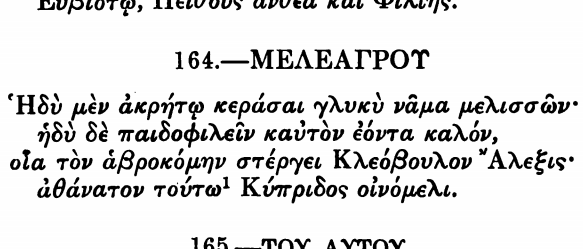
vigilando, agundo, bene consulundo prospera omnia cedunt. ubi socordiae te atque ignaviae tradideris, nequiquam deos inplores: irati infestique sunt.
論重估自由
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是我對日本某大學學生要求成立宿舍自治會為中心,以新左翼組織為主要人員的一系列鬥爭的觀察,並且我把其失敗的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原因歸結於「自由」這一概念在被不假思索地使用中消滅了自身,在開始議論前,以下一段是我寫在自己朋友圈的一個概要:
「對你日的左翼大學生沒什麼好感。雖然如果他們有活動還是傾向於參加,因為這些人已經是相對比較像個人的傢伙了。但是說實話,我覺得他們只是在搞某種cosplay吧。論做實事,我不覺得他們比教會做得更多(雖然我認為教會做得不夠多,至少和朋友告訴我的歐美的情況相比之下),論理論更讓人無力吐槽,請問讀那些新左哲學家然後抖機靈有什麼用?造梗,草生?搞的宣傳品不過是堆砌一些大家都同意的空洞的口號,要知道沒有什麼人瘋到宣傳不要愛和和平要恨和戰爭,問題是喊喊口號只能感動自己,捍衛不了他們珍視的岌岌可危的東西。況且他們珍視什麼,破樓裡面的嬉皮士生活?如果他們讓人覺得他們要求學生自治的目的就是過嬉皮士生活,儘管自治是合理的,這種垮掉的一代式的虛無有時也可以變得比大學的官僚主義更令人厭惡。況且他們有難以置信的把集會變成嘻嘻哈哈的狂歡的天賦,所以你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活動家被大學開除的時候,一同參加派對的人不會一同分擔他的厄運。況且這種輕浮使他們合理的鬥爭平白變得可笑,使屈辱從壓迫他們的官僚的身上轉移到他們身上。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熱衷模仿嬉皮士;老實說,如果你想在這個時代表現得很叛逆,你應該模仿的不是嬉皮士而是修道士。總而言之,這些人讓我想起泡薩尼阿斯(我想這個故事好像不是來自這裡,但我實在記不起來具體出處了)講述的那些可憐的斯巴達人:羅馬時代的斯巴達已經淪落成一個小村莊和旅遊景點,他們向遊客表演著名的傳說中古代斯巴達人為了鍛煉少年的意志,讓他跪在阿耳忒彌斯像前忍耐的鞭打;但是那裡早已連榮譽的殘渣都沒有剩下,儘管鞭笞確實和古時候一樣痛苦。」
一般来说,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和人们说云是自由自在的时候的自由是同一个意思,即云是自由的,意思是说云没有轨道,你不知道下一秒云会飘到哪里;但这个理解的缺陷在于,相同的云,也可以被说成是最不自由的,理由如下:云固然没有方向,但云的运动是由云周围的空气状态决定的,空气的这种状态决定了风的方向,从而决定云会朝什么方向以什么样的速度运动。因此提出这样的自由的理解的人会争辩说,造成云的这种不自由的原因是云没有意图,也就是说,云在自身中没有其运动的原因,而他们赞美云的自由的意思是,假若云有意图,云就可以向任何方向按其所欲的方式运动。也就是说,自由的意思是意图的实现。为了回答他们,我必须先确定当他们说意图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将想象中的考量变成现实的愿望,还是经过理性同意的冲动。我想没有人会否认,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动物,还是我们假设的拥有心灵的云,在从物理上被阻碍了运动的时候,都不能说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认为冲动几乎全部有其物理基础:例如饥饿的根本原因是胃空着,口渴是因为身体需要水分,因此假设我不得不一下午坐在学校的自习室,但是由于防疫需要,摘下口罩喝水是禁止的,我在口渴难忍时便认为这样的规定剥夺了我喝水的自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冲动的实现并不总意味着自由,因为冲动本身有可能是反自由的,因此荷马让奥德修斯正确地责怪肚子“不要脸”,因为它即使在人极度的哀伤中,也迫使人优先照顾自己的需求,在这个例子中,即使奥德修斯的愿望是为远离故土而悲伤而非进食。即使我的对手说,外在的束缚禁止一切运动,而内在的冲动只是使部分运动不可能,那么我要和他讲一遍那个勃列日涅夫和卖瓜小贩的笑话。让我们先考察第三种定义,即一个人同意了他的冲动,也就是说,一个饥饿并且想要进食的人自由地去吃东西。但是我要说,如果这种意愿基于物质,比如一个人想要进食是因为饥饿,或者进食令人快乐(“我有吃零食的自由”),我认为这和第一种情况仍然是一样的,即,物质世界的规律(a.k.a.必然性)规定了我们的生存,在这种世界的命运下任何物体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也就是科普读物所说的拉普拉斯妖,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也许可以去读一读舍斯托夫。因此我们回到第二点,即自由在于理性的推理,预测和判断,而不在于冲动或被接受的冲动。
我们明确一点:在同一个瞬间只有同一种运动的倾向存在。因此在运动现实地产生之后,自由就暂时消失了,意思是说,当你向前运动时,你没有向后的自由,除非你首先停止然后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的活动并非是为了自由,而是相反,如果认为自由指的是运动未定的状态。因此,霍布斯用一个错误的语源学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解释,他认为,deliberate的起源是拉丁语de-libero,也就是去-自由。因此我主张,固然可以说自由可能地存在于未定的状态中,但自由的完成是说找到它的轨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有心灵的云始终漂浮在天空中,那么它始终不是现实地自由的。
在人身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冲突。在那些失败的学生的自治斗争中,我先说明我坚定地站在支持自治和反对大学的官僚化的立场上,但他们的自由以其本身,即让最多的人达到最大程度的消极自由为目的,在我看来是不可靠的。这种共同生活像是一种股份公司,每个人都明智地知道自己想从中得到什么:廉价租金,看起来很酷的生活,充斥着空洞的左派口号和廉价的自我感动的活动;也清楚自己付出什么:把无所事事的时间拿来制作五颜六色的看板,在学校的雕像和墙壁上乱写乱画,但如果让他们和同伴一起承担危险和痛苦,似乎就显得干涉到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把文盲,即对书写和阅读缺乏能力叫做文字上的不自由,把瘫痪叫做腿脚的不自由,把聋哑叫做耳朵和嘴的不自由,这里的不自由指的是对能力的阻碍的话,我不禁要问,人的能力是什么?人的能力是和同胞的互相关爱,研究世上的种种事物,思索难以捉摸的神和永恒,这是我所认为的。因此,一个嬉皮士,我说的是这种精打细算的嬉皮士和一个白领,我认为二者很大程度上都不是自由的。如果这些人有一个目的,我假设,他们至少希望他们的斗争能成功,他们必须首先说明为什么自治值得选择,因为,当他们认为自治是做嬉皮士的保障的时候,那么显然,在当今的时代,如果认为嬉皮士的可取之处在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的话,那么这种生活和自治没什么关系,事实上被驯养的现代人更容易活得像一个嬉皮士。他们必须解释,这个官僚体系糟糕在哪里,因为它僵化,因为它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决断之上,因为它优柔寡断,因为它无原则。但这样意味着反对它的人需要有坚决的立场:和平意味着向挑起战争的人宣战,爱意味着为了保护弱者拿起武器,如果官僚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妥协,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反对官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重估价值,为了建立新的价值而奋不顾身。德语非常恰当地把救世主叫做Erlöser,意思是解放者,Erlösung,救赎,即解放者使我们自由的必要条件是我们和他一同被钉上十字架。
中性意义的阴谋,即非公开地谋划的事业,之所以说中性,因为除掉独裁者恢复自由的事业也可以用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用法尤其可以参见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李维》中关于阴谋的长篇论述,阴谋在拉丁语中叫做coniuratio,字面意义是共同发誓。而发誓的人被说成是”受缚“于他的誓言,这种用法我想应该是共通于世界各地的语言之间的。因此我可以强调,自由绝不是无方向;相反,现实的自由体现在毫不迟疑的追随行动中,我可以充满感情地说,我拒绝那种犯傻和做蠢事的自由,因为我不认为我在做了什么蠢事的时候是自由的:因为那时候我的脑子被扔在一边,处于无能的状态。所以当神学家们说,人在信仰中得到自由时,他们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信仰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夜间泳池关卡的灯笼草一样驱散心灵的迷雾,这是一个准确的说法。同时,那些悲观的人断言世上根本没有任何自由的时候,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就像欧玛尔海亚姆说”天地初开时的词句,要一直传唱到世界终结。“但我们暂时不需要在这种意义上考察这个概念,只要意识到,把一切抛进混乱,相对,和犹疑根本不是对抗自由之敌的有用的办法,我们必须重估价值,就像德尔斐的神告诉那位著名的住在木桶里的犬儒的,要他”改变货币的价值“。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