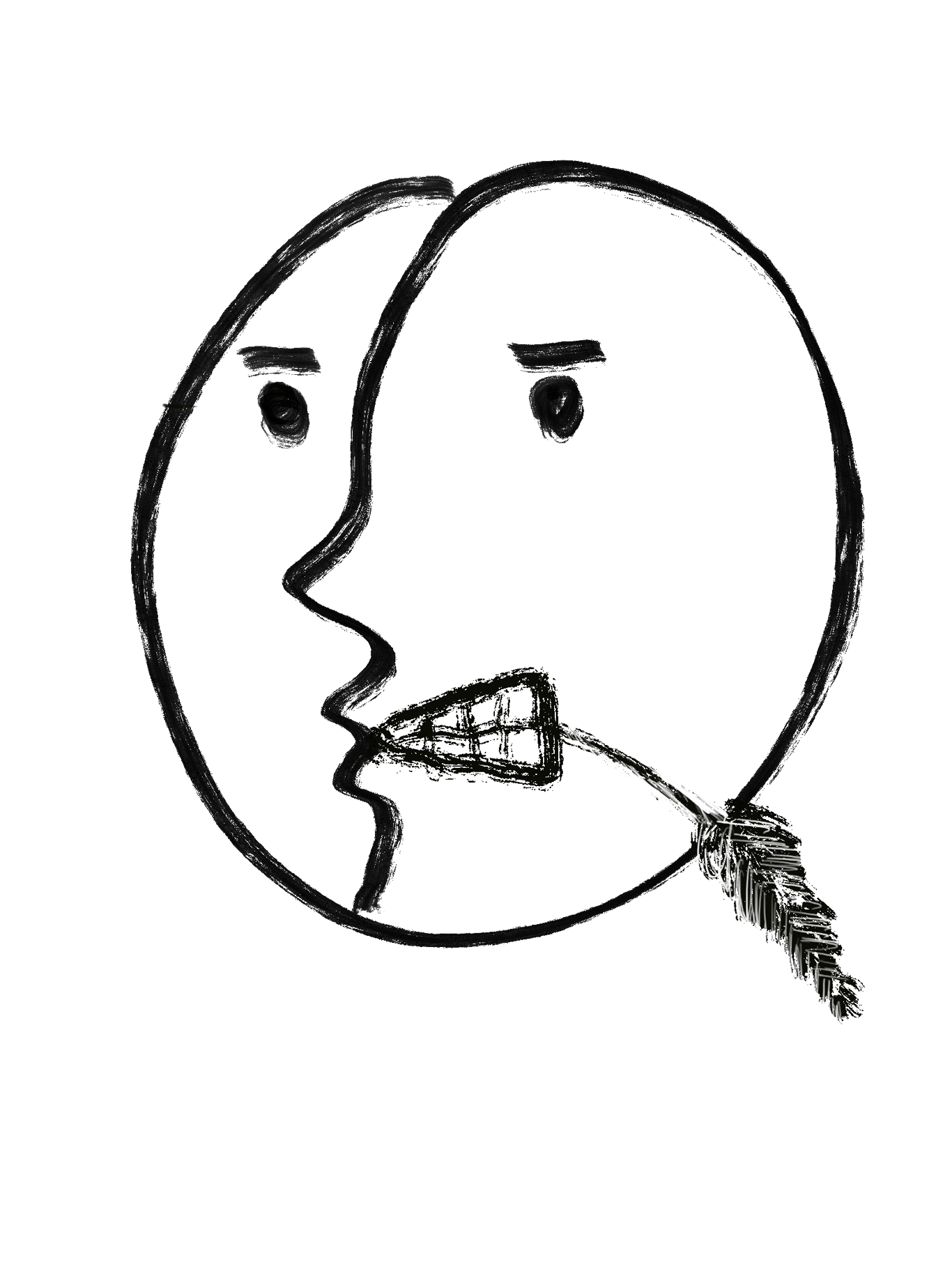
學中世紀哲學,暫時還沒死的怪咖野人。正在學習如何假裝人類。 ⋯⋯ 喔幹,學不會。
閒聊我亂寫的理念
我不在意文字被討厭
對我而言寫作完全是為了講我自己的想法,不是在轉述別人的思想,我一直覺得轉述別人的思想很無聊、但也不是完全沒意義,但如果是我來做的話就會覺得自己根本是在浪費大腦。同樣的,像用詞啊、節奏啊、結構啊什麼的行文美感也完全不重要,但也不排斥就是了。有些人就會比較偏向美感,比如詩或美文一類,也有些人偏向總結歸納。這些也都沒什麼對錯好壞之分,只是個人閱讀或寫作習慣不同而已。(那這邊如果有人想要抬槓說「人的想法全都來自別人」,那你去找跟我一模一樣的想法過來,找不到我就當你是在放屁。)
但也會有人希望別人認同跟遵守某種寫作規範,這就很討厭了,不會寫、表達不清自己思想的才需要用既定框架輔助表達,自己往框架裡面丟概念。像這樣用既定的模式寫論述,要麼容易邏輯混亂,要麼容易整篇廢話。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細看結論往往都是人人皆知的廢話大道理。
所以說我因為擔心自己變成自己討厭的樣子,那被討厭就比較無所謂了。
寫作的理念
在創作者被讀者視作創作者時,他們表達形式上的差異於我而言只是因為受眾群不同。比如「今晚的月色真美啊」這句,除了第一作者把這句話創作出來的意圖跟一部分欣賞這句話內涵的讀者外,多數引用者使用的意義,就目的論而言,跟「妹修幹謀?」幾乎沒有區別。但如果作為第一讀者去讀前面一句話,又會得到跟第一作者相近的意義,也就是說,對「今晚」句而言,引用者與聽眾之間產生了意義上的落差。但另一句「我想跟你一起看日出」跟「妹」句之間就沒有這種落差,因為這句話的第一作者想要傳達的意義,其實與「妹」句一樣,只是「我想」這句更有機率被誤解,或有機會被刻意誤解。那麼假使我寫作的目的就是傳達思想,而非達成目的,顯然「妹」句才是更有效且不容易被誤解的,「我想」句則是用來緩解尷尬的。
也就是說,我寫作的理念一直都是更直接、減少誤讀機率地傳達我自己的想法,而非「讓你讀完更容易相信我的講法」,後者其實會因為可以隱藏一些不願意擺出來的事實而變得比較容易產生古代宗教式的邏輯瑕疵。
是亂來還是自由?
像上面的舉例一樣,我也不喜歡迴避傳統或世俗的禁忌。其實我有點難理解日常語言裡的這種假掰現象,我沒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懷疑人們使用這些字的必要性。比如人們吃肉的本質,完全就是因為美味導致這塊肉原主體的死亡,但人們會刻意把這塊肉的主體轉化為客體來描述,刻意淡化死掉動物的主體性(事實上這整個過程才是區別於alter ego的他者化行為,但這類現象學概念我討厭所以不用),並用「飼養動物是由專業屠宰場殺掉」或「養殖牠們的目的就是被我們吃掉」這類理由(或藉口)來搪塞動物死掉的結果。進而,由此產生的諸如「可憐生命」等理念,更多取決於敘述主體對其共情的多少,而甚至不取決於作為客體狀況下的這個動物的生命化程度。所以這類所謂的「理念」,其實對寫作而言根本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用來傳達思想的理念,只是政治上或大眾心理上的某種趨向而已。那這些相對純粹的理念表面上的確很亂來,但亂來的表面並沒有影響語句的意義跟表達的自由,那麼這些「亂來」就又回到美學問題了。
對於這種自由的界限,在我看來可能就是知識跟對知識的接受程度。這邊的知識不是指狹義上的條目知識,而是一切知道或理解的東西都能被當作知識。那這種接受程度,就比如在超商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小男生下意識的動作表現出對自己母親的性慾。我會把這種性慾視作一種「正常」,由現代道德施加給小男生的性壓抑也視作「正常」,自此被我接受的整個過程其實並沒有明顯表現出傳統意義上(抱歉我不是佛洛伊德派的擁躉)的「禁忌」(因為小男生對自己性衝動的無知)。所以在我看來,賦予這種性壓抑禁忌意義的說辭才更像是欲蓋彌彰的藉口,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擔心提及這些詞彙、事件、動機,甚至「髒話」呢?假裝正經、秀學術背景、秀身高體重(?),能為我任何一句論證增添意義跟合理性嗎?顯然不能,那些都只會有機率增加古代宗教式的「可信度」。那已經有邏輯了,我還要那些文字垃圾幹嘛?拿來相親嗎?我又不需要。
跟正文毫無關係的後記
話說ideologia本來是個反形上學裡面很有內涵的字,為什麼被借用到政治裡以後就變得那麼噁心。感覺「意識形態」這種翻譯也是從政治學裡來的。所以中文的「意識形態」其實不包含ideologia的原始意義?
這幾天天氣好乾燥也不下雨,品塞乾在裡面卡住挖不出來好難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