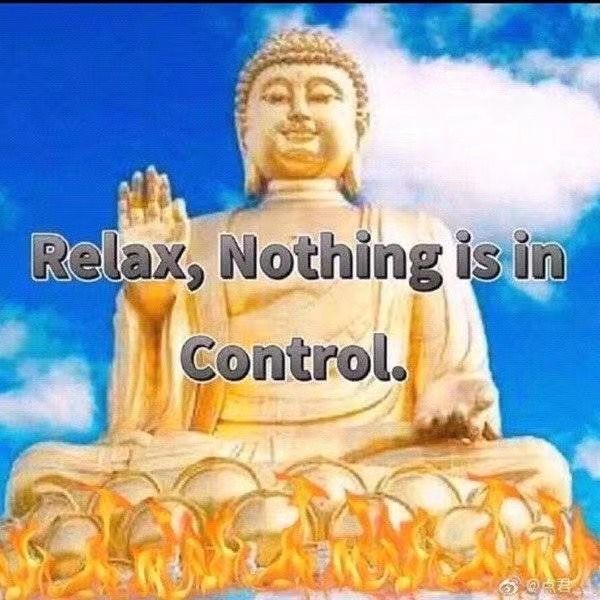
个体记录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
告别外婆
去年4月下旬,外婆离开了。五一假期,我赶回家与父母一起处理外婆的后事。那几天,我将这一经历记录在了每日书上。
今年五月,因为疫情无法回家。重新面对这些文字时,突然意识到,一年已倏忽过去。
告别外婆
01
5 月的第一天,一团疱疹找上了我。它们落在我右侧的嘴角,约莫五六颗,火红一簇。
清晨 6 点,我还未完全清醒,在闹钟第二次响起时,凭着惯性走向洗手间。我抬头照镜子,看见嘴边一夜猛地冒出的疱疹,注意力渐渐集中,也有些疑惑。
自打大学毕业,我很少长疱疹或者口腔溃疡了。
我知道这不是上火,而是一种病毒,单纯疱疹性病毒。它长期潜伏在体内,躲在神经节内,当感染者免疫力低下的时刻,或者面对压力,突然就表现了出来,难以捉摸。
也许,是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今天,我要去殡仪馆接外婆。
外婆在一周前的凌晨离世,享年 94 岁。而这一周,我的情绪都很复杂。
外婆的离开,我已有心理准备。清明前,妈妈喊我回家,说外婆挺不过去了。我算是见上了外婆「最后一面」。
可外婆已经不认识我了,也不认识妈妈。今年开始,外婆好像谁都不认识了。
卧床的第四年,外婆无法行动,无法吞咽,无法沟通。爸爸说,「今年」对于外婆,很没有意思。
从前,我在小说里读到,「衰老是极为不体面的状态」;现在,对于衰老的感知,变得很具体,甚至,有一些恐惧。
电话里得知外婆离开的消息时,心头微微泛起褶皱,又很快过去了。那一刻我很平静。或者,我不太知道,应该表现成什么样会比较妥帖。
心情过于平静,又让我有些愧疚。这一周,某些快乐将至的时刻,都会突然想起外婆。
我和外婆共同生活的时间有限,回忆零星,情感没有可以附着的具体物质,不免疏离。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还是失落的,含着一部分对亲人离开的失落,但更多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失落。
02
火化的台面上,留下外婆骨折后曾经安装在体内的钢板,以及一枚老式的 1 角硬币。它是不小心落在衣服里,还是曾经被外婆误吞下去,已经无从考究。
家乡的殡仪馆,需要家属自己去清扫骨灰,小心收进一方红色的布袋,亲自装盒。我此刻想起那个场景,还是会很难过。对于家人而言,这个过程过于残忍。
骨灰无法完全清理干净,有一部分附着在一块耐火的垫子上;还有一些,永远成为台面的一部分。
外婆的一生, 94 年,在那个瞬间,变得轻飘飘的。普通人的一生,无人著书立传。
小时候一直在外地读书,对于外婆的印象,来源于每年假期有限的观察,和妈妈的只言片语。
外婆离过一次婚,听说前夫家暴,外婆曾与他生养过两个孩子,但都没能成活。说起来,她也算当时的新式女性,不将就,也有选择。
后来,外婆在夜校认识小她六岁的外公,开启了第二段婚姻。外公是外婆的扫盲老师。
外公是 07 年走的,后面十多年,外婆因为子宫肌瘤和髋关节骨折动过两次手术,但都恢复得很好。中风以前,外婆身体算得上康健。
刚开始两年,我们会接外婆一起过年,觉得她一人太冷清了些,也方便照顾。
后来,外婆好像适应了一个人的晚年生活,不愿意再来了。逢年过节去看她时,她总是不在家,有时在菜地捯饬农活,有时候在老年协会打麻将,日子闲适而又平静。
有一年,外婆对妈妈说,自己入了基督教,突如其来的精神追求,让后辈都有些担忧。那两年,全能神之类的教派在乡村流行。
日子有来有往,如果不是 4 年前中风,外婆也许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03
其实,外婆不是妈妈的生母,而是妈妈的阿姨。再婚后,外婆没有再生小孩。妈妈 10 岁出头的时候,被过继到外婆家。
刚刚接过去的时候,妈妈曾经一口气跑好几里地,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跑回家里。
因为计划生育,我的一个表姐也曾被送到姑妈家「避风头」。我妈妈曾看见表姐哭喊着离开家,跟着流眼泪。
当然,这些事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少提,像是某种特殊的避讳。
只是,自打记事起,我从来没听过妈妈喊外婆「妈妈」,一直叫「阿姨」。但是,妈妈一直要求我喊外婆,而不是什么,大外婆,又或是什么,姨婆。
外婆,只能喊外婆。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的,但一直没有问原因。
04
我提一盏素色灯笼,走在人群的最前面。灯芯烛光跳跃,照亮灯罩上一尊潦草的佛。佛与灯,都是用来领外婆回家的。
爸爸双手拖着骨灰盒,妈妈用伞撑出一方荫蔽,跟在后头。听有经验的大姨说,骨灰盒不能见光。
棺材是在妈妈结婚后,外公就给自己和外婆备好了的,一人一口。外公还在世的时候,自己就选了一处墓地,还将过世的先祖迁至一处。自然,还空着一间墓室,留给外婆。
我们带着外婆抵达时,同村的亲友已经将棺材放置在坟前的空地;边上是外婆生前常穿的衣服、裤子,还有鞋,装了满满一箱。 要给外婆做一个「衣冠冢」。
点燃一束香后,我跟着妈妈,将外婆衣服一件一件铺平放入棺椁。整理衣物时,我看到一件做成衬衫状的羽绒夹克。这是多年前某个冬天,我和妈妈一起在商场买的,说好过年带回家给外婆。
妈妈那时说,羽绒衬衫当内胆穿里面,保暖也轻便。我自己也买了一件类似的。有那么一阵,全家都爱穿这样的羽绒衬衫。只不过,我的那件早已找不到了。
上衣是上衣,裤子是裤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和妈妈把衣服全部都归置好,组成一个人形,腰间留出空隙。那是用来放置骨灰盒的。
下午四时,骨灰入棺。
帮忙的老人烧了一圈稻草,放入左侧空置的墓室。我以为是要燃尽里头的空气,但妈妈说,这是帮外婆「暖暖屋子」。
今年的五月,比往年更热一些,稻草燃烧释放出的烟气逼人,温度开始让人不舒适,我恍惚起来。现实世界在抖动的火苗中,开始有些变形。
忽然之间,一只巨大的蜈蚣从水泥的缝隙中蹿出,落荒而逃。望见这只略有些肥硕的蜈蚣,我有点走神,想起了曾经读到的盗墓小说。
两年前,村中扩建道路,外婆旧屋的一侧厢房,连着一整排房子被推倒,只留下一间起居的堂屋。
拆迁那会儿,妈妈自顾不暇,周旋在中风卧床的外婆与工作之间,没去申请新的安置房。没能想到,外婆一病没能再起来,一直留在城里,没能回到自己的老屋。
后来,村里发放了一万元的赔偿款,这事儿好像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人打算去追究。
一起帮忙的老人经验老到,在墓室门口放了一只竹筒,充当滚动滑轮。众人合力抬起棺木,顺着竹筒,推至墓室深处。
棺椁入墓时刻,天还没有一点黑的迹象,大家嘴碎碎念:
「阿姨/外婆,住新家了。」
05
外婆的故事告一段落,我们已经送别她。
下山后,所有帮忙处理外婆后事的人,进屋时都需要饮一杯甜茶,寓意活着的人,自此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苦尽甘来」。
回家路上,我与父母聊起外婆生前的一些事,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两日,我们依然经常提起她,试图通过某些记忆的图景,去阐述自己对外婆一生的理解。
这也是我与父母为数不多的、讨论生命与死亡、健康与尊严的时刻。这样的讨论也意味着,他们终于愿意视我为一个成年人,不再回避。好像,人生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假期的后两日,嘴边的疱疹经历破裂、流脓、最终失去水分,在嘴边结下红褐色的疤。今日,在离开家的路上,毫无征兆地,疱疹的伤口裂开。血液沿着嘴角流淌下来,在纸巾上留下鲜红一团。
它的生长与破裂,连接着此次回家的一头一尾,仿佛某种情绪的萌生与消解。
---------------后记-----------
在我们老家,过年是需要给往生的亲人上坟的。太公外婆,也就是爷爷的父母这边的长辈,子女多,一大家族成群结队上香,人气冲淡了这件事本来自带的哀愁。
今年是外婆入土第一年,她没有其他子女,只有我和父母三人上山祭拜。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没有雨雪预报,天上却下了冰雹。
那天风很大,爸妈奋力拔除坟头长的草:半年时间已经长得有半人高。那天从山上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很难过,回家的路上在后座抹了眼泪。之前,我从来没有因为春节上坟的这一习俗哀愁过。
07年的时候,外公入土后,爸妈只在第一年来过,没让我跟着。妈妈说,外公不信这个,特意嘱咐过,不用来看。不过,外婆没说。
记录于2021年5月,修改于2022年4月30。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