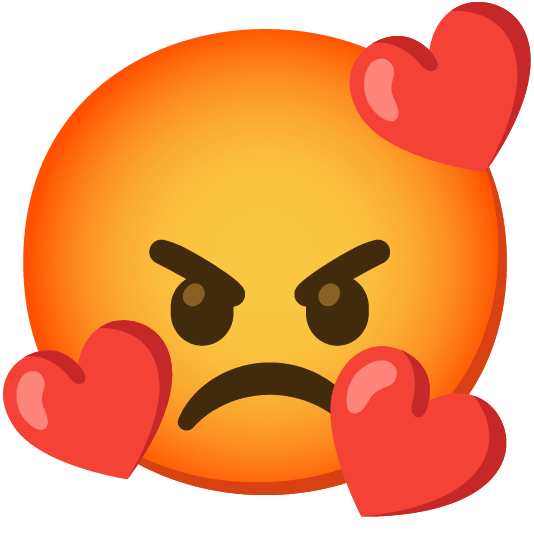
黄色的女人
有一年,我大概十岁,最多十二。是春天或者秋天,因为虽然我不记得当时的温度和我穿的衣服,但我记得对那温度没有感情也没有诉求,就是说没有热到或冷到需要哀怨、诅咒。你要知道,那可是在铁道上,冬冷夏热的地方。啊,说到这,我仿佛一鼻子就吸到夏日铁路上被炙烤的,混杂着机油、焦炭、垃圾和粪便,那热烈而凝滞的气味。说凝滞你可能理解不了,不过你要是在大热天的中午出门,顶着大太阳走上一遭,是会产生时间和万物都停滞的感觉。当然没有风,连知了都不叫。大概就是这个时候,鼻子能吸进大块大块的停滞。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二十三岁之前的记忆里夏天占比最大,它们都凝固在时间长河里了啊,浮浮沉沉总是不肯消解。所以我的这一段记忆很流淌、很飘渺,也显得尤为珍贵。我怕我不写下来,它要不了多久就会被2023、2024什么的,这些琐碎而凛冽荡涤和谐干净了。
是的,当时我通体舒泰,我独自走在铁路上。人很少,我走得又甚是从容,所以肯定不是去上学。应该是有风的,仔细听能听到路坝下蒿草的沙沙声。既然望过去,我要开始描述景象了。我不明白做这件事为什么需要深深地吸口气。
等以后我要做这段影像,我能想象,我会功利地给它上点时代的包浆,比如把光调成橙黄色,我就这德性。可那天真不是,那天整个都是葱郁的绿色(几乎能确定是春天):路边的蒿草是青绿色(有锯齿,你看到会觉得麻辣无比);天空是清灰色(云不云的……我脑子算力不够,没法渲染这细节,只晓得没有跟雨有关的焦虑);远方偶然勾画的山的脉线是铁青色(你说一个城市的远方没有山线是不对的。)
我是十二岁,不是十岁,因为肯定已经上了初中。小学腿短,枕木的间距是要用跨的,走起来会蹦蹦跳跳,脑子里必须绷着根弦,有回没绷住就把锁骨摔折了。但那天没有这个紧张,我只是想着目的地,但我不记得目的地是哪。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清灰天际下明亮的女人,穿着黄色的风衣,拎着一只棕色的皮箱,走在我的前面。我立即把所有的感官放到她身上。
我刚上初中,还没有看我姐的言情小说,听她的校园民谣;所以关于异性,关于爱情,我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调取,只有五年级看的《儿童文学》还是《少年文艺》里面几篇文章里写的,隐隐绰绰、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情愫;不对,情愫都大了,只是几缕微风般的扰动吧。
于是没有想象与联想,我只能全身心观察,观察那背影。这跟看李萍萍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是躲在背后,同样安全。看李萍萍我是有幻想的,现在想来有些丢人,我的幻想只是跟她挨得近一点,坐在她旁边,走在她旁边。高中后我才知道幻想跟女的过日子,但那时已经换了个姓薛的女孩。
我没法幻想眼前的陌生女人,要知道,这之前,李萍萍已经在我生命里断断续续待了三四年。对她,我只能感受不能创作。现在能记得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喇叭口的裤脚;头上绑着短辫子,不是红的。那时候十八线小镇不应该出现染发的,记忆这东西真不靠谱,是谁闯进我的海马体,把她辫子染红的?是不是你,姓薛的?你在20岁之后就一直是红毛吧!
最重要的一点,她是成年人,是个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她对我的魔力大部分来自于此。我认识最大的女人——当然是让少年郎心猿意马的——是邻居涛涛家大姐,也只是中专生;还有一个,虽然是真正意义的大人,但我没见过。是我高中同学的小姨,在市里上班。我跟她之间的联系是一盒磁带,可能是一张合辑,我只记得有巫启贤的《太傻》。我在同学家玩顺手借了这盒,原主人是小姨的磁带。回去听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磁带是香的!歌纸是香的!我鼻子里的味觉细胞至今还记得那是怎样的香。这个感官刺激相当大,以至于我在黑暗中听歌时会放很多感情在那个没见过的小姨身上。具体是什么感情,即使到了高中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小姨站在我面前怒吼:“你想干嘛?”时,我是绝对答不上来的。啊这样说来,原来暗恋的不耻在于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在你自己的心里面都没有个名分,那可不真猥琐?
她走得实在太慢了,皮箱应该很重,她需要两手提在身侧,时不时换边。我保持着距离,中间大概还能再插两个社交距离。我随着她的速度,心里荡漾着此起彼伏、轻飘飘的旖旎。我像是笼罩在她散发的魔法区域里,温热香甜。不过麻烦的是,我的步伐越来越不自然,叫我越来越不能忍受这节奏,这根本就是尾行。
我只能越过她。我也很想越过她,很想看看她的脸。但我知道我要小心翼翼,不能让她察觉。我从左边超越,昂首挺胸。偷瞄是这样的:我先看向左边的天空,接着叹了口气,皱眉往右看去。你能看出我这策划的是什么故事吗?我是毫无线索的,也许只是要表明:我这是有意义的动作,所以不是在看你。好一手掩耳盗铃。
我确定我看到了她的正脸,但我完全不记得眉眼,后继用文字补充的记忆写的是“一张艳俗靓丽的脸”。但当时的关键是,我之所以看到她的正脸而不是侧脸,是因为她正偏着头等我!我大吃一惊,还没泛起更具体的念头时,她看着我的眼睛,朝我笑了一下!当然我也不记得那个笑脸,但当下,我宁愿随便套一个:黑黑的圆脸,但下巴很尖;双颊上有雀斑,笑起来有酒窝,是狭长、竖直的酒窝,大概2厘米;额前有刘海,鬓角有碎发,向上卷起,正指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对这笑做出反应——当然她看我这事还没开始琢磨——她开口对我说话了!好一个一波三折!
她说:“请问……”
我一脸震惊,掩饰的、成熟稳重的保护色完全没有亮起。
“请问”她又说了一声。
“什么?”我停下脚步,接受这个意外,人又被她的魔法圈包围。
“妇幼保健院怎么走?”她低头看路,也停下来,抬起头来问。
她说得普通话。我身边只有知青和厂矿子弟说普通话,那代表着干净的衣服,没有鼻涕的脸,酒心巧克力,鱼皮花生,任天堂游戏机和下馆子。所以黄色女人在我心中的美好又升了三成,我的理智恢复,又开始紧张了。
我不敢看她,垫着脚指向远方,“那边有路口,下去笔直走,不多远就是。”
“哦好……”她顺着我的手望过去,迟疑了一会。我得以再次瞄了一眼她的脸,她抿了抿嘴,把箱子换了个手。确定了路口后她又看向我,我在她转头之前逃开,她的目光还是击中了我,可为什么那眼光里有很多歉意?
我分裂成三个人,老大想那个饱含歉意的目光,老二安静地当她魔法的俘虏,接受她发出的各种形式的辐射,老三那个王八蛋点点头,迈开步子,把我们三个带离了!
不过才走出一步,老大突然意识到什么,生生把我们拉住。我扭过头去看她,眼光在她脸上一划而过,“要不要帮你拿箱子?”我一口气说完这句,很有种。我意识到那个目光里不是歉意,而是求助,我对此愤恨不已,作为男人竟然没想到。所以在此情绪下,我念出这句一点都不结巴。要知道,我现在主动夸儿子时声音都是微颤的。
她的笑马上换了个光,一下绽放开。“谢谢,谢谢。”黄色女人激动地连连道谢。刚才被我压在最底下的老三能得要死,炫耀着跟我们说:“所以刚才偷瞄过去,她正看着咱,第一时间就是想求助了。”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理出来的,那么短的时间哪有这么多字句——虽然我二十三岁之前有电光火石间切割时间的超能力。再说,我接过箱子整个人都开始抖了起来。
这之前我拒绝了两人一起抬箱子的建议,一把抢过皮箱,单手拎了起来。但箱子的重量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只几秒我就坚持不住,忙加上另一只手。原来女人的力气并不比我小。我上了两手,比她走得还慢,还狼狈。这时的身体颤抖完全是力量不够的代偿。
黄色女人再次说两人抬,我倔强地哼了一声摇摇头。第三次她也不问,直接去抓提手,我立即松开左手。不是因为乐于接受帮助,而是她碰到了我的手,那是冰凉的指尖。
箱子带来的紧张完全消失了,两人两手刚刚好;走得几步,女人带来的紧张也消失了,因为我们开始攀谈。我问她去妇幼保健院干嘛,她说找哥哥,哥哥在那工作。
我渐入佳境。不用刻意控制,也能发出好听的、靠后的、浑厚嗓音。我讲了几个漂亮的笑话,我记得那蹦着高的得意,我整个身体又抖了起来,这回是孕激素或别的什么激素上涌的冲动。
开玩笑,我在跟一个成年女人谈笑风生!
不过这事没有在我的历练里添上一阙里程碑似的,“情窦初开”的前奏;而是成为我人生中无数个“恼羞成怒”和“抱头鼠窜”的情境小品之一。当然,这才是生活嘛。
我试着还原一下。我不记得转折点在哪,你也别管那么多,就像不用管我前面有多少胡说八道和借题发挥。且听着吧,我这是也要把你写进去。
“你真可爱。”
“一点都不可爱,我才不要可爱。”
“可爱好啊,小孩子不就应该可爱?像你这样,还帮助我。”
我沉默了三根枕木后说:“你去妇幼保健院生孩子吧?”
“小孩子瞎说八道!”
“我才不是小孩。”
“怎么不是,你上初中了吗?”
“我都高一了,你呢,有二十岁吗?”
“问女孩子年龄不礼貌哦,我都工作了呢。”
“咳,有什么啊?多少岁和生孩子都不丢人。”
“小孩儿你是不是生气了啊,说你小。”
“没有,没有,有什么可气的,我又不是小孩。”
“哈哈哈,你真的很可爱哎,一会到了请你吃猪血汤。”
“吃你妈的猪血汤。”我站住,冷笑着清亮地骂了一句。女人显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蓦地站住,瞪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从一个光屁股天使变成鬃毛森张的恶魔。
我已经先她一步停住,提箱子的手用力向下甩去,差一点把她带倒。箱子滚下路基,女人愣了会,脸上的神色转了几转,最后跑下去捡箱子时是委屈的。我又用土话骂了句最高级别的脏话,撒腿往前跑去。
我写不了这个对话——我现在对荷尔蒙耐受的阈值已经升了十倍也不止,怎么去同理那个敏感、自卑又莫名冲动的少年郎。鬼知道怎么建立那抽筋般的神经质的反射模型。我只是凭借扔掉陌生女人的箱子这个事实,以及记录在案的心之激荡,那些兴奋、沮丧、愤怒的点。嗯,我就是这样把它们连起来,连出的这件事。
再一次出现这样意义非凡的女人是在高二给我扎针的护士,医院里当然没有黄色风衣可穿,它换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流行的松糕鞋。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