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实修·转化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
野兽按:读了端传媒的《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以及中国数字时代在转发这篇文章时特别点出的一个评论:
【543217:补充一点。2月7日网上流传了一个为李文亮恢复名誉的联署,发起者将联署的信息公布在了matters上,完整的文件google可以查到,上次我看时有2500+人签署,然而,这一切信息也被网信部门收集到,共八百余人能够被精确追踪,并且这些人都会被警察找。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八百多人中的一个,那天四个警察进了我家,对我进行教育和口头警告。
他们去我以前的高中调查我(我是一名大学生,寒假一直在家这边),后续又给我爸打了一次电话。我还希望说明的是,端的这篇文章和很多报道一样,都给人构建了一种想象,以为惩罚从轻到重就是封号,请喝茶,禁止出境,拘禁什么的。但其实在基层处理中好像又不太一样。那里制造的恐惧是全方位的,比如说人们会担心自己的档案留下处分记录,从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再比如他们去我的高中调查我,比如会莫名其妙地给我爸打电话。条件好、有知识的人可能和底层的人的想象又不一样,后者可能会记住一些道听途说的恐怖事件(比如这边流传说有一个参与八九的学生被打了药,精神失常了),政治能够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就是,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他们,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才能,参与了政治,前途就毁了。这是一种彻底的恐惧,于是这些弱小的普通人就会彻底噤声。
总之我认为本文所描述的并不是言论审查唯一的运作模式。能够被揭露的黑暗固然是黑暗的,然而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黑暗呢?比如我在联署的名单里看到很多公务员、教师、国企员工、学生等利益非常容易受损的人的身影,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呢?我在联署里只是随手写了个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而警察在给我爸打电话时说,有另一个学生写了长篇大论,然后这位警察说“他废了”。这些人遭遇的恐惧和迫害是更加深重的,然而他们却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想起了今天凌晨三点多重读的徐贲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
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
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
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
李大猫在《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2020年2月12日 端传媒)提到:
很多人已经指出,目前在北京指挥参与防疫战的宣传和暴力部门,其优先级在卫生防疫部门之上(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履历也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而民众对疾病的恐惧,也使政府严苛的监视和管理更容易被接受。
比如网格化治理。早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就提出以“网格化”为社会治理方向。但因种种原因,仅有北京、昆明等少数城市尝试过这种当代保甲制度。而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央领导小组要求下,各地城乡均开展这种管理方式,将街道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的网格员上门掌握几十到上百户民宅人口构成、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情况,并进行日常监督。
又比如数据。腾讯、阿里等大公司掌握有中国大量用户的私人数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具体的数据品类和交易内容,以往还都仅限于业内和有关部门的掌握。疫情爆发后,有公司利用支付宝提供的数据,绘制了可能的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口流向图并公开,百度迁徙也提供了用户的迁徙路径。在平时,这种公开利用个人数据的方式很可能招致非议,但在“紧急状态”下,恐惧疾病的人们大部分都接受甚至欢迎了这种数据侵犯。
…………
至少在北京,打击小企业、驱逐“低端人口”、实现清晰化城市管理,是符合市政府近年来的一贯目标。这些措施暂时对防疫有效,但其继而提出的问题是,疫情结束后本就青睐网格化治理、现在又尝到甜头的国家,是否还会彻底中止这一细化到户的人口控制术?
很多迹象表明,无论对首都规划还是国家治理,本届政府都持有一种人类学家 James Scott 所说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modernism)的目标。这种治理目标是出于将繁荣等于效率,将效率等于秩序和稳定的逻辑,要求治下之地如几何图形般整齐划一,并能够用统计数据完全涵盖、用枝状网格统一指挥。无疑,有了抗疫这一战的铺垫,国家的社会控制网络将会更加健全和有效,更容易通过垂直下达命令,迅速扑灭可能的反抗行动。
这些年轻人的遭遇就是一个实证。这个实证也验证了许章润先生在《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里所说。
复次,内廷政治登场。几年来的集权行动,党政一体之加剧,特别是以党代政,如前所述,几乎将官僚体制瘫痪。动机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纪检监察为鞭,抽打这个机体卖命,维续其等因奉此,逶迤着拖下去。而因言论自由和现代文官体制阙如,更无所谓“国王忠诚的反对者”在场,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约,复以国安委一统辖制下更为严厉之铁腕统领,最后层层归属,上统于一人。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党国体制下又无分权制衡体制来分责合力,遂聚亲信合议。于是,内廷生焉。说句大白话,就是 “集体领导”分解为“九龙治水”式寡头政制失效、相权衰落之际,领袖之小圈子成为“国中之国”,一个类似于老美感喟的隐形结构。揆诸既往,“1949政体”常态之下,官僚体系负责行政,纵便毛时代亦且容忍周相一亩三分地。“革委会”与“人保组”之出现,打散这一结构,终至不可维持。
晚近四十年里,多数时候“君相”大致平衡,党政一体而借行政落实党旨。只是到了这几年,方始出现这一最为封闭无能、阴鸷森森之内廷政治,而彻底堵塞了重建常态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进路闭锁,彼此皆无退路,则形势紧绷,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形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经济社会早已遭受重创,风雨飘摇于世俗化进程中的伦理社会不堪托付,市民社会羸弱兮兮,公民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至于最高境界的政治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则一旦风吹草动,大灾来临,自救无力,他救受阻,必致祸殃。此番江夏之乱,现象在下,而根子在上,在于这个孜孜于“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定于人民主权、“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的体制本身。结果,其情其形,恰如网议之“集中力量办大事”,顿时变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证而已矣。
第五,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治国驭民。过往三十多年,在底色不变的前提下,官方意识形态口径经历了从“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和“四化”的富强追求,到“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再至“新时代”云云的第次转折。就其品质而言,总体趋势是先升后降,到达“三个代表”抛物线顶端后一路下走,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保江山”的“大数据极权主义”。相应的,看似自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因其动用奠立于无度财政汲取的科技手段,这便形成了“1984”式“大数据极权主义”。
缘此而来,其“微信恐怖主义”直接针对亿万国民,用纳税人的血汗豢养着海量网警,监控国民的一言一行,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而动辄停号封号,大面积封群,甚至动用治安武力,导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审查之际,为可能降临的莫名处罚担忧。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讨论的思想生机,也扼杀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社会传播与预警机制。
由此,“基于法西斯主义的军功僭主政治”渐次成型,却又日益表现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其非结构性与解结构性。职是之故,不难理解,面对大疫,无所不能的极权统治在赳赳君临一切的同时,恰恰于国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见肘,制造大国一时间口罩难求。那江夏城内,鄂省全境,至今尚有无数未曾收治、求医无门、辗转哀嚎的患者,还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丧黄泉者,将此无所不能与一无所能,暴露得淋漓尽致。盖因排除社会与民间,斩断一切信息来源,只允许党媒宣传,这个国家永远是跛脚巨人,如果确为巨人的话。

附录
端传媒 |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发自香港2020-0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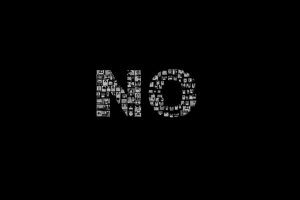
“我要言论自由”抗议运动中的部分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2月6日晚上11点,阿果和朋友在线上玩狼人杀,“预言家”发言时,突然说了一句:“为武汉受难的同胞默哀8秒钟。”直到退出游戏,阿果才知道——被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刚刚不治去世了。
阿果23岁,最好的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以一个摇滚乐队乐迷微信群为阵地。这个群有着鲜明的“反叛”色彩,平日除了聊音乐,也讨论公共事务,女权运动、计划生育政策、香港反修例运动,聊到炸群,又会在半小时内快速重组。
当晚,朋友们正在群里对李文亮的死亡表达悲伤和愤怒,李文亮的死讯却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中国新闻周刊》当晚11点56分发出即时新闻,指李文亮仍在抢救中,而一个小时之前,《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已经在微博确认了李文亮的死亡。一时之间,数以万千的中国网民都在求证:李文亮究竟已经去世、还是正在抢救?
“人已经死了,为了平民愤,又送进ICU。”一向激进的猫子在群里说。彼时,群里的活跃分子们已确认“要制造点浪花,不能就这么算了”。有人提议在口罩上写字,李文亮被迫在训诫书上写下了“能”和“明白”,他们要在口罩上写“不能,不明白”来悼念他。
阿果记得,只有一个人提出反对,他说:李文亮是否已经去世还不清楚,就算他死了,也不应该做这样的行动,有消费死者的嫌疑。猫子记得,那个人还说,为了平息民愤而对李文亮进行“表演式”抢救是很不人道,但若不是他们这么愤怒,政府也不会这么做。
“李医生的死,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多默回应道。相比多默,群里其他人对反对者的回应就没那么客气了,后者被骂急了,连续刷了五、六条消息:有本事你们上街啊?你们敢上街吗?我明天上街,有没有人敢和我一起去?
如今回看,群里的一些成员认为,可能是密集出现的“上街”引起了网警关注,才有了后来的集体“喝茶”。尽管发言者已被群主踢出,但他恼羞之下提出的问题——“你们敢上街吗”则变成了一个不时浮现、难以面对的困境——对它的理解,成为行动者之间最重要的分歧。

2020年2月7日,武汉医院后湖分院外,一名男子在鲜花面前鞠躬,纪念已故的眼科医生李文亮。 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母亲和他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由父亲拍照
23岁的猫子是从乐迷微信群得知李文亮死讯的,尽管他家就在武汉汉口,距离李文亮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只有几公里远。
“中心医院离我家很近,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会经过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去世了。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边时,你唯一的判断是,感觉很不舒服,应该做点什么。”
武汉封城之后,猫子一直待在家里,看书、打游戏、跟女朋友打电话、煲汤,也看到大量的病人求助信息。尽管身处疫情的起始点,但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病人,他并不比外界知道得更多。
母亲有很多朋友都确诊了,她会在饭桌上分享一些新闻上没有的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他有一个阿姨出现了症状,迟迟未能确诊,绝望之中向他母亲倾诉:“就这样让我去死吧。”猫子听到语音,难受了很久。
家里找不到纸笔,猫子临时用一支毛笔,在餐巾纸上写下口号,举在手上,请母亲给他拍照。最后的照片,是母亲和他各自戴着口罩,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由父亲拍摄而成。
母亲的加入让猫子有些意外:“如果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官方抓捕,我妈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李文亮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一个医生,因为一种朴素的道德感而说了两句真话,但连这种道德感都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她决定加入我。”
与此同时,从“狼人杀”游戏中下线的阿果陷入了疫情以来的第三次崩溃。
他住在湖北孝感一个小镇,湖北封省后,阿果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游戏世界里,偶尔往现实世界望一眼。除夕夜,阿果一直在转发微博上的求助信息,“特别灰暗,到处是人间惨剧。”他说,当晚看到新浪微博还在删求助帖,怒火中烧,发了一条朋友圈诅咒删帖员;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建议最高领导人在春节晚会上给大家磕头谢罪。激烈的言论引来一位公务员朋友的惊诧,阿果后来删掉朋友圈,他说,一方面是有风险,另一方面也觉得似乎不能完全怪那一个人。
另一次情绪爆发是1月31日晚上,《人民日报》转发报道,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小镇里很多人连夜去药店排队购买,阿果难受无比:“(他们)现在还在想利益。”
大二时,作为“一个普普通通大学的化学系学生”,阿果对前途感到迷茫,开始看西方哲学,思考一些大问题——宇宙的起点、自由意志、绝对精神、人的存在。康德一度很鼓舞他,人是自由的,世界是有目的的。
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也让他在公共议题上具备反思能力。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举报班主任之父性侵事件时,他也很气愤地在微博上声援。而中学时期,阿果还是一个会在钓鱼岛问题上发“虽远必诛”的人。
夜里一点多,阿果删了游戏,一边抽烟,一边听难受的音乐,找到一张白纸,写下“不自由,毋宁死”,举在手上自拍,但是效果不好。郁结之中,他又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血债血偿,天灾不等于人祸。”他打算第二天把这句写在纸上,拍照。

2020年2月8日,台北的民众悼念李文亮医生。摄:陈焯煇/端传媒
此前不久,四川宜宾的多默告诉母亲李文亮去世的消息,母亲没什么反应,尽管在意料之中,多默还是有些失望。
多默1月底就知道了李文亮的事。“他是法律上没罪,但是在政治上却被宣告有罪的人。”除夕夜,压抑之中,多默写了一段话:“我想,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救赎与希望,多年来臣服于红色的旗帜与信仰,我的过去与未来,似乎早已经注定。”
中学时,多默在学校门口看见几十个人追着一个人打,警察过了很久才过来,也只是站在一旁劝阻。这种恃强凌弱的暴力,在县城是家常便饭。另一种暴力更隐秘,家族里有一些亲戚在政府中工作,多默从小就看到许多腐败和寻租,甚至是间接的获益者。
“这个国家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好。”他在中学时期就意识到这一点。那时他开始听崔健、罗大佑、李志的音乐,顺着他们的歌曲关注历史和政治事件。反右、文革、六四、雨伞、太阳花、反修例……他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公民必须要铭记的,多默还相信一句话——“政府始终是为公民所服务的。”
在疫情进入普通民众视野前,多默就觉察到了不对劲。他是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从新闻上看到一个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新病毒被发现时,就断定情况会很严重。他提醒老家的朋友注意防疫,批评政府隐瞒消息,遭到朋友攻击。“他们说,我是为了反对政府而说出这些话,是一个恶意抨击政府的人。”
自去年6月香港反修例运动开始,这样的对话就频繁发生,多默一度希望能以政治常识和逻辑讨论香港人的抗争,但大部分同学和朋友听不得与官媒不同的言论,多默因此和很多朋友决裂。
凌晨四点,多默在一张A4纸上写下“不能,不明白”,遮住鼻子以下的部分,拍了一张照。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对李文亮的平反,是他作为公民的义务。
不过,对另一位参与者麦快乐来说,仅仅为李文亮平反,是不够的。
“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
“在口罩上写下如‘言论自由’的字样,可以的话,再在一张纸上写下更多的诉求,然后戴上口罩,举起诉求,拍照传播以抗议。”倡议者没有解释为什么要以“言论自由”作为诉求,不过不少参与者认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场悲剧的起点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麦快乐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让他们意识到“因言获罪”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如果当时(政府)不是训诫他们,而是采取其他防疫措施,可能就不会这样,希望更多人意识到疫情不是一个天灾。”
跟其他人不同,麦快乐加入乐迷微信群的时间并不长,也不常参与讨论。李文亮去世时,她在重庆,引起她注意的是微博的超级话题“我们要言论自由”——一个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话题,却意外收获了286万人次阅读、9684条讨论。
麦快乐看见各种立场的人、包括小粉红都很愤怒,感到莫名激动,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见革命的曙光了吗?”看见乐迷群在讨论行动,麦快乐决定加入。麦快乐在群里小有名气,她立场比较激进,在此时加入,也让阿果觉得很是激励。
正在读大学的麦快乐自认是“勇武派”,2019年女生节(一个发源于高校的节日,比3月8日妇女节提前一天)期间,她用打火机把学校里两条写着“与你契约终身 对你爱由心证”、“一切不服务女性的侦查行为都是不规范的”的横幅点燃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支持她,也有人认为纵火太过极端。麦快乐被辅导员批评后发了一个声明:“放火的确欠缺安全考虑,向学校道歉。我应该用剪刀来着。”

2020年2月8日,北京通惠河畔,市民前来悼念李文亮。摄:Sophie Wu
疫情发生之后,麦快乐一直过得很糟糕。除夕那天她和家人从重庆县城去了市区,在亲戚家过年,电视里播着春节联欢晚会。麦快乐觉得,“联欢”两个字已够糟了,更坏的是还有诗歌朗诵,白岩松和康辉深情款款地喊出“我们爱你们”、“众志成城”,对照她在网上刷到的求助信息、武汉朋友发来的情况,让她觉得很荒诞,而与此同时,家里其他人正在如常喝茶聊天。“那么多个人,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
麦快乐在口罩写着“不能,不明白”,手举着纸片:“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只有一种声音。”又补充了一句:“把言论自由还给我们!”
凌晨两点多,乐迷群的管理员阿北“爬楼”看完所有信息,他开始不自觉地想到一些具体场景:李文亮的尸体是不是安全,会不会被迅速火化;这个医生去世前有没有留下遗言嘱托;去世前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派出所训诫的场景……
第二天早上,家住长春的阿北跑到一个结冰的湖上,在雪地里写了一个“不”字,因为太冷,后面的“能,不明白”没有写下去。“不”字似乎也足够了,他想起自己曾经喜欢过的NO乐队,写过一些忧郁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下午四点,阿北把群里其他人拍的抗议照片,编辑了一条公众号文章,写了一段文字:“最近的事,尤其是他的离开,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我们所处的困境,我们面临的遭遇,这些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没法以嬉笑的姿态去面对,没法继续用潇洒的表达去阐释,因为要直面的是淋漓的血和真的人性。”
这条推送一直没能通过微信的人工审核。就在当天早上,阿果删掉了朋友圈那句“血债血偿”,“老实说,我确实是害怕了。”而麦快乐发在微博上的照片,被很多网民骂“废青”,随后被微博管理员删除。
“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秋后算帐很快来临。抗议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传播,又很快被删除。四、五天后,身在国外的群主接到警察电话,质问他们是不是在煽动什么;一个群管理员被警察和国保开车上门带走两次,她不再敢跟群友联络,怕牵连他们……不仅参与抗议行动的人被警察约谈,群里一些没有参与行动,也不曾在讨论期间发言的人也被警察找上门。
风雨之中,阿果和另外几个人在群里劝告:如果担心承担风险的人可以先退群。很快有几十个人退出。猫子很不满:“国家都什么样了,还不反抗吗?”他觉得行动已经有一些进展,应该再做点什么。他预演了被警察约谈的一幕,如果警察要看他手机,他会坚决拒绝。
“如果机会允许我一定会上街游行的,我可能不会是第一个人,但是如果前面已经有了一千个人,我一定会是第一千零一个人。”猫子说。对于行动中的风险,他觉得不是愿不愿意承担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承担。他谈起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正是上一代人不愿意承担风险,才把风险转移到了这一代人。”
阿果并不太认可猫子的激愤,“如果你被警察找了,你拒绝了交出手机,你可以说,但是你还没有被找,你这样轻飘飘地要别人反抗,是一种胁迫。”
阿果没有把话说出口,泼冷水的是另一个叫橡树的群友,他觉得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反对继续行动:“你们冒得起这个风险吗?”猫子回应:“那要不听话好了,听法西斯的话。”
“你们知道什么叫革命吗,你们知道什么叫法西斯吗,这个事情很危险,没想的那么简单,不要有什么妄想!”橡树说。
群里只有麦快乐冷冷地回应:“跪着还要搞革命。”这句话反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抗议的照片被传播到了墙外,被CNN和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黄耀明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些照片。但是麦快乐对行动仍有一些失望,她觉得“言论自由”的诉求被模糊掉了,许多人用的口号是“不能,不明白”,尽管其中也有要言论自由的意思,但是不够明确。
女生节烧横幅的事情对她来说是第二次政治启蒙,“一开始确实是一时冲动,后来整个事情的反响对我的影响也还挺大的,我那时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要发声之外,行动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李文亮去世第二天,国家监察委员会宣布派出调查组到武汉,全面调查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很多人的愤怒就平息了。“他们不生气了这件事情更加让我生气。”
在微信群吵架的时候,麦快乐一度萌生了退意:“大家都是年轻人,家境也比较好,可能现在喜欢摇滚乐,愿意去反抗,但是当这个体制不停打磨你,你可能就不一定愿意做了。”而对她来说,行动只有一个目的,让这个体制发生一些改变。而如果不愿意承担风险,改变一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手绘。图片来自网络
尾声
警察打电话到阿北家时,他已经离开长春去了上海。他把电话和住址通过家里人给了警方,等待他们上门。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比生命还要宝贵,你要怎么去面对那些事情。”阿北说,这是他决定对外说话的原因。
不过,他不得不解散微信群,把几百个人一个一个踢掉。这个群过去“炸”过不下10次,每次炸群,他都会发起位置共享,那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转移到下一个群。而这次没有下一个微信群了,一个管理员被叫到派出所约谈时发来消息,群里有人举报。他们中有些人转移到了Telegram,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有些人则不愿意再参与了。
多默有些后悔,他过年前和母亲出门去采购年货,母亲极有可能是那次被感染了。她咳嗽,发烧,CT显示肺部发炎。但是在四川宜宾县城,没有条件做核酸检测,无法确诊。
他记忆中,每个冬天都是在抑郁中度过的。今年,除了突然爆发的疫情,个人的生活也难以掌控。他用吸烟量来计算自己的忧愁程度,这几个月来,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在自己才看得到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生来便是长夜的子民。”
阿果则已平复了心情,回到谈恋爱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坚持说,某种形式的反抗一定会继续的,这是他赖以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阿北整理了抗议行动中出现的所有照片,大概有150张。麦快乐联系了记者,她觉得记录下这一切也是一种行动。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