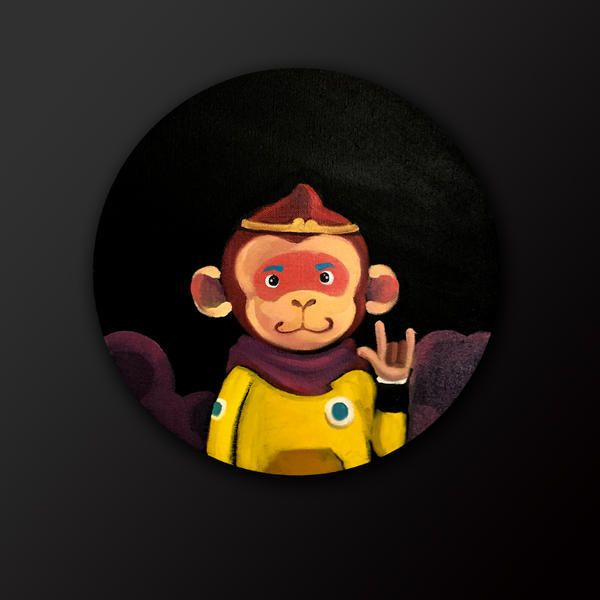
信奉女权 | 法学民工 | 爱好社科 | 左棍右狗 | ENFP♌ twitter: @NancyYunTang
「第三话♣3」关于梁庄的对话
欢迎关注我和@田园 的微信公众号跳跃的汤圆(微信号:jumpingriceball)

【2020.5.4 庚子·四月十三 — 2020.5.10 庚子·四月十九】
阿汤:
我写这篇读后感其实内心是有些惶恐的,感觉自己并没有资格讨论在中国的“梁庄”,或者是梁庄所代表的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父母也都是城/镇出身的人,我绞尽脑汁能想到的有关“农村”的记忆,来自于童年去拜访我的舅爷爷(我妈的舅舅)一家。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深入到文本之中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环境、教育中,“农村”始终是他者;作为《中国在梁庄》的读者,我的惶恐或许也来源于我的“他者”身份——我没有经历过农村,我没有和农村的直接联系,我有什么资格来对梁鸿笔下个体与集体的生命体验,产生反应?
阿圆,你问,我对哪个人物印象深刻。我觉得很多:梁鸿家族的男性们,从她爷爷、父亲,到哥哥毅志;梁鸿笔触下经历各异的女性们,自杀的春梅、挣扎于“理想”的菊秀,为被性侵的老母亲讨公道(且公道理解为死刑)的二婶,等等。这其中,作为对性别敏感的读者我,也会思考农村秩序中的性别关系与性别(不)平等。在咱俩的交谈中,我们母亲的经历体现了性别和阶级交叉的复杂性,走出老家的女性,是如何在宗族中获得了超越传统的地位(“上桌吃饭的姑奶奶”vs“不能上桌吃饭的儿媳妇”);但无论如何,女性并不能够拥有地方上、政治性的权力(无法想象出女性的村支书),对于上一代来说,更是有女性无法接受教育、而“男孩必须读书”的秩序。
另一个我想讨论的议题,是关于“教育”。曾经,教育(以及“高考”)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渠道,“读书好”是“有出息”的近义词。但为什么90年代及之后,这样的关联在被削弱?这仅仅是因为大学教育的贬值么?还是说中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已经没救了?(同时,农村和城市,为什么就一定要map on到阶级的高低?)
梁鸿在后记中,也在纠结她自身与故乡的关系。你怎么觉得呢?你和农村的关系如何?“农村”对于你的身份认同,又是什么的角色呢?
———————∞ ∞ ∞ ∞ ∞ ∞———————
阿圆:
由于父母都是中原农村长大的,我和农村的关系可能比你更近。梁鸿笔下的梁庄,跟我听父母讲的或是自己回老家见到的,有七八分重合——一样满是黄土和脏污的环境,一样空气里都是霉味的茅草老屋,一样贫穷、饥饿的成长,甚至一样的传统和人情逐渐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我和农村的距离甚至可能比你更远。虽然父母从农村出来,且他们的家人还有不少在老家,但从小到大每次回老家给我带来的不适感,以及面对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的恐慌,甚至让我曾经对农村有种刻意的疏离;这主要体现在比如回到老家后不和人说话,不碰东西,或者在自己亲戚来访时沉默地躲在一旁。这种现象,一直到成年后才有所缓解。
再说阶级。你问农村和城市为何要map到阶级高低,我想这不是个normative question, 而是客观上阶级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等同于农村和城市的二分。由于历史原因,农民承受了十几年动乱的所有代价,一贫如洗了太久,再加上户口制度,让阶级区分被制度化,更加顽固。除了经济上和制度上,农民在社会层面也备受歧视。在很多人眼里,农村就是穷,脏,愚昧,甚至“刁”的某种混合。转念一想,梁鸿笔下的梁庄难道不是如此吗?在写光河儿女双亡的那章里,梁鸿写道,“那一阵子,一堆人围在光河家里出主意,一是同情,还有一个,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呢,想着万一要得多了,说不定还能借来一点。” 如果我没有亲眼见过丧事时乡村的人情往来,恐怕很难想象,人们居然能在一个儿女刚刚双亡的邻居面前还能打小九九,想着弄点钱。但同时,这也让人认识到,“善良”和“仁厚”不止是种美德,也许更是种特权。不知你看了书后,对这个观察认不认同?
你还说到教育。90年代及以后,教育作为改变阶级的出路,明显在衰弱。阶级固化到了经济现代化的这个阶段似乎不可避免。我们父母那一辈,总体贫乏的资源只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上,一贫如洗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从一潭死水突然有了生机,于是给了一些农村出来的学生利用求学走出农村的机会。而现在,不再极度匮乏的资源更“分散”了——终于有多余一半的人口进入了城市,其中不乏以艰苦或危险的劳动养活农村里一家的工人和小商贩。同时,城市和农村的阶级壁垒也无疑在加固——好大学里农村小孩的比例越来越少,而农村小孩即使上了大学出来,由于大学学位的贬值,能靠自己找到工作的也是凤毛麟角。就像梁鸿写的,家里的孩子不再认为读书是出路,而更倾向于早早出去打工,还能赚点快钱。我想这也算是一个社会飞速工业化/资本化/现代化的某种必然结果。以钱为中心的新秩序迅速代替以传统/知识为中心的旧秩序,造成了某种别扭的错位。由于城市本来就是资本化的产物,这种错位在城市不太明显,在梁庄这样的村庄则尤为深刻。对于富有vs传统瓦解的这个tradeoff,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有办法避免吗?
最后说说一个我的个人感受:农村的沉默。在“穷”、“脏”、“愚昧”、“刁“这些外部印象之上,这书里写的(和农村给我的)另一大印象是沉默。从微观说,是能“忍”。从宏观上说,是难以想象的“失语”。梁鸿笔下的梁庄人,无论苦到什么程度,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很多时候让你直呼“人是怎么能在这种境况里活下去的”。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苦难又似乎毫无知觉;或许是有过知觉的,但表面上总是波澜不惊,最后要么强烈爆发(例如由于性和情感压抑自杀的春梅,以及奸杀老太的留守少年),要么沉淀为人生灰黄的底色(例如一直受挫郁郁寡欢的菊秀,儿女双亡的光河。)宏观上的“失语”更不必说——在这个21世纪的信息社会,我们每天翻开手机、电视,甚至书,读到的几乎全是在一小部分城市人之间流传的内容。有的说生活幸福,有的说世界药丸,有的说大家都药丸。然而无论哪种观点,似乎都这个国家的一小半人口毫无关系——他们可能没有固定的家,一年都见不到一次小孩,或者作为女性在家种地,供哥哥弟弟上学。这种失语,才是更让人绝望的。
不过另一方面,梁鸿写这本书是在00年代,我上次回老家也是好几年前了。上次回去的时候,爷爷奶奶早已搬进了县城,每人还配了一辆小电动车,过得还算富裕。对于很多农村人来说,过去的贫困已经过去,饿死的亲人已经饿死。褪去可以被搁置的底色,现在能住上二层小洋楼就是幸福生活。同时,城市中和城乡间依然存在的巨大阶级鸿沟似乎在造成新的困境。不过和穷相比,一切也许真的是在变好吧。

阿汤:
阿圆,你写道:“‘善良’和‘仁厚’不止是种美德,也许更是种特权”——这句话震到我了。
我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同意,是因为我买账马斯洛,总觉得人的需求是金字塔形态的。我妈曾经半开玩笑说,搞革命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不无道理。在经济基础达不到某条线时,或许我们以为普世的“善良”与“仁厚”的根本就不普世。
但部分不同意,是因为相信性善论的我,总觉得“屁股决定脑袋”,是不负责任的、只说了半句的道理。梁鸿描述的有一个细节打动了我:wg期间,她父亲被批斗时,是因为“一个老太太经验性的一句话”,也就是立娃儿他妈的善良,被解救的。人类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我总觉得是相通的;只是“农村”作为背景的故事,远不符合人口比例。(昨晚,我还被“only privileged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think about big questions, like what constitutes a good life”。之前好像读到过有关美国的社会调查,其实低收入人群中抑郁症患者比例很高、对优质心理咨询需求大,但这不影响我们把心理疾病归类为“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也许,我相信人类的共同点,超于其差异;也许是基于此,梁鸿笔下的“青年”,他们关于爱情、理想、意义的挣扎,我私自觉得我能感同身受。
你总结的“农村的沉默”这点很精确。咱们前一阵读福柯,不还讨论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么;在咱们这个资本至上、娱乐至死的社会里,“信息”与“讲述”大概就是“知识”的体现形式:谁有权说话,谁能说得出话,谁说话会被倾听?也许针对你所描述的“失语”,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做点什么。梁鸿在她的写作中,就在抵御这种失语(包括她采取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我个人对乡政府-村支书-村民的政治关系充满了好奇:为什么梁庄不是乌~镇?什么时候,老百姓可以用政治权利,发出声音?
这么一来,你我好似都是乐观主义者,没有彻底绝望。你问我如何看待“富有”和“传统瓦解”间的联系。我去南非时,最受震动的就是对“文化”二字的重新审视。文化总在流动,文化也总有主体、总有讲述者。当欧洲殖民者踏上非洲南部时,他们得到的“customary law”都是部落首领(一群老直男)的解释,而文化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语的;殖民者之后又用“落后”的滤镜叙述了历史。而近些年来,有性别意识的非洲学者、或女权法学家们,在思考如何重新定义理解所谓的“习俗”与“文化”。我觉得“富有”有绝对意义上的好,比如可以起码让“善良”与“仁厚”变得普世;但“富有”好似也有相对意义上的不好,是资本秩序取代传统宗族文化后,一种恍惚的空虚。但当我最乐观的时候,我心中的“传统”与“文化”都丰富、多层次——我希望女德这样的传统能够彻底被消灭,也希望对知识与教育的尊重,能被重建(哪怕这种尊重曾是科举制与高考的产物)。我感激梁鸿的讲述,健忘的时代需要更多的记录;我多希望所有失语的他她他们她们,能够讲述痛楚欢乐,分享经验教训。或许,我始终相信“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只是估计这个词和我小时候理解的,定义不同吧。
你又会怎么回答这个tradeoff的问题呢?我好像避开了阶级固化的问题——你觉得壁垒可能打破么?
———————∞ ∞ ∞ ∞ ∞ ∞———————
阿圆:
阿汤,心理疾病作为“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这个说法很有趣。梁鸿写的梁庄人中,有几个没有心理疾病的?恐怕很少。但由于农民们普遍缺乏这一套有关心理卫生的知识或者语汇(又cue福柯),在农村似乎没人会觉得心理的问题需要治疗,直到它严重到无法治疗。
你说梁鸿笔下的“青年”关于爱情、理想、意义的挣扎,可以感同身受,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本书我最喜欢的人物大概就是梁鸿她哥,那个四处闯荡,差点在收容所被打死,转身又在日记里品鉴《废都》,感叹“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却感觉是千里之遥”的文艺青年。我最心疼的,大概是梁鸿的少年闺蜜菊秀,一直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向往美好、自由、独立,却似乎被生活推向另一个方向,以至于感叹“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在他们的身上,我朦胧中可以看到身边亲近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影子。
而另一方面,你说这佐证了“人类的共同点,超于其差异”,我一半同意一半保留。一方面,人性的大部分好像的确是共通的——欲望,理想,激情,计算,等等。但转念一想,我们之所以更能对菊秀和毅志这些梁庄青年的经历感同身受,或许不止是因为人性的共通,更是因为语汇的共通。你看,他们谈论的概念,关心的东西,用以构筑对生活的理解的话语,跟我们的其实很贴近。而书里的其它人,比如始终沉默的志光,信主的灵兰,砍伤村官之后就刀不离身的清立,他们的经历虽然让人哀叹,但却没有那么强的代入感。或许他们的人性与我们的人性并不比菊秀们与我们的差别更大,只不过他们的话语体系跟我们不同,造成我们无法合理化他们的种种经历和行径(当然,另一方面,这些人在书里大都是通过第三人讲述的;这也反映了或许他们和梁鸿本人的语汇的差异也已经大到无法向她亲自叙述经历了。)
所以,或许关于人性的问题其实是关于语汇/知识的问题?这也跟你提到的“流动的文化”有呼应——如今,我们的“文化”对应着某一套较为普世的语汇,它也塑造者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然而,当我们或者梁鸿面对被排除在这套普世语汇边缘或之外的人,互相理解交流,甚至承认,似乎变得极为困难。于是,除非这套语汇能渗透到最难渗透的地方,或许有一些人会继续“失语”:即使说了,也不被理解。
关于物质和传统的tradeoff,我觉得如果它不可避免,那么一定是先保证物质要紧。所以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似乎不乐观都不行。另一方面,在那么多人先富起来,且那么富的今天,我们很难接受还有人在挨饿,更难接受还有法律在助长这种差别,更更难接受大部分人对此视而不见或噤口不言或顾左右而言他。对于壁垒的打破,我不是很乐观。虽然我们的确知道绝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会越来越好,但大多数人都衣食无忧或许同时意味着小部分人的忧虑更难造就变革。更进一步,如果被排除在经济成果外的人同时也被排除在狭义的政治对话和广义的话语体系之外,任何乐观的判断都很难令人信服。
哎呀,越写越丧,就此打住!
———————∞ ∞ ∞ ∞ ∞ ∞———————
阿汤:
阿圆:也许是这一年和所谓的“行动者”(organizer/activist)混迹比以往都多(也估计比以后都多),我又读了咱俩写得,会想: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有什么是可以行动的呢?
我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隐约感觉,关于“农村”的认识,我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而“语汇的共通”,大概也需要更久的修行(和可能的放弃与认输)。也许有一天我会拾起《出梁庄记》,也许终有一天我找到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资源,也许有一天我终将有机会去到想象中/现实里的村落,哪怕时过境迁、哪怕现代化把农村彻底抛在过去——也许有一天,我和“农村”,终将不是彼此的他者。
【2020.4.20 庚子·三月廿八 - 2021.4.18 辛丑·三月初七】
欢迎加入我的闲书之旅,欢迎转发,鼓励,督促。

敬请期待·forthcoming
「第四话♣4」 Minor Feelings: 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
by Cathy Park Hong, 2020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