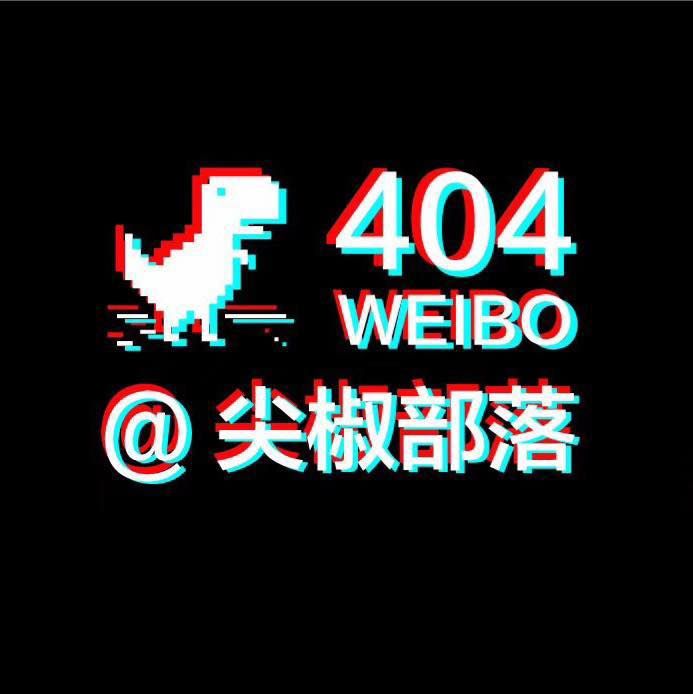
此處收錄了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台--尖椒部落--在七年中發布的女工原創作品精選。她們通過作品展示了各自人生路途中的思考、心境、掙扎和探索,以及在彼此的經驗中獲得的啟發、連結和印證。 尖椒部落雖已退出歷史舞台,女工的創作卻不會止步。 完整網站內容請見: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715122223/http://www.jianjiaobuluo.com/
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暴力:天罗地网,无路可逃?【同样为生计奔波,我们并无分别01】
“我的血顺着刀锋往下流”
“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这是著名学者潘绥铭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可以每周 1~2次发现“小姐”被杀的新闻,而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数十名最底层“小姐”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被抢、被强奸的经历。
为了偿还债务来到东莞的英仔,第一次站街,就遭受了严重的暴力袭击。

2008年3月18日凌晨,英仔被“客人”的面包车带到偏僻地点。接受性服务后,“客人”凶相毕露,用菜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进行搜身,从鞋垫里搜走了400元现金。之后,男人用刀划开她的脸颊,“我的血顺着刀锋往下流去,明晃晃的西瓜刀变成了红色。”那道刀疤今天仍然留在她脸上,10多厘米长,形同蚯蚓。
直到英仔主动把自己的小灵通交出来,才被一脚踢下车。“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男子曾这样威胁。
英仔记住了车牌号并准备报警,却被同行的“姐妹”园园劝阻:“我们是公安局打击的对象,去报警不是自投罗网吗?”
园园的脖子上同样有一条伤疤,大约15厘米长。那也是一次交易后,她遭到抢劫并割喉,险些丧命。“其实每个月我都会遇到抢劫,只是没有她损失那么大。”园园说很少带钱出门,就算带也都在20块钱以下。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过来抢劫——抢她们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哪怕将她们杀死。
大多数站街女都有着各种各样伤疤。“我们抓住过几个站街女,她们身上伤痕累累,连屁股上都被烟头烫过。”一个经常在这里执勤的治安队员说。
很多人都有在从业过程中遭到抢劫后虐待的经历。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深圳,两名“小姐”在出台时遭遇抢劫,之后脸上被刺青“妓女一号”。

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受到伤害,也几乎没有“小姐”敢报案。
潘绥铭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赵军曾有12年从警经历,他表示:“小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很容易被接近,交易对象具有流动性和不特定的特点,并且被侵害后报案率很低,因此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目标人群。
“小姐遭到不法侵害,理论上应寻求警察的帮助;另一方面,警察又对她们所从事的性工作进行查处,这是矛盾的。”
性工作者讲述狱警暴力和劳教生活
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废除,然而收容教育制度依然存在。该制度是一个不需要通过审判就可以直接将性工作者关押半年到两年的非法拘禁制度。
被“收容教育”的性工作者通常会被要求在车间里干苦工,一周工作七天,没有报酬,生产玩具、一次性筷子和狗尿片。
中国有200个收容教育所,一些曾经进过收容教育所的妇女们描述了里面昂贵的收费和狱警对她们实施的暴力。
在北京,一位叫李正果(音译)的女性性工作者讲述了自己对“警察上门”的恐惧。上一次被带到一个当地公安局之后,没有经过审理,没有律师为她代理,就被送到了附近河北省的一个收容中心。她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每天制作装饰用的纸花,或者背诵禁止卖淫的法律条文。

在她离开邯郸收容教育所的时候,又一件令她气愤的事发生了:她需要向监狱交纳每月大约300多元的生活费。
“下一次如果警察要带我走,我就割腕。”
中国政府未公布有关收容教育制度的数据,但是专家估计,每年有1.8万至2.8万名女性被送进收容所。亚洲促进会的报告显示,被收容者需要自己承担食物、体检、寝具以及香皂和卫生巾等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大多数妇女在六个月的收容期间会花费人民币大约2400元。
“所内的物价是外面的三到五倍。有些没有钱的性工作者只能通过替其他人按摩捏腿换卫生巾,两小时换一片。”
据妇女维权志愿者赵思乐所说,跟性工作相关的压迫非常明确地指向女性。尽管收容教育制度也针对嫖客,但他们向警察交付罚金就可以逃避处罚,并且江苏、福建等几个省的收容教育所明确说不收容教育男性。而性工作者,尤其是底层性工作者难以往往支付高额罚金,也不敢向家人求助。
民间女权人士叶海燕曾经也是一位性工作者,她说,收容教育制度其中的权力寻租空间是很大的,有时候需要用大量的金钱换取自由。
“十元店(即“一次十元”的意思)有一个姐姐被抓,贵州的一个大姐。被家里知道了,她们想找关系,刚开始说八千解决,到处借钱,后来又变成一万四千,最后是一万六千。”
2014年4月4日,赵思乐发出320份收容教育信息公开申请,9月9日,赵思乐委托律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广东省公安厅,这是国内首例关于收容教育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然而最终败诉。

“他们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制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家人吗?”赵思乐曾愤怒地表示。
即使免于被拘捕或强制收容,“小姐”们也可能受到来自警察的暴力对待。
4月6日凌晨,《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目击了东莞南城公安分局治安队员毒打“小姐”的一幕。“你们这种贱人?!”4个治安员用警棍狠狠抽一个自称阿红的女孩,“我就打你了,有本事跳河去?!”
“这些人就得狠狠地打!”一位治安队员说。
同时警察的执法也给她们带来疾病的风险——根据安全套判定卖淫嫖娼,这使得部分性交易场所不敢提供安全套,增加了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可能。
生命权高于“社会风化”
中国一份关于70年代出生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性工作者调查显示,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有更大经济压力,她们通常是原生家庭与婚后家庭的经济支柱。抚养孩子、赡养父母、买房等一系列生活压力都压在她们肩上。
由于农村传统社会性别偏见的影响,在学历、工作和婚姻自主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同时在家庭照顾、养儿扶老方面肩负更多压力,导致她们整体处于结构性弱势。
底层女性同时承受阶级和父权的压迫,在家庭贫困、缺乏情感支持时,劳动权益还受损,并且缺乏社会保障,其中一部分迫于压力进入性行业。
正是由于这些困境,很多底层性工作者即使遭受如此巨大的风险也不会转行“上岸”,也有的尝试去其他行业工作,但大部分最终又回到了性行业里来。

“底层女性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性工作者是不是一群想要赚快钱、好逸恶劳的女性?”
赵思乐说,“这个问题有很多前提假设,但女性真的有那么多机会吗?女性面对的竞争环境是平等的吗?当我们考虑说要不要性工作消失,或者性工作会不会消失时,我们要先考虑环境。是否男女获得一样的教育资源?很多人都说女性的外貌是竞争优势,这其实是性别歧视,它意味着一个女性要上升,就要搭配使用自己的性资源。”
学者赵军表示:“生命权无疑高于“社会风化”,不管权利主体的身份如何。从这一点出发,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是完全合法的。我以为,这也是警方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应当向包括“小姐”在内的所有国民提供的一种涉及公共安全的服务产品。”
参考资料:
人民网《中国女性性工作者调查:暴力猛于艾滋病》
网易女人《中国性工作者讲述狱警暴力和劳教生活》
新媒体女性《叶海燕×赵思乐:如何证明我们是/不是性工作者?》
延伸阅读:
请尊重原创,保护版权
本文为尖椒部落整理,欢迎转载,但请保留本段文字:转载自中国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尖椒部落(jianjiaobuluo.com)。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