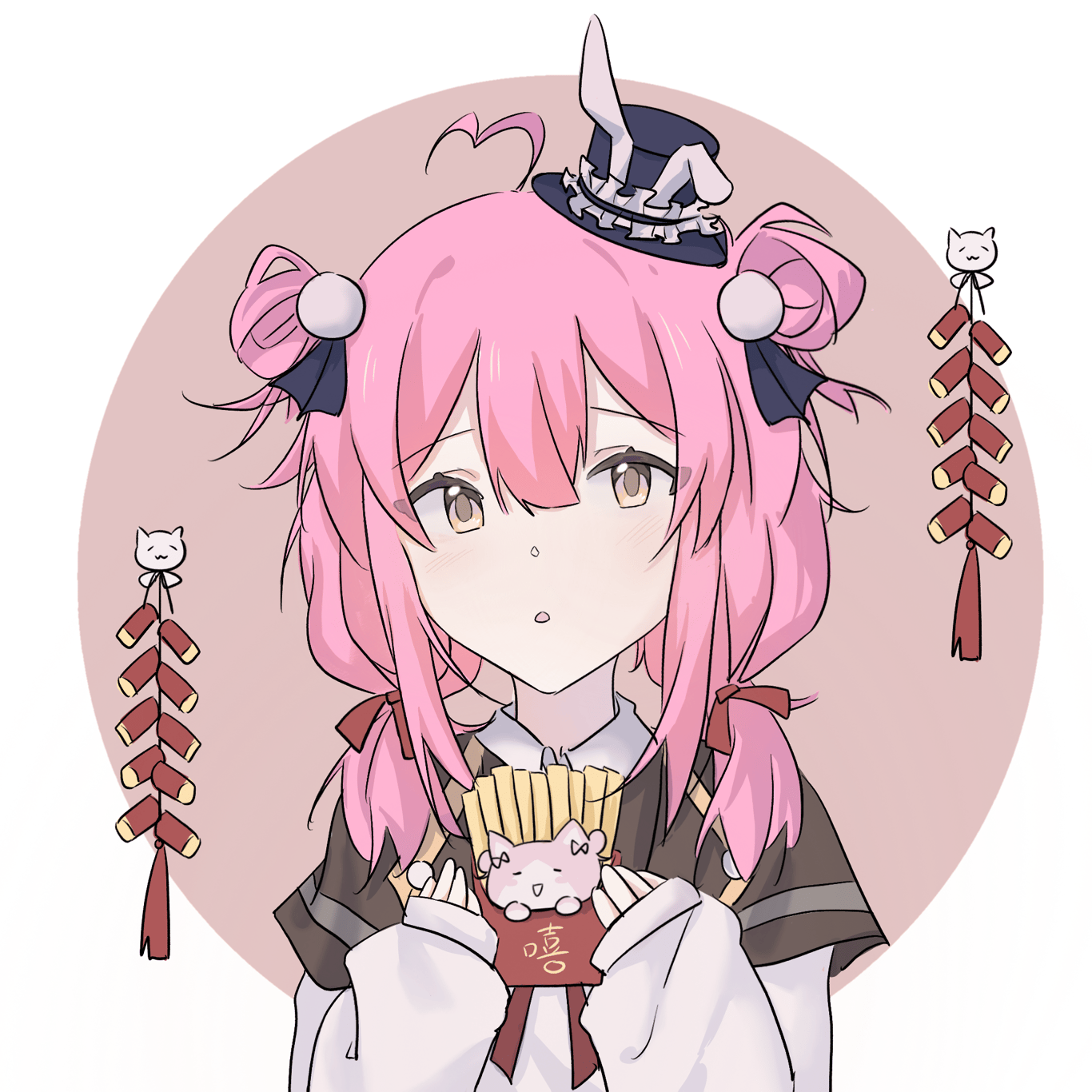
@realspadetaffy on twitter
以韦伯和霍布斯反对霍布斯: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摘要
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论人类的章节所言,推理不过是语词序列的加减,而学识也不过是不断通过推理获得的与那些语词相关的知识罢了。尽管放到现在,这个观点可能会显得质朴。但我们仍可以据此试着说:一个人的思想来源无非是其他人的思想的相加,比如我们可以说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来说,大家普遍都能同意霍布斯对其影响最大。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环境中,对其现实生成的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来自和他同一时代的人,此处我们谈论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本文我们将探讨施米特如何从霍布斯那里汲取政治的思维,并运用其受韦伯影响的现实政治观念之中。
韦伯和施米特
马克斯·韦伯其人一直以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称,然而其隐藏在忠实严谨的学者外表下的政治观点常常被人忽略。尽管韦伯在著作中并不掩饰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或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原则以及其所派生的官僚制度的赞许,然而,他也对此提出过多方面的批评。包括非常著名的“理性的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论,即随着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发展,人们会被束缚在名为理性的铁笼中,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只懂得效率,算计,并会被日益膨胀的官僚制所侵害,甚至个人自由都会处在官僚制的威胁下。
韦伯的论述固然有道理,然而并没有被其本人沿用到其对德国政治现状的批判中。在《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和政府》一文中,韦伯坚持了其对官僚制的批判,不过是以不同的角度切入的。这篇文章常被忽略,但笔者认为这是韦伯政治思想的最精华部分,所以在此处先给读者概括,提供阅读后面立论的背景。
在《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和政府》一文中,韦伯以对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政策的批判开始。他批评俾斯麦设计了一套庞大的官僚制度,其人又以铁腕手腕执掌权威,使得德国的政治凋敝,韦伯批评道:“…俾斯麦的遗产何在呢?他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素养的民族…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自身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做出必需的政治决策。”韦伯认为,一个官僚哪怕再专业,也不适合成为政治领袖。官僚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素养,无法期盼权力,更无法为了权力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此,韦伯将希望寄于议会制。事实上,韦伯终生都是议会制的支持者,在帝政时代就致力于对君主制的批判和对议会制度的支持。但韦伯对德国议会的状况并没有好话可说,他认为德国议会是一个消极的议会,原因是德国政府的权力并不对议会负责。帝国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时兼任联邦议会(Bundestag,上院)和帝国议会(Reichstag,下院)成员”。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部长或者首相绝对不会是帝国议会的议员。在韦伯看来,这样挑选出来的政治人物充其量只能是官僚,而不是政治家。哪怕一个在帝国议会里经验老道的议员,如果想要步入仕途,就必须离开议会,进入官僚系统,这样一来他的在议会里积累的政治素养也就被消解了。我们知道,在英格兰议会,执政党的内阁都是议会出身,反对党也时刻准备着影子内阁准备上台执政,在韦伯眼里这是积极的议会制,因为国家的权柄不光为议会所有,并且这套系统能够产生老道的政治家。而在德国,议会没有权力,皇帝则是出了名的无能且神经质。这一切,在韦伯看来,就是德意志帝国在政治方面的彻底失败。在此文中,他还探讨了德国政治的其他方面,不过对本文来说,以上这些已经足够了。
不了解韦伯的人由于韦伯对议会制的支持,通常认为韦伯是自由主义者。然而,韦伯支持议会制从来不是出于对自由或民主等信条的支持,韦伯对此并不在乎。可以看出,韦伯支持议会制的原因只有一个:议会制可以产生一个有能力的政治领袖;而他支持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的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信仰。总而言之,韦伯一直以来对“心怀超凡魅力(charismatic)素质”的政治家怀有企盼。在其著名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说到这里,我们想必已经能够看出韦伯和施米特政治思想的联系了。他们都反对过度扩张的官僚制和理性化,支持一个政治领袖来领导德国。不过施米特的思想要更进一步,除了他从霍布斯等政治哲学家汲取的灵感外,还有他对德国危机的不同认识。韦伯是以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视角看待一战后的德国危机的,即认为当下的重点是“重建德国”,用时髦点的话说就是“让德国再次伟大”;而在施米特那里则存在着一种危机感,他把德国的存亡当作一个时代性的话题,并以“挽救德国”的角度进行政治学的思考,或者化用施米特常用的概念,即挽救一个作为政治统一体(Politischen Einheit)的德国。他并不在乎德国形式上的政体,只在乎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德国不会陷入内战和分裂。
霍布斯主义的施米特
然而吊诡的是,素来支持议会制的韦伯在国民议会上为臭名昭著的魏玛宪法第48条---“帝国总统(Reichspräsident)有权宣布紧急状态,在此情形下拥有‘强制执行权’和‘独裁权’(大意)”---投了赞成票。虽然说韦伯支持政治领袖已经为我们所知,然而帝国总统的权力过大终究是不利于议会制度的。韦伯肯定也不是希望借此机会让麦克马洪式的人物当总统,因为他素来反对霍亨索伦王朝。我们无心探究韦伯这微妙的态度转变背后之原因,但毫无疑问,他的好学生施米特接过了这一棒,并据此发展了他根据德意志国的政治现实发展的主权(Sovereignty)学说。
关于主权,施米特最广为人知的论断是“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如果我们了解施米特对“人民制宪权”理论的支持,可以观察到背后的隐含信息:这个主权应当是在代表作为一体的人民,或者说经作为一体的人民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决断的,这个决断的一个常态结果是宪法(Verfassung),是维持政治统一体的秩序,而宪法中往往规定了主权者的权力,其中包括决断例外状态。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整体的人民将决断例外状态的权力授予了主权者。这一论断究其根本仍具有很重的霍布斯痕迹。霍布斯认为人们出于对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恐惧,订立了自然法来确保和平和契约的运行,为了确保自然法的实施,彼此签订契约共同让渡一部分权利给主权者。霍布斯认为,当主权者在保护人民免受战争这方面行使权力时,他拥有无穷的权力,而主权者又拥有宣战和宣布和平的权力,所以“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这一论断其实业已被霍布斯阐明,因为战争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例外状态。但是施米特也绝非简单地抄袭霍布斯的理论。政治理论自17世纪到20世纪最大的变化就是紧急状态的发明,这是一个处在战争与和平边界上的空间,其具体的生成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总而言之,这一模糊的边界概念的发明实际上扩大了主权的权力,使其能在和平时期运用战争的法度。那么从这个意义而言,施米特的论断的第二层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即“主权者就是决断什么是例外状态的人”,或者说“主权者就是决断什么情况才能算例外状态的人”。说得再清楚一点:主权者的权力所在就在于悬置“和平时期”的法律并颁布紧急状态法令,乃至于掌握最古老的“生杀大权”(vitae necisque potestas)的能力。
在《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中的第二论,施米特通过法学上驳斥了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的国家理论,阐释了主权决断的必要性,并且阐明了主权者的人格性。这一点施米特同样继承了霍布斯。霍布斯赞成主权者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因为他认为君主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结合得最紧密。施米特强调主权者的人格性,则更多是强调决断的紧迫和必要性。由此又可以联系到施米特对议会制度的批判。在《当代议会制度的思想史》状况一文中,施米特直接点名了韦伯,认为后者试图通过议会制选出一位政治领袖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在包括《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在内的许多文章中,施米特多次批判议会,乃至整个的政治系统都回避决断。施米特指责他们以商议为幌子避免决断时刻的来临,产生极端主义者篡夺政权分裂政治统一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施米特也希望他心目中的主权者,即帝国总统,成为宪法的保护者,此语词的意义,也即希望总统利用魏玛宪法提供的权力维持政治统一体的存续,因为如前文所言,宪法即维持政治统一体的秩序本身。
然而在历史上,德意志国总统并没有多么逃避这份权力。仅在1923年到1924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就援引了宪法第48条六十三次,而保罗·冯·兴登堡则在1932年一年就援引了该条目六十次。那么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动用决断的力量仍然没有挽救德意志国的权柄不被极端分子夺走呢?直到1932年,施米特还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一文中对德意志国的执政者们做最后的呼吁,通过政治决断来挽救德国,挽救宪法和总统制,等等。笔者认为,对此的答案可以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中找到。在此文中,施米特将政治定义为基于共同体利益的对敌人和朋友的划分。此处的敌人并非主权者的私敌,而是危害政治统一体存续的公敌(hostis)。施米特将这种决断置于相当高的地位:如果一个政治统一体无法决断敌人和朋友,那么它就会自行瓦解。尽管在施米特的原意里,此处的敌人更偏向外部敌人,然而在内部威胁到政治统一体存续的个人或团体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是敌人。不管怎么说,此处魏玛德国的领导人在决断上存在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他们虽然有能力掌握权力,但却拒绝使用它,也无法判断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我们可以拿艾伯特政府在卡普政变中的反应举个例子,艾伯特政府遇到自由军团政 变的第一反应不是号召工人组成城防卫队---这就是无法决断朋友---而是让诺斯克指挥国防军进行镇压。这就是无法决断敌人,国防军本质上同情自由军团,毕竟“国防军不打国防军”,然而艾伯特政府似乎是因为依赖军队的惯性,竟然在这种事情上找军队求助,这无异于自取灭亡。如果没有工人及时响应社民党政府的号召进行总罢工,威廉二世恐怕在 1922 年就重新成为德国皇帝了。
用霍布斯反对霍布斯
可以看到,施米特的决断论(Dezisionismus),以及其他的政治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即 是基于一种生存危机的反思。施米特写作的年代,魏玛政府几乎没有一刻喘息之机,随 时处在灭亡的边缘。这种处在生存与灭亡的夹缝使得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比起霍布斯更加 激进。虽然霍布斯写作的年代是英国内战,但当时查理一世已被处死,护国公成为英格兰唯一的主权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利维坦》一书的主题更偏向大乱后的反思,而施米特著作的背景则是呼吁当权者挽救魏玛政权和统一的德国。这一写作背景的 差异,也构成了二者主权学说根本的差异之一。
尽管施米特和霍布斯一样都支持以人格显现的主权者的决断,然而正如我们所说, 决断在施米特那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施米特将决断推至超然的,前理性的地位。施 米特在《政治的神学》中表示:“现代国家理论的一切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主权者和他的决断置于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正如施米特所言:法理学上的例外状态类似于神迹。例外状态是主权者作出决断的场合,正如神迹是神施展神力的场合一样。此处施米特的思路在于,让决断绕过迂回曲折的理性思索,使之成为即时的超然决断。因为理性思索的最终点始终是神学,或是其他形而上的东西。尽管霍布斯也阐明过这一点,但是他还是将主权和主权者的建构归于人们的理性和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由于主权的建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然法,身为主权者也必须屈居于自然法下。尽管在不违反自然律的情况下,主权者对几乎一切都有权利,并且可以发号施令,但是他不得逾越人们所交割他的那部分权力之外的事务,比如:人们的宗教信仰,个人事务,以及他们的生命本身。正是这微小的的私人空间,成为了撬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杠杆。事实证明,私人空间的发展最终挤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公共空间,政治最终越发地变成了商讨,扯皮和利益分赃的场域,最终,这个杠杆撬翻了绝对君主制,杀死了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一转变,也是 30 年代时随着国际霍布斯研究的进展所导致的施米特的转变。在 20 年代的著作中,施米特将霍布斯归于决断论的代表人物,根据霍布斯的“权威,而非真理制定法律” (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一句,施米特研究出了名为“霍布斯的结晶体”的权力结构,即权力是由超验的真理向下传递,通过把握真理的权威制定律法来庇护他的臣民。此处施米特的重心放在了人民对主权者的臣服以及主权者对臣民的庇护这一结构上,进一步强化了决断论的色彩。正是权威的决 断制定了法律,让那些本来互相攻击的人摆脱自然状态的孤独,可鄙和不幸。然而在 30年代,施米特开始逐渐注意到了霍布斯理论中的启发现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之前叙述的那一部分。 施米特在 30 年代对霍布斯的反思主要体现在《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象征的意义及其失败》一文中。除了谈及利维坦本身结构上的缺陷外,施米特还---如副标题所言---谈及了作为政治象征的利维坦。利维坦原是希伯来经典和圣经中的巨大海怪,但在霍布斯的书里,它是一个巨人,正如封面画展示的那样。利维坦在书中曾以活着的上帝,巨兽,巨人和巨型人造人的形象出现。但不论怎么样,霍布斯都强调了利维坦的生命性和人格性,哪怕是作为人造人的利维坦也是有主权者作为其操作者或灵魂的。然而随着技术化的时代的到来,国家越发地被视为纯粹的机器,其人格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提倡整体性的法学家当作独裁威权统治的象征加以驳斥。而面对着利维坦倒下的尸体,施米特以其为材料发展了自己的理想国。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一文中,施米特一改其他文章中的愤世嫉俗形象,大力称赞作为对立综合体(Complexio Oppositorum)的罗马教会:他认为罗马教会一方面作为普世教会(ecclesia Catholica)包容各种对立因素,另一方面有着神学-法律的理性架构,具有权威和代表原则。罗马教会的代表原则就来自于道成肉身的基督给予人的救赎,授予人的律法,并将权柄授予大门徒圣伯多禄这一事实。这已经呼应了我们谈到了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几个要素:自上而下的权威,形而上的主权根据,具有生命形式(基督的道成肉身)的利维坦,由权威(上帝)制定的法律;而作为对立综合体的天主教会,加上天主教的教宗永无谬误之教义,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的断言,即政治统一体为决断的统一,而非意见的统一。总而言之,一个(教理上的)大公教会显然是施米特心中类似理想国的存在。当然,施米特不可能真的支持梵蒂冈统治整个欧洲,我们还是从《罗马天主教和政治形式》一文分析他的政治观点。此文的中心在于代表原则和对立综合体这两个概念。对于代表原则,施米特的回应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人民制宪权以及超然的主权-者的决断。而对于对立综合体,在目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中,除了普世教会(在理论上)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了。对此的答案,对施米特来说,既然即无法从经济理性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寻找,那就只能从非理性和传统那里汲取灵感。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施米特很少承认,但他无疑在思想底层是支持一种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可能是教权法西斯主义。当然,他毫无疑问不是纳粹主义的同路人。首先,施米特不认同种族主义,也不像他老师韦伯那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更不符合一个普世的对立综合体的特征;其次,纳粹政权并没有解决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过度膨胀的官僚制,而第三帝国也把理性主义真正发扬到了韦伯说的“理性的铁笼”的意义(或者说是理性的屠宰场),这与施米特对形式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反对格格不入。最后,施米特于1936年被官方媒体批判后就已经和纳粹当局渐行渐远。不论怎么说,把施米特称为纳粹主义者都显然是不公正的。按笔者个人的意见,卡尔•施米特如果生在同一时间的意大利也许会有更好的学术生涯和名声。
结语
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理论集中诞生于德国于一战后遭遇大规模政治危机的时代,基于马克斯•韦伯对于官僚制和理性化原则的批判,对德国未来需要强力领袖的政治预期,以及批判继承了托马斯•霍布斯的主权思想,施米特产生了自己对德国政治的看法以及自己的政治理论。本文的目的是从谱系学和魏玛共和国具体政治环境的角度梳理施米特的政治思想。施米特的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是基于德意志国处于生死存亡状态的认识,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意识到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内涵以及其可适用性。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