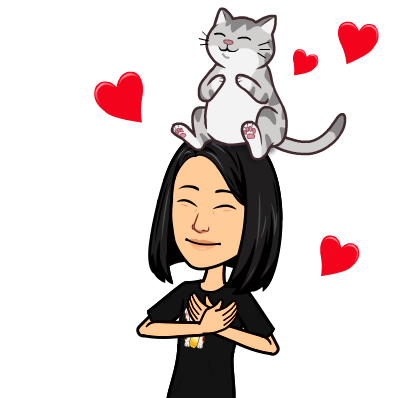
荷兰语学习者
“站在下水道,挥舞橙围巾”——荷兰阿富汗人撤离实录
原题:'Ga in het riool staan en zwaai met een oranje sjaal'
作者:Natalie Righton
来源:de Volkskrant
【未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这一周,有许多人被留在阿富汗,但也有数百人设法逃离了喀布尔。他们通过以下三种办法:下水道、幽灵巴士和秘密车队。

乘坐巴士
8 月 25 日星期三——8 月 26 日星期四
喀布尔的中午艳阳高照,塔利班士兵登上坐满荷兰人的巴士叫嚣:“我发誓,如果车上有没有外国护照的阿富汗人,我不会放过你们所有人!”
医生W.S.今年46岁,是荷兰Schiedam人,此时也坐在鸦雀无声的巴士上。星期三早上,她走进荷兰驻喀布尔大使馆,希望能够顺利通过塔利班检查站前往机场。她的邀请信上说:荷兰和其他国家“已经与塔利班达成协议”,荷兰护照持有人可以自由通行。
巴士之行越来越糟糕:荷兰人被混乱的交通困住。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步行或乘坐白色丰田卡罗拉前往机场,希望外国人能带走他们并给予庇护。
巴士内超过40度。孩子们晕倒了。一个男孩被送往医院。乘客们打开车门降温,阿富汗人想偷爬上车。
12.47:“人们开始恐慌。车外面的妇女想上车。”
W.S.用快没电的的手机向荷兰志愿者团队发信息和语音,该团队几天来一直在想办法帮她离开喀布尔。志愿者团队由10名前阿富汗记者组成,包括摄影师Eric Feijten、艺术家Lotte Geeven和基民党(CDA)国会议员Derk Boswijk。从上周日晚上起,他们开始想办法帮助W.S.和其他十多人撤离,指示他们如何安全到达机场的“荷兰入口”。
“公交车上已经出现了两次恐慌”,W.S.在半途中说,“一次是因为车上有一个‘黑户’,另一次是因为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求我们带她去机场。她的大儿子已经在机场,她喊着:‘我一个人没办法在这里活下去!’她上了车,但我们最终说服她下车。”
对于巴士上的许多荷兰阿富汗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时刻,因为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战乱时期,单身阿富汗妇女只能去卖淫,不然无法维持生计。
巴士上没有警卫、士兵或外交官,持有荷兰护照的阿富汗人只能自己想办法。然而,W.S.没有受到塔利班的人身威胁。大喊大叫的塔利班士兵明确表示,荷兰护照持有者不必紧张。他们只是威胁说:只要有偷渡者,就会截停巴士。
但W.S.的消息和电话让人担心。
15.30:“我想回去(住的地方)。我待不下去了。”
18.04:(在志愿者团队鼓舞人心的讲话后)“请不要给人虚假的希望。”
令所有人沮丧的是,巴士司机在晚上突然掉头,高速驶回喀布尔市中心。他觉得自己赚的钱太少了,他受够了。惊慌中,W.S.悄悄地发了一条语音:
21:10:“司机说:‘我赚得太少了。’我们现在开向市区。每个人都在问他:‘我们要去哪里?’ 但他不回答。”
过了一会,乘客向司机保证可以让他带一些偷渡者,成功地说服司机把大家送回机场。
周三到周四的晚上,有118名荷兰人乘坐3辆巴士到达机场。最初是一个车队,但在混乱中走散了。23 岁的医学生Musa跟W.S.不同车,那辆车也出了问题。巴士司机围着机场漫无目的地一直开,因为他找不到入口。
Musa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问志愿者团队能否用聊天软件发送入口的坐标。当外交部拒绝将入口告诉志愿者团队时,他果断地说:“我现在就给大使打电话!”
当这个年轻人在巴士上与Caecilia Wijgers大使通话时,一个塔利班士兵打破了车窗。电话里可以听到窗户破碎的声音。“一些孩子在鸣枪示警时惊慌失措。” 然而,Musa也没有受到塔利班的威胁。“厌烦胜过了恐惧。我们已经在路上待了二十个小时,没有厕所。你希望听到点动静。”
这位医学生被志愿者团队戏称为“回旋镖”。他每一次撤离都失败了,之后又重新与团队联系,问是否有其他路线。他尝试了将近两个星期都徒劳无功。
巴士是最后的选择:它只属于少数人,例如行走困难或精神濒临崩溃的残障人士。其他人都必须步行到机场,穿过下水道到达入口。Musa被允许乘车,因为他尝试了两周仍然无法离开。
周三到周四凌晨,大使让Musa通知3辆车的所有乘客返回大使馆。
21.50:“大使想要送我们回大使馆。”
21:51:“我必须通知3辆车上的所有人。”
但Musa说服大使再试一次。他们都知道回去不是最好的选择。美国人想要关闭机场,因为军方需要四天时间收拾东西。周三到周四晚上,恐怖袭击的威胁在增加。美国人要求关闭大门带来的压力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如果荷兰公民当晚不能进入机场,就很可能会被困在喀布尔。
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巴士准时到达。这并不容易,因为机场周围就是塔利班的临时检查站。
Musa与两名年长乘客下车与塔利班交谈。他们把车牌号告诉塔利班指挥官。Musa跟大使联络。一翻交涉后,现场的塔利班士兵接到命令允许这辆巴士通过。
塔利班士兵首先进入巴士检查护照。Musa说:“7名没有荷兰护照的阿富汗人被赶下车并遭到殴打。”然后他们被允许前往机场入口。当巴士进入机场后,入口关闭了。
他们是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内阁宣布出于安全原因,将停止所有疏散航班。
下水道
8月23日星期——8月25日星期三
几天前,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的第一周,荷兰的撤离航班都是半满起飞。最初的撤离名单上有700人——这个名单每天都在增加——但只有少数人成功到达机场。
持有荷兰、英国或美国护照的人也会被西方士兵赶走。他们通常能够通过塔利班的检查站,因为塔利班也希望所有外国人离开。但由于害怕袭击或恐袭,西方士兵封锁了入口。
荷兰外交官和士兵组成的撤离小组想出了一个方案。他们在机场旁的一条小路上设置了一个让同胞进入的秘密入口,在河边,旁边有条破裂的下水道。在荷兰撤离名单上的人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到达下水道后面的一扇门:附件是地图上的一个红点。
事实证明这些说明太模糊了。没有人能找到入口。记者和国会议员接到阿富汗人绝望的电话:他们围着机场走,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于是荷兰志愿者团队自发尝试通过信息和电话为撤离人员指路。
在谷歌地图的帮助下,志愿者团队连夜为撤离者指路——“这里向左,不,那里你必须向右走”。多媒体艺术家Lotte Geeven给撤离者发送橙色屏保,这样他们可以在黑暗中用电话向荷兰士兵传递信号。他们还被要求带上橙色围巾、帽子或雨伞——一切都是为了让荷兰士兵能在人群中发现他们。经过一个漫长的夜晚,8 月 23 日星期一早上,终于收到一条成功的消息。
07.29:“我们进入机场了。”
这条消息来自翻译W.N.。第一批成功找到“荷兰入口”的是三个翻译及其家人,他是其中一员。W.N.在谷歌地图上标记了位置,志愿者因此获得了“荷兰入口”的准确坐标。
更关键的是W.N.拍摄了一张靠近入口的地标照片:挂着土耳其和阿富汗国旗的一座塔。塔前面是下水道。事实证明,这张照片将许多人带到了正确的位置。
当时,外交部仍然认为不需要用软件引导人们到达正确位置。两天后,外交部让步了,因为这是让人们找到机场入口的唯一办法。他们决定与志愿者团队合作,并大规模使用该方法。士兵们站在入口前把荷兰人从下水道里拉上来,但入口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实在太难找了。
向人们指路并不难,任何语言问题都可以通过谷歌翻译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保持撤离人员的积极性。撤离是一场消耗战。尤其是抱小孩的人,他们没办法在泥泞中站立数小时。他们叫喊着让荷兰士兵把他们拉上去,但士兵没办法同时处理这么多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拿着荷兰的红色护照,在下水道中等待了数小时。
与站在下水道中的翻译G.H.的对话:
11:57:“求求你们。孩子晕倒了。不要丢下我。”
12.01:“我也快要昏倒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12.03: “不要灰心。我们来找你。”
12.04: “我没看到荷兰士兵。救命。我带着橙色围巾。”
12.05: “他们来了。他们会看到你的。相信我。”
12.06: “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进去。坚强点。”
12.15: “你还好吗?!” (……)
12.55: “我进来了!.”
15.04:“非常感谢你们!” (发送家人在机场的照片)
从周三上午开始,军队、外交官和志愿者团队合作得很顺利。“外面的”团队报告哪些家庭在下水道里,发送他们的姓名和照片。“里面”的团队确定他们在下水道的位置,然后突击队员将他们拉上来送进机场。
还不清楚有多少人通过这种方法进入机场。荷兰记者及其家属撤离名单上有117人。Free Press Unlimited认为,其中有97人获救,大部分是通过下水道进入机场的。据估计,志愿者团队用这种方法为大约150人指路。此次行动的经验也被其他国家采用,这些国家的撤离人员也难以进入机场。
人们最关注的撤离者之一是一对未成年的阿富汗双胞胎。他们在荷兰的哥哥E.G.联系了志愿者团队。在周一到周二晚上,孩子们告诉志愿者找不到入口。摄影师Eric Feijten收到他们的信息后立即给入口打电话,议员Boswijk也跟下水道里的双胞胎通话。他们戴着橙色的帽子,以便军队能够认出他们。
然而,同一天,荷兰医生W.S.没有找到下水道。她在入口门附近摔伤了。她心烦意乱,鼻子流血,轻微脑震荡。在入口附近徘徊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
在与外交部协商后,她被允许乘坐巴士。但她70岁的母亲——也在疏散名单上——却不允许坐车。因为这辆巴士是专门为荷兰人准备的,她的母亲只有阿富汗护照。
所以W.S.必须选择:救自己还是留下来陪母亲。这令人心碎。但大使不能将她的情况特殊处理,她说:“不管那有多可怕”。最后,W.S.将母亲留在了喀布尔。
虽然W.S.和Musa的飞机于周四晚上起飞,但内阁在给议会的一封信中写道,为将一些撤离人员“抛下”感到“痛苦”。据志愿者团队称,名单上至少有26人仍被困在喀布尔,其中3人持有荷兰护照。这大概只是冰山一角。据国防部长Bijleveld说,至少还有30名口译员和他们的家人需要被接走,外交部长Kaag周五表示,她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滞留。可以肯定的是,周四有200人正在前往机场,但外交部宣布暂停撤离。

秘密车队
8月14日星期六——现在?
与战争中的常见情况一样,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能否逃离。随着塔利班迅速逼近喀布尔,阿富汗人最近几周利用所有有影响力的人脉来自救。
8月14日星期六凌晨2点46分,《人民报》的翻译H.Z.发来第一封电子邮件:“家人们很担心我的两个姐姐和弟弟,他们为外国媒体和阿富汗政府工作了许多年。大姐每天都惊恐发作几次。(...) 因此我谦逊地恳求,如果我之前的工作对您还有所价值,您能帮助我的姐姐和弟弟登上飞机吗?如果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也不会向您开口。”
《人民报》的编辑和自由记者Minka Nijhuis——她也曾经在阿富汗为《忠诚报》工作——竭尽全力营救H.Z.的家人。呼吁政治家将他们列入评估名单,请愿、说服。但这没有用。尽管Kaag部长在众议院承诺翻译人员的亲属将获救,但仍不清楚H.Z.的家人是否可以乘坐撤离航班。
家人们认为耐心等待太冒险了。H.Z.的姐姐和弟弟,以及数以万计的其他人,试图自己进入机场。他们被枪击、昏倒、被搜身和喷催泪瓦斯。
就在他们快要放弃时,8月21日星期六,H.Z.安排他们登上了一个秘密车队。一些有影响力的阿富汗、美国和欧洲朋友能够就私人车队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塔利班同意让三辆载有撤离人员的货车通过——目前尚不清楚付了多少钱。这群朋友与中央情报局也达成了类似协议,允许货车在8月21日星期六夜晚至22日星期日凌晨开进机场。
这是H.Z.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他在加拿大的家中一直盯着通讯群,看车队如何“走私”他的兄弟姐妹。
23:46:“我们上车前已经统计过人数,29 人。”
00.50:“在从酒店去机场的路上”
01.52:“通过北入口检查站”
01.52:“你们进机场了吗”
01.56:“还没有,在门口”
01.56:“他们在检查最后一辆车上的乘客”
02.09:“有新情况吗?”
02.10:“我们进机场了!”
令Wijgers大使惊讶的是,翻译H.Z.的三个亲戚站在她面前。她检查名单:有人在名单内,有人不在。她困惑。有一个荷兰航班即将起飞,还有几个空座。大使把他们推了上去。
逃离的费用很高。在到达邻国巴基斯坦后,他们发信息感慨,然后他们到达史基浦机场,开始为那些留在阿富汗的人感到悲痛。
对于许多幕后的外交官来说,选择谁乘坐撤离航班就像辛德勒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选择”哪个犹太人能活下去或多或少有随机成分。当然,这些外交官并没有像辛德勒那样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们确实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当志愿者团队说到令人痛心的案例时,撤离协调员Arjan van der Roest和Melle van Dijk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喀布尔,大使Caecilia Wijgers必须在一瞬间做出决定他人生死的选择。例如,官方只允许受威胁的翻译将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带到荷兰。但是,站在下水道里的翻译W.H.怎么办,他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和两个成年子女以及几个孙子孙女?应该留下一些人带走另一些人吗?混乱之中,Wijgers决定将他们所有人都送进机场。
尽管做出了一切努力,但还远远不够。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疏散行动开始得太晚。结果是灾难性的。有数十名翻译滞留,其中包括30岁的荷兰妈妈,带着她持有荷兰护照的4岁孩子和持有阿富汗护照的未成年弟弟妹妹(10 岁和 12 岁)。周三,使馆不允许他们一起乘坐荷兰人的撤离巴士。妈妈拒绝与弟弟妹妹分开,于是在周三晚上步行前往机场,寻找下水道旁的入口。
志愿者Lotte Geeven花了几个小时通过电话引导她找到正确的入口。但是太晚了。当妈妈还在下水道呼叫时,机场关闭了。入口再也不会打开。荷兰停止撤离。他们一家人留在了喀布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四下午,这位母亲在喀布尔的避难所对志愿者团队说,“我来这里度假是因为我很久没见到父母了。我知道这有点危险,但没想到塔利班会这么快接管。塔利班掌权几天后,我的父母被带走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对于这位荷兰妈妈和她自己的孩子来说,还有一线希望。一旦外国军事人员离开,局势平静下来,塔利班计划恢复商业航班,持有荷兰护照的人应该能够飞离喀布尔。
“但是我10岁和12岁的弟弟妹妹怎么办?他们没有荷兰护照,不允许随行。我不能留下他们,不是吗?”
对她来说,解决办法是让荷兰给孩子们发放护照,或者让军队从城里偷偷接走他们。然而,荷兰在阿富汗不再有正式行动,因此希望寄托在外国军队的帮助或荷兰的秘密救援上。也许会有突击队,就像他们在上周末疏散207名大使馆员工一样。疏散过程仍然是一个谜。
在内阁周四寄给议会的信中,可以看到最后一丝希望。一架荷兰飞机将在喀布尔停留到下周二,“如果有机会,会将更多的人从喀布尔带到安全地带”。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