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爱好者
第五章 干净的白纸 为什么人们必须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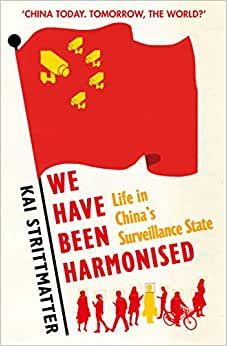
“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未曾成为过去。” 威廉·福克纳
党有充分的理由来庆祝。2019年6月4日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三十周年纪念日。这不仅是民主运动的终结,也是一个盛大节日的终结,一个让几百万人民为了他们重新获得自由和一个更加美好中国的梦想而欢欣鼓舞的节日的终结。广场上一个精力旺盛的学生大喊道:“我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但我知道,我们不光要这些。”1989年6月4日凌晨,他们最终得到的,是子弹和刺刀。隆隆的坦克让夜晚颤栗。成百上千的学生、工人和行人们被碾压、枪击或刺伤;至今具体数字仍不得而知。从党的角度回过头看,这是一次成功。比当时任何人能想象到的结果还成功。
“中国人必须学会遗忘才能生存。”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的幸存者、画家张晓刚,他选择了铭记。1989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自由的时光。人们摆脱了文革噩梦,新的领导人邓小平打开了国门对世界开放。用他的话说,要开放就不要在乎随着新鲜空气一起进来的“几只苍蝇”。张晓刚对这段日子记忆犹新。“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希望、这么多幻想、这么多美好事物。那是个诗意的年代。新华书店门口排着长队就为了买一本小说。”
1989是不平凡的一年。张当时在画的一幅画是莱特河岸上一个红衣少女。在希腊神话里,谁喝了莱特河的水就会完全失忆。在一月份,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日后被认为非常传奇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第一次展出了“地下”画家的现代艺术作品。展览会早上九点开始,下午三点就被警察叫停:神经过敏的文化部官员们发现展品粗野,太不合他们的口味。新一代艺术家的艺术语言他们一点都不能理解。张说,“我们当时就在现场,当时的想法是,中国必将越来越开放和自由。”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就要为他们的信仰、理想主义和天真付出代价。
6月4日很快就到了,坦克进了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诞生了。随之而来的鲜血和恐怖在那个时刻拯救了党,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权正在分崩离析。在粉碎了“反革命暴乱”之后,邓小平巩固了他和许多其它领导人的统治,他们被示威者谴责为腐败和裙带关系--今天,这些家族拥有的财富在80年代末是无法想像的。屠杀带给了政权非常珍贵的几十年时间,并让邓踩踏着真相和记忆上位。并最终为邓赢来了西方政客和商人的赞赏。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问题:“这样不是更简单么/对政府来说/把人民解散/重新来一次选举?”中国政府无需为选举犯愁,它只要重新塑造一群人民就行了。
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是1989年运动的英雄之一。在大屠杀之后他用一种确信来安慰自己,鉴于这些日子是如此怪异,鉴于这几百万的见证人,至少这一次,“让历史被遗忘的技术注定会失败。”(注56)几乎没人能料到方错的离谱。共产党只要简单地按下“删除”并把中国人民重新格式化。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震惊了世界--但在中国,它已被遗忘。1989年?“毫无疑问,是普普通通的一年,”诗人杨炼在诗中写道。
枪杆子和笔杆子协同作战。国家的军队杀害了示威者;国家的作家杀死了真相。乔治·奥威尔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了当下谁就能控制过去。”毛泽东曾希望他的人民是一张白纸,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独裁者希望人民集体失忆。党的宣传一直在进行重新排序和重新配置的任务。1989年6月4日后全国都惊呆了。当人们从震惊中复苏重新卑躬屈膝的时候,宣传机器就巧妙地开始淡化这些日子的恐怖。在之后的数年里,“反革命暴乱”逐渐成了“暴乱”,然后是“政治风波”,最后仅仅是一个“事件”。
到头来,甚至“事件”也冰消瓦解寂然无声了。就像是一张老照片逐渐褪色最终仅剩下毫无意义的轮廓和剪影。当北京的警察官员警告外国记者不要涉及大屠杀的时候,他们的警告用语是很模糊的,会说“敏感时间段的敏感主题。”他们甚至不会明确说出“那一年”或“那一天”。事实上,每年快到6月4日的时候”那一年“和”那一天“就重新出现在互联网的审查列表上。在微博上同样被禁的表达还有:”春夏之交“和”5月35日“,因为这些词语被大家用来替代”64“。维基百科在中国无法访问;它的中国替代品是百度百科,自称是”内容开放、自由的网络百科全书“。你能在百度百科上找到1988年和1990年的条目--但1989年是不存在的。这一年已经从历史上抹去了。(译者注,百度百科已恢复了这个条目,只是没有这个“事件”)
令人震惊的不是审查有多么努力,而是审查是那么有效。这可以做到。即便在这个时代--感谢互联网--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对整个民族进行洗脑仍旧是可能的。千百万中国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头脑智慧、思想开明,他们的成长伴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但一直到20来岁走出国门才第一次知道1989年发生在祖国的新闻。一部分人感到震惊;还有许多人至今拒绝相信。他们把自己关在党为他们编织的蚕茧里,拒绝接受类似的信息。一个在德国的中国学生写信给我:”你们西方记者何时才能不撒谎?你们就是不能接受中国已经强大的现实。”
公民权利活动家胡佳讲了2005年1月17日发生的故事,这一天赵紫阳逝世了。赵是自由派,是1987到1989年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前则担任过总理。(本章注释) 赵曾试图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作出某些让步,但被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主导的强硬派推翻了。胡佳认识他的家人,所以前往吊唁。他回家后,妻子曾金燕问他去哪儿了。他如实相告。她古怪地看了他一眼:“去谁家了?赵紫阳?他是谁啊?”
胡佳说:“我被吓了一跳,她是1983年出生的,她很聪明,也很挑剔,在人大上过大学,那是北京的一所精英大学。她这辈子都没听说过赵紫阳,一个曾经在几年时间上是--至少名义上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那一刻我明白了党对于我们头脑的掌控力。”
在美国记者路易莎·林为她的著述《失忆人民共和国》做研究的时候,她给100名北京的学生展示了著名的照片“坦克人”:穿着黑裤白衫的一个人,站在一列前进的坦克前面,他手无寸铁手里只有一个塑料袋,用自己纤细的身躯逼停了坦克,最近的一辆坦克触手可及。仅仅15名学生认识这张照片--令他们极为不可思议的是--这张照片是在中国北京拍摄的。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另外85个学生?他们耸耸肩,猜测这是科索沃或者南韩。(注57)
如果每过几年,甚至几周,你周围的世界就被粉碎,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重新配置,那么你心理上的根除--遗忘--也会更容易些。在过去二十年里,整个中国都被推倒重建,在一些地方甚至重建了几次。这给中国的城市带来了西式的居住风格,漂亮的塔楼和新式公寓一夜间拔地而起,造就了现代化的、千篇一律的城镇。同时这也抹去了人们曾经熟悉的一切。
画家张晓刚是这样谈论90年代的:“你刚一转身那些熟悉的老街就消失了,我离开昆明不过才一个学期,然后我就回来了--但我的家乡再也看不见了。全毁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废墟。”那一阵子,无论你去中国的哪个城市,都能看到遍地的瓦砾。再等一阵,你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复制品。张说:“我认为即便从全世界看,这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规模上,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这样的事情。每天,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改变的是你的城市,也是你的生活。这样的变化速度是畸形的。它远远超出了正常人心理接受的范围。“
通过改变城市景观和建筑来擦除记忆仅仅是集体遗忘的一种方式,而这样的遗忘已经成为中国人本能的生存技巧。普利兹克奖得主、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王澍是这样说的:”老房子可能是最后一样被抹去的事物了,这就解释了人们不再反对推倒重建。所有其它的事物,我们的古老生活方式,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早就被粉碎了,尤其在文革期间。老房子只是最后剩下的、空洞的残余。“
今天,中国有一百多个城市比芝加哥还要大。其中多数城市在过去十年里都比最初的规模要大上十倍或更多,在这个进程中它们也都根除了自己的历史痕迹。王澍说:”仿佛有人在中国扔了120颗原子弹。“90年代他设计的所有建筑,现在一个都不存在了,全都被推倒了。
有时候,在中国绝望的滚滚人潮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失落;一种巨大的不安。画家张晓刚和建筑师王澍都一早就决定通过倔强地记住来保持自己的平衡。在中国,这样做比任何其它地方都费劲。这也让你成为一个局外人。
这两人都是先在海外取得成功和声誉后,才在中国被认可的。张以他的家庭肖像画成名,他的灵感来自于文革照片:人们穿着毛规定的蓝布衣服,脸上是严肃死板的表情。几乎每一个对中国或现代艺术感兴趣的人都被他的肖像画迷住了,上面有着梦幻般的脸孔和催眠的双眼。他们都是严肃的,像平静的湖面一样冷静,但这种无声的顺从掩盖了感情的风暴;人类个体的痛苦和欲望在湖面下涌动。所有的画都有点轻微失焦;唯一生动的细节就是闪烁的黑眼睛。
张晓刚给自己在千年之交开始创作一个系列起名叫”失忆和记忆“。画家把在中国肆意横行改变一切的绝对力量看成是你必须要抵制的事物,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希望留住你的过去。但你这样做是在对抗共产党的权威,因为党认为记忆是一种危险和颠覆的能量。党是这样算计的:如果你让人们失去根基无家可归,他们就只能赤裸着颤抖着,跑到党的母亲那遮风挡雨的臂弯中。
张的作品灵感来自于他文革时的童年经历。从五岁开始,他就被锁在成都家徒四壁的公寓中,这房子是工作单位分给他家里的。和他画中的小男生一样,他骑着自行车绕着桌子转圈。这些画里面的窗子从不见阳光照耀。他记得”我们楼里面所有的窗户都用砖堵上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两年,因为红卫兵会时不时的对着楼房开枪。楼里也没有电;只能用油灯。
”里面暗无天日。就像一个地堡。我的眼睛都被搞坏了。“那段日子很糟糕?也许是,也许不是。8岁的张和他的朋友们觉得很酷。”我们有一大帮人。也没有大人来管我们。我们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文革是人性最黑暗的时刻之一。但对一些孩子来说--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人们从早到晚都在外面开“批斗会”,互相谴责彼此羞辱。红卫兵们抬着被他们折磨致死的“反革命份子”的尸体耀武扬威地游街。与此同时孩子们在楼道里跑上跑下,所有的大人都遥不可及,简直就是自由自在的童话王国。他们比其它任何时代的孩子都更加自由和不受管束。没有权威,不用上学,没有作业,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张在那些日子里见过很多死尸,还听到很多次打枪的声音。他说:“对小男孩来说这糟透了,但也很刺激。”
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给这个民族带来太多的精神垃圾。张说:“今天,这些都被遗忘了。”到2016年,从毛打响发令枪算正好是五十周年,这种遗忘格外明显。整整一年,没有一个纪念活动,也没有一个追悼仪式。没有争论,也没有自我批评。厚重的沉默覆盖了全国。党很明白,要是人们记得太清楚党就危险了。所以党为了眼前的需要必须把过去改写成一本辉煌的历史小说。
在毛死后,共产党的高层谴责文革是“十年浩劫”--但他们很快又补充说毛为祖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错误和功劳比起来不值一提。党算了算帐,结论是毛有“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三分错误还包括了在1958年到1961年“大跃进”期间被饿死的四千万人--在这个可怕的运动中,毛下令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农户都要把他们的铁制农具和锅子熔化去炼钢。毛希望在一夜之间就能把中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超英赶美”。到头来,中国没有了铁锹和铁铲,没有了犁头和铁锅,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主政后不久就宣布,对毛的任何批评都是不允许的。德国对于纳粹的那段历史有个术语叫作“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努力克服过去)--共产党称为“历史虚无主义”,敢这么干的人就等着吃官司。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部法律,任何人“侮辱或诽谤[共产党]英雄和先烈”都要被严惩--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党的光辉历史上那些英雄故事的真实性。在我去张晓刚画室采访他的那天,工人们正在更换天安门广场上的毛的画像:伟大领袖要用毫无瑕疵的新色彩来迎接国庆。
作家阎连科在2013年写道:“我一直以为历史和记忆会战胜暂时的越轨和失常,并最终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注58)“现在看来正相反。今日的中国,失忆战胜了记忆,谎言超越了真相。”恐惧是一个因素。在场者的沉默是对当权者的默许:在中国这些都属于朴素的生存技巧。你为孩子感到担心,对他们隐瞒真相,因为--如果不假思索地在同学或老师面前吐露真相--也许会让孩子身处险境。崔健是个摇滚明星,并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为学生演出,他的歌曲“一无所有”成为学生们的赞歌。有一次我问他,在中国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说是“装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是生活在独裁下的人们的第二本能。
阎连科对他的作家同伴和全体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谴责,他们在面对这种国家主导的失忆症时表现出沉默和胆怯。他写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打开的窗户,是当权者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怜悯施舍,而不是知识分子持续不断的争取赢来的胜利。”“一个在黑暗的牢房里度过数年的人必然对牢房里开窗引入光线感恩戴德。可他敢要求为他打开牢门么?”
恐惧只是原因之一。在1989年后,一些新的因素加入了。邓小平政权为人们(至少是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方案:赚钱,致富--但闭上你的嘴。人们接受了。往前看是那个时刻的标语:“往前看!”不要转身。更有帮助是这句话也可以念成“往钱看!”从此,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追求经济开放,同时拒绝放松政治管控。党仍然信奉共产主义神殿,仿佛里面的确藏有圣迹--即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被要求去尊崇的货色早就死得透透的。领导人把民族主义当成人民的新鸦片,这个有毒的小小绿植经过他们煞费苦心的培育,现在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
过去也许被遗忘了,但它并未真的过去。中国社会今天的运作方式,和文革中发生的一切密不可分。张晓刚说,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今天的中国光彩照人,欣欣向荣,你可别被这些表象给骗了:"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回到了文革时代。“对战争的研究标明,这一类的创伤会向下一代传播。如果今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不信任其他人;如果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假设其他人都在欺骗自己,这种态度的根源就是那个时代--丈夫背叛了妻子、子女把父母送进了劳改营甚至是断头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现在他们正在掌权。他们领导着党、领导着国家、还主导了中国的各种大生意。
中国今天的面貌跟1989年发生的故事更不可能分割。这个光彩的、有力的、野心勃勃的中国--有一个溃烂的内核。中国城市这些年的繁荣和增长已经把城市中产阶级变成了党最忠实的同谋。因为1989年之后理想在这个国家已经被禁止,他们都变成了没有底线的物质主义者。共产党领导者们的家族在这个过程中都毫无羞耻的暴富起来,其中最靠前的是李鹏家族,他曾在1989年宣布了戒严令。在这个社会里,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都滑向了普遍的犬儒主义。道德危机破坏了中国社会,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互信,也不再相信国家机器,毫无制约的腐败,生态环境的恶化--所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些致命时刻的规则设定。
当你被命令要忘却六四之夜,那么记忆就成了一种罪行。年复一年,在六月初微博就会把”悼念“设为禁用词。悼念被禁止了,从字面上和行动上。党到底在害怕谁?很明显就是那几个还固执地坚守着他们记忆的人。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表演:在六四的前几个星期当局就要让这些固执的人群闭嘴,或者直接把他们关进监狱。2012年6月4日张晓刚在微博贴出的画作,是一张捂住嘴巴的惊恐的脸,立刻就被删了。每年春天,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就会发现很难联系到”天安门母亲“,这是一个女性民主活动组织,她们拒绝放弃纪念她们儿女的悲惨死难。还有陈光,他曾是广场上的士兵,后来成了一个画家:他在大屠杀25周年前被捕,他和朋友组织了一次表演,他在一面墙上用鲜亮的彩色刷上1989到2014的年份数字,然后用白色颜料把它们覆盖掉。
1989年的大屠杀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闭嘴。在那些被称为中国良心的小众人群中--他们可能是律师、民权活动家、知识分子、作家--很多人都把1989年看成是他们行动的触发点。但总体来说,宣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记者和作家杨继绳说:”50岁以下的人对毛统治时期的真实情况缺乏真切的了解。“”他们认为毛很伟大,因为书本上和电视里都是这么说的。“
杨继绳本来是国家媒体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他利用这个便利在全国查阅了很多档案材料。在多年的研究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披露了”大跃进“运动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注59)杨找到的证据显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他估计的死亡人数是三千六百万;其它历史学家比如冯客(Frank Dikötter)给出的数字高达四千五百万。(注60)
有时候选择性记忆是被允许的,比如对于文革:数年后,文革题材的电影和文学作品被允许发行,可以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描述当时的混乱和残暴--但自始至终,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始终不允许讨论。这样的悲剧怎么会发生?谁该负什么责任?党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初是这个党组织推举毛担任领袖,也是这个党掌控的国家机器放任他滥用权力,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整个国家。
文革中一项野蛮的运动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和旧风俗。到最后,它试图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仅仅保留了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旧幽灵。讽刺的是,今天党的领导层又利用了人民对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混乱留下的深刻记忆(其它时段的痛苦记忆都被封锁和扭曲了):“中国不能再乱了!”宣传机器呼喊道,它明白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和饱受创伤的人民达成共识。接下来的口号是:“毫不迟疑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它的口头禅是“稳定”。所有的压迫都打着“维稳”的旗号。
和文革不同,虽然“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死亡,它已经彻底被遗忘了。党即便提起那段岁月,也会含糊其辞地说“困难时期”。党一次又一次给人民开出历史失忆症的药方,不然它就得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对日本的憎恨,不停重复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民族主义宣传的主旋律之一。如果人们意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按照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估计,可能“杀死的中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杀死的人数的八到十倍”,那又会如何?(注62)“也许有的人会说,日本人更残暴,因为他们搞砍头比赛,还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搞活埋。”林培瑞写道,“可谁能说哪个更残暴呢?在文革中有人被挖出双眼,1969年在广西,还搞出了吃掉阶级敌人肝脏的仪式。”
如果共产党从苏联倒台中汲取了什么教训--上海一名历史系的教授刘统是这样判断的--那就是党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它对如何书写历史的掌控。“摧毁历史,”教授此处是指官方钦定版本的历史--“是摧毁党的第一步。它会动摇群众的信仰。”(注63)
林培瑞提到的吃人事件引用自郑义1993年著作《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注64)这本书,和另一本记者杨继绳所著的开创性著作《墓碑》,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并在欧美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它们都是禁书。
杨继绳所在的杂志是著名的《炎黄春秋》。这不是一本持不同政见者的刊物;正相反,它是由一批退休的老党员创办的,当然他们在毛的暴政下吃足了苦头。杂志编辑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目标,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仅仅是为了“实事求是”。杂志披露的很多事件,把共产党宣传部门最热衷的一些故事变成了谎言。就是这些对历史真相的索求被习近平称为“历史虚无主义”:它动摇了信念,而这些信念本来是聋人和盲人的专利。
《炎黄春秋》是习针对试图翻旧账的这次运动的又一个牺牲品,2017年宣传部的官员们全面接管了这本杂志。创办人、老主编杜导正,刚刚住进医院。在他的病床上,92岁高龄的杜老谴责接管行动是“文革遗风”。早在2011年,杜导正就把中国的情形比作高压锅:“阀门拧得越紧,内部的压力就越大,总有一天要都炸掉。”第二年,习近平接过了权力的接力棒,自此这个阀门每天都在被拧得更紧。
失忆症这个机器不仅仅抹去党关于历史的谎言和罪行;它还不知疲倦地在小一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各种中小规模的失误、挫折、事故和灾难都掩盖起来,不然积少成多,人们不免要怀疑这个体制早已溃烂。那些足以引发思考和分析从而找到立足点的事件被轻易地蒸发掉,仿佛从未发生过。那些可以让人互相联络,足以建立有迹可循的模型的空间都纷纷被关闭。更常见的是,留下的只是一个消散的余音:那里有什么东西么?人们仅剩的记忆也被阴影和轮廓淹没了。
河南省的艾滋村就是一个例子。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鲜廉寡耻的党员干部和商人联手打造了利润丰厚的献血网络。因为操作者的贪婪和无知,这个网络的运作完全没有卫生理念,对医疗防范也一无所知,最终导致全村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只能一起等死。
另一个例子是2015年8月天津有毒化学品存储仓库的爆炸。将近午夜时,在一个高档居民区几百米远的地方,比摩天大楼还高的火球腾空而起。烈火在中国最富裕和现代化的城市中心肆虐,离首都不过两小时车程。起因是危险物品的非法仓储,而当局对这些致命的化学物品一无所知。毫无头绪的当地政府、腐败的官员、绝望的领导,他们给火场派去了大量消防员,结果却被毒气和火焰夺去了生命。结果是令人绝望的:200人在火灾中丧生或失踪;市中心出现了一个大坑;被污染的土地和建筑物。人们震惊了。但他们能得到的消息都来自社交圈流传的“人间地狱”的图片。在起初几天,党的机器似乎瘫痪了。
灾难后不久,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是广告业的行政高层。他和妻子决定移民。他说:“我们受够了。这次我们是碰巧才听说了天津的事情,碰巧这次被曝光了:他们得有多腐败,他们是怎样摆平一切,怎样官官相护的,真是视人命如草芥。但你想想,同样可怕的事情也正在周围发生,只不过我们从未听说罢了。”他告诉我他们正在为七岁的儿子寻找欧洲的学校。“中国都成啥样了。你从来都没有安全,也没有希望。你知道的,我们中国人啥都能忍。我们从来如此。可我们得让孩子离开这里,至少,给他的生命另一种可能。”
党当然分得清轻重是非。他们明白这种事故追根到底的话,是因为体制缺乏透明度、腐败和无能。但审查和宣传马上就卷土重来。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伤痛和悼念转变为新的英雄事迹,并为勇敢的战士、消防员和护士牺牲自己为党和人民服务庆功。接着很快--几个星期后--天津就从新闻中消失,再也不被提起了。
在英国,类似的事件--例如1989年的希尔斯堡(Hillsborough)惨案或2017年的格伦费尔塔(Grenfell Tower)火灾--会引发长达数年的对起因的分析、研究;长久的悼念和每个纪念日的活动。但在中国,它随风而去无影无踪。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了破坏性的大地震,政府要变的戏法就更壮观了。地震中丧生的人数高达69000,其中包括被埋葬在校舍瓦砾下面的5000名在校学生。这些校舍很明显使用了劣质的建筑材料--意味着这许多孩子不但是自然灾难的受害者,还是腐败的受害者。要掩盖这样的事实是不可能的,一开始这也的确引发了全国的怒火。
但在2018年,汶川地区政府宣布,地震十周年纪念日不应该是用来回忆的--而是应该用来表示“感恩”的。就在那一天,国家媒体上一篇轻松愉悦的文章声称,地震的受害者们对于“漂亮整洁”的新楼房和党和国家在大灾后给予的“大爱”感受到“涌泉之恩”。(注65)通篇没有提到苦难,没有提到失去孩子的父母的痛苦和控诉,其中一些父母因为长期持续抗议2008年的那些谎言和掩盖,最后被抓捕和噤声。
阎连科写道:“逐渐的我们习惯了失忆,甚至开始质疑那些继续提出问题的人。逐渐的我们忘记了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都发生过什么,然后我们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也变得麻木,最后,我们甚至会忘却了自我,忘却了下一代,忘却了我们的爱、欢乐和痛苦。”就这样,中国人对大跃进中饿死的人保持沉默,对文革的起因和根源保持沉默,对1989年在首都中心被屠杀的孩子保持沉默。但在这沉重的无声之幕底下,痛苦在翻滚酝酿,内疚和苦涩在发酵,它们散发的有毒气泡会不时从今天的中国浮出水面。其中最有害的就是没有回忆的乡愁,去除了真相的怀旧。这样的旧梦把过去的野兽变成了美女--而且希望旧日重现。
在2012年夏天,东海的钓鱼岛引发了和日本的又一轮冲突。在共产党建都后从未听闻的事情发生了:成千上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涌入的示威者可以自由表达人们对日本的愤怒。自文革后头一次,在北京街道上成群结队示威的人们不仅仅要求他们的敌人赶紧去死(有些标语牌上写着“踏平东京!”)--和这些充满仇恨的横幅一起出现的,还有人们挥舞的毛的画像,高喊“毛主席,快回来吧。”
再往前一年,重庆市那位极富号召力的领导人薄熙来,在建党9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也表露了相同的怀旧之情。这位在国内受到广泛赞誉的特立独行的党的领导人--他很快就会被党内对手习近平罢免--在他的城市广场召集群众唱毛时代的“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和新毛派都对薄熙来献上他们的热诚,欢呼他是中国的大救星,这些人至今仍然是中国互联网最喧闹的群体--当然大部分人已经把他们的希望转移到习近平身上了。正是这群人认为在大跃进中饿死几百万人是中情局发明的谎言。
只有少数信念坚定的人还在担心失忆症。前红卫兵、现在的律师张红兵(见第一章 词语)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安徽的一个小镇固镇他的家中采访了他。他确信“权力必须被关在笼子里,”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这是一场拯救儿童的战役,他认为:中国的儿童,再一次变得天真,容易误入歧途。张红兵十六岁的时候,把自己的母亲交给了刽子手。起因是,在某一天的晚饭时,她说她宁可要别人而不是毛来领导这个国家。
她对愤怒抗议的张说:“可是孩子,你对阶级斗争一无所知。”
儿子跳了起来。“谁是你的孩子?”他说,“我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如果你继续放毒,我就砸烂你的狗头!”
他的母亲也发脾气了,她说那好吧,让我把墙上伟大的毛画像撕下来,他的父亲也开始反对妻子:“方忠谋!你是个无可救药的反革命,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家庭一员。你是敌人。我们要和你作斗争!”儿子到革委会揭发了母亲,写的材料上认为母亲应该判处死刑。几周后革委会满足了他的愿望,把她处决了。
按照张红兵的说法,中国的学校对当时发生的事情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今天仍在培育奉献的主体,“他说,”奴隶们。被狼养大的孩子。“像张这样的人不但经常要被关心他们的警察请去”喝茶“,他们还要面对公众的愤怒来信。”你在搞什么把戏?“”我们今天生活得这么好。为什么你还要翻旧账?“”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和谐社会么?你想毁了这和谐!“张叹了口气:”为何中国人民的儿女了解得这么少?“
党太善于抹杀历史以至于有时把自己给坑了。2007年,成都的一个人权活动者陈云飞成功地在一家报纸上登出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当年轻的编辑询问6月4日的涵义,她回答说:”是一次煤矿事故,“他对这个答案表示满意。之后,他和其它两名同事被解雇--虽然他们的无知仅仅证明了国家审查机构的努力是多么卓有成效。
我是在北京市中心观看一场现代舞蹈演出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这场在国家大剧院的舞蹈,演出者是台湾云门舞集,主题是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所写的”九歌“。编舞林怀民在台湾创作了”九歌“舞剧,并在其中加入了大量现代元素。
即便如此,看到最后一幕时我依然毫无心理准备。舞台上一片漆黑。非常缓慢地,一辆坦克的影子从舞台后面逐渐显露。舞者们站了起来,起初只有几个,然后越来越多;他们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站得笔直的影子队伍,郑重而沉默地向坦克行进。突然:机关枪响了起来。舞者们摔倒了,抽动着倒向地面。
林怀民创作的这一幕是向独裁者蒋介石(1887-1975)的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致敬;对他而言,是在对1947年2月28日发生在台湾的大屠杀遇难者致敬。但有多少在北京的观众能了解这些呢?在这个离天安门广场只有200米的地方,在这个时刻,又怎么可能不把这一幕看成是对1989年6月4日的隐喻呢?我坐在那里,被完全雷倒了。
这究竟是如何通过审查的?2007年开张的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浮在水面的银色半球体,建筑设计是在申明中国已经是现代化世界的一部分。难道1989年的记忆已经从审查者的头脑中擦除了么?党的洗脑部门竟然能容忍1989年的受害者们在离天安门广场一箭之地被纪念。他们的影子归来了,即使只有一个夜晚。
最后,所有的影子都被收割,倒在了舞台上。无声沉默。从舞台两侧的黑暗中,其它舞者上场了,带着小灯,他们把小灯一个接一个放在舞台上,一直到所有的灯汇成了一片星辰大海。
本章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总理,非正式称为“总理”,是中国国务院的首脑,(宪法上说从1954年起和“中央人民政府”同义)是中国政府机关的领导人,是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的级别(一级)。
全书尾注:
56. 方励之(Perry Link翻译)《中国健忘症》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0/09/27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1990/09/27/the-chinese-amnesia/
57. Louisa Lim 《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Oxford 2015
58. 阎连科 “中国的国家赞助的失忆症” 纽约时报2013/04/01 https://www.nytimes.com/2013/04/02/opinion/on-chinas-state-sponsored-amnesia.html
59. 杨继绳《墓碑:毛时代的大饥荒纪实》NewYork 2012
60. FFrank Dikötter 《1958-1962 毛时代大饥荒:中国历史上最毁灭性的灾难》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London 2010
62. Perry Link 林培瑞 《政治和中国语言:莫言的拥护者们错在哪里》”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What Mo Yan Defenders Get Wrong", Asia Society, Asia Blog, 2012/12/27
https://asiasociety.org/blog/asia/politics-and-chinese-language-what-mo-yans-defenders-get-wrong
63. Deng Xiaoci "China defends Long March" 《中国为长征辩护》环球时报 2016/09/26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08494.shtml
64. 郑义 《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London 1998
65. 汶川确立“感恩日”,让爱的涌泉奔流不息 --新华社2018/05/06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