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日葵的爱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0%91%E6%97%A5%E8%91%B5%E7%9A%84%E7%88%B1&fr=pb&ie=utf-8&id=tb.1.1cd9ae0f.nzrRWDC8MqXgN29zPMwuCA
豫章书院关门6年后,被撕裂的人生与家庭

▲ 2020年7月4日,昔日学生重回豫章书院旧址,这里已经被一所美术学校租用。(陈劲 / 图)“我长话短说,我父母其实不是人,你知道吧?”徐渭清的音量颇高,盖过了少有顾客的咖啡厅的其它声响。

2023年1月14日,90分钟里,徐渭清将8年来的往事悉数吐露,其间夹杂着12次称父母“不是人”的怨怼。回忆结束,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等待着、一度打起盹的徐父上前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儿子说的许多话都来源于他的“妄想”。
徐渭清的偏激与“妄想”,始于8年前命运的一场急拐弯:中考失利后,他被医生认为有精神与心理疾病,随后被父母送入江西省南昌市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以下简称豫章书院)进行“心理疏导”。
在徐渭清父母看来,那段经历显然带给儿子更多创伤。回忆往事之际,他常常答非所问,不断重复着对父母的憎恶,以及对豫章书院创始人的咒骂。
2017年,豫章书院被媒体曝光以戒网瘾之名,对学生实施严重体罚、非法拘禁等,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警方同年立案侦查,豫章书院就此关门。
六年过去,不少当年豫章书院的学生,已经努力找回自己的人生。然而,也有不少的学生和家庭,还纠缠在往事之中。迷茫,困惑,怨恨,疾病……于他们而言,心上的铁网难以剪开。
1
“我可能是走出来了”
徐渭清难以“走出”一所他从未去过的高中。无论话题是什么,他总是反复提及那所心仪的名校。
考取名校的志向将他推入深渊。
徐母记得,2015年中考前,儿子的成绩要上名校就“有点悬”,他最终的分数也只够上不好的私立学校。徐渭清不愿意去,变得有些“走火入魔”,没有读高中。医生认为徐渭清有精神与心理疾病,但病因不详。
后来,有人向徐渭清一家介绍了豫章书院。“我也不懂,我寻思(豫章书院)可能对孩子心理疏导有帮助。”2016年,徐母将儿子“骗”进豫章书院,签约半年。
半年生活的印记,在7年后仍清晰可见。
2023年1月14日下午,辽宁省大连市,徐渭清给自家门前一片坡地上养着的鸡、鸭、鹅投喂饲料。那天大连寒风凛冽,饲料随风飘扬,几只狗对着栅栏吼叫。
被问及为什么养动物,徐渭清却突然说,曾经有老师劝他不要去豫章书院,因为那里都是坏孩子。
23岁的徐渭清常常答非所问。他只有初中学历,脱离校园生活有六七年之久,也没有找工作,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开着工厂、做外贸生意的父母维持。言谈之间,他一再重复在豫章书院的过往。

2023年1月,辽宁大连,徐渭清在家门口喂动物。(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 图)
“跟他沟通太费劲了。”与徐渭清相识多年的贝贝已不太想和徐渭清通话,徐渭清打贝贝的手机,他也不怎么接听。他设置了自动回复助理,结果发现,徐渭清会与助理聊天,问的多是考驾照的事。
贝贝也曾是豫章书院的学生,因为他的举报,书院创始人吴军豹等人的行为才得到舆论关注。2016年9月,在三个多月里历经了被打戒尺、龙鞭等种种后,贝贝终于离开豫章书院。
走出豫章书院的头三个月,贝贝晚上不敢在家睡觉,生怕再被抓回去。即便回家,他的枕头底下也总放着一把水果刀防身,他并不信任自己的家人。
如今,贝贝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托管辅导机构,合伙人教小学语文,他则上些开发大脑的课程。他还在家附近的小区经营水果生意,一周花上一两天找货、拉货、销售、配送,挣的不多,但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足矣。
豫章书院带给贝贝的印记难以抹去:他很少在家住,觉得家里没有什么安全感;因为在豫章书院时喝过洗衣液,他得了反流性食管炎,稍微吃多就会吐。但时间抚慰着他,他越来越少地想起在豫章书院的经历:“我现在可以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去聊以前发生的事儿,这可能就是走出来了。”
然而,贝贝对徐渭清始终怀有愧疚——2016年,当徐渭清的父母询问贝贝豫章书院内部情况时,在教官的包围下,他说了一些好话,这间接促成徐渭清在贝贝之后进入豫章书院。贝贝一直不知道,徐渭清对此事怎么想。
2023年1月15日,贝贝得到了答案。就在前一天,徐渭清说,自己能够理解贝贝当年也是被逼无奈。听到南方周末记者的转述,贝贝松了口气,“那我还是挺高兴的”。
2
“别人看我跟看怪物一样”
豫章书院岁月,在徐渭清的回忆中反复变幻色彩。某些时刻是令人厌恶的:总有人动他的日记和学习资料,还有老师对他说“奇怪的话”。但很多时候,他又记得不算难捱,甚至怀念起在里面交到的女生朋友。
但在徐母看来,徐渭清那段日子并不好过。那时,她每个月都会去看儿子,儿子每次都对她说:“妈妈,我要逃跑。”贝贝也很难相信徐渭清能交到女生朋友,因为豫章书院的纪律对男女交往管理非常严格。
在豫章书院待了半年后,徐渭清离开了。徐母发觉,回家后的儿子“(原先的)刺激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了”。去之前,他还只念叨中考的事儿;离开后,挂在嘴边的话又多了吴军豹与豫章书院:“天天就是在(说)不能原谅,天天就叨咕这些”。
仇恨开始在家庭中蔓延。“接回来之后,(他)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徐母说,她与丈夫曾尝试排解儿子的情绪,刚出来的一两年里,两人带着儿子四处旅游,可即便人在旅途,徐渭清的心也没能走出豫章书院的铁网。“你到哪去,他都寻思这几件事。”
曾在2017年被送入豫章书院的张乾元,离开后则总是心怀恐惧。他害怕“别人看我跟看怪物一样”。
那一年,因为贝贝的举报,豫章书院被媒体曝光。张乾元被母亲接出书院,此后辗转在黑龙江、山东的几所高中就读。一开始,他向新朋友介绍自己在豫章书院待过,朋友都不信。后来,朋友发现他所言不虚,便会把他乃至整个家庭都视作病态,“感觉我是那种混社会的坏孩子,或者说我家里人脑子也不太正常”。
张乾元感觉自己变得极为暴躁,“一点就炸”。高中老师因为他早读时看自己的书批评他几句,他就站起来,贴着老师的脸开骂;还有一回,老师没收了他的烟,张乾元情绪上来,与老师打了一架,险些被开除。
张乾元与母亲的关系也在持续崩塌。他喜爱篮球,进入豫章书院前曾想走体育生的道路,但母亲不认可,说法是体育生要么学习不行,要么就是家里“啥也不衬”(北方方言,即经济条件差)。那时,母子隔阂已然产生。
在豫章书院熬了几个月,张乾元更是与母亲渐行渐远。回到高中后,他考语言、刷学分,申请上了国外一所学校,但心中没有什么成就感,“我压根就不想学习,不想靠这种方式上大学”。在大学里,他除了要生活费,几乎不与母亲联系。他始终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一点也不后悔给我送进(豫章书院)去”。
3
父母的道歉
许多豫章书院的学生在回归家庭后,都不知如何面对将自己送入书院的家人。
离开豫章书院三个月后,贝贝夜里依旧不愿回家,搬到了心理咨询师的家里居住。他没有为借住付过钱,他猜测,也许是母亲给了咨询师不少钱。
相处时间大大减少,父母也不再如进入书院前那般逼迫患有抑郁症的他返学。可龃龉仍在,贝贝曾试图告诉父母书院内部实情,父母总是沉默以对。
在一个贝贝都已忘却的时间点,双方再次争吵起来。贝贝质问:“你们为什么要送我去书院,知道我在那儿遭遇过什么吗?”父母突然答道,当初这样做,是他们不好。那是父母第一次道歉。
父母的歉意没有成为僵硬家庭关系的转折点。直到2017年,接受一年心理咨询治疗的贝贝重返校园并住校,一周仅有一次的返家隔断了许多矛盾。

2023年1月,辽宁大连,贝贝在海边。(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 图)
那段时间,贝贝也曾试图在网上举报豫章书院,但帖子大都石沉大海。转折发生在他与一位网名为“温柔JUNZ”的人结识之际。受到“温柔JUNZ”此前撰写的有关校园教育的文章感染,贝贝将自己在豫章书院的经历和盘托出。
2017年10月,“温柔JUNZ”以贝贝的经历为基础,撰写发布了《中国还有多少个杨永信?》一文。文章迅速引爆舆论,媒体开始跟进报道,官方也宣布调查豫章书院。
豫章书院的负面消息铺天盖地时,徐渭清的父母很少看。“也都知道怎么回事,都已经发生的事了,你说再去恨它?就只能怪自己当时眼睛瞎了。”徐母说,可儿子天天看,“我们不让他看都不行”,一看就生气。
徐母尝试向儿子道歉,“我们就成天跟他道歉,弄错了,天天哄”。然而,徐渭清却记不得这些事情,“我父母没有因为这件事跟我道歉”。
不是每位豫章书院的学生都能等来父母的道歉,潘濬就没有。舆论讨伐豫章书院时,已离开两年的潘濬正处在无所事事的空白期。他猜测,父母并不了解豫章书院的所作所为,始终觉得是把自己送去“锻炼了一下”,因此未有悔意。
2015年被接出豫章书院时,潘濬15岁。进入书院前,他有“网瘾”,常常从早上起床开始打游戏直至凌晨;家中父母管得严,一度把电脑给砸了,潘濬就去网吧。
离开书院后,他害怕了一阵,担心再被送回。可没过多久,他就故态复萌,没回学校,平日里靠上网或是去酒吧消遣。经历了豫章书院的8个月后,本就不爱读书的潘濬“更不想读书了”,“什么都不想干,就想玩”。
父母感慨豫章书院没什么效果,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状态,同意他成年后再去工作。潘濬因此有了一段三年的空白期。可这段岁月并不平静,父母常因潘濬无所事事而骂他。
南方周末记者提出采访潘濬的父母,被他拒绝:“我爸妈不喜欢提这个事情。”
“我不想再去回忆它了。”潘濬也选择不再关注豫章书院的事。成年后,他子承父业,在父亲的装修公司上班,朝九晚五。他与父母的争吵渐渐消失,“父母觉得我去上班了,看到我的动力了,然后也开心了”。
4
“心里肯定有怨气”
在另一些家庭,关于豫章书院的回忆始终是隐秘而慢性的疼痛。
三次进入豫章书院的朱生良是2017年最后几批离开的学生之一。他回忆,每重新进入一次书院,他就在“变坏”的泥淖里越陷越深:第一次只是因为成绩不好,喜欢打游戏;第二次进去,他开始离校出去玩,文身。后来,他变得厌学,甚至学着书院里面的学生吸过一回某种药物里的粉末。
但朱生良的父亲不后悔将儿子送入豫章书院。每当谈起儿子,朱父总会加上一句,“怎么说呢”。当年,为了给儿子戒除网瘾,他在江西考察了七八所类似的学校。他清楚这些学校难免打骂学生,但“有的时候打一下、骂一下,我觉得也正常”。他最终选择豫章书院,是因为看它“正规”,打骂没有那么狠。对于豫章书院被迫关门,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学校要负些责任,可不同的人对其教育方法的接受程度也不同。
儿子进入豫章书院后“变坏”了吗?“说不上来。从现在来看也没什么感觉。”在朱父的记忆里,无论哪次离开书院,儿子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儿子另一些细微的心境,同样未被朱父察觉。当年被父母“骗”入豫章书院的经历让朱生良变得多疑,多年后与女朋友相处“疑心也很重”。他时不时做有关豫章书院的梦,梦里,他依然被关在书院中。
重获自由后,朱生良没有再回学校,而是谈起了恋爱,又在全国四处旅游。两件事花销不小,他没有进项,就找父母要钱,一个月要六七千元。若不够就接着要,“不给只能硬逼着他们给”。
虽说对父母有经济依赖,但父子之间的关系始终冷淡。“我也是挺怪我爸的,因为真的没有必要把我送去那种地方……心里肯定有怨气。”
朱生良抱怨父母不理解自己。他曾让父母给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但月薪三四千元的工作他看不上,也不愿给人打工。朱父觉得为难,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
后来朱生良又有了开家游戏陪玩店的想法,让父母借他十几万元开店。朱父觉得彼时儿子尚不成熟,拒绝借钱。他长期在外做生意,对儿子的管教并不多。“我觉得还是我们没管好。”
“他年纪也大起来了,他实实在在想要的,父母总要支持他吧。”2023年3月,朱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一年,24岁的朱生良终于在父母的投资下,开了一家水果店。那或许是父母尝试理解他而迈出的一步。
5
难解的心结
2023年年初,一款以杨永信的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等为背景的游戏《飞越13号房》上线。游戏中,玩家扮演一名“叛逆少年”,被送进行为矫正中心,在一次次抉择中,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蛰伏调查中,发现背后层层的秘密。
张乾元玩了这款游戏。面对游戏里家长被机构蒙蔽的情节、母亲送孩子去机构时冷酷的脸、教官体罚学生的画面,他说自己强行忍住了眼泪:这几乎是他过往生活的复刻,他太熟悉了。
在离开豫章书院的第五年,张乾元渐渐控制住了自己暴躁的情绪,多年来向他人倾诉书院往事帮着他解开了些许心结。但倾诉往事也意味着袒露过去,于他而言,进过豫章书院如同在监狱服过刑,是一种污点,也是一张难以撕去的标签。
往事带来的是耻辱感吗?张乾元说不清,可他总是不断设想,如果当初没有进入豫章书院,他会拥有的另一种人生。
豫章书院带来的创伤和纠纷,也让贝贝的人生彻底转向:回到高中后,贝贝过不惯集体生活,他想,这或许与书院经历有关,报案、接受媒体采访也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两者影响着学业,他最终放弃了高考。
2019年,“温柔JUNZ”再次撰文,曝光了豫章书院关门后的两年里,许多帮助学生维权的志愿者遭到威胁的境况。彼时,贝贝已经成年,他决意以受害人的身份,成为豫章书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之一。当年年底,豫章书院创始人吴军豹、校长任伟强等5人被批准逮捕。
2020年7月7日,豫章书院案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吴军豹等5人犯非法拘禁罪,但驳回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2021年12月,此案由南昌中院发回重审。

2020年7月,豫章书院的墙上还留有一些训诫标语。(陈劲 / 图)
2020年7月的宣判结束后,贝贝坐车离开法院,车上放着歌曲《曾经的你》。有记者问他,对判决结果满意吗。贝贝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声中有不甘。
但豫章书院内幕能几次引爆舆论,已经超乎贝贝的想象。在这件事上,他自认为已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极限。他并不后悔自己曾付出的一切,哪怕这让他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
更多的学生则远离了豫章书院的是非。张乾元不会主动了解诉讼进展,他更大的愤懑在别处。论怨恨,他恨不到吴军豹,“我只能恨我妈”。
张乾元深知,在单亲家庭,母亲一人把他带大并不容易。可这些年,只要母亲一哭,他就觉得母亲多年的努力“很傻”,他记得母亲送自己去豫章书院时都没掉一滴眼泪。他不愿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母亲,不想为本就冷淡的母子关系再添争执。
徐渭清与父母的心结依然难解。2018年年初,徐母将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一所高中求学。儿子住寄宿家庭,她则找了个旅店陪读。
徐渭清厌烦加拿大的求学生活。他不习惯那里的教学节奏,更不喜欢“管得宽”的老师。一次走在大街上,徐渭清突然踹了母亲一脚,“是因为我妈送我去豫章书院”。
“到那(他)还想着豫章书院的事。”徐母感受到,在加拿大,儿子渐渐变得情绪不受控制。有时徐母看见儿子生气了,就躲远些,等儿子给她打电话,她再回去。“后来一看不行了,他一直说想家”,两三个月后,母子二人回了国。
2023年3月,徐渭清与母亲再次来到加拿大,为入读一所职校做准备。徐母说,职校里有一位中国教师,能在克服语言障碍上帮助儿子,儿子也难得地显现出了一些兴趣。
回首豫章书院往事,徐母希望吴军豹能向儿子道歉。徐母觉得,这是解开儿子心结的唯一办法:“有一些事儿,我觉得话说开了,对孩子可能是有好处……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
然而,即使创始人道歉,或许也没有解开心结的魔力,至少徐渭清觉得他并不需要。往事带来的伤痕彼此嵌套,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人知道被豫章书院撕裂的伤口何时才能愈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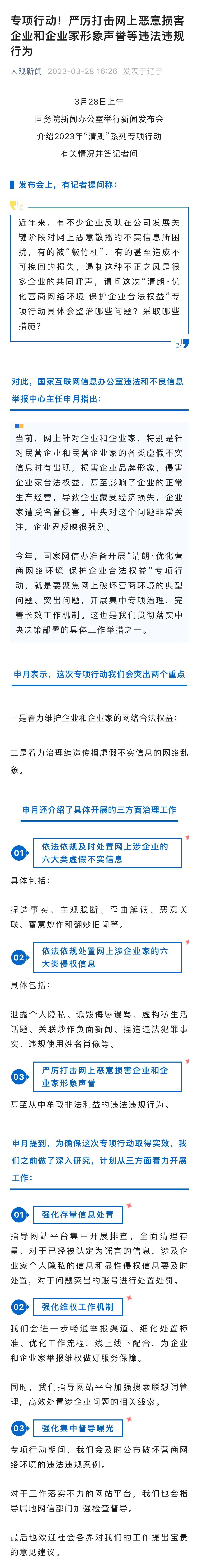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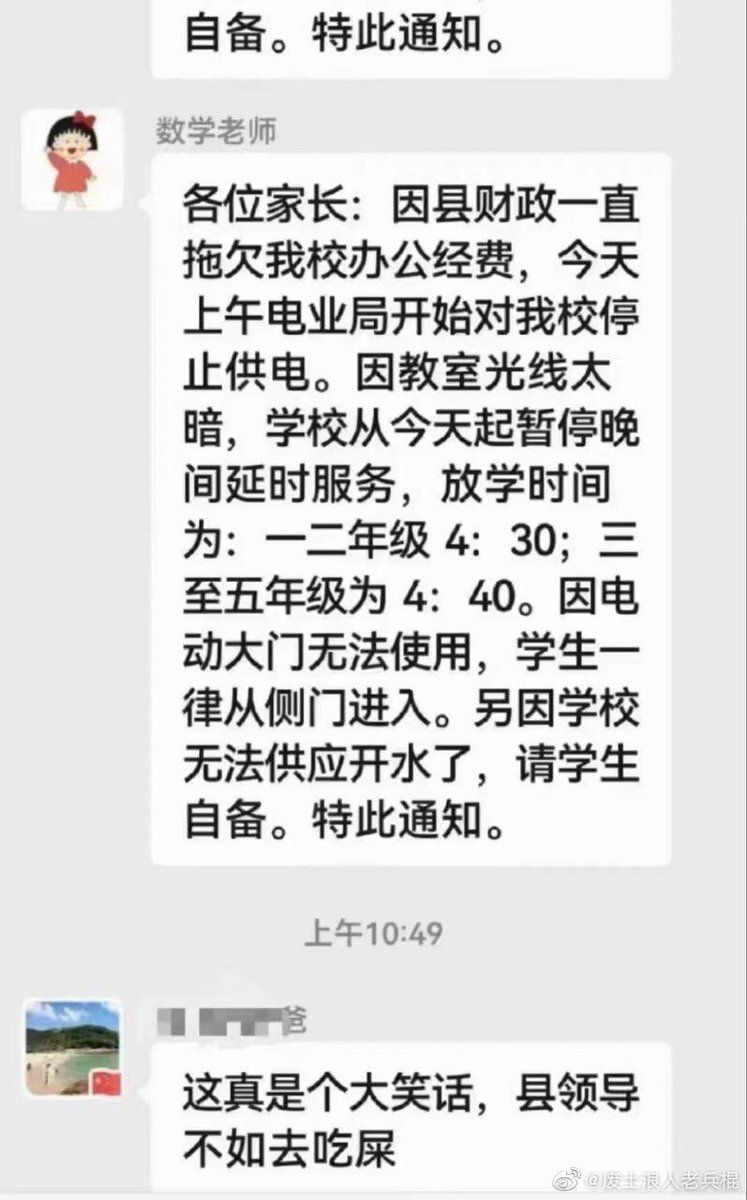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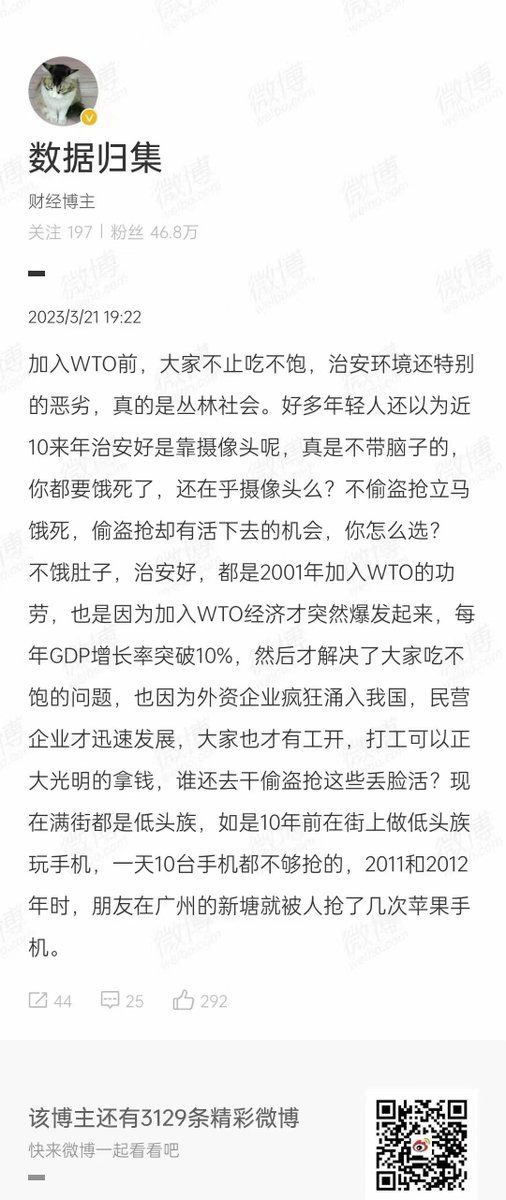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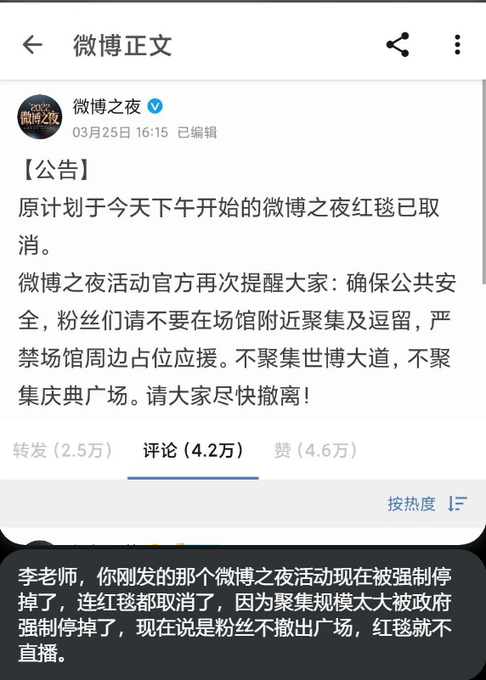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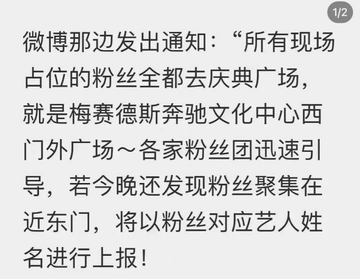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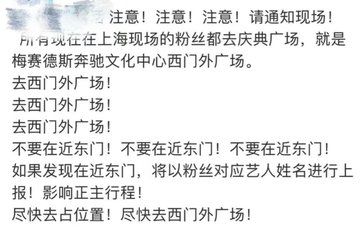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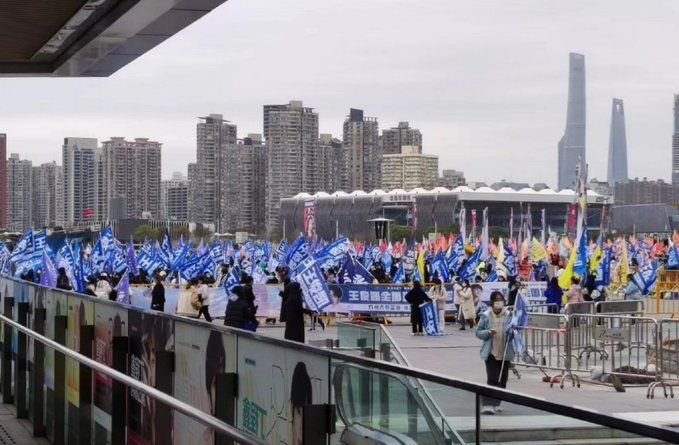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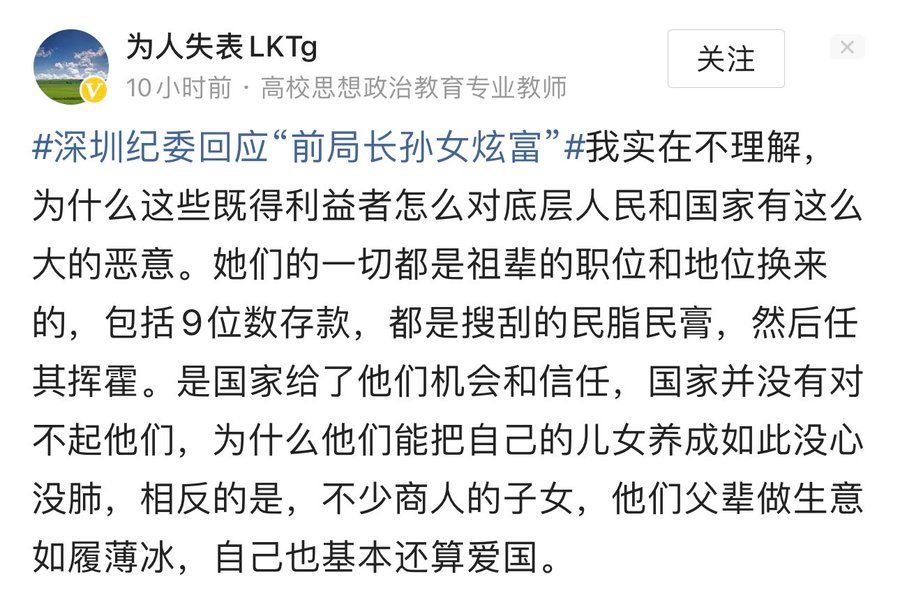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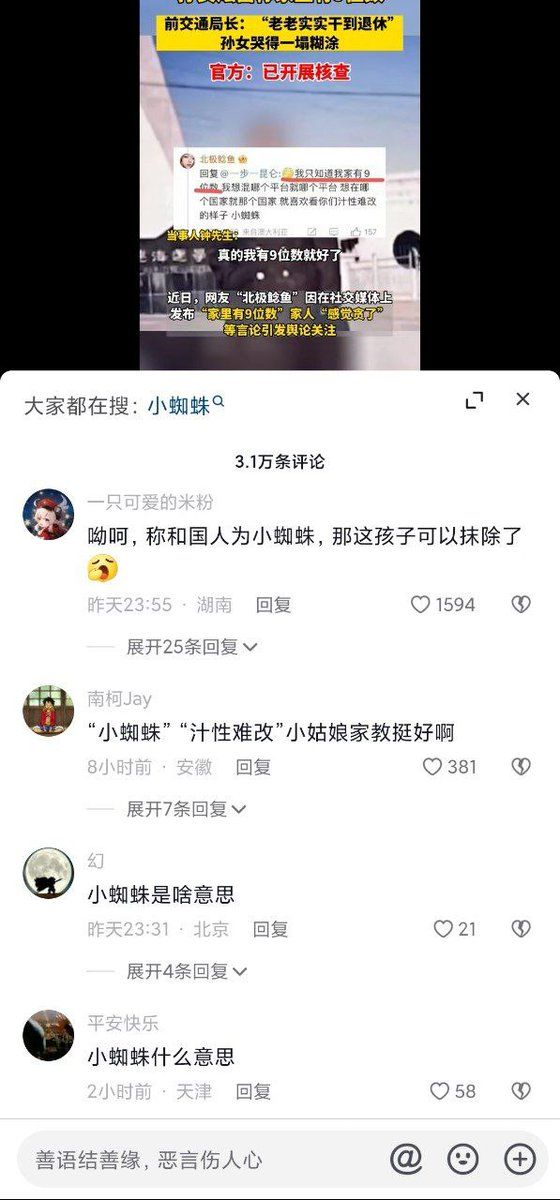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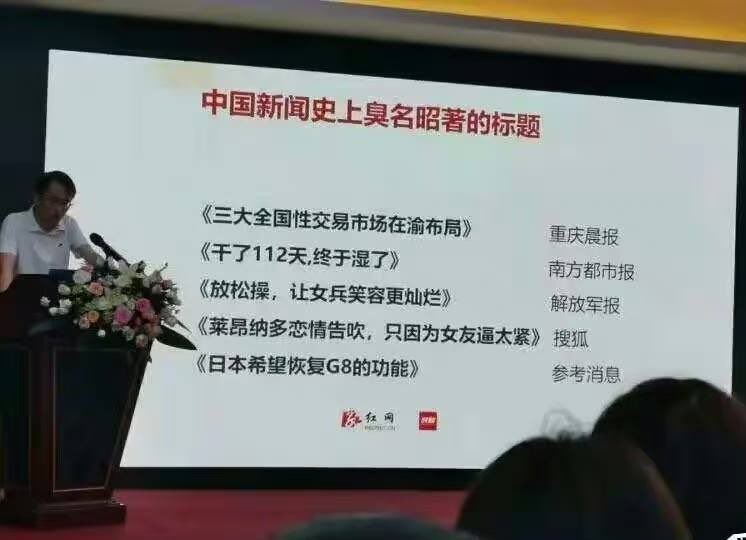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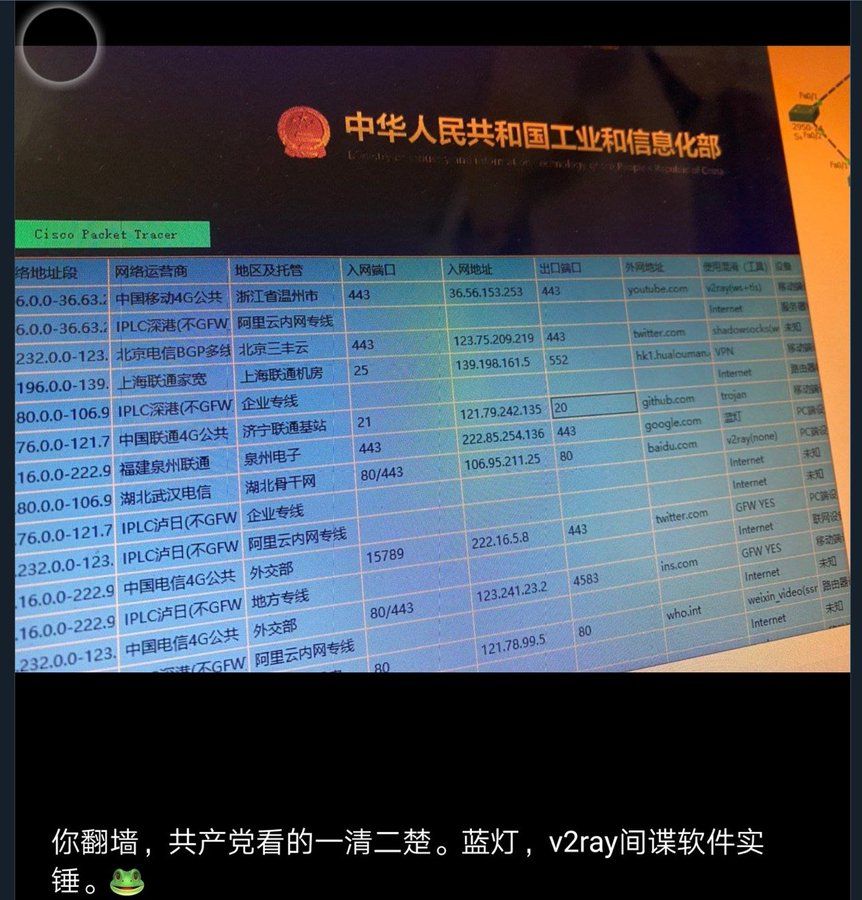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