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书评-通往猴面包树的永恒旅程
几周前我和朋友一起读崔娃的自传《天生有罪》,虽然从未看过崔娃的单场,但是我很喜欢这本行文流畅且诙谐的自传。刷《天生有罪》的豆瓣书评时,我无意点开了一个南非文学推荐合集,在众多南非文学大师的作品里看到了一本名为《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的书。我对南非文学其实知之甚少,只在高中时期读过一些Nadin Godimer的短篇小说,对南非的印象也仅限于曼德拉、Apartheid、广袤的非洲大陆这几个抽象而意义模糊的词。出于对“猴面包树“这个物种莫名的兴趣,我读了Wilma Stockenstrom的中篇小说《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这本书以第一人称意识流描摹非洲奴隶女性的自我探寻之旅,带给我非常奇特的阅读体验。本文是一篇剖析《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主要意象的散漫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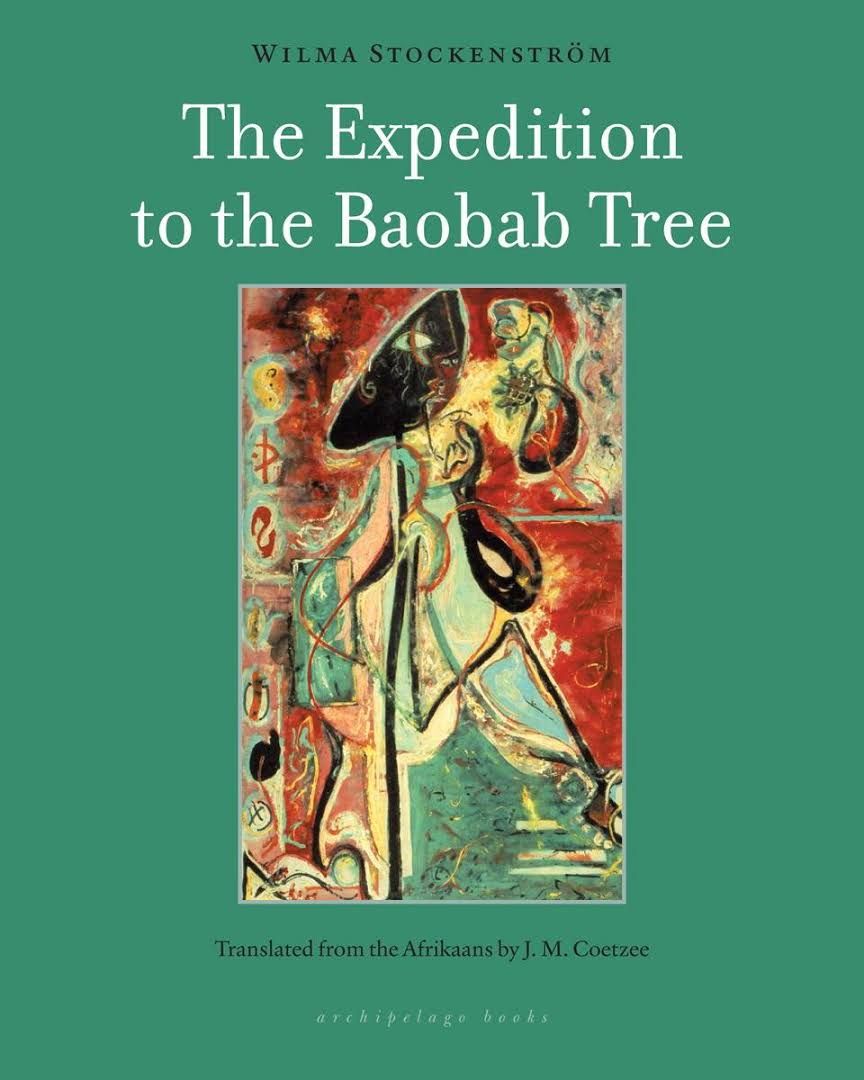
《去往猴面包书的旅程》是一本带有寓言性质的哲理小说。以往我读过的以奴隶制为主题的小说都是纪实文学,塑造的奴隶形象也多是带着浓重口音,心地淳朴善良而无思想深度的人。《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奴隶女性。“我”很少用平铺直叙的语言描述自己充满血泪的女奴生活,而是将碎片化的记忆夹杂在大量的诗歌、戏剧化的吟诵和排比中。书的开篇即是一段喃喃呓语般的自述:
“With BITTERNESS, then. But that I have forbidden myself. With ridicule, then, which is more affable, when keeps itself transparent and could not care less; and like a bird into a nest I can slip back into a tree trunk and laugh to myself. And keep quiet too, perhaps just keep quiet as to dream outward, for the seventh sense is sleep”
接下来的数十页都是诸如此类的晦涩自白,主人公的思绪游离于过去、现时、动物、人性、自然之间,我模糊地知晓了主人公目前生活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共享栖息地和水源,但对她为何孤身流落到野外一头雾水。在阅读了大段灵性的心理、自然描写后,我慢慢拼凑出了主人公的前半生:“我”曾经是一个女奴,幼年时全村被奴隶主掳走,目睹母亲被杀害,随后被拍卖、受割礼,转手于三个不同的主人。除了辛苦劳作生活环境极恶劣外,不断被强暴、生育,每个孩子养育到小腿高度随即又被卖掉成为奴隶。“我“的第三个主人是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因为欣赏“我“的美丽,有意让“我”接受了教育。第三个主人去世后,“我”机缘巧合随着一个商队去内陆探险,寻找一个坐落在沙漠中的石英城,但因为旅途艰险,最终“我”独自流落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沙漠,栖息在一棵倒立的猴面包树中,过上了离群索居的荒野生活。
猴面包树于“我”,既是一个返璞归真的庇护所,为“我”提供了水源、蜂蜜、药物、居所,又代表着“我”精神上的某种归属地。非洲大陆的本土居民饱受殖民风雨侵蚀,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而这种产于非洲的巨大树木却稳固地扎根于干旱的大地上,在残酷的历史变迁中巍然不动。猴面包树的存在几乎是永恒的。在殖民和奴隶制的语境下,“我”通向猴面包树的旅程,是一段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之旅。在出走前,“我”是一个破碎的、不完整的存在。“我“的身体因割礼、强暴、生育被撕裂,“我“诞下一个个孩子但又被迫与他们分离。而比肉体痛苦更甚的是存在的虚无。“我“敏锐地捕捉到了自己并非被视为人类,而仅仅是一件可被贩卖替代、可有可无的商品。面临着死亡和消逝永恒的威胁,“我”的自我意识觉醒了。
“I have already tried to imagine a kind of existence in which I was not a possession, but it did not come easily to me. What would become of me in the land of my origin? Would I, for example, have walked, sat, stood differently? Would I have entered into other kinds of friendship, accepted wholly different opinions? Would I have clung to religion? Would I have had a husband, and children by him only? Children I would have raised till they could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居住在猴面包树的树穴里,“我”以真菌野果为食,用鸵鸟蛋饮水,和猩猩、大象等兽群共生。在威尔玛的笔下,正因回到了荒野,远离了种种人类文明,“我”才得以找到真正的自我。每当“我”走出猴面包树的树干,凝视着不断后移的地平线,才重新感到自己是一个人类。在猴面包树的腹中,“我”重生了。脱离了奴隶制、父权和殖民主义的重压,“我”生平第一次得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威尔玛的意识流叙述淡化了“我”为奴时被虐待的具体遭遇,而将焦点汇集于“我”受困时的主观感受。我在阅读的时候常常感受到,“我”经历的困境表象为一个南非奴隶女性被如何剥削虐待,而其内核是一种人类、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永恒的存在主义危机。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常常因为个人化的消费主义,错觉自己拥有许多自由和选择,但剥丝抽茧我们拥有的所谓“自由”,剩下的不过是些后浪们能享受的消费娱乐泡沫。撇去具有时代特殊性的社会机制不谈,每个人类也仍是死亡、时间、劳作的囚徒。《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探索的核心是,背负着”文明”重压的人类,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是一本越读越渐入佳境的书。逼迫自己啃完开篇十几页艰深的自白后,我完全沉浸在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里,跟随着她一起思考生而为人/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不自由。在我看来,意识流的叙事美学很符合本书这样的女性主义文学题材。在西方哲学与主流思想中,理性是性别化的,换言之是一种专属于男性的品质。这种对于理性的构建强化了男性与女性、文明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意识流的叙事摈弃了以男性视角为主体的理性主义,强调个体的经验。人虽然仍在传统、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但个体对世界的认知却来源于直觉和感受。在《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中,“我“认为自己的实质是水,可以流动成许多不同的形态。“我”体中的羊水养育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又在浪潮般的阵痛宫缩中,将生命源源递送于世上。在经年累月的虐待下,依赖着灵性的认知和世界观,“我”得以维护人格和精神的健全。
威尔玛杂糅了诗歌、戏剧、小说的意识流文体,展现出了极少被描绘关注的非洲奴隶女性的精神世界。女奴生活的血泪和生而为人的种种困苦,被诗意的吟诵排比、充满了智性哲理的思考稀释了。碎片化的旅途回忆和流动的自我意识交叠着,读来让人感受到沉闷而钝的痛苦,但字里行间又有一种奇异而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南非这片土地才能孕育出的文字。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