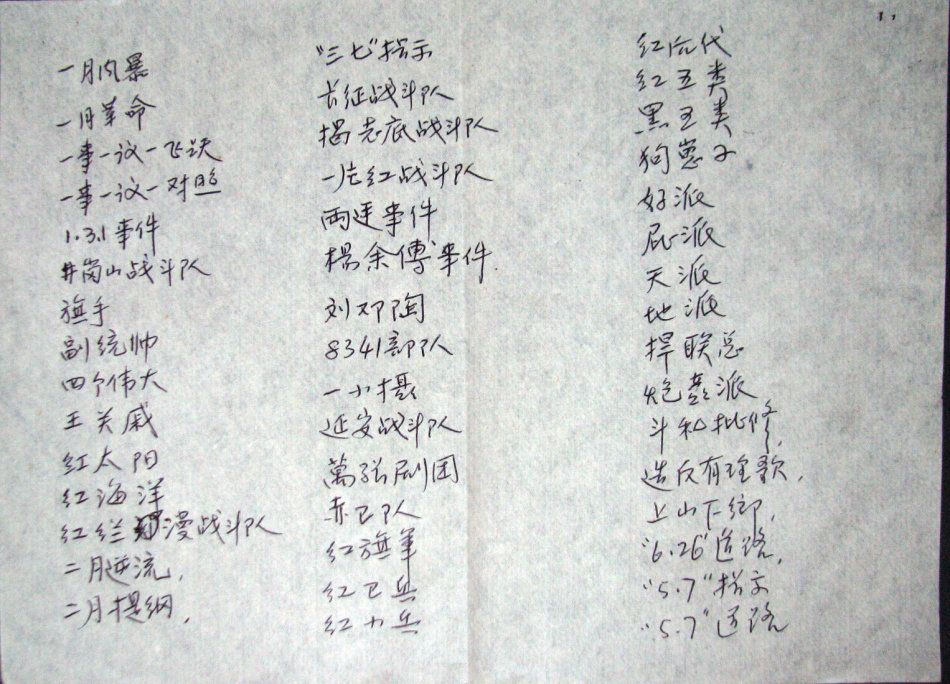
对49年以后中国历史感兴趣,鉴于中文互联网有关的记忆和记载正在被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移除,本博主要用作收集网络“垃圾”,“拯救”网络记忆和记载,可能偶尔会有点原创,稍微会转一点资料性强创见多的不被主流刊载的学术性文章。另外,凡华夏文摘刊登过的文章一般不cross post,当然也会有例外,视情况而定。
王莹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 ──刘绍唐的「传记」人生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劉紹唐的「傳記」人生
1996 / 8月
文‧王瑩 圖‧卜華志
一個人盡其所有做一件事情,並且連續做了三、四十年,會有什麼樣的成果?
文學泰斗梁實秋窮四十年的功夫譯出《莎士比亞》全集,成為國內研究西洋文學者的聖經;劉紹唐則蒐集整理了上億字的第一手史料,為國史上最具爭議性的時代,砌起一座「民國史長城」。
與硬梆梆的史料不同的是,不管自己是否為故事主角,它所報導的絕大多數是當代人自己的親身經歷,內中有著英雄血淚,梟雄事跡,更有著無數小人物的時代見證。因此,它能貼近一般人,容易引起共鳴。多年來,許多人從讀者變成作者,而「傳記文學」也得僅憑一老編之力,不靠廣告、沒有補助,毫無間斷地出版了三十四個年頭,被視為台灣出版界的奇蹟。
日前文建會頒了一個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給傳記文學社的社長劉紹唐,致詞時他感慨地說:「這是一個肯定、一種平反,也是一個遲來的榮耀。」
雖然他並未公開闡釋究竟所指為何,不難想像戒嚴時代數十載下辦一個記錄與針砭當代人物的刊物之辛酸。
歷史不可留白三十四年前,民國五十一年的六月,「傳記文學」誕生,集發行人、社長與總編輯於一身的劉紹唐剛滿四十歲,豪氣干雲,在發刊詞中一語道破中國自太史公作史記以來即乏傳記佳作的遺憾,也點出在那個還有文字獄的時代知識份子的顧忌:
「中國人提到寫傳記,要用自己的筆寫自己,就不免有些緊張……原因何在?簡單來說,不外兩端:一是自己寫自己,『為賢者所諱』──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傳之譏。也『為智者所諱』,寫自己難免要涉及同時代的政治,更難免要涉及到同時代的人,褒貶論斷,可能惹起許多無謂的糾紛──因此造成了我國歷史上的許多空白。」
當時,倡導傳記文學最力的是近代大思想家胡適,他任北大校長時劉紹唐正在北大念歷史系,對校長的崇敬加上對歷史的熱愛,種下半輩子致力於傳記文學事業的根苗。
胡適提倡傳記文學相當徹底,不但自己寫、勸人寫,同時到處演講,宣揚傳記文學的重要。劉紹唐還清楚記得,老校長在民國四十二年應邀到師大演講,以「傳記文學」為題講了足足九十分鐘,一再強調:「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就是傳記文學。」
那天聽眾中有心人不少,「傳記文學」創刊第二期中就有師大教授杜呈祥為文詳釋「傳記與傳記文學」的不同,文中述及當天胡適演講的大要,還呼籲主辦單位師大重新聽演講錄音帶,逐字錄出這場重要的演說。然而真的聽到骨子裡,決定以此為終身志業,把老師的言語化為億萬字行動計劃的,大概就只有劉紹唐一人。
本是傳奇人物其實,劉紹唐在那個時候已有相當名氣,他在共產黨進入北京不久後剛好自北大畢業,東北家鄉早已淪陷,許多同學、朋友也都已逃離北京。為了解決實際生活,他參加了中共的「南下工作團」,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學習」,就被分發到龐大的宣傳機構「新華通訊社」做記者,後來隨軍南下,又調到「第四野戰軍總政治部」裡工作,一年多的工作經驗和局勢觀察,讓他感覺到極權統治的危機與威脅,於是設法逃亡。
當時中共初初接收大陸,還在收服人心,尚未施出鐵腕,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展開,知識份子的浩劫於焉開始;幸運的是,劉紹唐已在五○年初逃到香港,並且把他在新華社和野戰政治部工作的所見所聞寫了六十一篇短文投到「中華日報」刊出,不久還出版單行本《紅色中國的叛徒》,在香港和台灣都很暢銷,一連出了好幾版,劉紹唐的名氣也不逕而走,成為青年反共作家,倒是他寫文章時始料未及的。
眾所周知,本來在國共內戰後期、中共佔領大陸之初,美國在馬歇爾和史迪威主導下的對華政策相當偏袒中共,未料隨即韓戰爆發,中共與美國在韓國戰場正面交鋒,台灣的政治立場和戰略地位頓成遏阻共產勢力在東亞擴張的重要據點,一時之間,美國全球反共政策既訂,反共也成為世界之主流。
劉紹唐以中國知識青年在中共機構的「學習」和工作經驗現身說法,篇篇都是第一手報導,大受當時自由主義盛行的美國學術界青睞,除了美新處的一本當年極為暢銷的中文雙週刊「今日美國」自行轉載外,紐約大學的兩位教授合力將其濃縮譯成英文,在紐約、波士頓和多倫多同時出版,由胡適作序,美國駐華大使館還寫通函到處推介;後來乾脆由美新處主事,陸續翻譯了包括日文、韓文、泰文、印度文、阿拉伯文及德文等十數種語文版本。
由於轉載並未事先告知作者,後來美新處還向劉紹唐買了一萬本中文版原著以為補償,他也因此很發了一筆小財,有人以為這就是他後來拿來辦傳記文學的「老本」,但劉紹唐說並非如此,因為他當時未成家,又一向愛交朋友,手頭寬鬆慣了,雖然五、六萬的「版稅補償金」當年足可買棟不錯的房子,卻被他不知不覺地很快花完了,後來辦「傳記」,其實是無本生意。不過他這塊國際聞名的反共金字招牌,在後來辦「傳記文學」時言論尺度大膽卻未遭大忌,可能多少發揮了點作用。
也是因緣際會從胡適力倡「為史家找材料、為文學開生路」的傳記文學,同時自己寫了一篇至今被奉為傳記文學經典之作的「四十自述」,到劉紹唐一頭栽入這令他著迷一生的傳記事業,還是有著一番因緣際會,其間也不是沒有幾許掙扎。
劉紹唐生長於白山黑水的東北遼寧,十歲時遭逢「九一八事變」,父親將他送入關內,從此開始了他巔沛流離的青少年生涯。
或許因為少年時就親身經歷國族的大動亂時期,他一直對大時代的歷史故事充滿興趣,「七七事變」時,他年僅十六歲,尚在中學念書,好不容易捱到抗戰後期,考入北大、清華、南開大學在昆明聯合招生的西南聯大,接觸到當時三校中如吳琀、劉崇鋐、雷海宗等華北歷史名宿,對治史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治史最需要的就是史料,史料就是人與事的紀錄,戰爭中人與事渺不可測,隨時都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除非有人有心將其記錄並保存起來,這樣的想法不時浮現在劉紹唐的心中,只是沒想到那就是他的使命。
抗戰勝利後他被分發到北大,雖然當時中共勢力已逐漸壯大,職業學生很多,北京城學潮不斷,劉紹唐仍然深深懷念那段在他一生中難得安定的求學生涯。當時教他或常對學生演講的代校長史學巨擘傅斯年、校長胡適,以及來台後他追隨了五、六年的恩師、也是史學家兼教育家的崔書琴,在在都影響著他的一生。
從香港來台後他就一直跟著老師崔書琴作助理,崔先生當時在台大教書,心胸豁達,黨、政、軍,以及中外學術界都有豐厚的人脈,劉紹唐也因而經常和這些學者耆碩、政壇大老多所接觸,每每在吃飯或隨性的閒聊中聽到許多精采絕倫的故事,憑著新聞記者敏銳的嗅覺和歷史學者精細的眼光,他常有一股衝動想要把它記下來,可是一拿出筆他們就不肯多談,平時工作很忙,一個人單憑記憶也記不完這許多,雄心一發即逝,但這個念頭卻始終沒有斷過。
惶惶不可終日幾乎沒有什麼預警的情況下,崔書琴在不到六十歲的盛年,因不知名的濾過性病毒感染而突然去世,劉紹唐本來孑然一身,原來跟著博學多聞又愛朋友的老師,簡直如魚得水,既有興趣盎然的工作,又有結交不完的朋友。當時也在台大教書、和崔書琴私交甚篤的美籍同事兼鄰居哈佛客座教授吳克博士,就對劉紹唐印象深刻——他常在崔書琴家幫師母帶小孩。
吳克研究的是中國御史大夫制度,也是個堅強的自由主義信徒,對共產黨那一套「畫餅充饑」的「人民萬歲」完全不買帳,所以和曾在共黨陣營「實習」失敗的劉紹唐很談得來。他後來在雷根時代官拜駐韓大使,可是對台灣和他的學者老友一直念念於心,退休後經常到台灣,今年五月才來過一趟,找到劉紹唐大談往事,還請劉紹唐陪他去給外交才子葉公超和新聞才子魏景蒙上墳,人家笑他比中國人還中國,他瞪大眼睛說:「我本來就是中國人啊!」。
回到當年,崔老師一走,劉紹唐本來只恨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的豐富人生突然就多出了二十四個鐘頭,只覺惶惶不可終日,一陣子跟著朋友去打麻將,卻始終培養不出對這「國粹」的興趣,又想自己才三十來歲,難道就這樣混日子?越想越不甘心,可是平日在一個國防部辦的雜誌裡兼差,衣食並無顧慮,真正想念的還是跟著崔老師聽故事、整理資料的日子,那不就是胡適說了又說,卻還未獲文史界響應的「傳記文學」嗎?
初生之犢?劉紹唐為自己重拾人生方向正感欣喜,立刻開始籌備工作,整理身邊已存的大批資料,找學者支持,並且趕快去報告在台主持中研院的老校長這個好消息;不料,知道辦雜誌不易、尤其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更難的胡適雖感窩心,卻不表鼓勵,反而提醒學生辦雜誌面對的是無休無盡的截稿期,稿源難以為繼、財源籌措不易,還有更重要的,做為史料,真實正確最為重要,一期稿子那麼多,蒐證工作馬虎不得,萬一來不及怎麼辦?再加上民國五十一年的台灣,根本可說是一片文化沙漠,知識份子最大的購書處是牯嶺街的舊書攤,而歷史是個冷門科目之外,當代史很可能開罪權貴,搞不好還得坐牢,他的老友雷震以國民黨重臣的身分都因為辦「自由中國」被送進了大牢,小小的一介書生劉紹唐怎能冒險?
劉紹唐本人倒沒想那麼多,他知道老校長支持他的理念,實際方面他也已經找到毛子水、臺靜農、查良釗等大師級的學者支援,沈剛伯、陶希聖、凌鴻勳、蘇雪林、梁實秋、梁寒操等數十位名家也都答應供稿,當然要奮力一搏,若是真有一天稿子不夠、錢不夠辦月刊,就辦季刊,胡適覺得也有道理,就這樣得到真正發起人的贊同。劉紹唐一向是說做就做的個性,只是史家的訓練和自小漂泊在外的歷練也給了他凡事謹慎策劃的習慣,既然東風已至,「傳記文學」在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創刊,首印四千本,唯一遺憾的是胡適並未親眼看到雜誌出版,大師在是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中研院猝逝,留下無限的追思和後來傳記文學中無數佳作。
一炮而紅,洛陽紙貴文化沙漠中的念書人大概早就饑渴已久,「傳記文學」創刊號中除了編者十分大氣魄地昭告天下讀者「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或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而「只要與時代不脫節、足以反映時代或為時代作見證者人人可寫。」當然,傳記文學的第一代作家幾乎人人都是名家或是名將,文筆好、見聞豐、又背負了那個時代許多人共同的記憶,所以甫一發行就賣光了,趕忙再加印一千本給外埠來郵購的讀者,這一炮也奠定了百年的根基。
現在不過六十出頭、當年即以「少年詩賦動江關」的才子李敖也是第一代的傳記文學作者,據劉紹唐說,在第一屆老國代下台之事成為眾矢之的的那個年代,李敖有一次打趣「傳記」,說是老國代的長壽健康之道有二──一是榮總保持身體康泰,二是傳記護衛心靈不減。很多人也以為傳記的讀者大概也和書中人物差不多年紀,才特別愛看「天寶遺事。」
其實,傳記的讀者無論在年齡層或地區上都分佈得相當廣,據自第一天發行起就和劉紹唐共甘苦、卻被幽默的老公形容為「最大長處是雖無助力、亦無阻力」的劉太太說,傳記文學確實有許多老讀者、老訂戶,但三十多年來世代交替,讀者也並不見減,可見對歷史鍾情者還真不少。
讀者都是老翁?念台大時起就每期必看「傳記」、並自承所獲甚多的新聞局官員魏蔭駒,就自己多年看這本雜誌的心得分析,對「傳記文學」有興趣的讀者,一定是喜歡讀史、對近代史有相當概念、某些看法,同時關心所處的這個大時代的人,從「傳記文學」刊載的當事人的經歷當中,可以看到一個事件的血肉、感情和深度,歷史因而活了過來。
他記得是在念大一時開始看「傳記文學」,當時言論尚未開放,而傳記的尺度已經相當大膽,史料比學校教的歷史豐富、周延許多。當完兵之後考入新聞局,被派到南非進修英文,他把月薪存起一半,回台北後就把「傳記」合訂本一次補齊,後來派駐國外時也是如此,一回國就去買合訂本,補齊收藏,他認為這是當今世上唯一值得收藏的雜誌。
至於看「傳記」有沒有具體的好處?魏專委說當然有,而且不勝枚舉,「傳記」中所載,無論是王公貴冑或是販夫走卒,都有其精采之處,有的可學習、有的須借鏡,看大學者如何治學、看軍士將領如何研判軍情、看外交家如何折衝樽俎,以至於鄙陋小人如何誤事、誤國,甚至誤盡天下蒼生。「一部春秋史,千年孤臣淚」,「傳記」的天地遼闊,真是難以一語道盡,不過光是對他在工作上的幫助就很值得談。
舉一個較特別的例子,記得早年新聞局國際處的副處長陳宗堯,英文一把罩,本身是哥倫比亞大學近代史博士,很有學術地位。一回在台灣開「中國近代史研討會」,請他也提一篇論文,陳宗堯請幾位同仁幫忙蒐集資料,他自己則專門去找英文資料。
魏蔭駒清楚地記得那次的主題是袁世凱,他把「傳記文學」中所有相關資料都收齊,分類後交給長官,結果陳宗堯寫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論文與會,資料中最齊全的就來自「傳記文學」。
史林高手,洞燭機先這次的經驗使魏蔭駒對傳記文學自興趣提升到學術層次,有一陣子很想去念歷史,準備未來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去工作,但他在該所作研究員的好友張力勸他打消此意,因為真正的研究工作枯燥不堪,速度奇慢,十年前作的口述歷史沒整理出來的還有一大堆。
近史所所長陳三井則認為,劉紹唐在三十幾年前辦這本刊物,並且維持水準至今,用的雖然不是傳統學術研究考證歷史的方法,但對中國現代史的貢獻是無法衡量的。他搶救下無數第一手的資料,包括手稿、照片、文件和個人的記憶,喚起許多人對歷史的感情,投入研究、寫作等積極的參與工作。
傳記文學亦史亦文,劉紹唐曾說:「中國傳統其實是文史不分的,所謂六經皆史,我覺得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就是史料學,假如沒有史料,那麼歷史就無從研究起,而傳記文學和歷史學、史料學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文學家不承認傳記文學屬於文學沒有關係,史學家可不能不承認這門親戚。」
正宗近代史大家陳三井不但推崇劉紹唐「功在史學」,並且還評估傳記文學雜誌的成功要素有三:一是速度快,和正統歷史性刊物簡直不可以道里計,更不似中研院的一個研究費時經日,產量自然很少;二、具前瞻性,能夠「洞燭機先」、蒐到可靠新史料時即可隨時再開拓研究領域,不像學術研究,一個人抱著一個題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考據、蒐證,不可能臨時換跑道、開新域;三、能夠呼應時代的脈動,與新聞事件相關時非常機動,可以滿足讀者的求知慾。
當然,在這三點之上,最基本的要件還是史料的正確性和文章本身的深度,陳三井認為傳記文學在這方面十分嚴謹,所以他不甚同意外界封劉紹唐為「野史館館長」的稱呼。以治《胡適口述歷史》和《李宗仁傳》而享譽國際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也是劉紹唐和傳記文學社中編輯人員最敬佩的老作者唐德剛,也認為劉紹唐不是什麼「野史館長」,而是「中國史學界兩千年來私修國史的傳統下,當代最有成績的接班人。」
唐德剛治學深入、頭腦靈活,是胡適「不疑處有疑」的治學方法最佳詮釋者,對這位舉世推崇的一代大師,唐德剛仍然堅持奉行胡適哲學,常常質疑胡適的論斷,自稱「三七論」,對胡適學說三分接受,七分懷疑,為此還被文壇耆老蘇雪林罵作「猶大」。但他對劉紹唐的邀稿本事卻佩服得五體投地。
誘人入殼記得最初傳記向他邀稿時要他把「胡適口述自傳」譯成中文發表,但他覺得把自己的文章再翻譯一次實在太無趣,毫無創作的喜悅可言,於是斷然拒絕。劉紹唐並未勉強他,只提醒他說,「找其他人來譯也可以,不過總得找著名史家才行,萬一譯得不合你原意,我們也不能說,到時你的作品弄砸了可怎麼好?」唐德剛一聽有理,馬上乖乖地去訂了一部微影片閱讀機,準備翻譯,但沒想到機子寄到還要一陣子,這時劉紹唐的長途電話又來了,「雜誌已經給你預留了版面,你先寫個序言,談談當年採訪校長的花絮好了!」於是唐德剛開始動筆,用他已好久不用的中文一個字一個字地弄出一篇文章。可是閱讀機卻還沒有到,劉總編再找他:「上回的序很受歡迎啊,再寫個下集吧!」後來又寫了個(三)。等到機子寄到,可以正式開始翻譯時,劉紹唐的要求是先別翻了,多寫點跟胡適做事的經過,就這樣一寫寫了十期,還出了傳記叢書「胡適雜憶」,然後才說:「差不多了,現在讀者興趣更高,可以翻譯口述歷史了。」
唐德剛後來想起這段就覺得好笑,自己怎麼這麼「聽話」?現在唐德剛更成了「傳記文學」的文膽和劉紹唐的摯友,一個愛其才,一個敬其識,劉紹唐一提到唐德剛就讚不絕口,直說,現在像這樣史學造詣一流又有文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來越難得了。
陳香梅也曾在一篇為「傳記文學」銀禧誌慶的文章中寫到劉紹唐的邀稿風格:「紹唐初辦傳記文學時來找我索稿,他把他的計劃和我說了半天,他不但每月出一期月刊,而且還準備出書。我當時嚇了一大跳,心想你這月刊都存亡難卜,怎麼還有大想頭,提出一大堆出版計劃。紹唐兄一邊抽煙,一邊談他的大計。他沒有書商的市儈氣,卻有一種萬事不經心非常可愛的氣質。我想為此很多人願意為他動筆,我當然也不例外。」
不過向劉紹唐查證他邀稿的能耐,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威脅啦!利誘啦!反正無所不用其極。」
官史?野史?歷史拾荒者?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則認為,劉紹唐的史料蒐集與整理,對國史的貢獻無法「一語道盡」,尤其是「漢賊不兩立」的時代,許多近代史上重要人物未能來台,從此便如斷了線的風箏,幸虧有「傳記文學」收錄了若干這方面的人物資料,不致於完全留白。他認為傳記文學是否可視作傳記史學還有待商考,但可以與國史互補則是無庸置疑的。
劉紹唐對於別人說他治的是官史還是野史毫不在意,反正除了這次得到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拿了三十萬獎金外,他從未拿過政府一毛錢的補助,想當然爾跟「官」扯不上邊,他有時乾脆稱自己是歷史的「拾荒者」,被捨棄的史料、被忽視的故事,他拿來當寶貝整理、打點,要拼出歷史的原貌。他所擔心的,不是別人對他的評價,而是還能辦多久的「傳記文學」,有沒有好稿子吸引讀者?
記得「傳記文學」甫出之際,可說是篇篇驚豔、字字珠璣,他常常通宵看稿,並非是為了趕截稿期,而是不忍釋手。他記得當時還特別去弄了幾個鬧鐘,每隔一、二小時要響一次,提醒自己第二天還有要事,總得睡一會兒,可是還是常常克制不了地非要看完不可,一宿未眠是常事。
近來這等教他眼前一亮的稿子越來越少了,如果說的是北伐、抗戰、國共戰爭等常探討的題材,很難推陳出新,而老一輩的作者紛紛凋零、新一代的作者後繼乏力。「傳記文學」的資深編輯邱慶麟也十分感概,眼前的時代越來越開放,中國人的領域越來越寬廣,在這片「傳記文學」土地越來越肥沃的時候,種花蒔草的園丁卻越來越少,賞花人是否也會因此卻步呢?
劉紹唐常把「傳記文學」的作者分成三代,第一代說的是自己的故事,所以最精采;第二代說的是聽來的故事和自己的看法,也時有佳作;第三代若是還作第一代人物的故事,就只能在故紙堆裡研究,史料價值仍在,動人心弦則難矣。
不過也許他身在林中,沒注意到另一個因素,那就是他生長的那個時代本身,在巨變中激盪出崇高的國魂和的耀眼人性光輝,一個個精采的故事自然成形,旁觀者吳克博士看得清楚:「三○年代是中國最好的時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大舉侵略喚醒了中國人,知識份子不再一味反政府,知識青年和販夫走卒連成一線,他們終於認同孫中山給中國的藍圖,正是民族的尊嚴、民主的理想。不平等條約廢除了、中國站起來了,知識份子覺得要對中國文化許下終身,劉紹唐瞭解這一切,他也許下了他那一份終身的諾言,就是『傳記文學』。」
只要青春不改,世代延續,中國人的故事存在一日,「傳記文學」自然會辦下去。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7f0faec3-2463-4c3d-831d-c69718615c57&CatId=7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