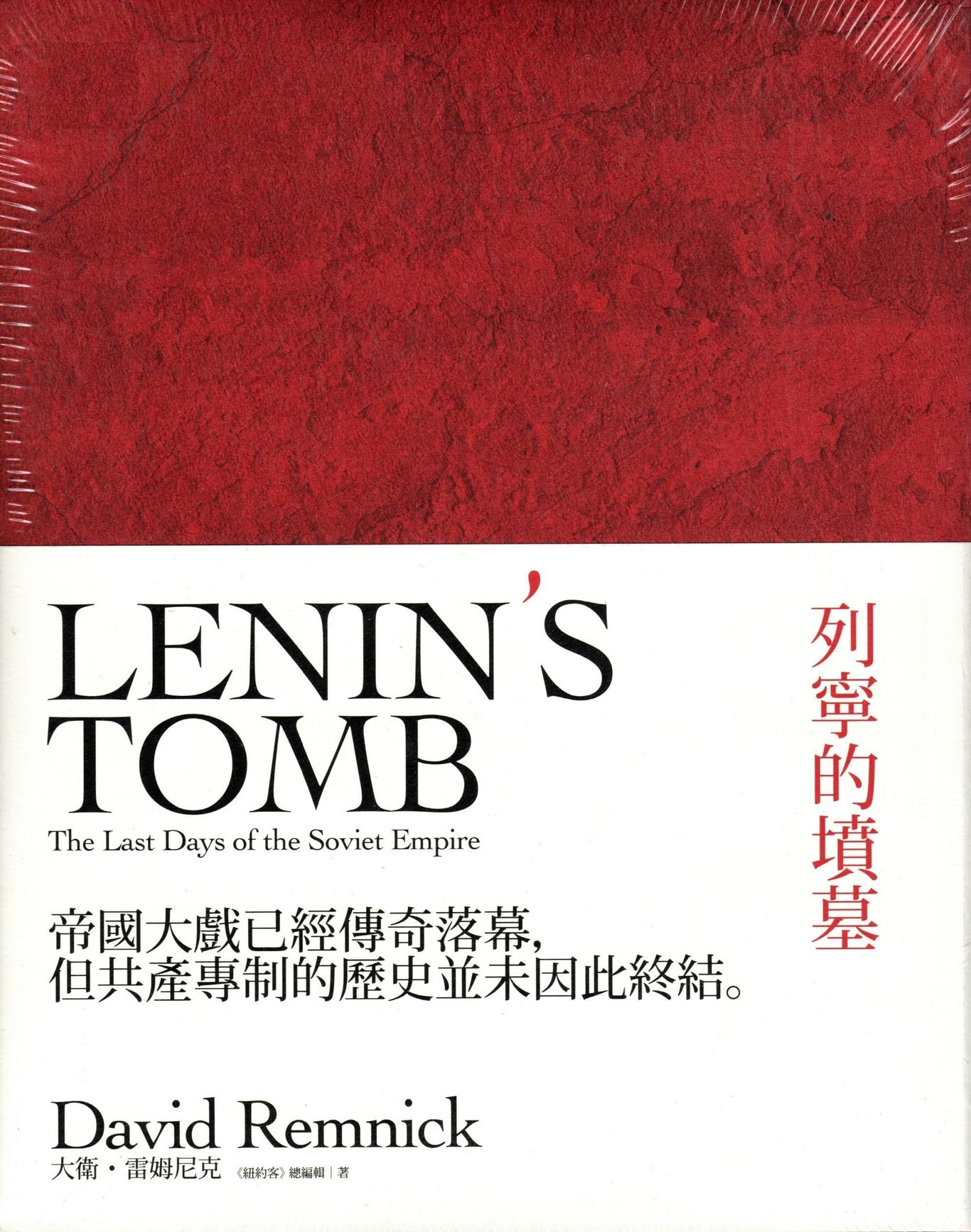胡瘋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9章第Ⅱ節:盼望著,盼望著
蘇維埃領導人沒有像他們在四月危機中所做的那樣,利用他們的群眾授權為自己謀取權力,而是選擇支持一個已經名譽掃地的自由主義政府。他們越來越被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守護神,而革命——為了麵包、土地與和平——的主動權,則落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手中。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9章第Ⅰ節: 一個遙遠的自由之鄉
政府的主導思想是由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所塑造的,而這些價值觀又是在人民爭取自由、反對專制的鬥爭中產生的。這種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有兩個主要觀念:對國家作為強制力量的本能的不信任;以及對地方自治的信仰。由此可見,一個遙遠的自由之鄉才是推動俄國走向文明世界自由國家的唯一源泉。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8章第Ⅲ節: 末代沙皇
眾所周知,“光榮的二月革命”,據說是一場不流血的事件。“想像一下,”一位同時代的人寫道,“在俄國發生了一場偉大的革命,竟然沒有流一滴血。”據說,這也是唯一一次沒有反對派的全國行動。“我們的革命,”一位國家杜馬宣傳家告訴赫爾辛福斯的水兵們,“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表達全體人民意志的革命。”革命被描繪成一種精神上的復興,人民道德上的重生。梅列日科夫斯基稱之為“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基督徒的行為”。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8章第Ⅱ節:不情願的革命者
到2月28日,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權力中心:塔夫利宮的右翼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它擁有最接近正式權力的東西,但在街上沒有權力;而左翼是蘇維埃,它在街上擁有最接近權力的東西,但沒有正式的權力。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8章第Ⅰ節:街頭的力量
一個年輕女孩從示威者的隊伍中站出來,慢慢走向哥薩克人。所有人都屏氣斂息,緊張地注視著她:難道哥薩克人不會向她開槍嗎?女孩從斗篷下拿出一束紅玫瑰,向軍官遞過去。停在半空中。這束鮮花象徵著和平與革命。然後,軍官從馬背上彎下腰,微笑著接過花。每個人如釋重負、欣喜若狂,人群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烏拉!”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7章第Ⅲ節:從塹壕到街壘
在柯倫泰看來,只有列寧宣導的武裝起義才有可能結束戰爭。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恢復人類意志的力量,以及對客觀力量的掌控。這不僅僅是“分析”,她在日記中記錄下列寧關於戰爭的論述。“這是行動。這是一個政治綱領……讓街壘來回答戰爭。”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7章第Ⅱ節:瘋狂的司機
9月份,立憲民主黨政治家馬克拉科夫在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中總結了自由派的窘境。他將俄羅斯比作一輛汽車,由一個瘋狂的司機(尼古拉)以無法控制的速度開下陡峭而危險的山坡。乘客中有自己的母親(俄羅斯),也有稱職的司機,他們意識到自己正被帶向不可避免的厄運。但沒有人敢抓方向盤,因為害怕造成致命的事故。司機知道這一點,嘲笑乘客的無助和焦慮。“你們不敢碰我,”他告訴他們。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7章第Ⅰ節:鋼鐵洪流
他們準備在河岸上建立陣地,卻發現腐敗的軍官已經賣掉了建造塹壕所需的所有鐵鍬、鐵絲網和木材。在沒有大炮和彈藥補給的情況下,他們竭盡全力地堅守著,損失慘重。許多人戰鬥時,除了空步槍上的刺刀外,一無所有。到5月底,他們終於被迫放棄普熱梅希爾。隨著德軍逼近俄國邊境,利沃夫(倫貝格)也很快被佔領。正如諾克斯所說,這是一場“機器對人”的絞殺。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Ⅳ節: 為了上帝、沙皇和祖國
車站裡沒有旗幟或軍樂隊為他們送行,據外國觀察家的說法,大多數士兵臉上的表情是凝重和順從的。正是他們可怕的戰爭經歷點燃了革命的火焰。沙皇孤注一擲的賭博必將給他的政權帶來毀滅。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Ⅲ節:押注強者
事實上,早在1914年之前,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就已經停滯不前了。斯托雷平曾聲稱,至少需要二十年來改造俄羅斯農村。但是,即使改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速度繼續進行,該政權也需要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建立起強大的農業資產階級,他們顯然已經決定把自己的未來押在這個上面。土地合併運動,就像沙皇政權的其他改革一樣,來得太晚了。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Ⅱ節:政治家
斯托雷平的政治覆滅只能用他作為政治家的失敗來解釋。如果他更精通“可能性的藝術”,或許他可以為自己和他的改革爭取更多時間。斯托雷平曾說過,他需要二十年時間來改造俄國。但部分由於他自己的過錯,他只有五年的時間。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Ⅰ節:議會與農民
這場莊嚴的對抗只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的一個預兆。從1905年到1917年2月兩次革命之間的整個俄羅斯政治歷史時期,可以描述為保皇黨和議會勢力之間的鬥爭。起初,當這個國家尚未從革命危機中恢復時,宮廷被迫向杜馬讓步。但隨著1905年的記憶流逝,宮廷試圖收回自己的權力,恢復舊的獨裁統治。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5章第Ⅲ節:大浪淘沙
對於農民和工人來說,這些新的政治自由並沒有什麼直接利益。他們自己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得到滿足。1905年的經驗告訴他們,要尋求社會革命,而不是追隨自由主義者的政治領導。隨著杜馬時期的失敗,他們的幻滅感變得愈發強烈。在《十月詔書》之後,反對派運動的兩極分化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憲政理想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徹底分道揚鑣。

《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致謝
我的兒子亞歷山大·本傑明是以出生在末代沙皇時代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出場太晚——正值共產黨第28屆代表大會(也是最後一屆代表大會)——沒能自己經歷這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戲。我們的第二個兒子諾亞·繆爾來得更晚一些。我希望終有一天,亞曆克斯和諾亞能訪問一個民主、繁榮的俄羅斯。

《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結語:“我心苦淒戚”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折射了舊制度的痛楚——共產主義青年時代,戰爭,監獄,集中營,與克里姆林宮的鬥爭,被迫流亡——在經歷了那麼多以後,如今,75歲高齡的他,終於為這段旅程畫上一個完整的圓。他拿到了回家的車票。“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會回去,”索爾仁尼琴說。“這太瘋狂了。沒有人相信。但我知道我會回家,死在俄羅斯。”

《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五部:莫斯科大審判
幾個星期後,俄羅斯憲法法院裁定,共產黨可以在地方一級自由集會,但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共產黨是非法的。黨的資產和財產仍然由俄羅斯聯邦民選政府控制。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的時代,終於在法院的判決聲中——落下帷幕。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5章第Ⅱ節:“沒有沙皇”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也是整個革命的轉捩點,他們的情緒突然從不相信轉變為憤怒。“我觀察周圍的面孔,”人群中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回憶道,“我沒有看到恐懼,也沒有看到驚慌。不,那些虔誠的、近乎祈禱的表情被敵意甚至是仇恨所取代。我在每一張臉上都看到了仇恨和復仇的表情,不管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男人還是女人。革命真正誕生了,它誕生在最核心的地方,在人民的內心深處。”

《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四部:“第一次發生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下)
陰謀者們發動政變是為了拯救行將崩潰的蘇聯帝國,保住他們在其中的權位。他們的失敗卻成為壓垮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哪個波羅的海獨立運動,沒有哪個俄羅斯自由主義者,能像他們一樣把這一切徹底推翻。現在,亞佐夫終於明白這個道理。“我什麼都清楚了,”當他們把他帶上一輛窗戶上有鐵柵欄的麵包車時,他說。“我真是一個老白癡。是我親手毀了蘇聯。”

《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四部:“第一次發生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上)
“我們的祖國,這個國家,這個偉大的國家,歷史、自然和我們的前輩希望我們拯救的國家,正在走向死亡、分崩離析、陷入黑暗和廢墟之中……我們變成了什麼樣子,兄弟們?”這種啟示錄風格的語言,國家之船緩緩“沉入虛無”的意象,暗示邪惡勢力正在出賣一個偉大的國家。

《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5章第Ⅰ節:愛國者與解放者
由於大饑荒,整個俄羅斯社會都被政治化和激進化了。民眾和政權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再也沒有回頭路可走。用莉蒂亞·丹的話說,這場饑荒是革命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向她那一代的年輕人表明,“俄國的舊體制已經徹底破產了,俄羅斯似乎正處於某種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