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歡文字,熱愛閱讀。怪癖是買了新書之後會一邊嗅書本的味道一邊吃吃竊笑。 聯繫方式:boxuan0531@gmail.com
為你閱讀|撒哈拉的故事|三毛,與她眼中的荒漠沃土
今天要講三毛,還有她筆下那些奇思妙想中誕生出來的金黃色地沙漠沃土,不過在那之前,我得先說一下,我真的被嚇到了。

那天我在閱讀從縣立圖書館借回來的克莉絲蒂系列小說。
前一天我則在看三毛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我把撒哈拉的故事閱畢後,就擺在我桌前的「借閱書區」,換了一本克莉絲蒂的《白馬酒店》來閱讀,那是有些年紀的書,文字的印刷透露出了年代感。
等到我閱讀完畢,心想:「真有趣的故事。」同時看著借閱書區,還有什麼可以接續閱讀的書。看著《撒哈拉的故事》,又看看手上的那本《白馬酒店》。
「欸?!三毛主編?」
三毛?是那個我知道的三毛嗎?
是那位在老公差點在流沙中死去,又差點被叫來的救兵強暴的那位三毛?
是那位在黑夜中獨自在家中哭泣,目送荷西的公車遠去,在荒漠中感到孤寂的三毛?
還是那位在駕照考試中展現她女車手般的氣魄,殺進上校辦公室默背交通規則的三毛?
不意外地,就是她,那位獨一無二,荒漠中美麗的天堂鳥,我們熟悉的三毛。

這引起了我的興趣,對我來說,撰寫《白馬酒店》以及前幾年翻拍成賣座電影的《東方快車謀殺案》的作者─阿嘉莎·克莉絲蒂,根本是上個時代的人啊。孤陋寡聞又沒什麼時間感的我,總覺得克莉絲蒂小姐生活在一個莊園、公爵、貴婦名流的時代,也許她作品中的魔幻感,模糊了我的時空距離吧。
而三毛,也許是小時候在課本上看過她的名字,雖然聽說她早逝,不過也許那種:「她也曾跟我一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感受,讓我覺得與三毛更親近些。
沒想到一查,兩位同為優秀作家的女士,還曾經一起在同一個時空中,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看過同一輪明月,這可讓我太驚訝了。
小時候總聽大人說三毛的文章多好又多好,其實閱讀國文課本上的選文,自己卻沒什麼感覺,當下只覺得跟考試有關,還有那些生難字詞以及解釋要背起來,完全沒有玩味到那書中的故事,更遑論意境。也許考試總是這樣吧!把孩子對於文字的興味都搞砸,對於文學的胃口都搞差,再來說台灣找不到優秀的作家。
一旦跟考試掛上鉤,誰期中考後還願意繼續閱讀那些選文,再優秀的文章也只想敬而遠之。
我不抱期待地借回家,打開書本之後卻被那些貧瘠沙漠中的肥沃文字吸引,再也關不起來,如同一個潘朵拉魔盒,我迫不及待只想知道更多,那具有魔力,攫取閱讀人的注意力,於是,我也愛上了那片三毛居住過的撒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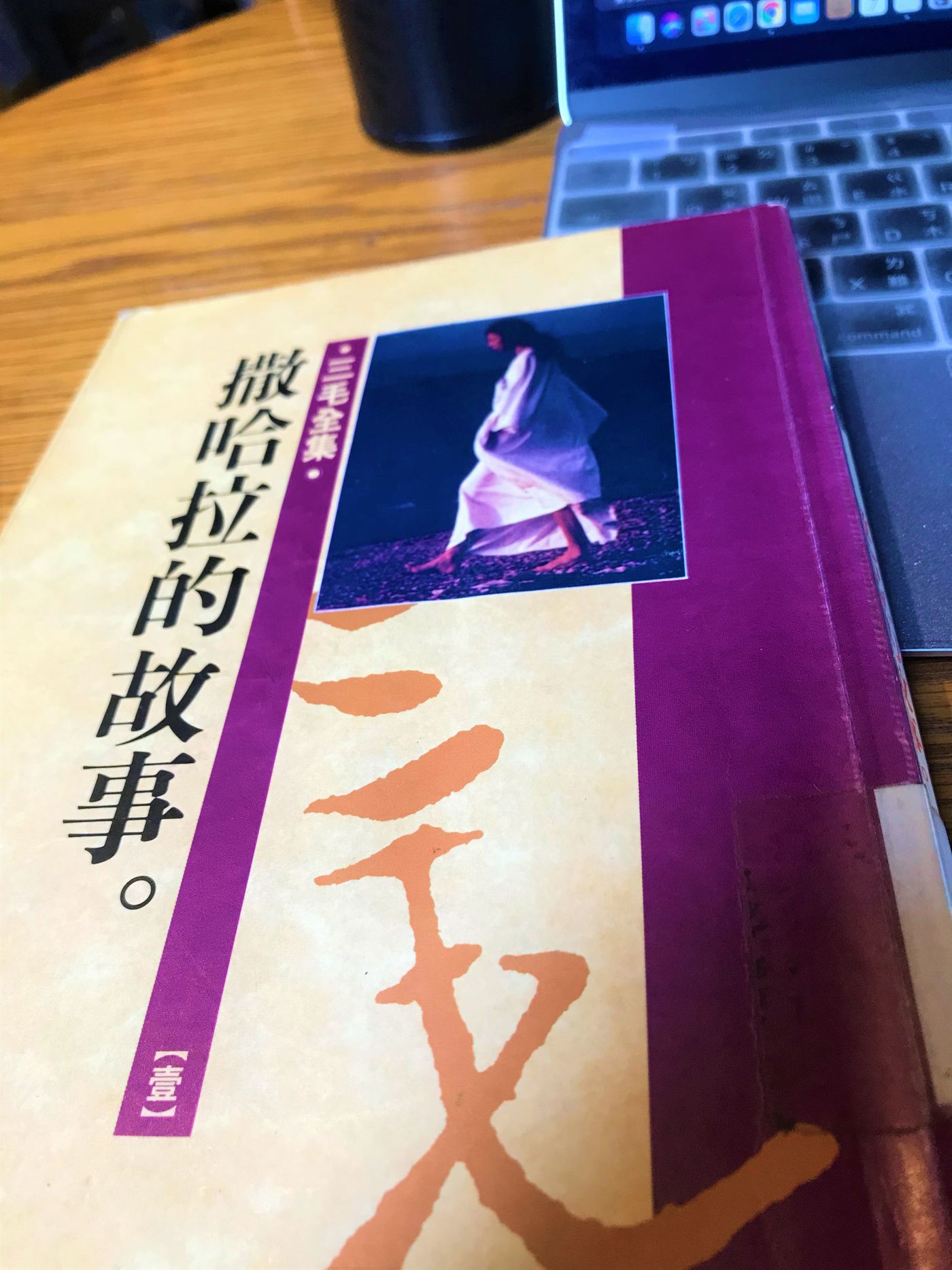
「咦,什麼東西?中國細麵嗎?」
「你岳母萬里迢迢替你寄細麵來?不是的。」
「是什麼嘛?再給一點,很好吃。」
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絲:「這個啊,叫做『雨』。」
「雨?」他一呆。我說過,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說話自然心血來潮隨我高興。
「這個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場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凍住了,山胞紮好了背到山下來一束一束賣了換米酒喝,不容易買到喔!」
荷西還是呆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內的「雨」,然後說:「你當我是白癡?」(三毛,1976:19)
這段文字也許用詞有些年代感,現在台灣已經不再使用「山胞」這語詞,改以「原住民族」稱呼,而把原住民族與愛喝酒的形象連結,也不見得公允。畢竟這段文字已經橫跨四十五年的時空,但除此之外,那文字中表現出的三毛,以及他跟丈夫荷西之間的互動,讀起來依舊可愛動人。
我很欣賞三毛的文字,不見得是詞藻有多華美,故事也不見得有多精巧的安排。
我自己是認為,三毛的文字很「保鮮」,其實他的作品拿到現代來看依舊新鮮,除卻那些用詞上的差異,其實說真的,要跟我說是年輕的作家我也信,褪去大時代悲苦的敘述,或是稍嫌長輩的說教與講道理,三毛真正做到的,是真摯地坐在你我的身邊,成為與我們分享生命故事的人。

「聽不懂就算了。姑卡,我先請問妳,妳再去問問所有的鄰居女人,我們這個家裡,除了我的『牙刷』和『丈夫』之外,還有妳們不感興趣不來借的東西嗎?」
她聽了如夢初醒,連忙問:「妳的牙刷是什麼樣子的?」
我聽了激動得大叫:「出去──出去。」
姑卡一面退一面說:「我只要看看牙刷,又沒有要妳的丈夫,真是──。」
等我關上了門,我還聽見姑卡在街上對另外一個女人大聲說:「妳看,妳看,她傷害了我的驕傲。」
感謝這些鄰居,我沙漠的日子被她們弄得五光十色,再也不知寂寞的滋味了。(三毛,1976:126)
明明是想說自己的東西被到處「不問而取」,卻偏偏說自己的生活五光十色,當然這是一種反諷,但文中卻不見那種憤怒、喪氣等負面情緒,閱讀完後,反倒只覺得有趣,那種因為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不同而出現的溝通不良,以及那些風土文化,也因為三毛的敘述而變得鮮活起來。
或許是經過潤飾吧,當下三毛可能無比憤怒,但是那些在沙漠中的挫敗生活,卻透過她的文字慮鏡而變得精采。
也許事實是「沙漠生活無比苦痛」,客觀條件「是的!」非常痛苦,但在本書的最後一個篇章前,我卻一點都感覺不到,我只覺得三毛享受那些在沙漠中的經驗,與鄰居們活得很「精彩」。即使是這篇散文中把高跟鞋給弄壞,再送回來的姑卡,也都在另外一篇散文中,看見三毛與他的連結,被迫結婚的痛苦,不想懷孕的秘密。
也因此,我一直以為三毛過得很快樂,卻沒想過自己待在沙漠中,不得不學會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三毛,其實可能很寂寞。

有時候荷西趕夜間交通車回工地,我等他將門卡嗒一聲帶上時,就沒有理性的流下淚來,我衝上天台去看,還看見他的身影,我就又衝下來出去追他。
我跑得氣也喘不過來,趕到了他,一面喘氣一面低頭跟他走。
「你留下來行不行?求求你,今天又沒有電,我很寂寞。」我雙手插在口袋裡,頂著風向他哀求著。
荷西總是很難過,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他眼圈就紅了。
「三毛,明天我代人的早班,六點就要在了,留下來,清早我怎麼趕得上去那麼遠?而且我沒有早晨的乘車證。」
「不要多賺了,我們銀行有錢,不要拼命工作了。」(三毛,1976:209)
我聽說曾有人跟著三毛遠行的足跡,去尋找當年《撒哈拉的故事》裡面的內容是真是假,聽說鄰居對於她──三毛,的敘述跟她自己在書中所述並不相同,也聽說有人去翻找荷西當年的學經歷,發現他根本沒有大學畢業。
其實我只想說,我們都知曉這些故事也許根本沒有這麼浪漫。

想想得隻身一人與男友一起移居到沙漠裡,到底會有多辛苦。離開了從小生長的環境,重新學習當一個「人」,有多困難,怎麼可能如書中所述這麼浪漫美妙,也許偶爾有可談的有趣經歷,但那也都是跌倒又瘸條腿後,才領會過來的經驗。
而在這貧瘠的土壤中,誕生了那些帶點潤飾過後的浪漫,妝點自己平時的艱難,那麼,是不是事實又有什麼要緊?更遑論丈夫的學經歷了,如果荷西真如書中所述地與她相愛,願意為了三毛的自由意志,跟著她到沙漠找工作,我們又何須用學經歷,或家世背景來論斷他倆的情意呢?
最後,雖然我與三毛的緣分尚淺,但我驚異於這大我快兩個輩分的奇女子,想想在那遙遠的台灣,誕生出這樣的文字,那樣的作家,她的作品與沙漠中的奇遇,乘載了過去的台灣人,讓我們有機會跟著她的筆,夢回那遙遠國度的撒哈拉,遠離戒嚴牢籠的思想箝制,也許在撒哈拉,那片黃金沙漠,才擁有更真實的自由吧!

維基百科 (2021)。三毛(作家)。舊金山:維基媒體基金會。線上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25日。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毛_(作家)
三毛(1976)。撒哈拉的故事。台北:皇冠。
贊助我一杯咖啡,讓我知道在創作路上有你陪伴。
成為我的讚賞公民:https://liker.land/zxx0531/civic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