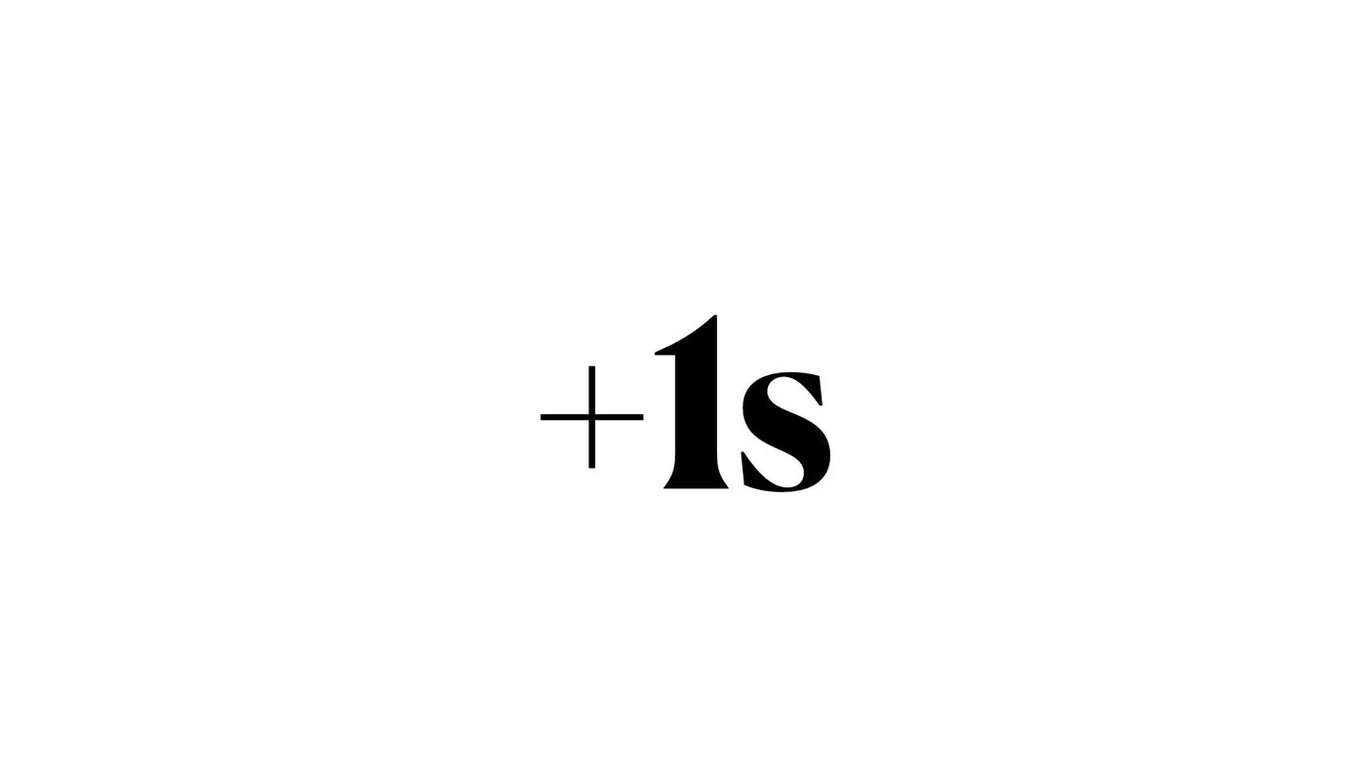
哈利波特.eth
Ars longa, vita brevis
这是一篇《Amadeus》的不太想说技术的影评。
我并没有特意重新再看一遍过。我只想说说,当你忘掉这些演员后面有摄像机,而是只有你的的时候,粗粝,不经过
叠嶂的知识加工,又最经时间考验的记忆中感受。
上一次,是几年前纽约圣诞节前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家精品旅馆找出了一份保存完好的胶片拷贝,于是在自家的地下小影院举办的放映。画面自然有一些岁月的划痕,观众三三两两不过十人,制作人和女主角也在席间,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便是Q&A,大家各自侃侃而谈一个小时,从筹备到拍摄的过程,也少不了一些趣事,直到观众所有问题问完,仍是依依不舍。那时我突然觉得电影艺术和观众该有的距离原来就是彼此面对面,没有托起来,也不需踩下去,坦白说,踩也是很费力的,谁想一天到晚放眼望去只能踩,只能恨呢?
个人的奋斗可以有,历史的进程不可无。这电影拍摄本身相当的应景。福尔曼流亡美国,拍完《飞越疯人院》以后,自己都没想到有一天能回到祖国老家拍电影,全程剧组宾馆被装窃听,拍到哪里秘密警察鬼鬼祟祟跟到哪里,好像一部关于莫扎特的biopic能搞出什么通敌卖国的阴谋诡计(虽然也不是没可能)。
铁幕下长大的福尔曼,太清楚那些不是东西的东西是什么个东西了。没有赤色的创伤是很难拍出《飞越疯人院》的。18世纪的维也纳虽然没有干部书记,但家长式的威权资格老要管教管教桀骜不驯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老爹门口一站,哪管你写得好不好,上来就失望煤气灯,让人自动觉得有罪喘不过气来。几个老不死眉来眼去三言两语,几下就能塑造出那种令人作呕的教导主任式的压抑。到底是霸占着解释怎样是艺术和什么是美的权力。德不配位,但就是放在了能压你一头的上面的位置上,掌控着你能自我实现的边缘。这就是我们对《飞越疯人院》里的护士长或者《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里的乌姆里奇源自于童年近乎PTSD式的生理不适。你可以说他们代表或者象征着那种抑制生命生长的恶;你也可以说恶的触手爪牙,物理的延伸,别的啥都不干干不了怎么就偏偏来制你。个体消亡附依了也好,还是长出来的盘纸错节,他们唯独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有人的形态,只是恶的平庸,只能是抽象的“他们”。
而萨列里不同。是人。是我们。你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萨列里的煎熬,虔诚,牺牲,委屈,虚荣,不甘,愤恨,羞愧,嫉妒。你也看不到“他们”有萨列里的欣赏,懊悔,自责,甚至最后真正的钦佩。莫扎特死前短暂的一瞬,是通过萨列里的手写下来的。
你怎么就不懂呢?
不不不,你太快了,我不懂啊。
那一面催,一面一副急着要哭的样子,还有紧接着以为作业已经可以交差,而天才才刚要施展才华的反差都让我揪心。这些都是太过熟悉的感觉,只要你有过一刻想要争取。中学时候一道数学题做不出的懊恼,平静下来花好久做了出来,却总有人不打草稿就能说出答案的,你想到的当然不是把你同学干掉,而是嫌自己太笨,这种智力的崇拜当然是病态的,可是我们又无时无刻地被逼着赤裸地比较,从文艺复兴的画家们到中学课堂,“你有还是没有”的问题都在折磨着我们。
但萨列里最后还是触碰到了他一生都觊觎的那点神性了,尽管是那么短,他也在那一刻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明白了有些东西高于我们。高于个人,甚至高于作者,接手的人知道有更大的责任,要保留下来,就像维吉尔死前想要付之一炬的《埃涅阿斯纪》诗稿。他的救赎并不是垂垂老矣时在精神病院承认自己是凶手的忏悔,而是莫扎特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开始了,毕竟……他也完全可以烧掉或者说是他写的不是嘛。
反观他们呢,始终就只有那种你能奈我何的傲慢,好像校长站在领操台上放眼望去,几百个人齐做广播操就是好,齐是自我意志的延伸。瞧他们乱涂乱画莫扎特手稿的给得意的,有萨列里的勇气承认什么是美什么是好么?好在小人得志虽然卑劣,但看来没有什么深度。太监坏,也就是坏在sm道具花样多而已。要去humanize他们是很难的,做正常人做的事也似乎不可想象。你指望他们眼里,他上帝算个什么东西?
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虽然正能量和封建毒草这样的词很蠢,但这里的毒草也未免太多了一些。要么是春药,要么是毒药,过把瘾,求速死,做鬼也幸福。真正给你力量的几乎没有的。壮志凌云一定要浇灭,才华横溢一定要辜负,伤痛和无能上瘾。连李白也是“且放白鹿青崖间”,仰天大笑,避世吃老酒。
萨列里本应是最懂莫扎特的人,结果不做高山流水,偏偏要做特供审查员打他的七寸。有个不懂还得硬装懂的皇帝,几个指手画脚的乐师做领导,有个从小摁着他窒息的爹,有个养女儿跟养狗一样还“你弹你弹呀”的土豪(philistine)老板,有个势利眼丈母娘。甚至他自己也肆意挥霍着才华。得承认,唯一有点倒霉的倒是他的老婆。
何等的孤独。美好的东西像是世界的囚徒,但也有如希望自由和真理啊,关都关不住。
莫扎特走投无路接私活写出了《魔笛》,这相当于在情感公众号上写《安妮娜卡列宁》了;丈母娘叽里呱啦追着一顿骂,他眼睛一亮,镜头一切切到夜后咏叹调,本意是幽默,可怎能叫人不动容呢?(我当然知道这不是真的。)
我人下流,但我的音乐不是。(I'm a vulgar man. but I assure you, my music is not.)
莫扎特的音乐就是一支穿云的箭,是莎士比亚说得最好:
Who doth permit the base contagious clouds
To smother up his beauty from the world,
That when he please again to be himself,
Being wanted, he may be more wondered at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foul and ugly mists
Of vapours that did seem to strangle him.
—Henry IV, Part 1 1.2.205–210
牢笼里的鸟儿要唱歌,栀子花都是痛痛快快地香。肖申克里功放(正好又是)《费加罗的婚礼》,Sia的大俗歌里唱的那样,我不管,我要唱,走调也要唱,不唱就会死。不是争一口气,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不是只有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雨水冲刷疮痍大地,石头缝隙迸出的一朵花。
原来人间的美是这个样子给人力量,给人希望,像那句话说的,猛然发现,并非死亡漫漫,而是生无止境。悲剧是悲剧,前半部阳光明媚意气风发,后半部寒风凌冽雪上有霜。但抹抹眼泪又何妨。美好的音乐确确实实是留了下来,生命一瞬,艺术永恒。阉不掉,谪不了,美属于我们全人类。
福尔曼18年去世了,所以夏天时候,我在电影节上看了他生平的纪录片,不长。这是那天最后一档,意料之中的是观众寥寥无几,我又想起纽约的那个夜晚。一对老夫妻开始还兴致勃勃,刚15分钟看完导演父母在集中营双亡后就起身离去。
……
结尾,福尔曼搬回了捷克,最后他说几句话,我概括大意是:他们虽然已经倒了,但我们被他们弄坏过的脑子,还要好久好几代人才能修好。
我深以为然。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