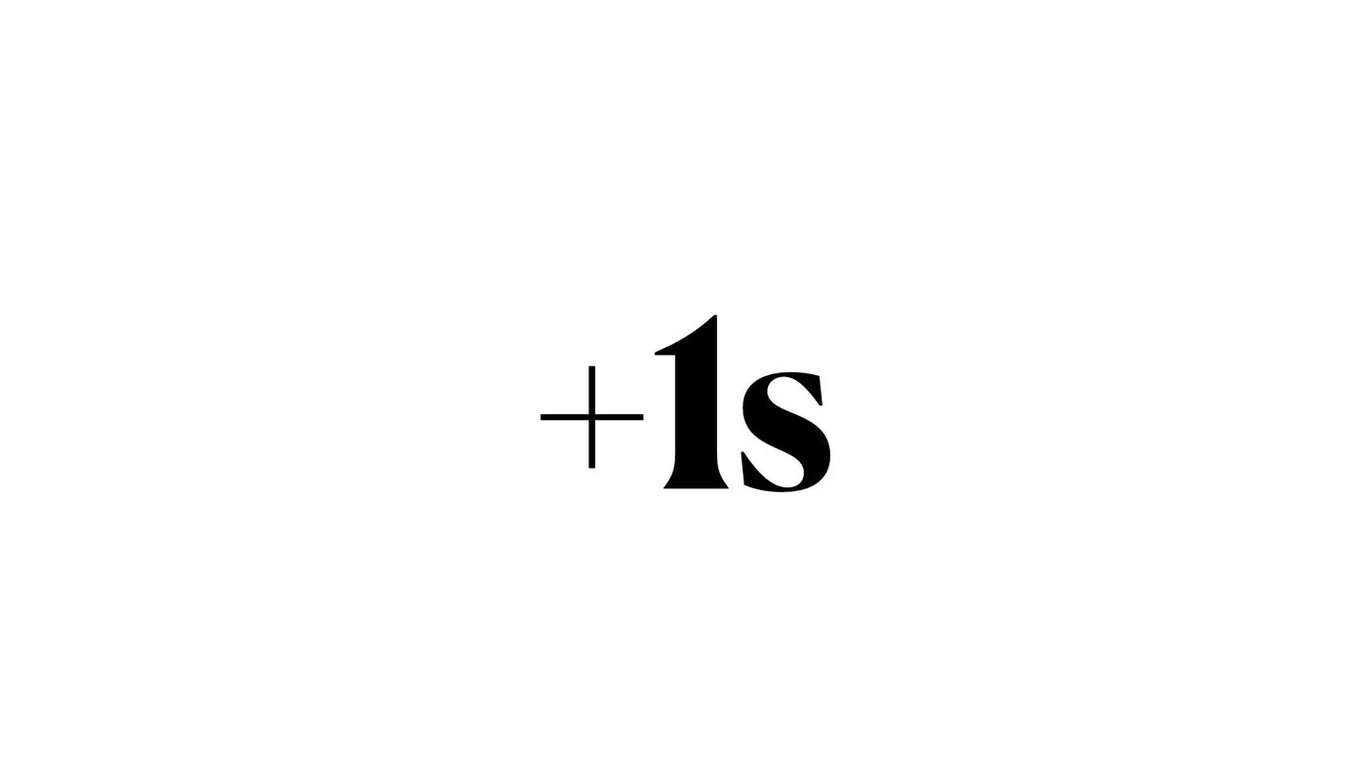
哈利波特.eth
遥远的地方
我并不喜欢每逢重复而机械的自我介绍,我提及耶路撒冷时取悦和讨好的意思,我只能说我跟学校在那里交换过半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边跑。
……
那里离我渐渐远去,也从未赋予我觉悟的意义。许多独特放在一起,只觉到没有更特殊的沮丧。凝视着那里,好像有了“世界”的义务,可是越看越缥缈,曾经很近,如今很远。事实上,我从未平衡好世界公民还是上海市民的身份,也包括任何一种体面人的身份。
玛格丽特走到哪里都会是众矢之的。众矢之的,我指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会舍身取义,把一个团体里其他的组员联合起来孤立,攻击,嘲讽自己的那个人。
在没有喝醉的时候,玛格丽特经常会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蠢话,比如“我们都是美国傻逼”,或是“我们最要好了”,一开始我会在她说完有的没的之后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这么蠢,真的没关系,不是她的错,it’s not your fault。这些善意的羞辱换了花样说了几次以后,我就直接对口型,不出声了。拍肩膀这个混账之极的手势也很快传染了其他人,有时候玛格丽特就算是打个喷嚏,也会有人替我去拍拍她。
我怀着某种秘密的心情写着她,因为几年后我翻阅着不倦千里寄到我家的校刊的时候,有不服气的轻佻,也有节节败退的骄傲。她车祸去世了,而她在我的记忆里,又是这种那种的形象。我不止一次地想用某种和她的死有关的词句为某些抒发心情的日记式的不知所谓的感怀文章起头,但那些到底都没有写成。公平地说,玛格丽特的“症状”是酒精放大的。喝了一点度数不高的烂红酒之后,她就开始反对被人的任何反对,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最弥漫的硝烟的导火索是以色列的犹太平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窘迫现状负责,至于谁反对谁的反对,就不如情绪的爆炸来得重要。
那是一次周二下午例行的小组晚餐。玛格丽特和摩根准备披萨、墨西哥卷和意大利面,我吃得似是而非的饱。已经不是第一个月了,男男女女的话题都枯竭,我们以为对当地不再一无所知,觉得有义务更热烈地讨论这片土地的挣扎,煎熬,苦难。晚餐进入第三个小时,围坐在长桌边的人逐一减少,只剩下面包屑和干燥的脾气。争论还未结束,玛格丽特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拿着红酒瓶,涨红着脸拍着桌子对仅剩下的两个男生大吼:我他妈的就不懂了,你妈的,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你听我说,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政府一天到晚他妈的在操巴勒斯坦人,那你让他们对什么负责?无需否认,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前途,玛格丽特的愤怒饱含可贵的天真(naïveté),但成长的曲折辛酸嫁接在世界的问题才更迸发了出来。她接着说她这一辈子活到现在,从没有人认认真真听过她一言、一语。
两个小时后,摩根抽泣着冲到男生的房间里哭诉,说自己受不了为什么玛格丽特会冲着她这么一个无辜的人大吼大叫。好像我遇到过很多人都不能忍受一点大吼大叫,觉得这是针对个人的伤力很强的武器。之后的整整一星期,摩根都睡在男生宿舍的沙发上,春假两人环游欧洲的计划也暂时蒙上了一层阴影。
还有一件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们结队周五晚出行,入夜深了以后,突然发现玛格丽特喝醉走丢了,于是一行人出于兄弟姐妹的同门义气,开始骂骂咧咧地找人,玛格丽特始终不见踪影。同伴责难地摇头,我转过身,在张灯结彩的小巷,看水烟的雾气,听阿拉伯音乐。
起初大家憋了一口戾气,后来就感叹一下,房间里的大象,不看。
在克里斯和麦卡面前我时常觉得自己有语言功能障碍,或者严重的口吃,两人之间你来我往地讨论地缘政治,枪火管制甚至约会逸闻,我都蜷坐在大厅角落的沙发里静静倾听而不插话。有一次我兴之所至,想给克里斯圆一个故事,可是却把发推的动词“tweeted”说成了“twittered。”看,我恼羞成怒至今不能放过自己。我开始觉得世界上此时此刻发生的时事新闻那么繁琐和无聊(几年后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并一次又一次在心里默默追溯古罗马共和国最后百年的动荡。我从不想沉溺于过去而对世界毫无感知,我也不认为世界是一个环形的废墟,可是又如何能多此一举地证明我的态度既不是迂腐也不是吊古?
我努力地下载着最新的补丁,更新换代细小的零件,从充满破碎的隐喻和典故的中古世界中跌撞出来,意兴阑珊地看着更磅礴、更琐碎的当代世界,但无法抗拒的是童年长日将尽的周日和成年之后的周五,许多个周五,或者周一,亦或者周三,我都被世界之巨大immensity,囚禁得喘不过气来,无法化茧成蝶,死灰,只有在成语里才会复燃吧。
我曾经嘲笑他人试图改变的决心,又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承认,体制化的权力和价值输出的存在着绝对关系。凯莉一口咬定我宇宙观是精英主义的,当时我并不清楚那算是什么,但确定并不因为她在耶鲁上学才这么说。可是当我发现我已经燃尽很很久,一旦开始拥抱无能,甚至对犯贱跃跃欲试,精英,不精英的对立似乎又豁然开朗。凯莉多才多艺,有时也显得独来独往。她无比崇尚奥古斯丁,对神学得心应手。一方面她能跟我侃侃而谈《忏悔录》,另一方面却搞不定学期初每周接她的巴勒斯坦当地出租司机。我们一行人几乎每天都要跨过巴以国境线,而一出安检便有结队的出租恭候大驾。凯莉自以为司机是她的好友,趁机向他讨教阿拉伯文,而司机也开始整天念叨凯莉在哪儿,凯莉在哪儿,直到有一天凯莉自己终于意识到这局面让自己极度的不自在,为时已晚,误会已经酿成,之后索性从此把司机当做空气。我不想宣称自己早就感知了空气中凝结的悲喜剧,那未免太避重就轻。她曾说起过那个司机坚持要单独同她见面的烦恼。我默默听完。我过关时,也一次又一次看到那司机搜寻的眼神想要倾诉不解和落寞。最后,出于无奈的凯莉同意与他一次说清个楚,我又恰巧在她们相约的咖啡馆。多年来,性别和身份的战场硝烟弥漫。再想,我只是对身为女人的疾苦有忠诚却不切身的体谅。对此,冷眼旁观我仍抱有很深的愧疚。
老师和凯莉或许都是带点有点浪漫主义的卢德分子(这样归类是有些激进了),两人都拒绝用脸书,或者任何社交媒体。我或许自觉理解,却并也不太想佩服。所幸他们是浪漫主义的那一类,而不是党同伐异的那一种,是正襟危坐的自持,而非剑拔弩张的敌意。和凯莉一样,我的老师也察觉到了我尖锐的cynicism。其实……我也不想的。或许是他想起了伊万卡拉马佐夫,老师告诉我一定要把《上帝之城》给好好看完。我笑了笑。老师说: 不论何时何地开始,都为时不晚。
那时我仍在扬言要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不是现在惊讶如此多的人对这本书一无所知后像摩门教徒一样推销。但是请记录在案,我仍然同意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他本该是个一流的剧作家,而非一流的小说家,这个桂冠非托尔斯泰莫属。
甫到圣地耶路撒冷那一会儿,大家就已经在规划春假这整整一周该如何安排。直到放假前一周,我才发现,中国护照只有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三个选项,出于懒惰,我去伊斯坦布尔。克里斯不关心享乐,找到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武器训练团队, 气势汹汹地号召大家一起加入,人越多就越能商量个便宜的好价钱。一群人先是反反复复扭扭捏捏地推脱,接着又是大费周章地用传真搞定了无犯罪记录,一来二去,终于定下某个周日。那周周五我们从巴勒斯坦难民营回来,偶然听当地朋友说起这个良辰吉日会有近百万人在以色列国会游行。克里斯开始说催泪弹和CNN国际新闻,身上是一种我如今仍能唤起的跃跃欲试。他想错过这个机会,周日下午早早到了国会门口,发现人群尚未集结,游行尚早,而第二天又要早起上课,只得悻悻作罢。最后武器训练也不了了之。
春假临近以后,大家开始互相询问计划和安排,玛格丽特问我,你春假准备去哪儿?
——伊斯坦布尔。
克里斯和麦卡问我,你春假准备去哪儿?
——伊斯坦布尔。
摩根问了克里斯和麦卡周围一圈人之后,最后一个问我,哎,你春假准备去哪儿?
——伊斯坦布尔。
我极力避免无意中对一个人说两次同一件事,所以总是静候别人来询问,或者事先抱歉自己不知道是否已经说过。频繁的询问,好像隐射着什么不安,好像直到踏上飞机前的一刻计划都会跟不上变化,还是对他人能和自己一起犹豫的期待。春假前两周,原先约好的朋友纷纷放了我鸽子,我也没有惊讶,判决早已下达,只是锤子敲得慢了些。
临行前,因为航班同样早,麦卡用他的万豪白金会员在特拉维夫的海滩开了间房用来休息,我负责次日凌晨的出租车费。周五晚上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不能用手触摸开关,电梯每层楼都要停,从下午开始,大街小巷空空如也,只有特拉维夫靠海一带还有那么点生气。吃完一顿中规中矩的寿司之后,麦卡异常兴奋,拉着我到海边散步。那天温度宜人,海风吹在身上很暖。像老俗气的电影里那样,海的那一头只有黑暗,把一层一层的白浪衬得好看。我以为这个夜晚给我的感受会和下雨天在全家便利店吃盒饭一样,但是麦卡突然拍拍我的肩膀,往前方一指:
你看到那个写着“小猫咪”的牌子了么?那一定一定是个脱衣舞会。
很多事你得为了能讲故事而去做。
麦卡说,入场券我包了,不要矫情。
现在,要么睡三个小时,要么摸奶子。我都嫌麻烦,但我去了。介绍脱衣舞娘入场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每个人都穿着将近二十厘米的高跟鞋和白色天使小翅膀,我想了想包装和产地。入场结束,麦卡反复说,你要等,看准,再出手,这是一门艺术和学问。旁边突然坐过来一个胖嘟嘟的美国人,来自巴尔迪莫,开始花钱。我不安或者幼稚的是不想把一切当成一种习惯。让她们过来一次的价钱并不贵,这时麦卡拿出钱包抽出几张纸币,神经兮兮地告诉我:这些是学校发的用餐津贴。我说,中国有句谚语,跟你说的是同一件事。
麦卡如果不戴眼镜,在法律意义上的盲人。女郎在他的怀里扭动的时候,恰好把他的眼镜给摘了,我想起来,那是总是被爸妈批评的那种“没有精神”。
三个小时以后,我们身上是强生婴儿润肤露的味道,来到本古里安机场。旅途一路平安。飞机在伊斯坦布尔降落以后,我在大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行李,看了很多很多遍土耳其电视剧和汇丰银行的广告。拉着小箱子出自动门的时候,天空是灰的。这个星期里有一天,我在独立大街(İstiklal)的一间咖啡馆二楼,看了水枪,盾和烟。
我不爱旅游,匆匆过客总让给我想起人行道上的咖啦咖啦行李箱。
去那里,本来就不是因为什么执着,甚至很多年过去还对交换没有去成罗马耿耿于怀。
耶路撒冷确实和我毫无关系,如果耶稣怀念木匠间里的清香和天堂没有的璀璨星空,我只能说,那是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
后记:
玛格丽特车祸去世,开的是她的甲壳虫。
麦卡去了HLS,和我众多的朋友们再次成了同学。
其他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