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中国社会运动、网络自由观察者。
祭晓波:那个打捞光明的结巴
时光已逝,哀思依旧。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是为记。
野渡
庚子年7月13日
注:在大陆网络发表时,因刘晓波是敏感词,所以文中称为结巴(晓波口吃,所以朋友们亲切地称他刘结巴)
一
无时无刻不想为结巴写点东西,提起笔却又无话可说。世间没有天堂,在血写的现实下,语言是如此的无力,既不能让逝者的灵魂稍感安慰,亦不能让生者醒觉奋起。
然而,终归还是要说些什么。
他的声音,他的名字已在这片国土上成为敏感词而消失,他的肉体亦被消失,不说些什么,如何面对他生命的牺牲与祭奠。
二
与结巴的相识,缘于网络。
在互联网的早期,我创办的网站以先后开了48次成为一个网络传奇。结巴是网站的忠实网友,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国以来,独立于体制立场的民间网站便应运而生。在民间网站中,尽量避免敏感时政问题、专打擦边球的自律者多,而坚守信息自由立场的勇者寡。在极少数敢于突破言论封锁的民间网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无疑是大胆而坚韧的民间网站之一。”
在他1999年重获自由到2003年的那几年,他在帝都是很寂寞的,作为结巴,在肃杀氛围下,他一直被主流的体制知识分子圈所排斥,社交不多,所以有大量时间泡在网络上,而我所创办的《民主与自由》成为他最喜浏览的网站,他注册了一个叫“水皮虾米”(水之皮,即是波;虾米,霞闺名霞妹的谐音)的网名在上面发帖以及和网友交流。在网站屡封屡建中,我与结巴渐渐熟悉,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常想起与结巴一起共渡过的相隔千里以电脑一线相连的每个夜晚。
那时候,他喜欢写完文章后通过skype朗读一次给我或者达功听,在朗读时他感到语句有问题就停下来立刻修改,接着再继续朗读,那时候他一点也不结巴。因此我是他很多文章的第一“听者”。
那时候,我们都喜爱足球,而他一提起喜欢的巴塞罗那球队和梅西,就滔滔不绝。每个有球赛的周末,我们就开着聊天软件,边看电视直播边在电脑上聊天评头品足。
那时候,他闲适时喜欢说起他所经历的人和事,说起王朔对他的帮助,说起王小波的往事,臧否人物。
那时候,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际遇。打压时他第一时间撰写了文章《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声援;当我需要摆脱被驱赶的困境时,他出面多方筹措,使我得以安顿;当我家人住院时,他第一时间致电慰问;即使在他失去自由前,他还担心着我的生计,交代其他朋友尽可能想办法给我找更多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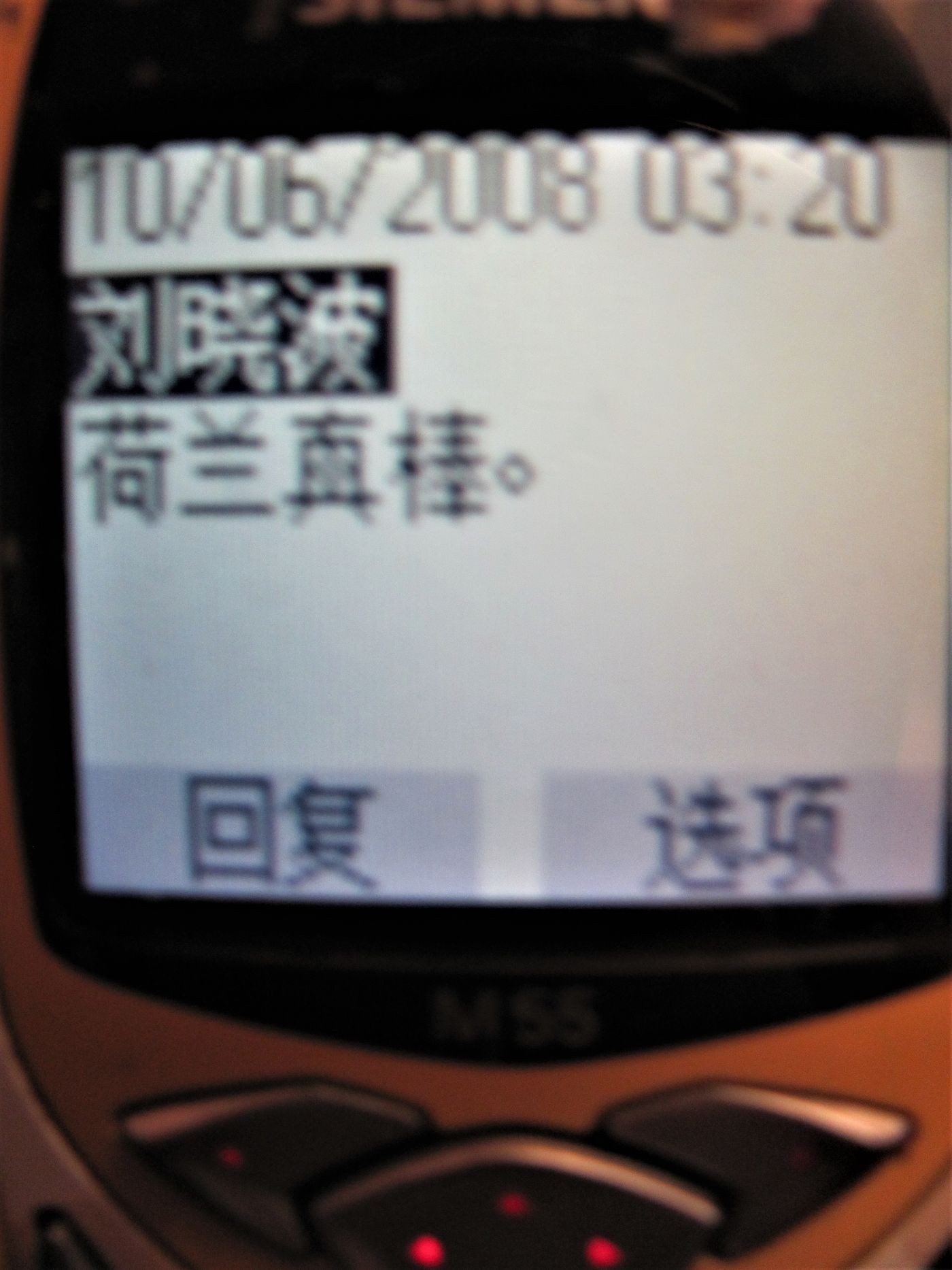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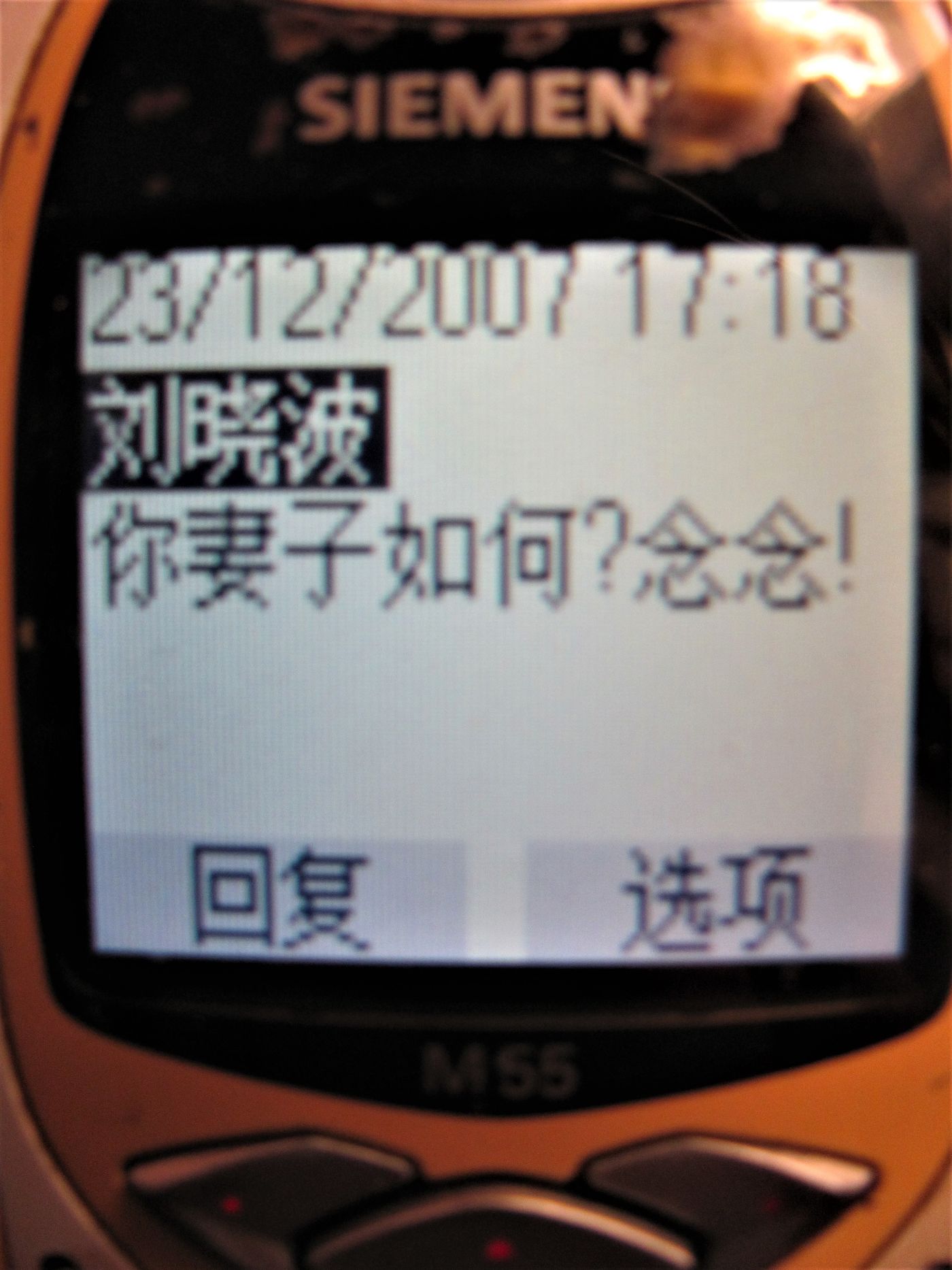
我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冬日。当我按响他的门铃时,他迫不及待地从楼上三步并作两步赶下来开门,然后伸出双手拥抱的场景。想起那个晚上我们在他家客厅畅聊至凌晨六点,直到我迷迷糊糊地在沙发上入睡,醒来时看到他已细心给我盖上了棉被,准备好了饭菜,那一刻直到现在的温暖。
在他出事前几天,我们还在聊着入冬后的帝都太冷,他计划和霞南下广东避寒。我已经在安排着他到来时的行程。
没想到,那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行程。
他走了,我失了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一个兄长。
这种痛,是灵魂的抽搐。
三
在结巴患癌消息传来前几天,和结巴的一些朋友相聚,因为计算着他已在里面八年,离重见天日的时间已不足三年,我们还热切讨论着他出来后,面对今时今日天花板越降越低的现实,他应如何才能弥补失去的十一年时间,观察和适应上这对异议者更残酷的时代。但没想到比他失去自由更残酷的事情已降临到他头上。
八年间,无数次在梦中还见到他,而希望同样与梦一样不绝,觉着还有三年,就可以再听到他熟悉的结巴声音,听着熟悉的国骂口头禅,一如昨日,在电脑的skype上,谈论着巴萨队那水银泻地的华丽攻击,谈论着民间空间的生长。八年了,我们所喜爱的梅西仍然是球场上的国王,但风霜悄然染上的发鬓已在宣告他的时代渐渐迈向终结;八年了,期待温和推动的民间早已梦碎铁幕。岁月就这样无情地改变着世间,改变着人心。
四
这八年的时间,中国从后极权时代走向了新极权,江胡时代挣扎成长起来的自由空间被全面清场的铁拳碾碎。八年前,无数人为民间空间的增长而激动,渴望更多的自由,期盼着社会的渐进转型,结巴的“我没有敌人”代表着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希望与梦想。但事实上,以对《零八宪章》的围剿和对结巴的判刑已然显示着这个政权的刚性和强硬,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恐怖时代的到来,但是《零八宪章》那么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却只抓捕结巴一人,及其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沉浸在喜悦的自由阵营忽视了极权狰狞的獠牙已越来越近。
以对结巴和《零八宪章》群体的围剿为标志,重新加强社会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极权主义成为政权唯一的姿态。限制了社会自我组织与发育,控制社会个体对政权的挑战,迫害人权成为常态,而结巴夫妇所付出的代价是受难者中所受最残酷的。他们夫妇的遭遇是这中国正在向黑暗沉沦的铁证。
而这一切,是在狱中信息完全被堵塞的结巴所不知道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所挚爱的妻子所经受的磨难,这完全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他在狱中的遭遇大相径庭。那时的他可以和所炽热相爱着的刘霞在狱中结婚,而在新极权治下的今天,他却只能被癌症,妻子被抑郁症,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
五
但他的灵魂是自由的。所有在结巴生命后期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于他的温和、宽容、谦卑,与八十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坛黑马截然相反。这宽容的精神来自于生命的沉淀,来自于刘霞爱情的温润,更是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的必然。
前期的激进与后期的宽容在他身上奇妙地合为一体,这是长河劈山开路然后融入海洋的浩瀚胸怀,而没有激烈为自由而抗争过的宽容则只不过是死水一潭。
所以,他不但是言说者,更是行动者,这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里是绝无仅有的。他以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盛世中国”皮囊下的荒谬与可笑,他从不认为党国有一丝一毫改良的可能性,相反,他认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是民间主体性的首创者,为此他不但以笔为旗,鼓励抗争,更身体力行,创办和发展笔会,不是为了办成作家的“Party”,而是要构建民间政治反对的人际网络,事实上在中国互联网早期的网络异议表达运动里,由他发起的各种网络签名乃至《零八宪章》的签署,这个民间政治反对的人际网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六
在他出事前一个月,我们俩聊起共同的一个朋友刘路在美国申避的事。
他问我如何看,我说:“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是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国家,我的信念一直是: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
然后我反问他会如何选择出国的事。他说他要出国,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国自由了,他才会带着霞周游列国去,好好弥补这么多年对她的亏欠。
他选择了这条荆棘路,他对得起这个国,朋友,同道,道义,但是他唯一亏欠的就是霞。
他的一生,不是在里面就是走在向里面的路上,他为这个对不起他的国做的已太多太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只想以违背他信念的努力,来为他亏欠的至爱换取不再受苦的自由。
七
他为自由而战三十年,为生命自由、国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奋战,必成为自由战士弥足珍贵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绵长。
每个白昼
都要落进黑夜沉沉
像有那么一口井
锁住了光明
他坐在
黑洞洞的井口边缘
耐心
打捞着掉落下去的光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