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riter
大卫∙格雷伯:我原来不明白强奸有多普遍。而后那硬币掉落了

我原来不明白强奸有多普遍。而后那硬币掉落了
大卫∙格雷伯
2017年11月5日
写这篇专栏文章非常困难,因为它关于我母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因于2011年在纽约一个豪华酒店性侵一个女服务员而被捕一周或两周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一个埃及商人在纽约另一个这样的酒店因类似的性侵被短暂拘捕。
这首先让我感到困惑。这几乎不可能是抄作业犯罪;想想围绕拘捕的剧情和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辛苦的工作,不可思议会有任何人看到这会说: “好主意,让我也来侵犯一个女服务员。”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商人、政客、官员和金融家一直都在强奸,或企图强奸酒店工作人员。就是那么普通,被侵犯的人知道她们没有一点办法。
在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案子中,有人——出于不管什么复杂的政治原因——可能拒绝了去打通常会打的电话。有丑闻。结果是,当下一起侵犯发生的时候,幸存者可能对自己说, “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如果一个顾客试图强奸我们,我们真得可以打电话给警察?” 并真得这样做了。当然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最终,这两个女人都被静默了,两个男人都没有被判有任何罪行。)
我在这儿真正想引起关注的是我最初难以相信的反应。“当然事情很糟;可是不可能那么糟。”即使一个满口女权理论的左翼学者,都会本能地抗拒富人和有权力的男人经常性强奸或试图强奸打扫屋子的女人的想法,这种事一直在发生,酒店业每个人都知道它在发生(因为他们必然知道),那些富有和有权力的男人因而知道他们可以秋毫不损,因为如果任何他们侵犯的女人真得拼命抗议,所有人都会步调一致去让这麻烦问题消失。
当然正是这难以相信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懒得去接受我们认识的人会做这种彻底赤裸裸的侵犯。欺辱人的流氓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做了没事的。我写过这个。
欺辱不只是欺辱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三向关系,是欺辱者、受害人和任何拒绝对侵犯有所作为的人的关系——所有那些说“男的就是男的”,或假装侵犯者和受侵犯者之间有什么对等的人,那些看到冲突而说“谁挑起冲突并不重要”的人,哪怕在现实的情况中,这比什么都重要。
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观众还是观众只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没有区别。你知道如果你反击会发生什么。你知道人们会怎么说你。你把它内化到身心。没多久,即使什么都没说,你也忍不住想他们会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性猎取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欺辱,但是像所有欺辱一样,它最重要的是通过摧毁受害者的自我感而运作。
我有另一次相似的,可怕的意识觉醒的时刻,在读艾玛·汤普逊女爵士(Dame Emma Thompson )关于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所说的话的时候。不是因为她观察到他的猎取,就像她所说的,“不过是冰山上的尖儿”——这当然是真的,但并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让我惊愕的是一个词。她描述了韦恩斯坦的行为是典型的女性自古以来面对的“系统的骚扰、贬低、欺辱和干涉”。
让我惊愕的词是“贬低”。
这是故事开始变得私人的地方。
让我给你讲讲我的母亲。妈妈有天赋。十岁时到美国,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她跳了很多级,16岁就进了大学。而后她退学去帮家里(那是大萧条期间),找了一个工厂的工作,缝制胸罩。
那时工会有一个疯狂的想法,想要推出一部音乐喜剧,全部由纺织工人演出。这出音乐剧《如坐针毡》(Pins and Needles)让人人惊讶,在百老汇红极一时,我母亲露德·鲁宾斯坦(Ruth Rubinstein)是女主角。
她被誉为喜剧天才,这我可以证明她绝对是,登上了《生活》杂志,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和著名的滑稽艺人、脱衣舞娘、歌舞表演明星吉普赛∙罗丝∙李(Gypsy Rose Lee),有三年她和社交名流厮混,被八卦专栏八卦。之后她又回工厂工作了。
最终她遇到了我父亲,那时是个水手,他找了一份胶印工作,她专心抚养我和我哥哥,参与各种本地社运活动,偶尔也做兼职。
孩童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她为什么她没有继续舞台生涯,尽管她狂热关注戏剧;或者回到大学,尽管她给家里塞满了书;或者追求自己的职业。
后来我问她的时候,她只是说,“我缺乏自信。”可有一次我记得听到“性交易角色”(casting couch)这句话,于是我问她,她那个时候有这种事儿没有。她抬眼说,“唉,你想我为什么没有追求演艺生涯?我们中有些人愿意和制片人睡觉。我不愿意。”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掐住哈维·韦恩斯坦的脖子。并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蛆将我的母亲赶出舞台。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打碎了某些东西。我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特别的事情真正发生了;但结果是让她相信她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智识肤浅;而不是天赋才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假货。
就像所有和酒店有联系的人同声一气告诉女服务员她们不值得被保护免受强奸者侵犯,我母亲的环境中的一切都共谋告诉她,如果有人告诉她,只要她没有私下作为一个兼职性工作者做私人表演,她继续在舞台上演出就没有价值,不管她取得怎样的成就,她也没有任何怨诉的理由。
结果就是她的自我感崩塌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无数暴力的继承者。许多暴力以我们永远不能知晓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生命。我母亲是困在一个小盒子里的巨人。在她后来的生命中她仍然极其好玩搞笑;可是她也搜集绣着“别期望奇迹”的茶巾。
她抚养我相信自己注定成就伟大(就像她,我也被认为有天赋),然而,我也会多日陷于难以言说的沮丧,最终总是让她大发作,因为没有打扫自己的房间而骂我可怕、自私、不关心。
只有到现在我才理解,她是为了还要管我的房间而发作。后来她部分是通过我替代性地活着,但我假设,也为她没办法控制愤怒的内疚而遭受折磨,那是她能活她不得不活的那种生活的唯一方式。
有权力的人的暴力以无数种方式毁坏我们的灵魂。它让我们在相互毁灭中共谋。对我母亲来说太晚了。她十年前已经去世,带着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细节。可如果我们现在还能为她做什么,难道我们不能至少打破那种同声一气步调一致吗?
让我们停止假装这些事不可能真得发生——而且一旦我们知道它真得发生,还会告诉那经历这事的人,“好吧,你还期望什么?”
注:
1:格雷伯提到的工会是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2:《如坐针毡》(Pins and Needles)有关链接和视频,以及1962年该剧25年纪念版重演链接:
https://www.ibdb.com/broadway-production/pins-and-needles-1066
https://masterworksbroadway.com/music/pins-and-needles-1962/
https://jacksonupperco.com/2016/12/05/before-the-curtain-rings-down-iii-pins-and-needles-1937/

3:露德·格雷伯 (Ruth Graeber) 关于 “如坐针毡” 的采访档案,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Ruth Graeber interview on "Pins and Needles". Kheel Center for Labor-Management Documentation and Archive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rmc.library.cornell.edu/EAD/htmldocs/KCL06036-081av.html

“如坐针毡”背景介绍:
Pins & Needles, An Oral History by Harry M. Goldman. Kheel Center for Labor-Management Documentation and Archive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rmc.library.cornell.edu/EAD/htmldocs/KCL06036-006.html
4:露德·格雷伯演唱的剧中歌曲 “连锁店的黛西”(Chain store daisy)音频链接:
5:关于自己的哥哥,格雷伯有一条推文:
David Graeber @davidgraeber Replying to @nntaleb
my brother having recently died, I was her sole support, and primary carer, too. Someone from a working class family can't just ...
8:15 AM · Sep 22, 2016 from South East, England
译后记:我一直想,如果大卫∙格雷伯从来没有为女性说话,他是否真得那么革命,真得那么值得尊敬?他的启发可以当真吗?这篇文章是他为自己的母亲和女性而写的,他无愧于人们的爱戴追随了。大卫∙格雷伯言行一致,做出了榜样,这也让我想说出一直想说的话,男性不是女性的对立面,男性也是、也可以参与到女性的解放中,只要他们能够放下束缚自己的 “父权耻辱”,开始讲自己的亲密关系中女性的受辱故事,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朋友的欺辱史。即使是原谅世人一切恶业的宗教,也还需要你先有真实的作为:忏悔或者哪怕诚心念 “阿弥陀佛”。人面对欺辱,要有作为;面对他者的被欺辱,要有作为。这种作为即是面对自己的内在的反省和激励,也是面对他者和世界的承担与支持。
格雷伯说让他真正惊愕的是对女性的贬低, “贬低”这个词让他体会母亲的遭遇。作为一个女性,在中文社会的任何社会空间,被贬低、被轻薄、被刻意无视和边缘化、被静默、被侵辱,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存在环境。格雷伯一刹那间的惊愕让自己觉知,而作为女性,总是要默默无声地在心里说: “你们真好意思啊,不觉得羞耻、可怕和可笑吗?” ——就像在看着愚比王的人鬼宫廷演出一场永不羡慕的荒诞剧,戏中角色不知道自己在演戏,不知道这是地狱的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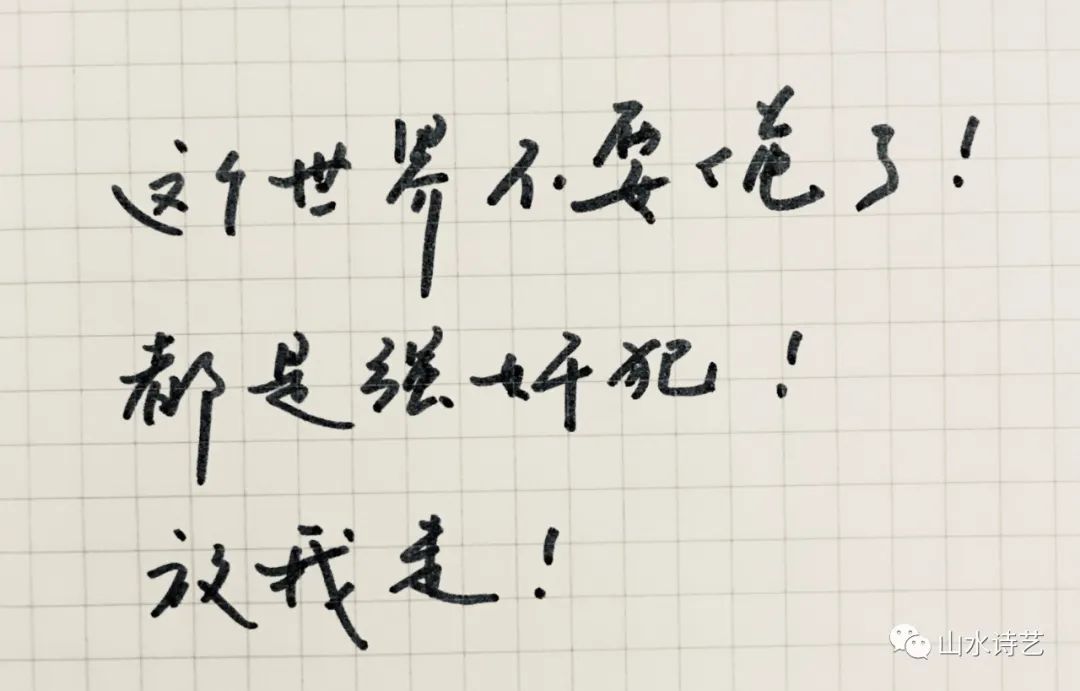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