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夫之人,以为有女。
“雅尔塔在下雪”——疫情日记
“我一直在等您,苦苦地等您。雅尔塔在下雪,潮湿,刮风。但久居本地的人说,还会有好天气的。”

一、“我多想往后看一眼,我多想绊倒以后,就能回去......”
夕阳渐渐熄灭的时候,树的阴影里雪迟迟未化。半环形的山脚下是一个村庄,墙壁与黄土、与冬季的树干一样坚硬,一样干枯寒冷。窗户黝黑,窗棂的暗红色被风剥去。似乎是一个死去的村庄,无形刀剑杀伐中被抛弃的村子。“村子里还有人吗?” 列车行驶过长长的隧道,光便更暗一些。雪闪耀着荧荧微光,烟囱和工厂立在蒿草堆里,显得生机勃勃,树桠光秃秃的鸟巢里似乎都要有幼鸟的绒毛掉落。
村子里还有人吗?等到日头的最后一抹殷红终于从残破中抽出,我才想到,在傍晚,这样的村子是不需要灯光的。一种熟悉的昏暗就这样降落,灯绳静止垂落,没有人把它拉下。在那些无尽的冬季黄昏,年老和光影的呼吸一样缓慢。我打开门走出去,在体温流失之前抱起干燥的柴火。姥爷会挑拣粗壮的几枝丢进铁炉里,玉米叶翻转两下,在窜起的火苗中迅速萎缩。他手上的斑被照亮,小臂上干活时被割伤的伤痕被照亮,我看到姥爷手指灰黄,手指之间烟的灰烬,掉进木头和煤的灰烬中。
在彻底的黑暗到来之前,我的村庄没有灯光。
还有家对面的那个山坡,山坡下的空地,一年是沙堆,一年是麦浪,一年是松垮的玉米地,再一年又被废弃。山坡之上是一排平房,火烧云和晚风都不能将它照亮 。“是一个兔厂。” 姥姥告诉我。在深冬,狗吠声从厂里滚落,空气洁净,冬日芳烈。我和哥哥第一次顺着山坡跑了上去,纷飞整夜的大雪积得深厚,一切是那么平和,童真。狗哈出团团热气,人们的谈笑声蒸腾。我们终于看到那些兔子 —— 铁钩亮得刺眼,贯穿它们的脖子。耳朵,赤裸的皮,红宝石一样的眼睛,非常小的伤口。它们的心脏剧烈跳动,钩子便越深,雪堆般被剥下的白色的绒毛,没有沾上一滴鲜血。
“我们不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空盘旋,从上往下凝视,而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参与其中——我们“被抛”在这里,而 “被抛性” 必定是我们的起点。” 这一段回乡的路是那么可疑,无处栖居。工厂究竟在生产些什么?村庄是怎样流转,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是怎样使之离散?死去的兔子它们去了哪里?驶向故乡的列车昏昏欲睡,封闭烘热,车厢的连接处挤满了站着打盹的人。春运里,每一张面孔都疲惫,疲惫也喜悦。在 “被抛性” 的粗粝里,我惶恐着,没由来地想到黑暗,想到迟迟未亮的灯光,想到死亡……就这样抵达故乡。人们蜂拥挤出车站,母亲说,我是人潮中唯一带着口罩的人。
那是疫情爆发的前一夜。
二、“而我,则在陌生的枝桠中辨认出铁。”

一月二十三日。
“都在把武汉的人当潜在病毒,其实没有人关心患者就医的情况,没有人关心武汉的市民如何保障接下来的安全。” 更没有人关心在武汉没有住房、没有私家车的人,没有粮食储备的人,无法支付昂贵口罩费用的人……他们不在飞机场,不在高铁站,在大巴和卡车里,在回乡的喜悦和未成形的恐慌中,梦是断裂的,颠簸的,黑乎乎的。近日似乎每一天都在和家人争论、争吵,从瞒报模糊的信息,滞后的宣传警示和应对机制,消失的深度报道,被扣押的记者,到公民的言论自由,“众志成城”的叙述,对医生奉献牺牲的歌颂……以及反复的提醒,请求,测体温。扑面而来的焦灼把一切都淹没,雾霾笼罩,整个城市变得不确定。
我想起很多个夜晚,战争的夜晚,流离失所的夜晚,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鼠疫的夜晚,爷爷去世的夜晚,婴儿的夜晚。而这个夜晚,街道昏黄,落日湿软。每隔一段,我看到环卫工人拿着扫帚和垃圾桶站在松树前,车流飞驰,他们静止着,好像景观融化掉落的碎片。鼓楼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21世纪不动产连锁店已经放假,晚上9点钟,小卖部老板把高高堆积的年货搬进店里——他们没有带口罩。当新闻联播用一分钟时间介绍疫情时,当湖北卫视用煽情的词汇遮蔽医生的超负荷工作时,我知道在感染科工作的大姨仍在医院。“我早就危在旦夕了,我们现在都危在旦夕,因为我们的秘密与谎言,我们根本就是他们的化身。” 春天虚掩着,人人处在一个自我隔离的状态。我想,不仅仅是瘟疫,将我们分开。
三、“雪片落上了苹果树......我们面临初次的痛苦”

一月二十八日。
妈妈从睡梦中突然坐起,她哑着嗓子说,“ 科室最近太忙,大姨生病了,现在自己住在213(从前的老房子)隔离。”手机屏幕一篇文章,《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倩倩的自述停在春节零点那一刻,“我想我们也算过了一个不错的年,爸爸要买的那么难买的药,我买了很多很多,妈妈也说她有护工了。我想我们一家马上就要团圆了。” 时间显示已经是深夜,混沌的黑暗堆满整个房间。妈妈慢慢躺下,说了句别担心,快点睡吧。
放下手机,闭上眼。白天读的句子逃窜出来,“死神已经向他靠拢过来,不过它已经没有任何形状,只是占据了空间。” 眼泪持续地灌进耳朵里,整床被子潮得像条河,我的耳朵太痒了。大姨,我的耳朵太痒了。
也有几次像这样哭过。我从不在母亲或者其他家人面前流泪,但见大姨却总是没由来地哭。好像觉得在她跟前我可以永远做个孩子,可以委屈,可以脆弱。大姨身上常年带着医院消毒水的味道,空旷,悠长,像夹生的香蕉,有些艰涩,却让人安全。第一次因为生病住院时,大姨就是带着这样的味道走到我的床前,给我剥开一根香蕉。这是一种多么好吃的水果啊,干净、饱满、香甜厚重并不言说。穿着白大褂的大姨像整个城市一样简明净洁,令人紧张。那是夏天,阳光从透亮的玻璃洒进来,病房里有沁人心脾的凉意。童年的睡眠,是一朵山花镇静地垂落,我学会在走廊来来回回的声响中,辨别出大姨的脚步声。
在国外呆了一年后回家,正好碰上大姨的生日,我和哥哥带着花束去医院找大姨。感染科单独设在新医院一栋灰黑色的平房里,走道弯弯绕绕。大姨的办公室很窄,一张桌子,一张床,放满书的铁皮书柜,一个洗手盆和立着的衣架。我们面对面坐着,大姨的声音爽朗,笑声脆亮,我的手心、脊背却崩地很紧。有种味道轻盈盈地顺着墙壁游走,横亘在我们之间,好像冬天枝头的一颗石榴果实,有不易觉察的迟缓与疲惫。姥姥身上也有这样的味道,妈妈从前告诉我,那是人变老的信号,衰老的味道。一阵酸痛重重打在鼻梁,溶解了全部坚硬,我又哭了起来。大姨用两只手不停地帮我擦着眼泪,也擦自己的眼泪。她什么也不问,只是一直重复着,“小柳是个好孩子,小柳是个多好的孩子啊。特别坚强,特别优秀。”
死亡没有形状,它会占据所有空间。那种恐惧会真实地攥着你,用全部的重量压着你。08年大姨做了一个大手术,我又从县城来到市里的医院,只不过这一次,我们的位置调转。大姨躺在病床上,嘴唇苍白。那些关切和问候我怎么也说不出口,大姨拉拉我的手,让我坐在她旁边。我问大姨,疼吗。大姨说,好疼,半个腰那么长的刀口。然后是沉默,无尽荒漠般的沉默。那个下午,我吃完了整整一排香蕉,果皮青绿,涩味蛰居,我没有剥一根香蕉递给大姨。
在没有边缘的无助里,我想着大姨的手掌,拿着手术刀的、干净有茧的手掌。夜晚在阴冷的湿意里摇摇晃晃,一片昏暗中大雨如注。我湿淋淋地穿过,而后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芬芳的晴天。是童年的老院子,大姨搬两个凳子放在院子中央。我小跑着跟过去,趴在大姨的膝盖上,就像7岁、8岁、12岁时那样。阳光柔嫩,桐树有淡紫色的香气,我闭着眼,手指关节放松。大姨低着头,顺着光线给我掏耳朵,她的小臂温暖,太舒服了我都快要睡着。“我愿意用一切交换她的平安,她一定不要有事。”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对自己说。想到倩倩或许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想到此刻800里外的城市,有多少人在眼泪中无眠,我觉得自己不能痛苦更多。

四、 “只有人类 相信,告别有一个词”

一月三十一日。
好几天没有出门了,今天午觉醒来决定和妈妈出门走走。因为车辆稀疏,道路显得愈发宽阔。太阳高远,风很清冽,几朵蒲公英在料峭里飞旋着落在脚边。我们都感到很畅快。过马路的时候风变得强劲,妈妈停在马路中央,她紧紧揽着我说,“柳,我突然有些晕眩。”
临汾是盆地,远山层叠的轮廓在大风天里变得清晰。天那么蓝,阳光眩目,河滩的灰黄铺展开来。我们静静伫立在路中央,植物枯黄,楼宇空空荡荡,鸟声无处可寻,视野之内没有一个行人。这种空旷又深又重,时间和恐惧像潮水一样缓慢,靠近。痕迹和连结在静默里失去踪影,造路的人,种植的人,街边的商贩,骑三轮车呼啸而过的快递员……昨日的摺叠明灭变得空空荡荡。直到一辆车驶过,直到我们知道有人驾驶着一辆车驶过。
四顾茫然间,我想,可能这就是结局了。晴朗、无人、失去、沉重的梦魇一般。妈妈讲起03年的疫情:被隔离的儿子无法参加母亲的葬礼,她在四方的院子里洗着永远也洗不完的衣服,邻居姐姐给我一块糖果,那块糖是如何令她恐惧万分。“最后呢?”我问她。“然后,非典结束后,我就带着你离开了。”
结局会降临在阳光普照的季节:医生战胜了病毒,权力拯救了苦难,我们对高处信任,对错误宽容,被歌颂的会继续被歌颂千遍万遍,英雄的城市依旧荣光。可是啊,可是我想记得。我要记得虚假,撕裂,隔离,苛刻。我要记得被牺牲的,被放弃的,被暴露的,被忽视的——他们本不必牺牲,他们本应团聚,好好活着。我要记得贫穷,一无所有地给予,记得诚挚,在歧视和不平等中理解。“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 我要忘记数字,记得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悲苦。我要忘记鞭炮,记得这条眩晕的河道。我要记得做事,互助,行动,信心。我要在几年后重复的恐惧和绝望中记得, “结局是失败的,这是一个耻辱的新年。” 我会告诉我的家人,朋友,爱人,“然后,新冠结束后,我就离开了。”
五、“之后,我们可能还活着,和月亮一起”

二月九日。
出了小区后顺着滨河路走,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右转进五一西路。夜晚的道路空无一人,城市的灯光被抽离后,我的散光愈发严重,红绿灯融化着快要滴落,跳动的数字难以辨认。过了秦蜀路街口,就是五一路了。两旁的桐树枝干伸展,在莽莽黑夜里相逢。等到依稀看见平阳南街那个落寞下去的大饭店,车已经不知觉开到朋友家巷子口了。
然后是五一东路,左拐进迎春南街。迎春南街再往北就是临汾火车站,上高中的时候,火车的鸣笛声总是紧紧抵着梦的边缘,它让我睡得很好。路过六中,校门口空空荡荡,万家福连锁超市好想要彻底熄灭似的。超市对面有两家还亮着灯的小店,灯光被夜色泡得松散,有逼仄的绒光。然后左转,是解放路了,是我们走过千遍万遍的解放路。
褪去人烟阜盛,解放路有种肃穆的寂静。在被隔离的日子里,故乡城市终于显出了它本来的样子,狭窄,老旧,灯影和树影斑斑驳驳,在夜晚显得哀愁,哀愁又宽厚。我觉得自己正往山穷水尽处开去,沿途都是告别。车开到解放西路路口时,整个年少时光和此刻的难过一同沉溺下去。
再回到滨河路,已经算走过小半个临汾城了。我们决定下车去古城公园走走,顺着往昔的记忆还能想起公园一些:未结冰的河,塔松和圆磨石头,仿元代戏台,和用木板拼接的摇晃的桥。我们跑几步,像狗一样跳了几步,空气寒冷清透,一张肆意的网刚刚撒开,笑声还没凝固,然后我们看到了月亮。
月亮挂得很高,却那么满。一个硕大的圆月,切断了世界的所有瞬间。我们都觉得手足无措起来,湖水平静,好像已经这样平静地存在了几百年。有一个老人沉默地路过,几十年人生尽头都沉默一般,那样路过。
我们谈到了李文亮医生,然后又迅速掐断了话题。走过小路,爬上城墙,这是公园的最高处了。远处被修缮过的古城墙整洁、高大、规则,同样圆满的月亮给它镀上一层光辉。我想起15岁时,城墙还是一片荒土。那会儿,我和母亲在学校附近的小巷子租房住。狭长的巷子最深处抵着一个断裂的土坡,各式各样的垃圾顺着土坡滚下去,掉进肮脏的护城河。冬天租住的房子没有地方洗澡,我和母亲会提着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走向更深的巷子,沿着这条土路向下。坡中间是一间台球厅,台球厅旁是澡堂。
湿漉漉勉强不滴水的头发,澡堂里氤氲的黄色灯光,所有的声音在水汽里泡胀,湿湿软软云团一样碰撞着鼓膜。热气笼着人的身体和各种沐浴露的味道,有一种黏腻的香。湿气在空间里又重又紧,并不温暖。离开热水时牙齿的战栗和未擦干身体就套上一层又一层衣服的刺挠感,它们在感官里浓稠地凝聚,又在上坡的路上慢慢散开。母亲说,这段路就是古城墙,下面的污水就是护城河。
这两段护城河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又是假的呢?我甚至不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站在高处向远望去,黑暗象群似的睡在城市。我们听到有一个人向着深不见底的沉寂大声吼叫了一声。声音穿过之处是一片虚空,它响亮地捶在我心口,却没有一片叶子为之震落。可月亮还是那么圆,还是那么满,我们拼命地说着,像是无法承当什么。身边的朋友是真的,所有的回忆是真的,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被斟酌,它未曾也不会是任何预言。在这场纯净盛大的秩序中,我拼命回想着,奔逃着,我想月亮一定会记得。月光皎洁,一定有什么还活着。
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察到这会是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夜晚。有它在我就不会被打败,不会被死亡。我惶恐万分又迫不及待,冷风冷树,云雾清澈,我心急如焚,想让一种勇敢发生在今天。
六、“There's a reckoning still to be reckoned and there's gonna be hell to p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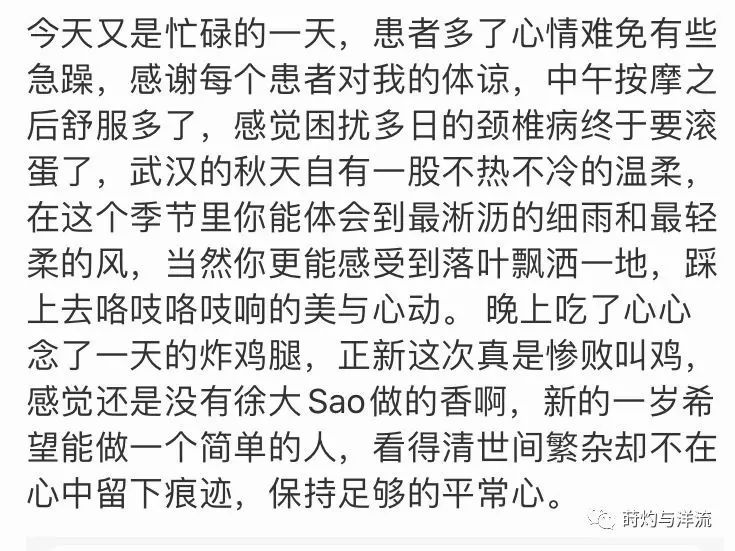
二月六日,二月六日,二月六日
致高尔基 1899年1月25日 雅尔塔
我一直在等您,苦苦地等您。雅尔塔在下雪,潮湿,刮风。但久居本地的人说,还会有好天气的。
贫穷的肺病患者纷纷涌来。如果我是省长,就会用行政的措施给他们安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面对他们,不好意思过我的安逸的温饱生活!
看他们乞求的面容,看他们临死时盖着的破被子——心里很痛。我们决定为他们建造疗养院,我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因为找不到其他办法。如有可能,您把这份呼吁书,拿到与您相熟的尼日尼和萨马拉的报纸上去作番宣传。也许会从那里寄来一些捐助。前天,《开心》杂志的诗人叶彼德诺夫在此地一所病患收容所里去世了。在去世前两天,他说想吃苹果蛋糕,当我把蛋糕送到他手里时,他刹那间有了精气神,病痛的喉咙发出了沙嗓的声音,高兴地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好像见到了乡亲。
您很久没有给我写信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喜欢您久居彼得堡——那儿容易得病。好了。祝健康和快乐,上帝保佑您,紧握您的手。
您的А. П. 契诃夫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