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人,寫作者,哲學愛好者,男的女性主義者。
性別歧視的權力結構: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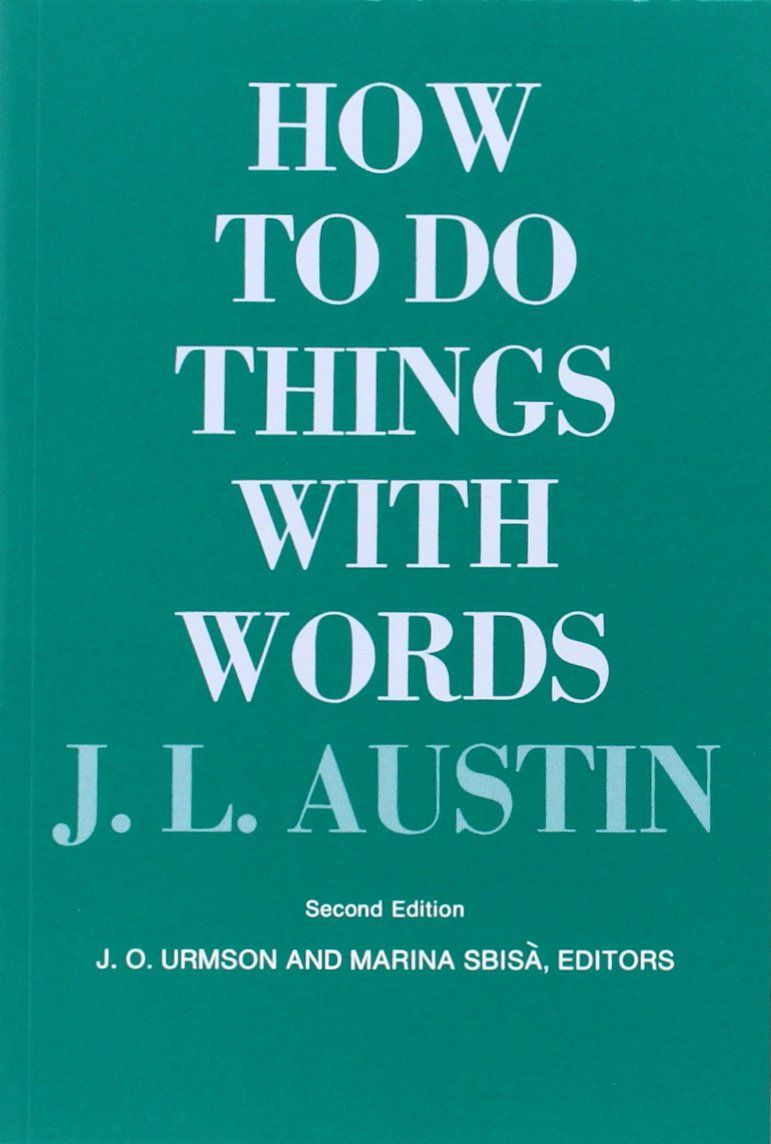
去年台灣立法委員選舉時,民進黨在台北市第三選舉區推出了吳怡農先生作為候選人。由於吳怡農身材壯碩,面容姣好,受到不少女性支持者愛戴,有不少人甚至幻想自己是「吳太太」(即幻想自己是吳怡農的太太),並在社群媒體上不斷讚嘆吳怡農有多帥氣、多性感。於是有不少男性出言批評這些女粉絲,認為如果性別調換的話,讓男性粉絲如此意淫女性候選人,一定會被指控性騷擾;既然男性不應該意淫女性候選人,那麼女性也不應該意淫男性候選人才是。
我認為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終究還只是在形式平等的層面思考問題,而沒有探討到性別關係中的權力面向。所以我當時決定寫一篇文章,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切入,借用哲學家 J. L. Austin 對「言說行動」的探討,來更深入分析這個課題。我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女性主義哲學家 Rae Langton 對「言說行動」理論的借用與發展。從某個程度來說,我這篇文章也算是舉例說明了當語言哲學碰上女性主義時,可能有怎樣的發展。
最近立委候選人吳怡農因為身材壯碩又長得帥,被一些女性粉絲公開意淫。女粉絲們留言說出了「想當吳太太」、「想摸他胸肌」、「想吸他下麵(面)」這類的話;還有人說吳怡農上衣扣子沒扣好,害她整晚睡不著覺。
於是有人說,既然男性不應該公開對女性政治人物說出「想摸妳的奶」之類的言論,那麼女性粉絲也不應該公開說一些類似的話。但與此同時,也有人替女粉絲們辯護,說「男性意淫女性」和「女性意淫男性」在父權社會中有著根本不同的意義,不可一概而論。
我看了兩方陣營的評論,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完全同意任何一條評論。既然無法按讚了事,只好自己寫一篇,表達一下意見。
首先我想要反對一下其中一種類型的意見,那就是:「男性對女性的意淫,除了嘴巴說說之外還會付諸行動,所以很不可取;女性對男性的意淫,則只是說說而已,比較沒有關係。」
認同這類型意見的人,可以思考下面這件事:2005 年,還不是美國總統的川普在鏡頭前說,只要你成為明星,就可以對女性做任何事,包括「抓她們的下體」(grab them by the pussy)。川普競選時,這段錄影被起底公開,而川普則辯解道──他只是說說而已,不像有些人真的會去做,所以算不了什麼。
這是一個合理的辯解嗎?
我想,這類說法的問題在於,它把「說」和「做」看成可以明確區分開來的兩件事。但我想任何接觸過認知語言學或語言哲學的人,都會馬上警覺到其中的陷阱。因為在真實的人類社會處境底下,大部分的「言說」都離不開「行動」。
英國的語言哲學家 J. L. Austin 有一本讓我腦洞大開的書,叫做《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用言語來做事情。這是一本永遠改變了語言哲學的書,裡頭就在告訴我們,「言說」其實就是一種「行動」。所以他不單說「言說」,也不單說「行動」,而是合起來說「言說行動」。而在所有的「言說行動」中間,又可以區分出三種類型。
這三種類型的分析,後來在基進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了驚心動魄的應用。我不想抽象地解釋這三種類型是哪三種,我直接講三個我改編的例子比較快。
- 首先,想像一下一個人用只有自己聽得到的音量跟自己說:「我想吃飯。」這句話沒有被別人聽見,因而不產生任何社會果效。但他的確是說話了,他說這句話的那個動作,也就是單純的一個言說行動,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他會說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
- 想像一下第二種情境,有一個奴隸對他的主人說:「我想吃飯。」這句話就不單純只是言說了,它同時還是一種懇求。這個奴隸在懇求主人允許他吃飯。當然,主人可以不同意。無論如何,這個奴隸做出了一個「懇求」的言說行動。
- 最後,延續第二種情境,假設主人對奴隸說:「我想吃飯。」這時就不單只是言說了,也不單只是懇求了,它是一道命令,命令奴隸趕快把飯菜準備好。這時候,無論奴隸接不接受,主人都已經做出了一個「下命令」的動作,而且是在說的同時就完成了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有了三種言說行動,一種是單純說話的言說行動;一種是說完之後等待別人回應,但人家可能不理你的言說行動;一種是說完的同時就完成了某種行為的言說行動。
我們來看一下,奴隸可以完成哪些言說行動?奴隸當然可以完成單純說話的言說行動。那「懇求」之類的言說行動呢?也可以辦到,只是主人不一定要憐憫他。那「下命令」這類的言說行動呢?完全做不到。只有主人做得到。換句話說,只有主人才能完成全部三種言說行動,而奴隸最多最多,只能做到前面兩種。
那這個區分有什麼意思呢?它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完全相同的一句話,被「不同權力位置」的人說出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行動」。而有些語言行動,是只有「有權力的人」才做得出來的;沒有權力的人,是完全做不出來滴。
七〇年代的色情女星 Linda Lovelace 拍攝了劃時代的色情電影《深喉嚨》,片子票房達 600 萬美元,但出賣色相、出賣肉體的 Lovelace 總共只拿到了 1000 元美金,且還不說劇組對她的百般虐待、哄騙和脅迫。在她後來的人生當中,Lovelace 成為了一名反對色情產業的女性主義者。她出版過一部回憶錄叫做《Ordeal》,裡面就寫了她在色情產業中親身經歷的種種剝削和暴力。
書出版後,想像不到的諷刺事發生了──這部批判色情產業的回憶錄,和其他大量色情出版品,被商家放在同一個區塊一起販賣。換句話說,她這部反對色情的作品,被當作了色情作品般地被販賣、消費。哲學家 Rae Langton 寫道,她收集到一份當年的廣告型錄,上面第 426 號商品叫做《禁忌的性幻想》,第428 號商品叫做:《性派對的情色體驗》,至於第 427 號商品, 就是 Lovelace 的回憶錄。
對 Rae Langton 來說,這件事的啟示就是:女性沒有完整的言論自由。因為對男性來說,他們不但可以「說出」任何政治立場的話,同時也可以「主張」這些政治立場;但是女性卻只能「說出」反對色情的政治立場,但沒人把這些反色情的主張當作主張,而是反過來當成色情材料。這就好比在 A 片裡,女星說要就是要,說不要也還是要。而在很多真實的情境下,女生的「不要」其實就只是單純的言說而已,或者至多是一種懇求,而從來不是一種單方面說了就算數的「否絕」。
回到吳怡農的事。在區分了三種不同的言說行動後,我想我們大概很容易看出,「男性留言意淫女性政治人物」和「女性留言意淫男性政治人物」,兩者只在單純言說的層次是相同的。真正重要也困難的是,兩者在語言的第二和第三個層次上,到底有多大差異?我想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備註:文中講的三個例子,不是 Austin 原本的界定,而是哲學家 Rae Langton 受 Austin 啟發後給出的界定,並且也已經過我的改編,和原著有所不同。
備註二:其實也有很多男同志在意淫吳怡農,但我為了縮短文章,便宜行事,先套用異性戀的架構。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