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日葵的爱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0%91%E6%97%A5%E8%91%B5%E7%9A%84%E7%88%B1&fr=pb&ie=utf-8&id=tb.1.1cd9ae0f.nzrRWDC8MqXgN29zPMwuCA
公务员的痛苦,值得同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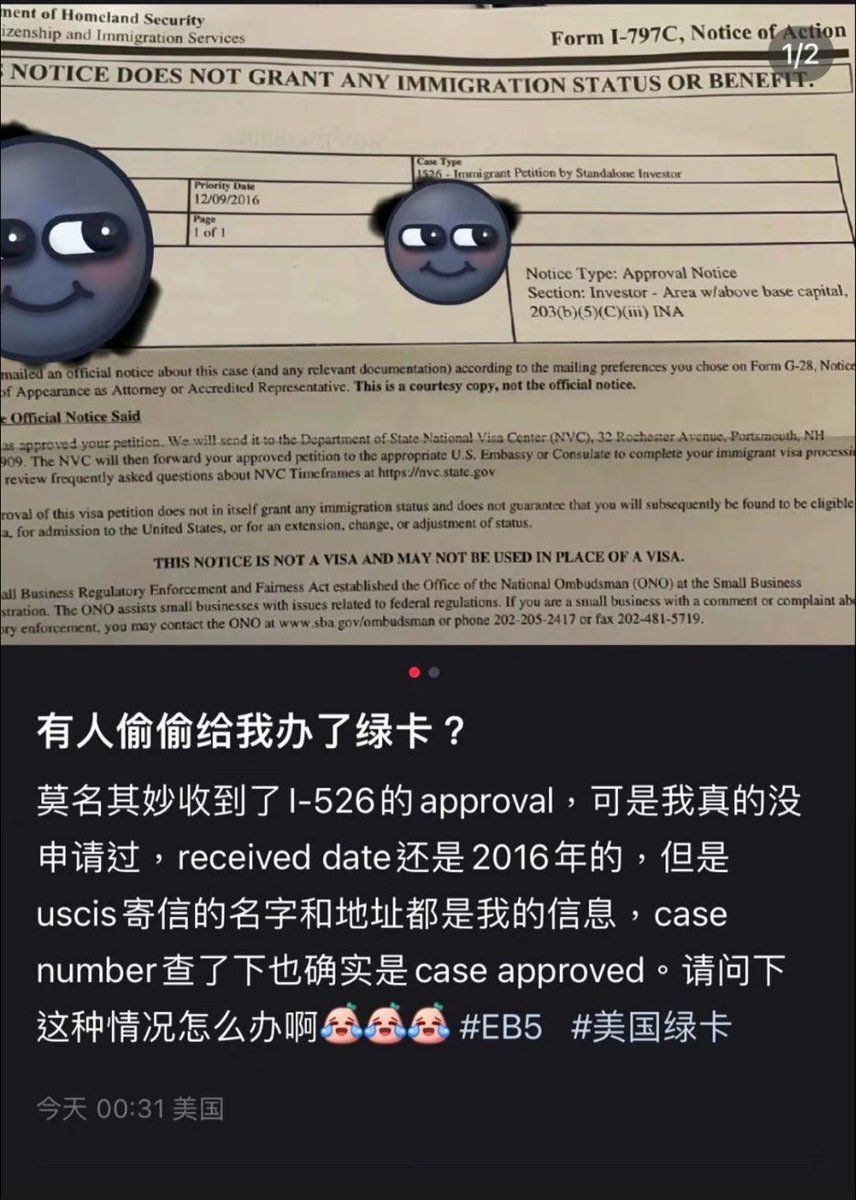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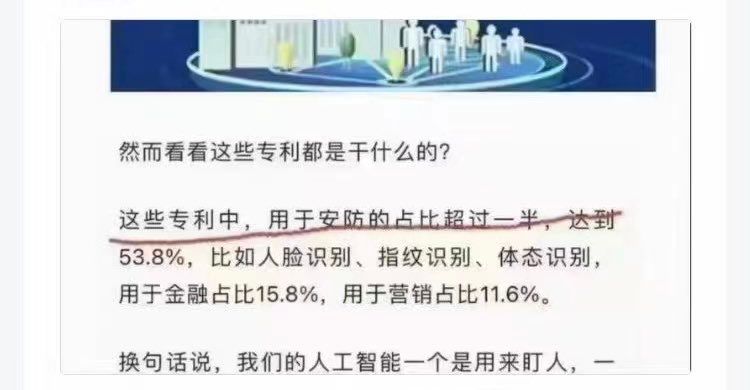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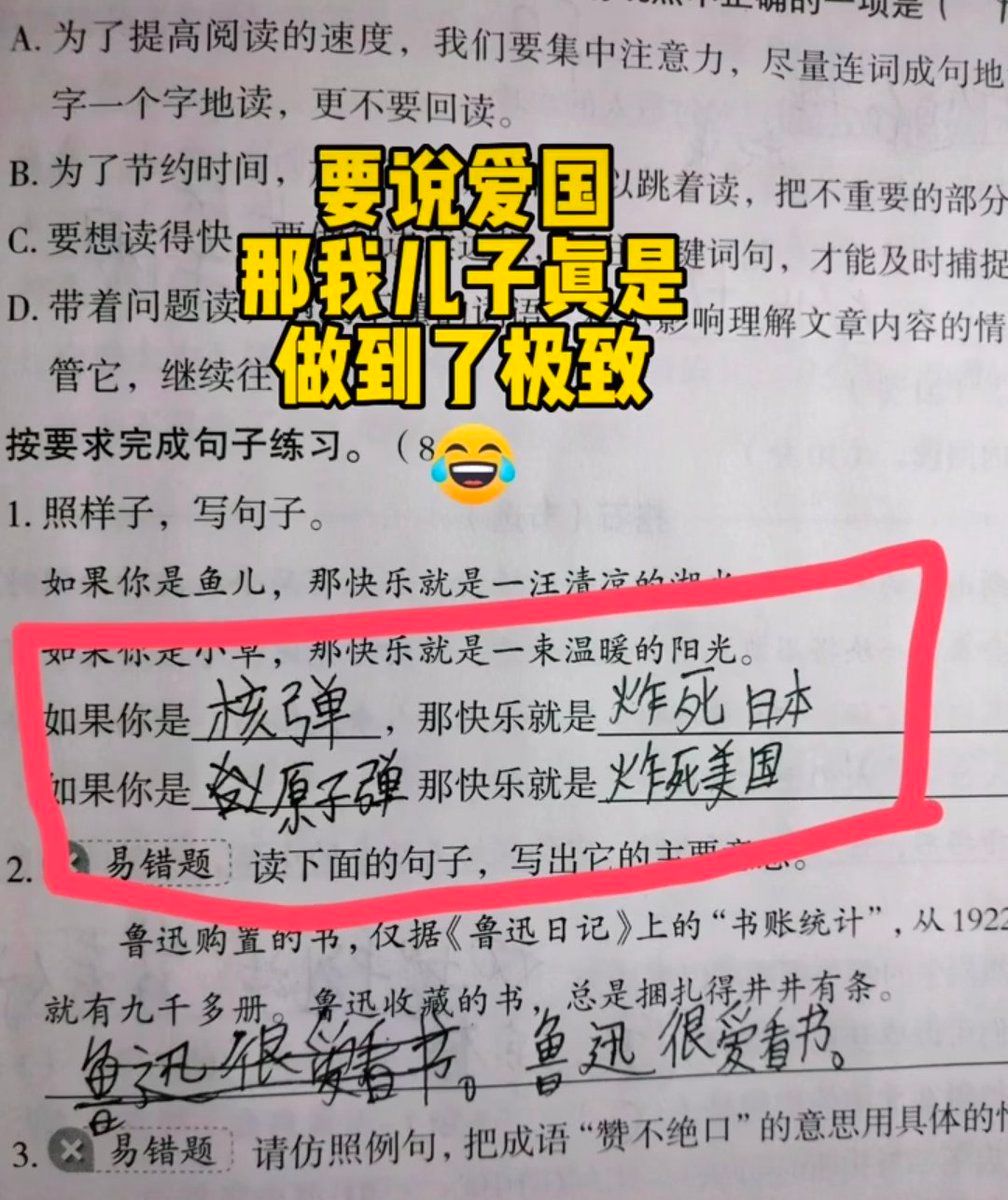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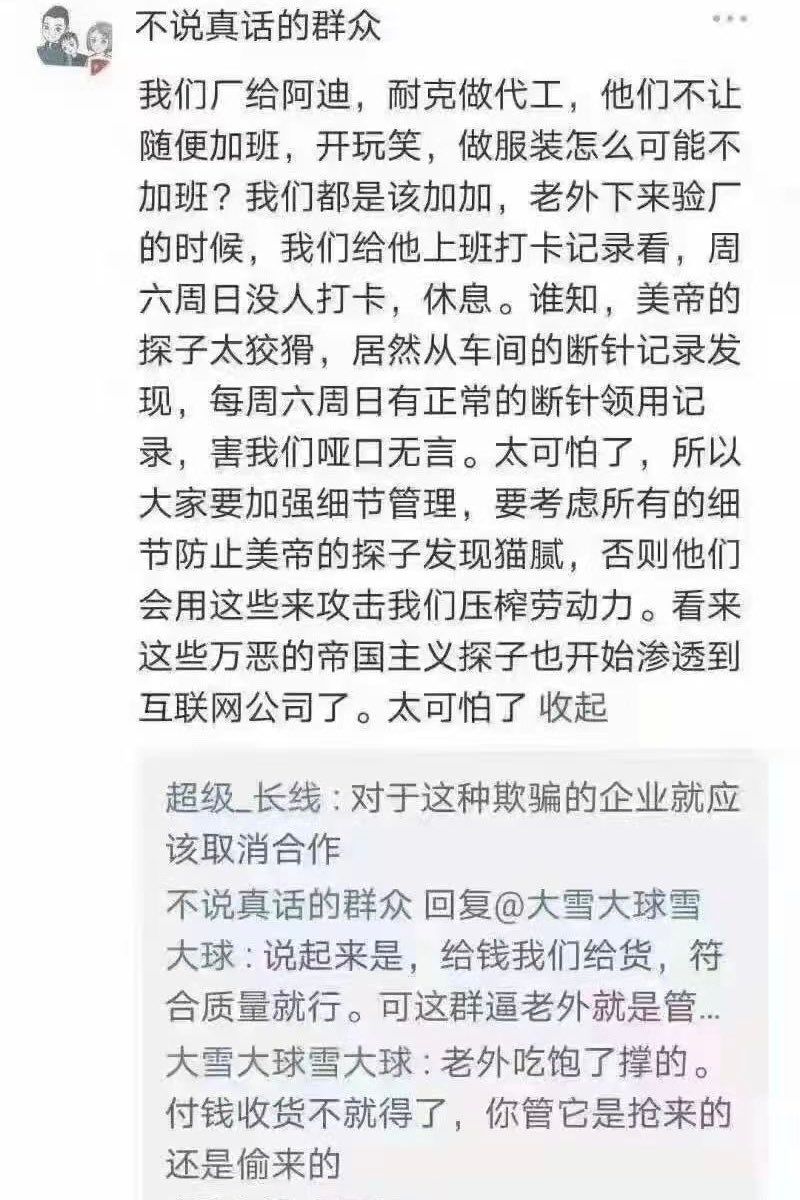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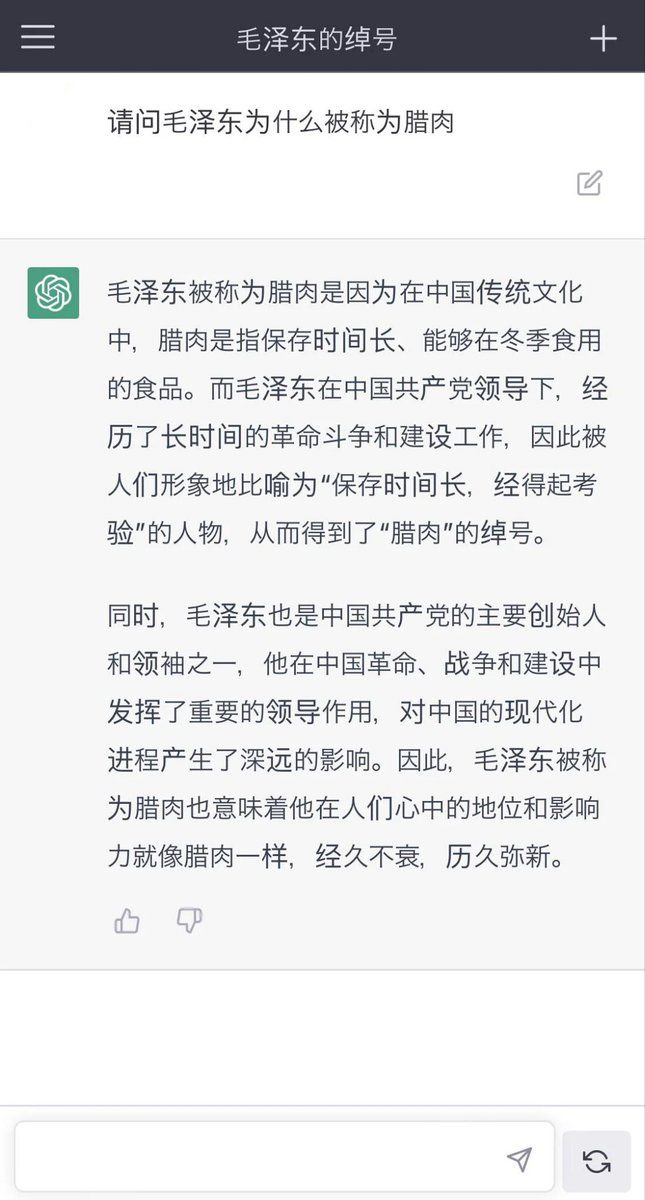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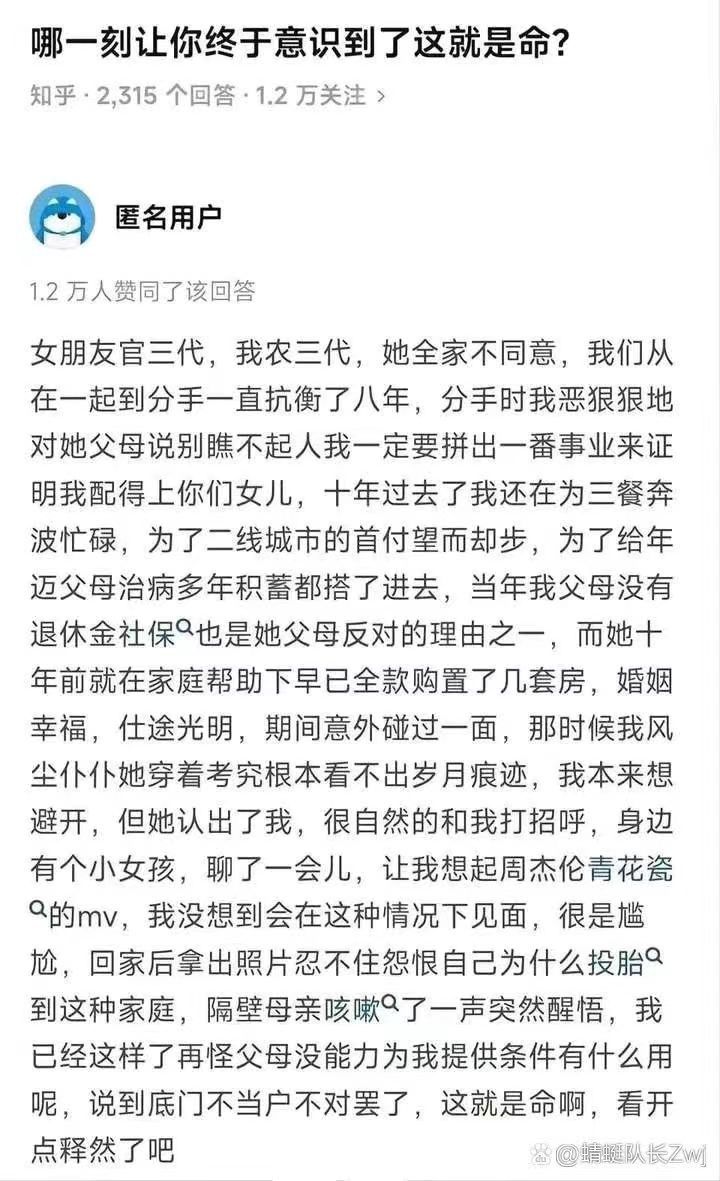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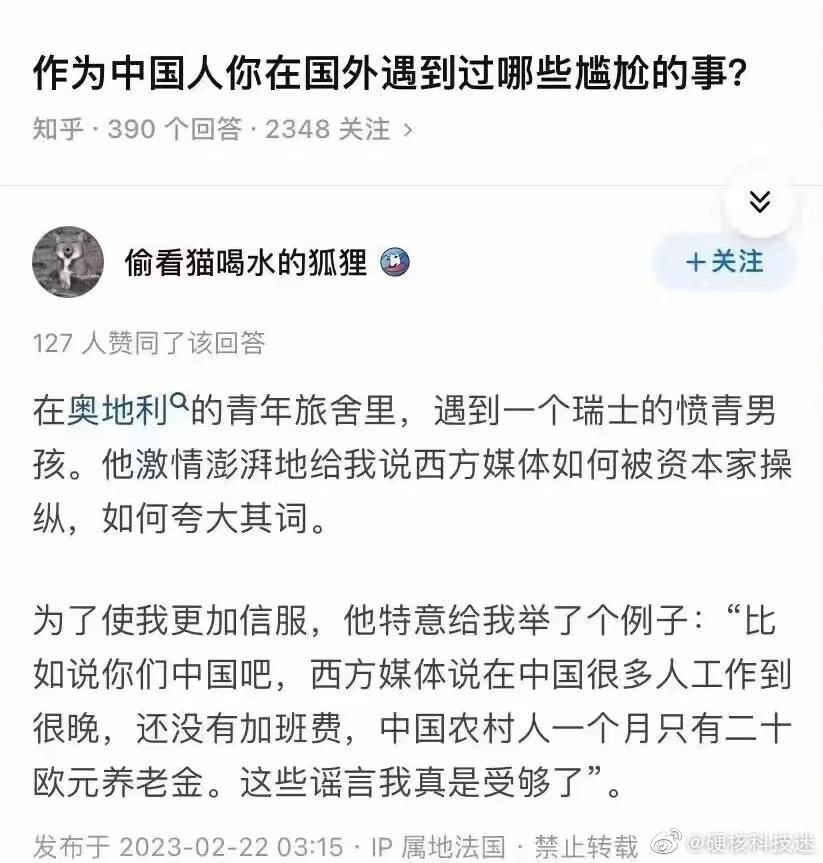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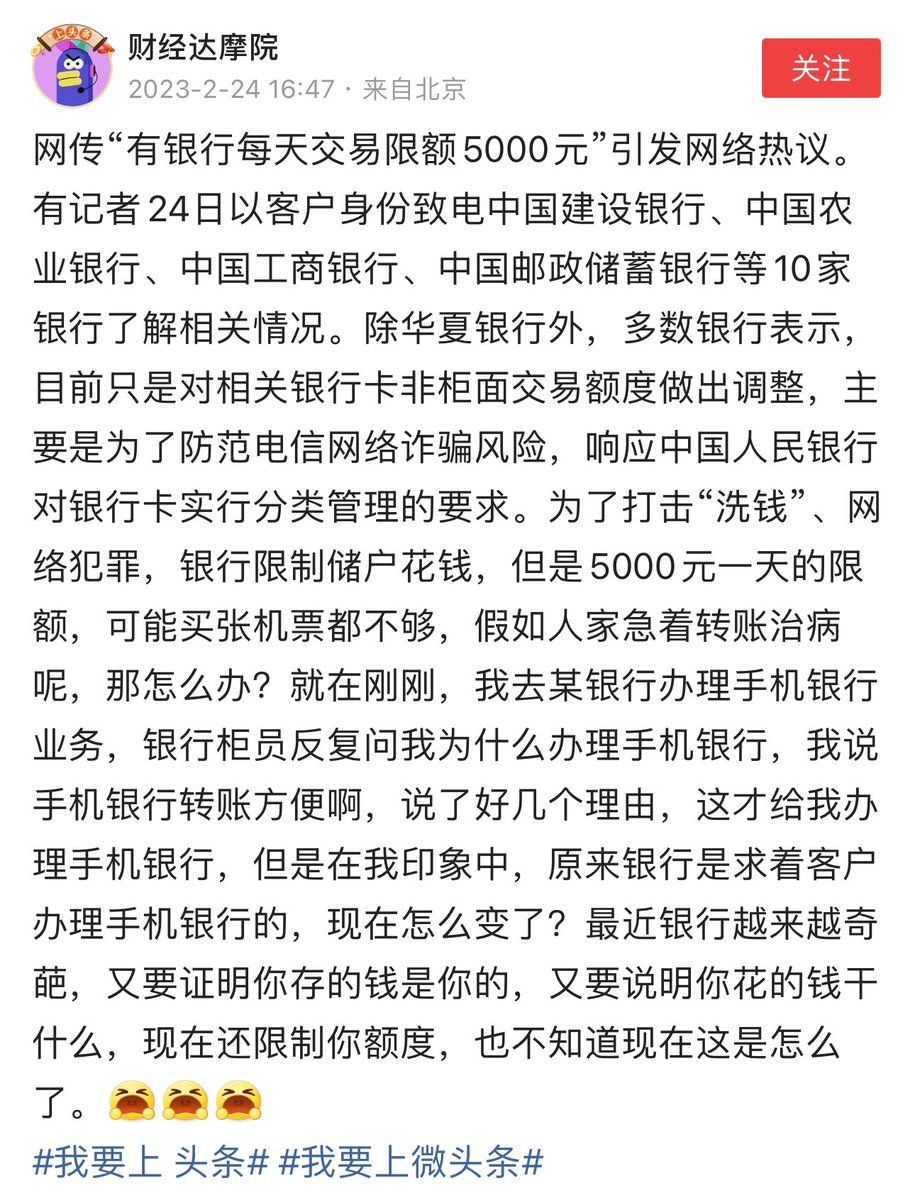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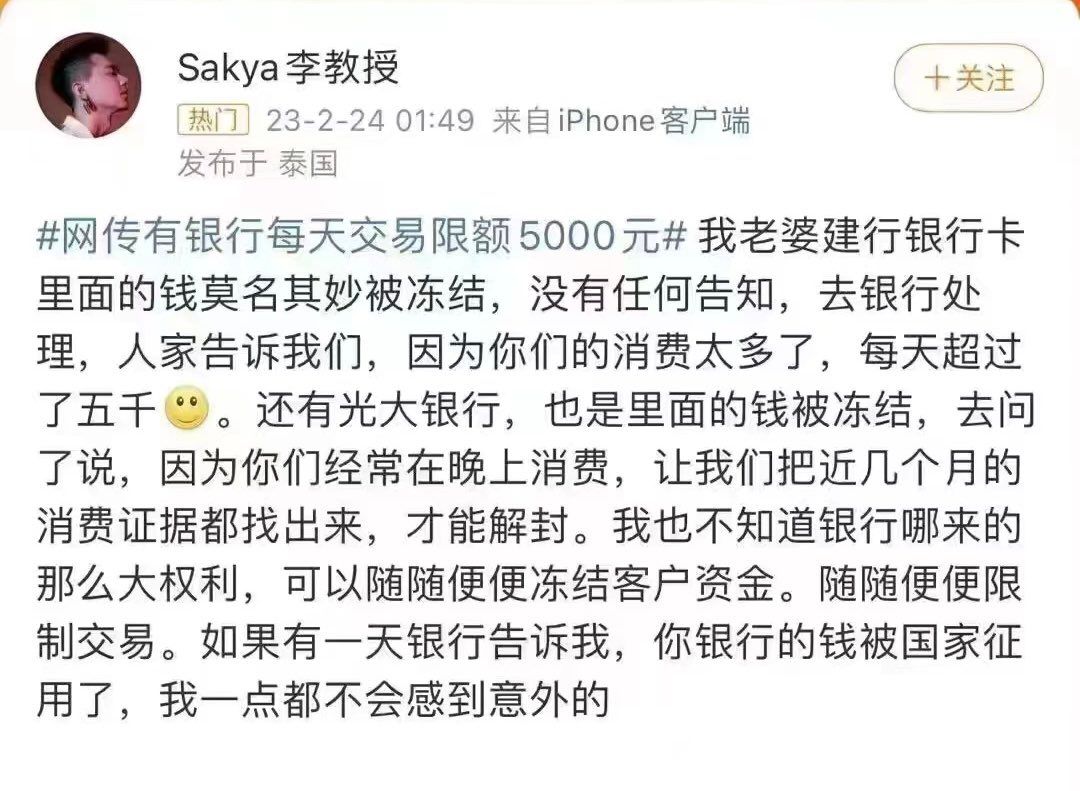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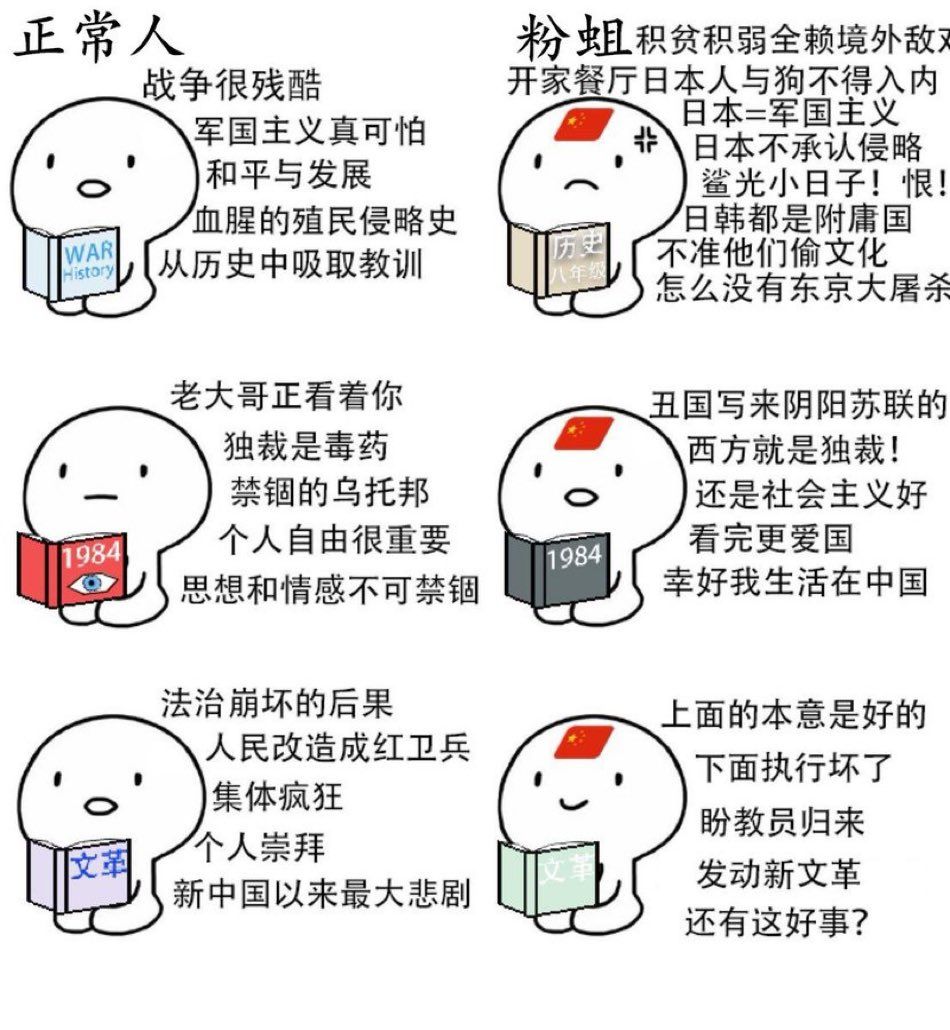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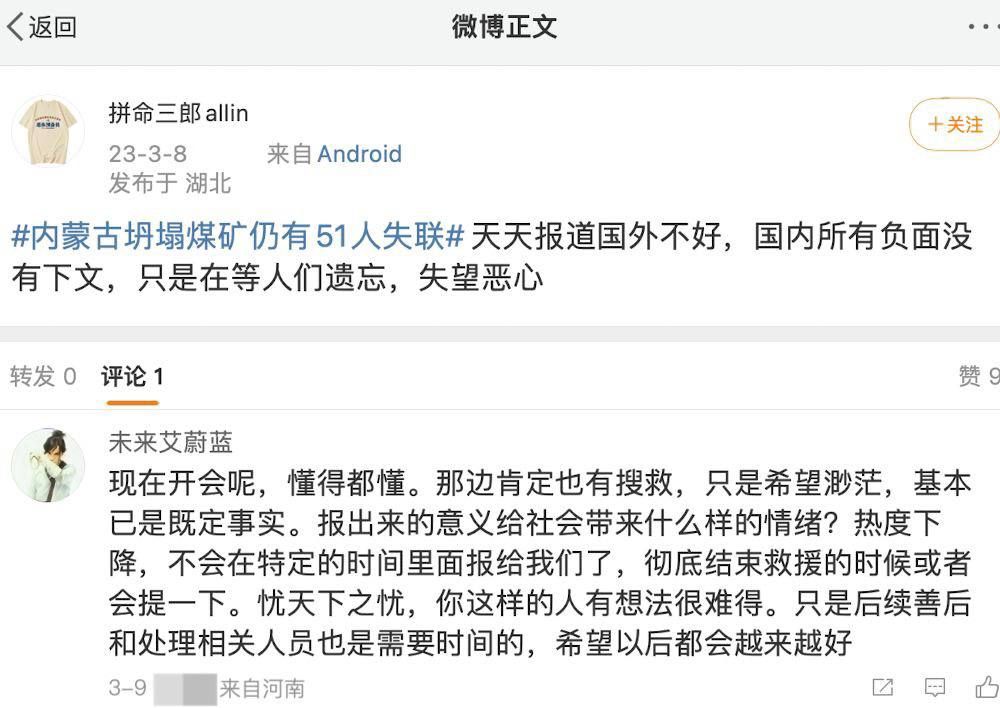

又到了每年公务员“国考”出成绩的时间了。2023年国考招录3.71万人,却吸引了超过250万人报名。这意味着每60人只有1人成功上岸。长年来,最热门的岗位出自西藏边境一所邮局,至少2万人在竞争1个名额。
在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种“最优的选择”。考公就被认为是那个正确答案之一。但人生的选择真的有最优解吗?
我的同学徐奇两年前成功上岸,考到了离家很远的小县城。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当初上榜的狂喜只是一瞬,随着他真正进入单位,意外接踵而来。去年冬天,我去他那儿住了一个月,体验了从未有过的体制生活。我想知道,对于这些上岸了的年轻人来说,公务员真的是更好的选择吗?
徐奇本来没想过考公。2020年初的时候,因为防疫,老家街上店铺都关门了。他妈妈在镇上开网吧,平时没多少人来,全指望过年赚一笔,结果落空了。有一天,徐奇在自家网吧打游戏,突然进来一群人,指着他问,“这里怎么有人上网?”他看见有人举起手机冲他拍照。徐奇妈去解围,说这是我儿子,他们没有开门营业。她解释了很久,还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和户口本来证明母子关系。
生意人经常被为难。家里开网吧,光是办证照就很难,地上掉个烟头,那就是一千块罚款。疫情期间,不知谁传出风声,要想开门做生意,按规定买一套防疫设备。那是好几万块钱,徐奇妈最后没舍得买。后来他妈就总跟他说,那谁家亲戚的小孩,正在备考公务员。
早在大学毕业前,他就琢磨着回老家上班。回想过往,他在城里读初中,班上只有他从乡下来,因为脚上一双小白鞋,被穿耐克的中产小孩嘲笑。他整天跟人打架,“来啊,尽管叫人来啊。”他朝他们喊。从此他对城市印象很糟,大学去了更大的城市,他站在人满为患的街上感到心慌,但好在熬四年就可以回老家。
徐奇也不是没参加过校招。那天在省城,他坐在面试官对面,对方问起毕业院校,他说了,面试官迟疑片刻问,是一本吗?他毕业那所学校是211,在省内算是出名的。他越想越气,“公家单位挑年轻人也就算了,你们企业也挑?”
走出那个房间,徐奇决定去考公务员。
他妈听了很高兴,立刻给徐奇报培训班,几万块钱出去,眼睛都不眨。她告诉儿子,只要能考上,花多少钱都无所谓。熟人介绍了一家小机构,地点离家有几公里远。徐奇从家里骑摩托车去上课,不久后被交警扣下,因为他没有驾照。学完行测,还差申论,没想到小机构卷钱跑了。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钱没了,而是申论怎么办。同班的女孩推荐徐奇去上另一个集训班,七天一万多。
在那里他碰到一个刚退伍的室友,睡觉打呼比雷声还响,他整夜失眠,最后买了耳塞。后来他转去更大的机构,被迫在酒店封闭苦读21天,像是在坐牢。新室友仍然打呼,他第一晚睡在了教室里。班上同学年纪区分很大,有大学生,也有三十好几的中年人。后者比前者更拼命,连下课都在用功。35岁是个槛,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第一次是省考,两百多人抢一个名额,他考第七名,还差四分进面试。他妈却莫名看到希望,催他接着考。连续失利几回,他变得急躁。当时他毕业快两年,没收入,只能向家里要钱。他妈也不敢对外说他没工作,这又刺激了他。起先他还挑挑岗位(他最想考老家的公安),现在不管了,他从三个冷门岗位里挑了离家最近的M县。尽管M县位于东南沿海,他在地图搜索这个县城,发现只是米粒大小,他转动鼠标滚轮,把它一点点放大,房子、道路和桥徐徐展开。即便知道那地方小,但眼前的画面还是让他惊讶,“镇太小了,估计连(老家)一个村都没有”。
最终他笔试拿到了第二名。看着对面坐着的面试官,他很犹豫,“那边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喔?”
“没关系,你先去占个位置咯,后面再慢慢想办法出来咯。”面试官见得多了。徐奇发现这个岗位没有标注“五年服务期”,这样顶多待两年就能跑。他还想回老家当公务员。
很快他得到了上岸的通知。全家最兴奋的是他爸。他爸年轻时是镇上出了名的混混,这辈子没正经工作过。有次聚会时,他爸最好的朋友指着徐奇说,你现在已经有些官样了。他有些莫名其妙,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他,但有些东西又好像不一样了。

第一天上班,徐奇想得很清楚,无论刮风下雨,他苟过这两年就行了。他的单位属于监管部门,曾经一度很光鲜,然而改制后逐渐边缘化。这种单位兴许不会那么累,他想。在局里,他挑中一间靠近厕所的办公室,这样同事就不会聚集在他这。他也没去申请茶盘,这样领导就不会来他办公室喝茶。他希望自己越透明越好。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他从家里搬来了台式机,下班回去打游戏。
徐奇早上八点半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去隔壁的会客厅。一套黑色的长沙发围着一张长桌,上面摆着茶盘,六七只白色茶杯四散开来。昨天在这里喝茶的人真不少。他倒掉茶杯残留的水,清洗每个杯子,接着是茶壶,最后让它们各归其位。他的余光扫到旁边的烟灰缸,娴熟地清理掉里面的烟头,然后他抽出两张纸巾,平铺在烟灰缸里。
洗茶杯在他的预想之中。高中时他听班主任讲,有个年轻人进单位,整天给老同志泡茶,后来年轻人为晋升而苦恼,那个老同志出手写了份推荐书。有好几个新人愿意洗茶杯,一个同事只在领导眼前做这事。可徐奇不一样,如果有人在场,他索性就不洗了,生怕别人以为他在拍马屁。
当初单位问徐奇能不能提早一周来报到,为单位评比做材料。第一天,主任带他在整栋楼转了一圈,“就像开学一样”,下午就开始干活。有天他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主任摇醒他,语气温和地说,帮我弄下这个文件。徐奇后来说,“他太年轻了”。意思是,每次他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主任拆分下来的任务。于是,他领到了更多的活。
为了赶时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加班,就这样连续干了21天。评比的奖项拿到了,但奖金没下来。一个新同事告诉徐奇,单位也让她提早报到,但她直接拒绝了。什么事都没有。
有天早上,局长把徐奇喊到办公室。局长问,有人会做公众号吗?徐奇摇了摇头。另一个同事也说不会。局长看着徐奇,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他,这个任务是他的了。这件事困扰他很久,为什么局长偏偏选中他?后来他听说,因为他做材料时表现太突出了。
从接手公众号开始,他已经很难韬光养晦了。公号内容多是些会议和宣传,写起来不难,但审稿很繁琐,要途经好几个领导,局长最后拍板。最麻烦的一篇推送徐奇写了两天,交上去给领导修改。其中一句——“也不都是十全十美”——领导认为听起来是有人十全十美,显得自大,于是删掉了“都”字。有天半夜,徐奇接到电话,局长喝多了,指责他在推送里写错了单位电话。他赶紧认错,然后发现别人一开始在素材里就搞错了号码。
谁也没想到,因为做公号需要直接跟局长汇报,他被迫跟局长走得越来越近。同事当着他的面说,你现在可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了”。他还被发现和局长通话都录音——因为局长口音重,他怕听错,但也被认为是高明的经营关系的手段。渐渐地,局长还会拜托他做一些小事,比如帮朋友的小孩到网上参加知识竞赛,“得拿满分”。
请注意,以上都不是徐奇的本职工作,总有杂七杂八的事莫名砸到他头上。一个关系一般的A同事因为手上的事做不完,就来找他求助。他好心帮忙,弄得差不多了发给对方,对方居然埋怨了起来,“你怎么格式都不给我弄好?”去年他帮没法早起的B同事签到。后来领导检查签到表,没发现代签,但发现签到的名字和日期写反了,不符合格式,把B骂了一顿。B又把怨气都撒在徐奇身上。还有次开会前,C同事想把领导交代的任务甩给他,他同意后才知道离会议开始只剩半小时。他没来得及做完,挨了领导的批评。
徐奇觉得自己很无辜,窝着一肚子火,没几天又消气了。他认为人情就是体制内的硬通货,即便你帮的是小忙,对方都会记在心上。所以下次他还是愿意给同事帮忙。
如今徐奇离摸鱼的初衷越来越远。当他卷入体制越深,就越难抵抗这台机器。原来人的意志力并非自己想象的那般坚定。单位的电脑连输入法的切换键都是坏的,有一次五分钟内蓝屏两次,早该报废了。徐奇申请不到新电脑,干脆用自己的笔记本办公,得心应手。他写推送也越发熟练,甚至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敷衍。他开始看不上那些摸鱼的同事,认为他们无法赢得自己的尊重,他说出这句话时,连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
有段时间徐奇想跑的念头不那么强烈,他妈想给他在M县买房,他也认真考虑过,似乎留在这里也行。但没过多久,他内心的平静又被打破,这次,掉进湖面的石子来自同事们。
有些同事“基本不干活”。早上九点过后,慢悠悠来,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急匆匆走。下午四点,3楼的健身房全是人,可五点半才是下班时间。他在停车场看到同事的车,但一整天都见不到人。他在办公室写材料,隔壁传来同事的声音,在讨论昨晚的世界杯。他们互相串门,屁股坐下,就有人开始泡茶。他尝试加入他们,又不知道说什么,双手揣口袋里,微微前倾身子,挂着笑脸,安静地听他们扯家常。
有人问徐奇,你从哪毕业的?得知答案后,同事很困惑,你来这边干吗?这种学历在这里完全是大材小用。
同事慧姐爱劝年轻人考公,她说,你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上岸了就轻松了。如果你是985大学研究生,还学文科,她就说得更直接,“企业没那么好混,除非你是有技术,可是我们文科哪有什么技术?”她拿自己的丈夫举例,当初在省城一家游戏公司画图,一个月至少要交五张图纸,再一遍遍修改,压力很大,还年轻但头发白了。丈夫后来辞职回老家,也就是现在这座县城,进学校当老师,白头发真的少了。
至于她,之前在一家投资相关的国企待了五六年,怀孕了,不想再和丈夫异地分居,才去考公。慧姐成功上岸,起初她也嫌弃那个地方偏远,借着产假的由头,在家歇足大半年,拖着不去单位报到。
有些时候她后悔这个选择,因为当年的同事们都发达了。只要不提到钱——否则她感觉自己这辈子好像越过越差——她对公务员的身份感到满意,“幸福指数很高”,“如果你不想进步的话,至少不会饿死你”。
徐奇和慧姐并不熟,后者是两个孩子的妈,即便把他按在慧姐面前,他也想不出太多共同话题。慧姐从不主动揽活,每天只需上报些数据。每次路过慧姐的办公室,往里瞥一眼,她几乎都低头看手机。他心想,凭什么只有年轻人在干活?
一位很熟的小领导安抚他,你是前途无量的人,在这个年纪要多学本事。他们摆烂过度,也可能翻车。之前就有个人生完孩子,产假结束好几个月都不来上班,单位就开除掉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同事,想“震慑”这些过于划水的人。同事听完哈哈大笑,说你傻呢?人家靠老公的关系,调到市教育局去了。他说:“领导没必要骗我吧?”同事笑得更欢乐了。
他害怕变成慧姐那样无欲无求,那种生活让他觉得荒唐。
同事阿明开导他,“不要焦虑这么多,这只是一份工作。”当徐奇在加班时,他站在门口喊,“还不走?单位又不给你加班工资。”阿明上份工作是做销售,做到了公司业绩之王。疫情最严重时,其他同事都卖不出去,他的业绩还是最出色的。没什么秘诀,就是陪客户吃饭喝酒。
有天早晨阿明醒来,突然想到如果35岁被裁员该怎么办?很快的,他辞掉工作,考到这家单位。阿明熟练地陪领导应酬,给领导挡酒,甚至还跟领导去游泳。领导也邀请过徐奇,但他说自己不会游泳。徐奇说的是实话,可当他看到阿明的办公室挪到了领导对门,心里又很不痛快。
在一天早晨,同事们半开玩笑地喊阿明“明记”。组织部让阿明去挂职村支书锻炼。徐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点了根烟。“没办法,我心里已经不平衡了。”他承认。
他坚持住在离同事很远的郊区。领导多次让他搬到城里的宿舍,他就是拖着不动。搬过去离领导的住所也很近,绝对会被叫出去喝酒,他一个人躲在郊区,应酬能推就推。那些推不掉的饭局,他表现得很局促。通常他不知道说什么,埋头吃东西,偶尔给领导敬酒。只有话题扯到他的老家时,大家才会想起他,什么你们那的人很会做生意啊,脑子很灵活啊。他只好附和几句。
但有一回,他去倒垃圾,回来时撞见了领导。领导和他对上眼神,接过垃圾桶,然后取出一件垃圾袋套上。他有点愣神,那瞬间竟有一种快感,果然这种东西还是得让人看见。
徐奇的另一个同事小王三十好几,离婚了,带着小孩住在隔壁县,每天开一辆豪车上班,往返120公里。据说他一个月的油钱抵得上其他人的工资。除了工资,小王还在老家收租,他不缺钱。要不是没法接手家里生意,他不会想考公。对他来说,进体制是体验生活,图个社会地位。不料这个富二代莫名被单位发配去乡镇。徐奇推测是领导不喜欢小王,他很认真地说,如果单位想培养你,怎么会把你下放?
说是乡镇,规模更像一个村。办公室总共五个人,都是中年男人,他们在楼上搞了间厨房,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讨论吃什么。

“乡下就是这么无聊。”一个寸头大哥说。他平时在单位的空地种点菜,胡萝卜、包菜、茄子,每到周五下午,领导回城里前会带些他的菜走。谈起种菜,寸头大哥的兴致比上班高了不少。他带同事们去观摩菜地。四四方方的,有两个停车位那么大,用十几根长木条和破布围起来,边上是个小木屋,几只鸡从门口探出脑袋。大哥略带惋惜地说,鸡是别人家的。他往前几步,挽起袖子,弯下腰,徒手在菜叶上连抓几条虫,随后双手插进裤兜,像是在欣赏艺术品。
同事小王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然而人在乡镇,他也硬着头皮想显得合群一点。他跟着他们去菜地,站在那里,捧着手机打王者荣耀。
有一天徐奇和领导抱怨总要写公号,领导告诉他,要不是你在干这事,单位也可能会把你送去乡镇。他张大了嘴,不知道领导这句话是真是假。

只需一件小事,苟两年就跑的信念就彻底崩塌。单位通知徐奇,在这里待满五年才能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的电脑里还保留着报考时侯的招聘文件,可没人和他解释为什么上面没写明“五年服务期”。他算错了关键一步,“感觉被骗过来,五年之后我就29岁了。”
这事成为徐奇最大的心结。有个同事对他说,“其实不用五年就能调走。”徐奇脱口而出,“我操,真的吗?”很快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反应过度,暴露了。同事笑着说,“你果然想要走。”
也许是单位老油条太多,领导不愿放跑年轻人。听说徐奇的女友在其他城市,领导也不绕弯子,问他:“她会来这边吗?”他说不清楚。“我估计可能不大现实......像我们单位女孩子没结婚的有好几个,选一个也可以。”另一个领导私底下对同事阿明说,“你能不能把徐奇搞分手掉,我想给他介绍个这里的女朋友。”
事实上,外地人没有一个不想跑的。去年新招的硕士生,报到第一天,就被同事瞅见他在手机上搜索:公务员辞职会有什么后果。当天,全单位就都知道了。
同事马哥曾经也是他的盟友。马哥已经参加了两次遴选和一次省考,做梦都想考回自己老家。可惜每次都考第三名,离前两名差很多分。马哥不年轻了,比考试,真拼不过那些年轻人。他的心气快被消磨殆尽。有天他开电动车载徐奇去诊所做检查。路上两人聊起来,马哥感慨道:“你还有机会,哎呀,我现在跑不动了。”有人在街头看到马哥牵着一个女生,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单位。
上面提到的那位硕士生,大概率也不跑了。徐奇听说那家伙迅速找了个女友,本地人,还是县某个局领导的女儿。
“估计一辈子就在这儿了。”徐奇叹息,“他还是太年轻了,没搞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回家。家人在那,家族在那,资源和人脉都在那,他还有一套市区的房子。他越是想跑,对家乡的印象就越好。在他的描述里,老家一片平地,他喜欢骑电动车出门,伴着晚风一路开到城里。可你看M县,隶属山区,地势起伏,车都不好骑。
与徐奇相处的那一个月,我听到无数他对现状的不满,每次他的情绪达到顶峰时,我都以为他要来一句“老子不干了”。去M县前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徐奇的郁闷——一个年轻人将被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困住,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
换作是我,第二天就交辞呈了。可是徐奇从未这样做过,不敢辞的理由有很多——“家里花了太多钱”“现在政策还不明朗”“还没做好转行准备”“不知道我的档案会不会被扣下”......

当我和他更熟一点,我发现他在单位里并非自己形容的那般无所适从。每天他往身上塞两包烟,一包是16块的七匹狼,留给自己;另一包则是60块的中华。他爸从家里寄过来的,教他分给领导。他告诉我,领导或多或少会买中华烟的面子。
他不是那么轴的人。最讨厌的饭局他仍然会去,领导派下来的活他也会做完。我来之前他向领导请示过,等我到了,他带我见领导。A领导和他的外公有些交情。B领导是他的直属上司。
C领导本来不在我们的计划里,只是那天偶然碰到,便坐下来喝了会茶。C对年轻人躺平嗤之以鼻。我顺着话说,徐奇工作很专注,都不出去应酬,我的本意是帮徐奇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走出办公室,徐奇对我说,你不应该那样说,领导都喜欢能出去应酬的人。
从考公上岸那天起,徐奇就是全家族的希望。他去参加表舅婚礼,表舅喝的烂醉,扶着徐奇边走边说,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做官的人。很多人都和他说过这句话。好好做,他们说。徐奇点点头。
他外公是位退休的老干部,每回见到徐奇,都要把他拉到身边聊天,一聊就是几小时。外公恨不得把全部的为官之道教给外孙,什么“县老爷就是皇帝,基层公务员就是奴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也不管徐奇听没听懂,老人家就是开心,还送给他一本叫《和任何人都聊得来》的书。
徐奇的表亲们都不太顺遂。大表哥读到初中,勉强谋生;大表姐遭遇婚变,暂住在二表姐家;二表哥去深圳做生意,亏一大笔钱,现在躲家里;表弟之前在电子厂,干几个月就跑了。外公对徐奇说,家里这几个小孩都没出息,只有你比较出息。
徐奇从小就是不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学习一般,打架也一般,总是处在平庸的中位数。这两年好多了,偶尔他会想,自己考上公务员还挺牛逼。

离开M县后,我在老家见到了徐奇的妹妹徐青。前不久她刚辞掉工作,开始考公。
她妈很欣慰,花五万块报了最高级的班,意味着徐青随时能上机构的任何课。省考前一天,她妈去山上烧香祈福,为她带回一张符,点火烧成灰烬,混在水里。她喝下那碗水,腹泻不止,不得不带病上考场,遗憾失利。她只差0.6分进面试,但论起表现,要比徐奇那会强很多。

徐青看起来信心十足。她谈论上份工作,在职场中被领导穿小鞋,她感到委屈,继而决定离开。如果进体制,同事们几乎都是一辈子“锁死”的,总要互相留情面。她的想象里,体制内的氛围会更纯粹。
我们聊起徐奇的现状。听说他想跑,徐青满脸困惑,甚至不明白老家的平地为什么有那么美好。她妈也不明白,一个大男人怎么矫情起来了?她爸就是一句话,工作没什么不开心的。
徐青去过M县,那里不比老家差,而且生活节奏慢。她记得徐奇的办公室很大,还只有他一个人,宿舍也不错。每次她都能在超市刷她哥单位发的购物卡。“我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她说。
我试图解释徐奇为什么想跑。徐青表示,她知道他的工作琐碎、劳累,但她认为基层就是这样,考公时就应该“做好觉悟”。她不理解她哥千方百计想调回老家,“(估计)他想回来当妈宝”。
辞职的想法像涨潮,总是一阵一阵的。等潮水退去,徐奇又犹豫了。今年春节他告诉我,暂时不辞职,如果两年后没调走,他就辞了重新考。有一二三四五个理由支持他再等两年。可是你知道的,我认为那时他不会走。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