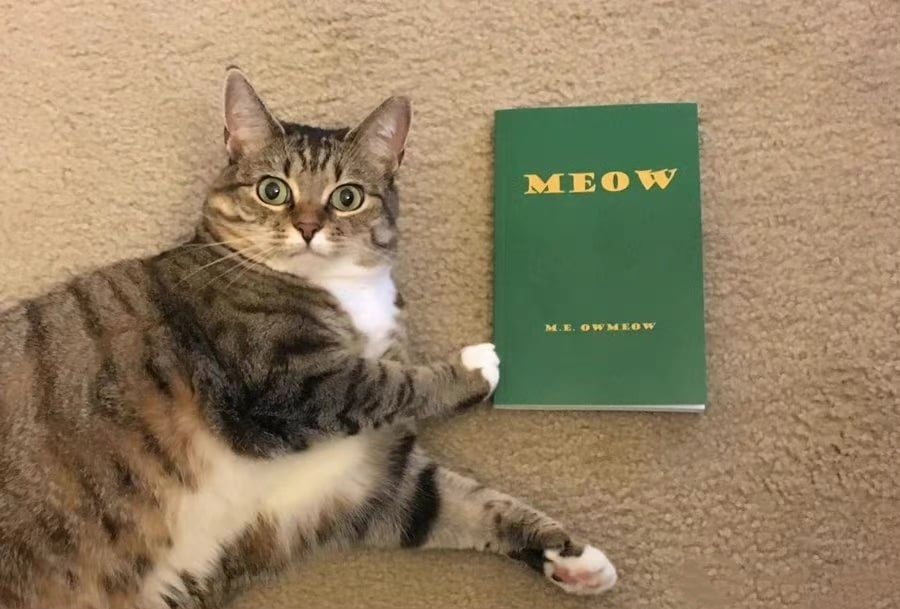
關於我:揹著一袋子語詞的流浪人,暫居瑞士 主業:破碎語言研究者,馬特市湊整五整十點贊數人 副業:寫詩的 歡迎互拍互fo!
【蜉蝣鎮回憶錄】序言及蜉蝣鎮鎮名考
在蜉蝣鎮上高中的第二年,我班換了化學老師。老師是個壞脾氣酒鬼,他臨近退休,上課的精氣神依靠課前半個小時攝入的酒精來維持。

在某一節課熟悉的白酒暴烈氣息中,有一只小飛蟲好像是醉得不省蟲事,跌跌撞撞地落到了我手邊的空桌子上。片刻後,不知道哪裏又冒出一只。它也跌跌撞撞,落在兩張桌子的縫隙上。我猜它倆大概都是從座位旁窗戶縫飛進來的......只消半節課功夫,教室每個人和小飛蟲都成了酒精受害者。離我最近的那只和我小拇指指節一般大小,搖搖晃晃地走到桌上那一格金色而微熱的太陽光裏,像是尊略遭酸蝕的大理石雕像,但它的精致與華美,你仍可瞧見端倪。它身子後吊著尾須,線條流暢,應著醉酒老師的咒罵聲擺動。
教室裏每個人都齊整地擡著頭,一動不動。這四十五分鐘裏,那酒氣的中心自詡為神,要教室裏的一切都俯首歸依。他被酒精染紅了脖子和臉,以噴濺神聖口水的嘴為中心形成一個漩渦,試圖把我們全都牢牢吸在漩渦邊緣,要我們在他的震怒之言中信仰他,並對著他用了十年包了漿的教案行敬拜儀式。然而,這些小蟲子卻是例外,它們煩躁地應著這高分貝的吼聲擺動尾須,好像要把神聖口水和醉「神」的怒語全都甩回去,頗有褻瀆之意。我頓時對這小蟲有了興趣,打破了不準動也不準低頭的戒律,噢,確實是從旁邊這寬縫裏進來的,一看窗外水面,大抵全都是漂亮小飛蟲的同類,大片大片地,好像起了薄霧,所以它們到底是什麽......
憤怒的醉「神」扯起我的領口,罵罵咧咧地把我扔出教室,我的好奇心戛然而止。教室無數雙偷偷斜著圍觀我的眼睛前,唯有一只小蟲貼著窗面,自顧自地擺動尾須,絲毫不受這場風波的影響。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奇異的小蟲子,出於未竟的好奇,在那天放學挨罵間隙,我偷偷把剛才提及的窗面上那只摳下來藏在手心。回家路上我總算問到,這小蟲子叫「蜉蝣」,而當人們說出它名字時,它早已經浸在我一手的汗裏一動不動了。
是的,就是我的家鄉蜉蝣鎮裏的那個「蜉蝣」。蜉蝣鎮三個字一度對我來說非常虛幻,在見到這種小蟲前尤為如此。在過去,我更傾向於認為我長期生活在一個恰巧叫「蜉蝣鎮」的地方,而非我作為蜉蝣鎮人在蜉蝣鎮生活。因此,我更喜歡說「我生活在一個小地方,這裏以一條河和幾座山為界,界線裏面的人和其他地方人一樣,上學的上學,工作的工作,不過也有不上學不工作的,人們都管這片區域叫蜉蝣鎮」,而非小鎮人從小便能夠脫口而出的「我是蜉蝣鎮人」。
單論鎮名,我對它的認識常常停留在長輩的方言口音裏,所謂標準讀音裏,課本中古人的詩文裏,還有詩文旁邊被紙張紋路禁錮的蜉蝣插圖裏。單單這些途徑來認識小鎮是非常蒼白的,它們無法直接解釋清楚為什麽這個小鎮叫蜉蝣鎮,以及作為蜉蝣鎮和蜉蝣這種小蟲有什麽聯系。
第一次知道我居住的地方叫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已開始記事,長輩們要我去鎮外一座發達城市的小學上學,做自我介紹時記得說自己的家鄉叫蜉蝣鎮。依著傳統,作為小孩,你不知道也不能拒絕你接收到的訊息,尤其是當大人們想要你接收的時候,捂耳朵的動作都是不可以有的。那個時候幾個大人圍著我,對我說:「我們這個地方叫蜉蝣鎮,我們都是蜉蝣鎮人,來來來,你重復一遍,蜉蝣鎮,蜉—蝣—鎮——」
我當時就憑借著還不賴的模仿能力把這三個字照念了下來。為了討好他們,我還把「我們都是蜉蝣鎮人」這句順便說了出來,贏得一陣咧嘴露齒的掌聲。後來帶著他們教我的發音,我去了上外地上小學。老師知道我是外地人,便讓我在課上回答自己來自哪裏,借此讓本地人同學們聽聽外鄉人之音。我按那時大人們教我的念法老老實實地和老師說了,「fóu遊zhèn」。老師聽完立刻皺眉頭想了一會,問我是不是在說「fú蝣鎮」。我感覺她應該和我說的就是同一個,不想再多折騰,就直接點了頭,老師便停止繼續追問,我也明白她的興趣並不在此。緊接著,老師告誡我們:「在學校裏要規範發音,切忌說方言,那麽剛才說話帶著蜉蝣鎮口音的Y,請你坐下,以後要註意了。還有那邊那個誰,你不要再對著你同桌模仿錯的讀音了,免得錯習慣了改不回來!」我在一片哼哧哼哧的憋笑聲裏坐下。
此後,礙於這次尷尬經歷,我很少在公共場合提及蜉蝣鎮。老實說,長輩們的方言或者帶著口音的念法曾給我帶來一種親切感,可是這種親切感僅創生一年半載,尚未成熟,就變成了一種因犯錯而招致的羞恥。與此同時,那正確的讀音,它居高臨下地,哦不,我應該說是頗有救贖情結地,憐憫小鎮之鄙陋對我唇齒舌的戕害,欲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是來自小鎮的難民。它給我的嘴戴上城市高樓幕墻製成的矯正器,從兩瓣嘴唇起,連到牙齒與齒齦,上下顎,舌頭兩面,再到咽喉。每天早晨,我從有關故鄉的夢中醒來,摸摸我被矯正器折磨得酸疼的嘴,都感覺這時的嘴和故鄉夢裏的嘴如此不同——這嘴為何這麽陌生?我剛想發出這樣的疑問,人們便對我說,為了早日擺脫難民的身份,我必須化陌生為熟悉。
後來我矯正成功,將矯正器歸還給施舍與我的人。歸還並致謝的那一刻,我已然被城市人勉強認作融入他們的新成員。說「勉強」,是因為城市人時不時就要提醒我,我出生地並不在此。後來回到鎮上讀中學,我已經習慣了那套標準發音,但也從不去糾正長輩們,因為這無傷大雅。再者,讓他們知道,自己接受了一輩子的東西,在他們敬仰的城市學校裏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會遭到嘲笑甚至禁止,也太殘忍了。這時,我已被小鎮人看作是「去城市上學的稀奇人」,「操持著新口音的學生」,而不再是純正的「小鎮人」。在他們眼裏,作為「小鎮人」的那個我,在七歲坐上去城市的列車那一刻就已絕命於鐵軌上,在這世間僅駐足短短七年。噢,我猛然明白——從此我就是個流浪遊魂,余下一輩子都要背著這陌生的嘴巴四處遊走。
直到會寫字,學了字形結構,我才看懂往返學校和家的車票上,作為起點站或終點站的「蜉蝣鎮」三個字,原來正對應著家鄉小鎮的名字。我學到小學二年級才知道「蜉蝣」這兩字怎麽寫,有時候也能寫作「浮遊」,但是人都說,做鎮名時只能寫作「蜉蝣」。人們也說,鎮名是只小蟲子的名字。我不理解的是,既然要用蟲子做小鎮的名字,這麽多有名有姓的蟲子,為什麽偏偏選用蜉蝣作為小鎮名,而非蜻蛉啊蜣螂啊蟋蟀這些的?又以及,為什麽這麽多年沒有人告訴我這「蜉蝣」到底是個什麽樣的蟲子?當我能想到這樣的問題,而非默然接受,就意味著我是真站在外鄉的角度去看待「蜉蝣鎮」了,因為真正認同自己小鎮身份的人,怎麽都不會去追問「為什麽」吧。蜉蝣鎮就是蜉蝣鎮,好像沒有那麽多的理由。
上一段的那個兩個問句多年以來纏繞在我腦海裏,求問無路。直到那節化學課,見到了真的蜉蝣,在壯觀的現實場面和班主任的咒罵聲裏,我大概有了些尋找答案的頭緒。
那天我像個晾在鬧市即將被燒死的異教徒,站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他朝我大吼道:「我不是聽說你原來在那個什麽市上過學嗎?怎麽跟我們蜉蝣鎮學生是一個德行,甚至還不如呢?你上的是個什麽學?你真是白費你爸媽錢!丟臉!!」
我的這位老師絕對不是個例。小鎮很多人,一邊要遠行的孩子對外人表明自己來自蜉蝣鎮,有時甚至要求我們語氣裏帶著自豪,一邊又像這位老師一般暗暗貶謫小鎮人,要我們早日脫離這個破爛地方,脫胎換骨做一個發達城市的人,否則就真是莫大的恥辱。這種矛盾體可以概括成是,新一代生長於蜉蝣鎮的人都有且僅有一個使命——在非蜉蝣鎮之地做蜉蝣鎮人。但事實上,大多出去了的人,即便最終在心心念念的大城市定居成家,或僅僅和我那會兒一樣接受過難民適應性矯正,也還是會被當地很多土著認為是外鄉人。
更令人難過的是,這個使命,假使其重點是離開蜉蝣鎮,嚴格意義上每個人都無法實現,因為根據小鎮習俗,人臨終前必須要回鎮上老家度過最後時光,否則不能回鎮辦葬禮,孤魂將會遊離在外不得安寧。歷代小鎮人是害怕這點的,確有人並無所謂自己生後之事,但ta們的親友在社交場合常常會被迫和ta們捆綁在一起——「你那可憐的親友呦,ta在外面不會難過嗎,你們為什麽不努力一下讓ta那會回來過呢?」此話一出,必定無人感到舒適,但人就總愛這樣多嘴,愛看看人因尷尬和自責皺起的臉,樂此不疲,但從沒有誰去細想自己為什麽要這麽問別人。在這種人與人萬事相連的關系社會裏,你的生活與生命並不僅僅只是你的。那些無所謂自己魂靈境況的人,若是在小鎮有什麽掛念之人,必會顧慮他們之後的生活選擇回到小鎮。若是顧慮無法消除,他們就要抱憾終生,且飽受小鎮人責備。

說回我因看蜉蝣挨罵的那天,在一頓劈頭蓋臉的責罵後,我灰溜溜地跑去那個飛出蜉蝣的肇事小池子,近距離看蜉蝣奇景生成地。到了那裏,先前遠看像是霧的蜉蝣群,近看顆粒分明。
這下子我突然想起來語文課和生物課的沖突——語文課裏我們在學古老的《國風•蜉蝣》,生物課裏我們在看蜉蝣的生活史。古代的詩人好像特別喜歡在自然之物上寄托點自己的情感,一位詩人用了,若是口口相傳被采編作了經典,就可以給後世沿用千年。蜉蝣就是這樣一個被沿用這麽久的典例,因為有位無名詩人看到它在神采奕奕地、光鮮亮麗地在空氣裏活了一天不到的光景就離開了。噢,這小生靈生命真短啊,ta悲嘆道。可是這讓ta聯想到什麽,究竟是ta自己的命運,還是ta擔心的小國國君,我們已經不可知悉。不過ta就這樣寫下了首詩,還被采風的人看中了,只是人家並沒有把ta的名字也順帶采走的打算。你說詩人是幸運兒,好像也不完全是。
蜉蝣的境況也遠不及幸運,甚至詩裏的「蜉蝣」,指的是蜉蝣,還是別的蟲子,比如蜣螂,蜻蛉,都一度沒有定論,它在我們的母語裏,竟長期不是一個指代明確的詞。人們始終牢牢地記著的,還是「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還是政治隱喻,有時候也是衍生來的Carpe Diem。大多不去做深究的人們就認為它只是莫名地冒了出來,數時數日又匆匆離開。後來有人帶著科學沖撞進了人們樸素的情感世界,他們告訴我們,蜉蝣成蟲前其實還有在水底下默默呆著,時間長的能有三年。蜉蝣出來以後不吃不喝,它們只是離開它們長大的地方繁衍後代便氣絕而亡,後代繼續在水底長大。那不為人知的三年啊,你們怎不想想,這相比之前人說的一天,可是長上千倍了!
到此,我突然就再不想沿用傳統,因為人在感嘆的,其實是它們在水上被人瞧見的時間短。與其說是這蜉蝣這精致小蟲的生命短,不如說是它們在水上的光鮮時間短。蜉蝣蛻幾十次皮,到在水上成蟲才能算是蜉蝣嗎?我又想起新一代小鎮人的使命,這一類比,可真是巧合中的巧合——蜉蝣鎮的人,是要出了蜉蝣鎮才能摒棄自嫌地說自己是蜉蝣鎮人嗎?
我看過蜉蝣鎮的地方誌,地方誌只說鎮名於四十多年前正式確定,名取自那首可愛的小詩。書裏也指出,這麽取名,並非因為我們這鎮是這首詩的故鄉——小小曹國所在地。要我說,給這小鎮命名的人,若ta取的「蜉蝣」義並非沿用人們對《詩》裏「蜉蝣」的理解,那ta很可能是個極富巧思的明白人,太明白了。
以上就是所有我對蜉蝣鎮鎮名一些不專業,不守學術規範,且夾雜過多個人情感經歷的考證了。
那天我看到小池子,突然一反經典解讀傳統地將蜉蝣和這蜉蝣鎮聯系起來,獲得了那樣的頓悟。你看這會兒,我也是能夠在自然之物上寄托自己情感的人了。不過,要是我在答卷上寫下我這樣離經叛道的說辭,準要在考試分數上遭大殃。我那時一直沒敢把我這突然悟出的想法分享給老師與親友,就這樣一直藏到了現在,因為我向來不能當即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看法,更別提在之後以不卑不亢的姿態為自己的看法做辯護。我只能偶爾抓住時機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花上那麽下子時間把我想說地寫下來。通常來說,我其實沒有那樣的時間。我現在匆匆忙忙寫下這麽多,只是想抓住休養期的小尾巴,以免在它結束以後,我離開蜉蝣鎮,生活再次被學業與工作全面占領,致使它連在我腦子裏都沒能有個安身之地,和我的肉身一般遊走於異鄉。
初見蜉蝣之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又跑去看那個池子,水面上已經飄了好多死去的蜉蝣,還有些看起來就是所剩時日不多的樣子。我還沒有聽這些瀕死小蟲子其中的任何一只說說自己在水下的生活,上課鈴就響起來了。我和它們的對話還沒有開始,就先到了臨別。那串刺耳的鈴聲以為自己收住了我為此苦苦思索的心,其實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念念不忘,甚至還要持續上好多年。[1]
那次與蜉蝣的談話被終止後,我坐回位置上,看著旁邊的空桌子,這張桌子一年前還坐著人。她是土生土長的蜉蝣鎮人,在生命最後一陣子才從水底飛出,人們有所關註,只是她剛飛出來在上空一厘米不到,什麽都沒做就回水面上長眠。這是小鎮的一個故事。有時候,蜉蝣鎮人,就像蜉蝣一樣。
寫到這裏,我好像回憶了過多往事。不過事必有因,我的生活已然走到四分之一,人們說我這是到了精神上危機感重重的年齡,時不時會找尋這個時期之前的時日重溫這很正常。我沒在小鎮的時間有十年,將近一半。但其余十多年時間裏,除去開始記事前的那三年和睡覺的時間,我在此地看並看見,聽並聽見,凡有問必尋答案才肯罷休,凡有傳聞必經求證才肯確信。
我親歷,感受,並收集到了小鎮這二十幾載及之前發生的種種故事。有過去很久的,也有過去幾年的,有些真實事件離奇地讓你感覺不可能是真的,有些傳說又讓你感覺現實裏它真的就這樣離奇地發生過。這些故事裏的主角生命大多時間裏在外人看來普通至極,人們在說起ta們時,把ta們全都歸為一種思考的動物,總結出一套公式來統一描述ta們。
人們大多讀到這些,也無暇細究,看看這樣的總結就各自忙碌去了,所以我想我知道那麽多,止當珍貴記憶私自收藏即可。誰知我休養的這幾年裏,外地的友人們與我聊天,逐漸對我家鄉這個小鎮及我在小鎮上的生活產生濃烈興趣,並表示如果我只在口頭上說,不記下些什麽是有些可惜的,畢竟這小地方發生這麽多精彩事件,我本人也是,可外界不是流言便是忽視,小鎮人對此如此輕視,也太說不過去了。
在朋友長達兩個月的苦求下,我終於打算寫作一部回憶錄。我不確定我的寫作會給人什麽樣的觀感,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回憶錄寫作,經驗尚不足。但我一定會如實地把我所見所聞寫下來,盡力展示蜉蝣鎮最純正的風貌。
[1]這句話化用了莎士比亞《理查二世》中葛羅斯特公爵夫人的話——"I take my leave before I have begun, for sorrow ends not when it seemeth done."(「我的談話都還沒有開始,已要向你告別,因為悲哀看去好像已經止住,其實卻永遠沒有個完。」)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