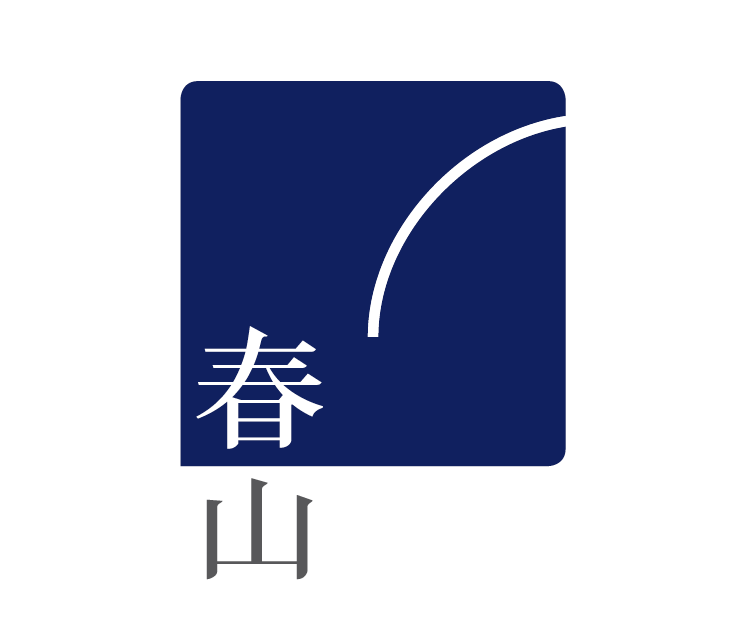
以春山之聲 Voice、春山之巔 Summit、春山文藝 Literati、春山學術 Academic 四個書系,反映時代與世界的變局與問題,同時虛構與非虛構並進,以出版品奠基國民性的文化構造。臉書:春山出版。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堂為德國社會而上的正義課──法蘭克福大審
作者: 蔡慶樺
出版社:春山出版
點此購買《美茵河畔思索德國》電子書
點此看春山所有的出版品
一堂為德國社會而上的正義課──法蘭克福大審
張開雙眼的正義女神
在法蘭克福羅馬山廣場(Römerberg)上,有一個知名地標:正義女神噴泉。這座噴泉的中心矗立著一尊右手執劍、左手高舉天秤的女神雕像,象徵司法的執法權威與判定正義與不義的功能。不過這尊正義女神特殊的地方在於,她並未被蒙上眼罩。
正義女神(Justitia,拉丁文Iustitia)是羅馬帝國時代即出現的神祇符號,在羅馬神話中是一位代表司法、降臨於邪惡世間的女神,幾千年來成為正義化身,今日在德國各司法機構都可見到其雕像或畫像。一般在德國各處可見的正義女神形象有三個主要的特徵:天秤、劍以及眼罩;分別象徵公道、權威及無私。蒙上眼罩的女神,看不到世人的背景、身分,只知道衡量對錯,是真正的大公無私。
可是,為什麼法蘭克福的正義女神不蒙上眼罩呢?
這座噴泉歷史悠久,十六世紀即己存在,但一開始噴泉並無正義女神像。在一六一二年羅馬皇帝於法蘭克福加冕時,藝術家霍克愛森(Johann Hocheisen)受委託完成了正義女神像及噴泉基座,奠定了今日所看到的模樣。當時女神腳下流的不是水,而是酒,全市的居民在此為了自己是帝國子民而共感榮耀。經過幾百年,噴泉毀壞,在十九世紀末由法蘭克福酒商集資重建,修復基座,並將原來的女神由石像改為銅像,但姿態不變,依然是手執劍與天秤、沒有蒙眼的女神。而基座上刻上了這些拉丁文:
Justitia, in toto virtutum maxima mundo, Sponte sua tribuit cuilibet aequa suum.
正義女神,在德行的世界裡是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神祇,以公正之手,給予每個人其所應得。
從這行文字可以看出,創作者希望的正義女神能以公正之手,給予每個人其所應得。可是以今日的理解,不蒙眼是否真能公正?其實不蒙眼,是因為更古老的正義女神形象就是如此。最知名的蒙眼正義女神形象,是塞巴斯提安.布蘭特所著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中的插圖。這本書於一四九四年出版,描述中世紀時各種瘋狂與愚昧的人類,是德語區的暢銷書;翻譯成拉丁文後,更影響了整個歐洲世界對於瘋狂的想像,例如法國哲學家傅柯就在《瘋癲與文明》中引述了這本書。
《愚人船》第七十一章中出現蒙眼的正義女神。該章描述的是上法庭、好爭辯的愚人,這種喋喋不休的人企圖透過口舌之辯逃離正義的判決,而配圖就是名畫家杜勒(Albrecht Dürer)所畫的木板畫,正義女神雖然手執天秤與劍,但是被愚人遮蔽了眼睛,無法施展其公正之手。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十五世紀時,蒙眼對於正義來說並非好事,因為將無法看清那些狡辯之辭,相反的,睜開眼睛才能真正給予每人其所應得的。
等待太久的審判
從這個睜眼的正義女神正可思考法蘭克福大審的意義。法蘭克福正義女神的對面就是市政廳,而一九六三年時,這裡正是法蘭克福大審的審判進行處。
這個被媒體及民眾稱為奧許維茲大審的重要司法事件,正式名稱為「起訴穆爾卡及其他人」(Strafsache gegen Mulka u. a.),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法蘭克福市政廳開始。那一天鮑爾對著來自全球的媒體,強調這場德國已經等了太久的審判,對於這一代人的意義。他說這場審判可以讓我們學到一堂課(eine Lehre, eine Lektion)。最後這堂課進行了二十個月,開庭日共達一百八十三天,被起訴者二十人。
先從奧許維茲的背景來思考,為什麼這場審判如此必要。德國在戰爭剛結束時,立刻在同盟國的主導下舉行了紐倫堡大審,可是那場審判針對的是主要戰犯,而非參與種族滅絕的共犯。然而,如果沒有那些士兵、警衛、技術官僚、醫生等等,不可能系統性地執行大屠殺任務。可以說紐倫堡大審確定了納粹的無人性罪行,可是如何處理那些主要戰犯以外的共犯者, 戰爭結束後近二十年,沒有人願意碰觸這個議題。
對德國政府來說,這也是個尷尬棘手的議題,戰後阿德諾總理就曾表示,希望德國在同盟國的指導下盡快結束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因為他不希望德國人長期被分裂為兩種人:政治上清白的,以及有汙點的。後來西德政府甚至立法豁免那些參與納粹罪行程度較低的人,並把一度因去納粹化而被開除的公務員再找回公務界來。
這種想趕快結束去納粹化工作的心態,可以從下面數據看出。終戰隔年雖然通過了《解除國家社會主義與軍事主義第一○四號法令》(Gesetz Nr. 104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試圖釐清曾參與納粹者的罪責,然而在同盟國主導下的去納粹過程充滿形式主義,不管是同盟國或聯邦德國都只想行禮如儀。根據該法,與納粹有所連結的人必須接受審查,審查判定五種類型:主犯(Hauptschuldige)、有罪者(Belastete)、輕罪者(Minderbelastete)、同行者(Mitläufer)、免罪者(Entlastete)。其中同行者與免罪者被判定可獲得去納粹化證書。
直到一九五○年代初期,同盟國占領區大約審理了三百六十萬件案件,其中只有一千六百六十七人被判定為犯下戰爭罪行的「主犯」,二萬三千零六十人被判定為「有罪者」,超過十五萬人是「輕罪者」,超過一百萬人是「同行者」,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是「免罪者」。無數納粹黨員因此拿到去納粹化證明書,如果考量法令中對於同行者的定義─雖加入納粹但只以非常不起作用的方式支持,或者並非軍方成員;以及免罪者定義─雖加入納粹,但只是被動地參與,甚至主動進行了某種形式的抵抗,因而自身亦受到某種損害。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怎麼可能絕大多數的納粹黨員都被認定為只是名義上加入、甚至曾經抵抗。這樣浮濫地審查,也讓去納粹證書被戲稱為「洗潔證」(Persilschein)。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白與有罪之間的區分被置之不理。為了下個世代能夠勇敢地立足,這個議題終必須觸碰,其中牽涉到的戰爭罪行、服從正當性、責任倫理,都必須釐清,不能就當成這場戰爭從未發生過一樣,這是對犯罪者的包庇,對下一代的剝奪,也是對受害者的汙衊。因此,西德在一九五八年時成立了「納粹暴行調查中心」(Zentrale Stelle zur Aufklär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verbrechen),開始調查當年的共犯結構。
在「納粹暴行調查中心」成立後,追查當年暴行的必要性才被凸顯,而奧許維茲集中營的倖存者,於一九五九年控告當年集中營的守衛與祕密警察,這個案子的文件透過記者來到鮑爾手中,他決定執行正義,貫徹正義女神的教誨,給予每個人其所應得的─犯罪者應受懲罰,而受害者的尊嚴也應該被回復。
奧許維茲就是一個明確的不義發生之處。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大約九百天,德意志帝國鐵路以大約六百班班次的火車,將各地的猶太人解送到這裡;這些囚犯們一下車就會被「擇選」(Selektion),那些帶著小孩的老弱婦女會立刻被送到毒氣室裡;共有約八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一抵達奧許維茲後立刻被毒死;大約有二十萬個猶太人被「擇選」為可用勞動力,在營養不良及惡劣無比的勞動環境下工作。最後,共有九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七萬五千個波蘭人、兩萬一千個辛提人和羅姆人、一萬五千個蘇聯戰俘、一萬五千個其他背景的人,在這個巨大無比的集中營營區被謀殺。
由這麼龐大的數字可以想像,要使這座滅絕營順利運作,背後必須有強大官僚系統支持。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有大約八千二百名衝鋒隊隊員在此服役,其中有二百人是女性。這些奧許維茲的管理者們中,大約有八百人被審判,大部分是在波蘭法院。德國法院總只起訴了四十三人。法蘭克福在一九六三年的這次大審,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奧許維茲大審。
為社會啟蒙
鮑爾於一九五九年接到案子,交辦給年輕檢察官庫格樂(Joachim Kügler)、佛格爾(Georg Friedrich Vogel)、維瑟(Gerhard Wiese)偵查,另外也從其他地檢署調來檢察官瓦爾洛(Jahannes Warlo)協助─他召集這些年輕檢察官,就是因為他們年輕,沒有機會在納粹帝國時期受司法訓練,因此意識形態未受影響,可以突破戰後被納粹時期舊世代所掌握的司法界。當時司法界與納粹牽扯之深,除了可以從戰後留任的納粹司法官人數看出來,也可以用一個名字來說明:威爾那.海德(Werner Heyde)。海德原是符茲堡大學醫學教授,在納粹時期是執行安樂死計畫中心的醫學部門領導人,殺人無數惡名昭彰。戰後原被囚禁於戰俘營,一九四七年海德趁押送途中在符茲堡轉車時,脫逃成功。他逃到基爾(Kiel),化名薩瓦德(Fritz Sawade)繼續行醫,而他主要收入的來源包括地方法院的醫學鑑定委託。法院中許多人其實知道這位薩瓦德醫生的真實身分並包庇他,包括石荷邦(Schleswig-Holstein)的檢察總長。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幾位檢察官突破層層困難,調查偵訊大約一千名嫌犯,傳喚約八百名證人,歷經數年才展開審判。
為什麼要花這麼久的時間?因為鮑爾堅信,起訴那些共犯結構不是為了為個人復仇,而是要讓德國社會學到關於正義的一課,這無關私人,而是公益。他希望案例蒐集得愈多愈好,以便能將納粹暴行向社會整體呈現。他也多次向國際媒體強調,這個審判是要查明當年罪行發生的政治歷史條件,是要對德國社會啟蒙。當時參與的一位檢察官就在一封信裡這麼形容當時鮑爾的態度:「鮑爾博士想以最現代的工具,以及一切可使用的觀看素材,讓這場審判眾所周知,例如照片、攝影等,都必須發揮重要功能。」
於是在鮑爾主導下,不只法蘭克福的正義女神張開雙眼,德國民眾也必須取下他們的眼罩,仔細觀看這次審判。便有媒體評論,鮑爾打這場官司的方式,是強迫整個國家一同直視當年曾對一個民族犯下什麼樣的罪。
您要說的是,您當時並不知情?
鮑爾認為大屠殺必須被視為一個所有在集中營服役過的人都共同參與的罪行,無論這些人是守衛、醫師或門房;也就是說,所有處在集中營裡的工作人員都是一個行動整體(Handlungseinheit),對這個整體屠殺計畫直接提供協助成為共犯(Mittäterschaft),沒有這些人的存在,這個計畫不可能被執行。他這麼說:「誰參與操作這個謀殺機器,也就對於謀殺被執行同負罪責,不管他做過什麼。這裡的當然前提是,他知道這謀殺機器的目的,當然,在那集中營裡的、或與集中營相關的人員都知道,從守衛到高層,毫無疑義。」
這是與當時主流法界意見相左的。例如聯邦高等法院認為,集中營裡發生的慘案,還是必須以刑法對謀殺案的規定來審視,必須針對每個個案分別調查,沒有所謂整體共犯架構。聯邦高等法院強調:「在奧許維茲案件中涉及被告的部分,並非是個別的特定犯案者所結合起來的確定的犯罪體(Tatkomplex),而是出於各種不同原因的殺人行為,有些是接受命令,有些是自主行動,有些是犯罪者,有些是共犯。」
這兩種立場各有道理,事後證明這場審判,並不是一場成功的審判,被送到法庭上的,許多都是一些負責不重要工作的人,真正應該負起責任的許多重要共犯,都因缺乏證據,在戰後無憂無慮地開始新人生。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當年那個審判如何讓人失望。負責本案的一位檢察官庫格勒,被鮑爾選中承辦此案,就是因為他被認為是一個「並不信任國家的檢察官」(nicht staatsgläubig),能突破利益關係清查。而在他深入調查後,不幸地卻加深了他對國家的失望。他在審判結束後辭去檢察官職務,轉任律師,到死都未再擔任公職。他的墳上刻著一行當初他還在檢察官任內最常問的問題:「您要說的是,您當時並不知情?」(Sie haben es nicht gewusst, wollen Sie sagen?)
幾年後,被稱為六八世代、不曾涉入法西斯體制的人們,走上街頭,向被稱為四五世代的父輩母輩們,重新提了那個不曾得到滿意答覆的問題:「您要說的是,您當時並不知情?」只是,這次是用暴力的方式。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