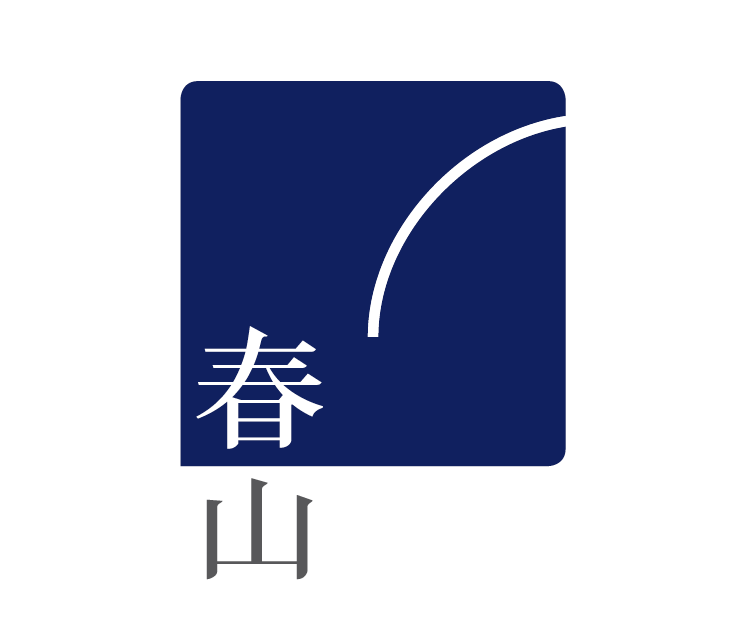
以春山之聲 Voice、春山之巔 Summit、春山文藝 Literati、春山學術 Academic 四個書系,反映時代與世界的變局與問題,同時虛構與非虛構並進,以出版品奠基國民性的文化構造。臉書:春山出版。
《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書摘: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挑戰
《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
作者:劉紹華 @劉紹華
出版社:春山出版 @春山出版
Readmoo 電子書購買連結 https://readmoo.com/book/210116152000101
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挑戰
二○一四年三月學生占領立法院後,學術界與社運界也在立法院外開辦「民主教室」,由學者與社運人士輪流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相關議題開講。當時我剛從中國的田野研究回來,在民主教室觀察了兩天後也上臺發言。平常我很不喜歡上臺,總認為那是一個不適合思考的位置,或者說是不適合我這種習慣把思考的時空拉長,因而反應比較慢的人的位置。之所以決定加入演講的接力賽,是因為占領立院運動的癥結點與中國有關,和以往的運動主要是攸關內政的性質不太一樣。我想,自己做了多年的中國研究,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思考背景,也算回饋社會。我當時的講題是〈從中國的發展來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該文後來在網上廣泛流傳,甚至傳到對岸。很多人告訴我是因為用大白話來談中國的日常生活,深入但易懂。我自己的感想更是:不少一天到晚羨慕或批評中國的臺灣人,其實不太瞭解中國。我以口語描繪中國日常現象的目的,不在妖魔化中國,也不在簡單地反對或支持服貿,而在於提醒大家,我們表面上觀察到的中國現象,背後有著迥異於臺灣經驗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歷史。有些讀者與我有共鳴,也有不少讀者以為我也是「尋巫」中國的一員,以為該文讓親者痛、仇者快。
對中國國家意識形態與行徑保持批判的眼光,是多數中國研究者的基本共識,但批判與尋巫仍是兩回事。中國攸關臺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們其實不具備誤解中國或對中國盲目的條件。所以,當《思想》季刊欲回顧占領立院運動來邀稿時,我很樂意繼續提供自己對於中國的客觀與主觀理解,希望有助於臺灣,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國相關事務的思辨。
和各地的中國研究學者聊天時,我都問過一個類似的問題,亦即他們認為當前中國最突顯的價值是什麼?答案意外地雷同,大致是民族主義。之所以說「意外」,是因為我以為有人會說是「道德混亂」、「信任危機」、「物質主義」等當前中國研究中常見的論述或主題。而之所以答案「雷同」,是因為即使與上述論述或主題相關,其實背後都有民族主義的影子。
早年西方漢學家與歷史學者研究中國時,大多有一個共通的想法,就是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因素讓龐大多元的中國得以歷久延續?儘管在歷史長河中,中國歷代政權的版圖不斷變化,時張時縮,糾紛戰事頻仍。但如此之大的國家為何能長期處於或朝向一種抽象統整的政治狀態?於是,關於中國人的心理、哲學、文化、社會、歷史、科技、宗教、政治、族群、禮俗、風土、動亂等各種切入點的研究,都在試圖理解那個高大遙遠抽象的中央,與龐雜多元的地方網絡,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究竟是如何形成與作用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說:「中國政治史上所經歷的外族入侵,非但不會削減固有的儒家傳統,反倒會將之強化。因這些外族統治者會將儒家思想視為一處理普同人性、而非處理單一地區或種族的思想。」換言之,中國的地域主義從古至今依舊明顯,但與天朝京城的中心認同同時並存。明明是好幾個尋常國家規模的中國,究竟是如何成為一個中國,是個難解但迷人的問題。
在龐大中國的常民生活中隨處可見民族主義或大或小的影響。這些印記充滿了中國之為一個超級大國的特性與限制,也顯示出活在其間常民的驕傲與卑微。中國有其中央集權的國家特性,但這也是多元地理規模與人群情緒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社會體,無法籠統理解。忘卻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特性而對中國逕下斷言,媚俗靠攏或妖魔化中國,都只是顯得一廂情願。
欲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複雜性,進而理解基於此而延伸的國家狀態表現,得從中國歷史與社會經驗出發,而無法只從外部瞎子摸象。如果我們以地狹人稠、雞犬相聞、視草根為正宗精神的臺灣經驗,來理解龐大牛步、地域主義明顯卻政治一統的中國,就很難把握是什麼樣巨大綿長的歷史、古老延續至今的文化民族主義,以及近代屈辱與近日翻身的集體複雜情緒,在左右著一般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情感。我不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現象可用官方意識形態來簡化解釋。在中國的歷史、詩詞、口語、典故裡充滿了對大山、大湖、大漠、大平原、風土人情的想像、詠嘆、嚮往與驚懼。試想,生活在一個充滿深厚歷史積累存在與民間故事的時空中,那種深到骨子裡的生命與身體延續感,也許可以讓我們些微體會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矛盾。
***
民族主義在當前中國所展現出來的具象,最明顯的該是愛國主義。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表象,包括一切以流行語「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為目標的發展主義與消費行為,以及晚近出現形形色色致力於貢獻付出的志願者現象。
「愛國」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在臺灣,對很多人來說,「愛國」似乎是個髒字,不敢、不願、也不屑愛國。因為我們對於自己屬於哪個國一直爭論不休。但「愛臺灣」則是人人擁抱的善言,雖然我們心知肚明,彼此心中的「臺灣」定義,也不見得是同一回事。我們就是如此的相守、相爭或相罵。但對大多數的國家而言,包括中國,愛國可能不是那麼燙手的議題。
電影《宋氏王朝》一開始就定義了毛蔣政權相爭與中國的愛國定義,以一刀切的標籤定位影響當代中國甚鉅的宋家三姊妹,宋靄齡、宋美齡與宋慶齡:「一個愛錢、一個愛權、一個愛國。」「愛國」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致是個正面字眼。
政治學或社會心理學指出,愛國主義是人群認同與動員的根本,但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與後果。從自身認同及國家出發的民族主義普世尋常,類似的概念之所以在有為的知識圈經常成為一個髒字,在歐美哲學思想有長遠的歷史,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官方民族主義」密切相關。這種源於國家,且以服膺國家利益至上的意識形態,所引發的問題,大至帝國主義挾其現代性之姿席捲世界所造成的不公,小至各種排他形式的大惡與小惡,如二十世紀末期發生在波士尼亞與蒲隆地的「種族清洗」。超級愛國主義可能成為嚴重排斥異族的動機與論述根源,甚至引發戰爭。於是,愛國主義這個基本的現代人群政治概念與感受,在自由主義與普世主義者的眼中,大抵是個髒字。某回我和一位著名的德裔歷史學者聊天,他說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然後眨眨眼笑笑說,他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對。一個沒有什麼不對的概念卻要笑笑解釋,大抵是因為政治不正確。
但是,歸根究柢,基於生物性種族差異的民族主義在西歐的發展,與前現代中國的文化沙文主義並不相同。對前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大致不涉及生物性的種族概念,而是文化中心的同化主義。當代中國著名的已故人類學者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以漣漪來形容傳統中國鄉村的人際關係,如同向平靜無波的池塘扔進一枚石子,以自己為中心,泛起一圈圈同心圓,人際關係與群體認同就如此一層一層向外推。外散的同時,認同的力道與利益圈可能逐漸弱化,但仍藉由抽象的禮義教化與集體和天朝連結。鄉土中國的同心圓人群認同模式,在西方民族主義現代性引入後,成為有志之士推動集體轉型的標的。
自清末以降,組成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各種革命勢力,都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現代性力量,欲促成鄉土中國轉化成一個巨大的現代想像共同體,成就一個現代性的民族與政體秩序。換言之,如果我們考量中國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包含中國自古以來的華夏中心主義、地域社群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溫和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超級民族主義等等,我們也許可以區別不同的概念與實作光譜。
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文化民族主義或常民地域主義不曾退卻,而官方民族主義更接手一脈相傳的政權治理根柢,成為中國現代性發展中的關鍵動力。這個現代性無疑是外來的移植品。我在孫中山的翠亨村故居博物館裡,看到《建國方略》的英文標題(其實應該是其中一冊《實業計畫》的標題)是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恕我原本無知,乍見這英文名稱令我訝異,但隨即能理解:中國的現代性發展確實是一種龐大的國際發展實驗計畫。原本讓中國得以模糊一統的傳統特性,加上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概念,讓異己區辨、人群分類、國家想像與認同等,出現更為翦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秩序。民族主義就此生根,官方的、地域性的、甚至種族性的民族主義混雜,比鄰而居,卻關係緊張,但又有個共同的國家認同。參與社會主義建國大業的費孝通,因而提出「多元一體」的觀念。在一個充滿歷史記憶、多元民族的土地上,這個企圖要使民族國家的人群相安的模式,勉為其難也無可奈何。中國接受外來概念的轉型過程,百年未竟。
在這樣混沌但龐大的模糊秩序中,生活在大塊土地上不同區位的人們,大多必須得削尖了腦袋才能在芸芸眾生中被看見,不然只得老實甚至卑微地過日子。存在感這件事,是與土地生養、社會關係黏在一起的,不見得理所當然地我思故我在。
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結也不必然高亢激昂,卻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就像沈從文,一九四八年被郭沫若大力批判後宣布封筆,後半輩子被共產黨壓抑得只能鑽進苗族服飾的研究。黃永玉在《比我老的老頭》憶及表叔沈從文,一九五○年代第一顆蘇聯衛星上天,當時舉國向蘇聯學習的中國也是歡欣鼓舞,連沈從文都歡喜得脫口而出:「啊唉!真了不起啊!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 ……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如此吃盡黨國苦頭的文人,也不免在某些時刻揚起民族主義的內心激情。這大概是無數近代知識分子共享的情感糾結。活在那豐富綿延悠久的土地上,近代以來飽受屈辱蹂躪,以至於毛澤東建國時喊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句高昂的口號,可以讓眾人歡欣鼓動得雞皮疙瘩也站起來了。中國確實從匍匐倒地站起來了,但廣大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因此站了起來。他們依然是歷代龐大中國政權下面孔模糊的老百姓,無數人仍舊屈膝卑躬地討生活,但多數人依然愛國愛鄉愛土地。個體在面對社會不公時,愛國可能是個人未來出路的夢想所繫,也可能是心中痼疾。就像老舍《茶館》裡的經典喟嘆:「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
在龐大混沌但又巨大抽象的社會秩序中,要如何體會「我」的存在感呢?
如果把大躍進、文革時期的瘋狂躁進,和今日由網購平臺發起瘋狂購物風潮的「光棍節」並列,予人身臨跨越時空情境之感。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光棍節前夕,我在電視上看到淘寶網的發起人馬雲,個頭不大的他站在「高大上」的舞臺上,鼓舞中國網民一起在光棍節當天共創網購銷售額的奇蹟。沒多久,只見十一日到來的那一刻,交易額就像紐約時代廣場的新年倒數計時一樣,吸引眾人激情地盯著數字看。不同的是,光棍節購物狂熱的交易數字額是不斷急遽攀升,而且是眾志成城,龐大的中國網民一同加入奇蹟製造。據稱,十一月十一日當天,淘寶網全日的營業額為三五○.一九億元人民幣,堪稱世界紀錄。
看到那些畫面,令我想起毛主席在天安門舉手向眾人揮舞,臺下臉孔模糊的萬民極度狂熱、卻又絕對服從的詭譎秩序,共創革命激情。光棍節上網購物這種受資本家號召消費的現象,在社會主義中國(至少官方仍如此自稱)不但未受抵制,反而成為傳奇。在電視機前,我恍惚地以為,在中國,創造奇蹟的民族主義仍在熱烈傳唱,只是戴上了「姓社」或「姓資」的不同面具。鄧小平引用的四川諺語「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不僅可用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路線的辯論,也頗適用於對民族主義的挪用。
這種以堆積小人物抑悶的民族情結,來創造國家奇蹟的現象,在龐大沉重的中國顯得異樣地突出。渺小的個人要衝出黑壓壓的人際線真是難上加難。以微小但眾志成城的方式來參與一件「大事」,也許有機會體會自己在「高大上」經濟金字塔中的存在感與些微成就感。
中國追趕現代性的步伐、規模與方式向來令世界矚目,近年來更是以「光速」超英趕美,大躍進般的狂熱似乎不曾稍減。當前巨獸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既讓中國人感到國家榮景的希望與驕傲,也可能讓一般人感覺無力渺小,疲累至極。「拆」這個字,自一九九○年代起不斷成為大街小巷、裝置藝術、各類影片、多元文本中最常見到的字眼之一。設身處地想一想,所有的老東西、你熟悉的東西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拆掉。生活在如此變化萬千的環境中,身心得應付、調適不斷改變的生活空間,那真是一件令人異常疲累的事。被拆掉的地方通常會在一、兩年內就蓋上一大區一大區比臺北大學特區還要龐大幾倍的新高建築,每個建築都在比巨大、比氣派。
全球最高的二十座建築,九座位於中國,全球百座最高建築則有四十二座位於中國。中國不僅高樓雲集,其飆高的速度更是不斷刷新世界紀錄。據媒體報導,中國高於二百米的建築,從二○一二年的二十三座增長至二○一三年的三十六座,占全球等高建築總數的一半。預計二○二○年時,全球最高的二十座建築,十一座位於中國。已完成或夢想興建的高樓不一定建在中國的超級都會中,不少二、三線城市也努力加入這場高度競賽。在這種帝國氣勢般的城市發展中,民族主義隨著經濟指數飆漲。中國站起來了,而且站立的制高點更足以睥睨低落偏遠,有人順勢發達,落後疲累者更是所在多有。沒有機會高攀的多數人,在宏偉的城市裡屈身,蹲守在金字塔底端只是愈顯渺小,實質的存在感愈來愈低。
中國藝術家徐冰是位能夠充分展現中國特性但又超越中國的天才,曾把英文寫成漢字形象揚名國際。他二○一○年完成的作品《鳳凰》,與中國這塊全球最大規模的超級工地密切相關。這件作品在上海世界博覽會展出時便引起熱烈討論,二○一四年初在紐約展出再度引爆風潮。這件中國《鳳凰》在世界巡展,但它的血淚之鳴,我想應該只有在中國才能適得其所吧。
二○○八年時,徐冰受邀為著名的北京環球金融中心建築製作雕像。他進入建築工地時,震驚於混亂破敗的施工實況。他沒想到在技術如此發達的時代,如此聞名高端的建築實際上是以低水準的技術修建而成。外地移工在工地上的生活也相當不堪,他簡直難以想像,甚至感覺不寒而慄。於是,他以在那處工地搜集而來的建築殘片和工人用過的勞動工具,做為創作展翅起飛的鳳凰雕塑材料。徐冰曾對媒體形容這座遠看巨大美麗展翅飛翔、近看卻傷痕累累的鳳凰,「經歷困苦,卻依然保持着自尊。總的來說,鳳凰象徵著未曾實現的希望與夢想。」
當前中國「高大上」的發展巨像,何嘗不就是這尊鳳凰?遠觀時眾人稱奇,近身生活則是另一番酸甜苦辣交雜的滋味。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都夢想創造出獨一無二的鳳凰,以之象徵王朝企及的吉祥、興旺與神聖之力,但此奇珍異獸也反映民族主義發展榮景下底層浴火的哀鳴。
二○一四年春節前夕,我收到一位中國年輕讀者的來信,告訴我她讀了拙著《我的涼山兄弟》後,覺得這本書不可能在中國出版。但她希望更多人能讀到此書,所以下定決心,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日下班後用電腦,以及通勤時在公車上以手機輸入的方式,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書稿全數打畢,然後把完稿送上網,甚至寄了一份給我。她寫道:「啊,終於趕在年前完成了這件大事!」讀了這封信,令我異樣地感慨,這位年輕讀者就和我知道的眾多中國年輕人一樣,經常天真無悔地全心投入一件他們口中的「大事」。實際上,那不見得真是件大事,但能在個人無力可施的偉大榮景中,為自己帶來些微生活意義與存在感的事,的確也不是小事。
在民族、愛國等原本樸實天真的心情下尋找社會與生活意義的心情,是塊多大、多吸引人的龐大社會能量與資本啊。政權如是看,鴻商富賈亦如是看,有志之士者更當如是看。
***
中國到底有多大?我以為數字與人口無法充分說明。我們先來假想切割中國的土地,不論是費孝通或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中國版塊論中,都顯示出「北方草原」、「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中原地區」等,在生態、族群與文化上的明顯差異。由中國境內區域的多樣性觀之,檢視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現象、經商貿易、政權治理,都很難迴避區域與族群差異。這麼大的國家如何統整?
某回朋友拿了一張中國藏區老人的照片給我看,他們想用那張照片當作臺灣某出版品的封面照。但發現該名老藏人身穿毛裝,猶豫使用該張照片是否會引發爭議?我的回應是,在藏區,穿毛裝、把毛澤東相片與班禪喇嘛或達賴喇嘛照片並列祭拜的現象稀鬆平常。天高皇帝遠,常民膜拜的是同樣高遠崇敬的抽象領袖。而在同樣的區域,也有境外媒體關注的藏人自焚,而自焚的直接動機,常是將自己的忠心與生命奉獻給達賴喇嘛,而外界的分析則著重此動機的間接政治意涵。對於行為的解釋有各種可能推論,但我想強調的是:一個龐大的政體,如果不是神權或聖權,如何一統人心?
我向來相信,世上最強大的力量,是象徵的力量,而民族主義與宗教是為其一。
多年前,我和一位美國人類學者躺在紐約河岸大教堂外的長椅上仰看天際。朋友突然說出:「教堂是地景上最大的傷疤。」我瞭解他的意思,他是哀嘆宗教帶給人類的分裂與衝突。偶爾,走在中國的校園裡,會看到某類海報,要觀者小心邪教。某回我對一位中國人類學者說:「民族主義才是最大的邪教。」他沒理會我,不知是禮貌性地不同意我,還是心裡同意但不願公開討論。
中國歷代政權都有各種手段讓民族主義或愛國精神得以由天朝外射。皇恩浩蕩,上追炎黃,下封地方宗祠與神祇,秩序井然。現代民族國家手法雷同。先來人群分類,再依據現代政治架構重劃行政區域與層級。由村落、鄉鎮、縣市,一級一級往上爬,再到首都,及於中央政府。人民的視野,無論新舊,便是循著這一具象化的時空面向逐漸拓展。同時,中央或民族集體認同也循著這樣的時空面向雙向流轉,高遠抽象的民族主義或愛國意識,也就有了活路得以深入個體人心。
即便這是一條諸多新興民族國家,包括臺灣都走過的路,但我們該記得,中國的龐大與久遠的歷史,定當讓它走得很不一樣。始終讓那裡的統治者或眾人念茲在茲的,不僅僅只是個體的苟延生存而已。尊嚴,能襯得起土地規模與綿延歷史的尊嚴,是集體眾望,甚至是集體犧牲有理的眾望。人觀於中國,始終與集體密切相連,個人的權利義務想像,即使脫離了家庭社群,也難脫離國家的龐然無際。
二○一四年,習近平在法國向世界表明中國是一頭「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以此修辭來回應世人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帝國崛起時向周遭眾人宣示其和藹可親,是何等滑稽之事?然而,仔細想想,中國歷代朝廷,也常以和平的說詞征伐鄰近邦國。只要周邊蕞爾小國肯臣服成為藩屬,也確實有機會享受天朝的和平相待、甚至諸多援助。中國之為大國,非今日之始。
二○一四年三月學生占領立法院運動結束後,六月間《天下雜誌》訪問了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她警告臺灣若依賴中國太深,會讓臺灣變得更脆弱,「失去經濟獨立,將會影響你們的政治獨立」,一語直指臺灣人的恐懼。但臺灣真的需要希拉蕊來告訴我們這件路人皆知的事嗎?先不論所言的道理,希拉蕊必然以臺灣內部的對中思考來包裝美國的對中政策。美國與中國的較勁是甚囂塵上。代表另一種利益聲浪的《華爾街日報》,八月初評論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中國大陸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即將完成。該報以〈臺灣自甘落後〉為題,對臺灣加入區域經濟停滯不進的爭議,發出警訊。學理上,任何的評論與預測都可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國家與民族主義的動向,從來就不盡然只有理性思考。
面對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統合,我們恐懼有理,甚至,世界都為之忌憚。只是我們確實無法僅以自我保護的思維來決定是否加入區域經濟。我不諳經濟事務,但對中國的影響圈有別種認識方式。中國繼美國介入亞太區域經濟統合之後,也企圖競爭引領另一類區域經濟統合。中國幅員廣大,鄰國涵蓋東北亞、北亞、中亞、南亞、東南亞,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幾乎與所有鄰國,包含北韓,都聯手發展各式經濟特區。中國的區域經濟勢力甚至早已深入非洲,其規模之龐大,世界都瞠目結舌。二十一世紀初國際學術界的新興研究課題就是「中國人在非洲」,可見一斑。
近十多年,一度被航空業取代的鐵路業再度興起,主因就是中國與美國都在發展鐵路與公路系統。中國大規模興建鐵路、公路,廣泛貫穿連接鄰近國家,加速區域經濟往來。中國高鐵「走出去」的策略自二○○九年起展開全球布局,參與歐亞、中亞、泛亞、泰國、中東歐、非洲的高鐵籌建,並計劃駛向拉丁美洲。二○一四年七月間,習近平在巴西首都會見祕魯總統烏馬拉時強調,中國、巴西、祕魯三國將針對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合作共同發表聲明。一般估計,造價粗估一.二兆美元的兩洋鐵路完工後,將可打破美國長期控制巴拿馬運河以壟斷國際物流的霸權。
二○一四年七月金磚五國(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在巴西年度集會,有意催生「金磚開發銀行」,企圖挑戰以美元為首的金融霸權,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之外,另闢蹊徑,成立大型新興開發銀行,提供金磚五國改革、融資、紓困與建設所需資金。野心勃勃的金磚五國,人口占全球四二%,經濟總生產力近全球四分之一,企圖合縱連橫改變當前世界的遊戲規則。誰都看得出,五國當中,最有力道的中國,極可能是與歐美分庭抗禮集團的領頭羊。
無人能忽視中國的霸氣。各國與中國簽訂協議之時,都感受到強烈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威脅,但亦無法自外於中國影響的現實,所以同時致力於知己知彼的往來策略。世界各地眾多的反美主義者當如何看待中國崛起與發展國際平行治理體系的企圖?我相信,一定有人樂觀其成,也有人感覺大事不妙。
由英美肇始的全球化,弔詭地促成中國崛起,繼而引發歐美諸國焦慮。當前,全世界不論是頂尖大學還是三流學校都急於跟中國各地高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姊妹校、成立該校的某某中心等。這些學校進入中國,除了發揮知識價值的影響力外,當然更著眼於中國龐大的教育市場,還有研究發展上可觀的合作空間。而中國除了開放讓外國大學進駐,並送出大量留學生到世界各國,也反向地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學府砸重金成立「孔子學院」,例如史丹佛大學就拿了中國四百萬美金。外界對此雙向輸出的評價有異。西方向中國進行價值與知識輸入時,視為理所當然;但當中國向西方進行反向的價值與知識輸入時,西方學界雖接受龐大資金挹注,亦不乏強力批評者,包括著名的人類學者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然而,批評歸批評,世界各學術領域的大師,仍持續挺進中國,一睹人類史上最快速的發展進程,並盡情在繁榮之地引領風騷。
***
憂心臺灣被中國吞併的人常說臺灣應走向世界,而不該過度靠攏中國。我相信,這是多數民主國家的基本國際觀,具備獨立自強心志的國家都不該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但在全球化時代中,發展受益最深也形塑全球發展模式甚鉅的中國,雖然不代表世界,但卻是認識世界的重要大站。對臺灣而言,甚至可能是最關鍵的一站。原因無他,在講究規模的全球化時代,對世界各國而言,中國既是關鍵對手也是重要夥伴。
中國官方民族主義向來不是內縮就是擴張,少有例外。中國歷史上從來就少有平靜無事、天下與鄰國都太平的日子。曾經,中國自閉內縮,臺灣也就在那股中國向內看的民族主義風潮中得以喘息、走出島嶼、向外爭取生存空間。如今,中國繼開放自我後持續向外擴張,臺灣的國際空間受到明顯擠壓,我們也反向地開始內縮。即使我們堅信中國不是我們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徑,但緊鄰發展擴張主義的中國,我們能如何突破困境?
臺灣要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嗎?是對抗什麼?對抗中南海的民族主義方略,民間混雜的文化民族主義,或是常民的愛國主義?我們能夠辨識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形式與意涵,甚至辨識自己是基於什麼樣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回應包羅萬象的中國現象?也許我們可以更為理解與關注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這有助於我們辨識民族主義是否被不同立場者誤用、濫用,以免因模糊認識與抗拒中國民族主義而陷入自閉式民族主義的陷阱之中。
中國的各式民族主義異樣地在那塊土地上並存,由官方民族主義為主導的愛國意識,成為治理的根基。而臺灣呢,我們不僅沒有共識的官方民族主義,也沒有具共識的愛國意識,卻有夾雜了多重認同的民族主義表現,我們缺乏一統的國家政治理念。臺灣經驗是福是禍,難以判定。只是,欲認識截然不同的中國對手,我們需要超越自身的經驗限制。
「和平崛起」的中國,是帝國的歷史與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共構的藍圖。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發展應會持續下去,不是對內便是向外。犧牲落後者的發展榮景短期內也不可能落幕,集體安全與國家榮光的歷史訴求深植人心。不論外界厭惡或抗拒,民族主義中國並不會成為過去式,至多換代,以不同形式呈現。這是中國歷史的熟悉基調。
不同的民族主義者能共處嗎?二○一四年暑假,我們在中國中山大學的珠海校區舉辦「兩岸人類學營」,有二十五位來自臺灣,以及近百位中國、香港及澳門的學生參加。幾位臺灣學生穿著「運動」標語的T恤、背著「運動」書包進入中大校園與課堂。大部分的臺灣學生都抱持明顯的臺灣意識,其中更不乏堅定的獨立立場者。而中國的學生中,具備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也是不遑多讓。學生之間,是否進行過政治立場的討論我不清楚,但從他們嘻笑玩樂、密切合作的樣子看來,即使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仍可能玩成一片。或者,在這種暑期營隊的過渡情境中,大家得以互相維持基本禮儀,接觸與理解為先。畢竟,活在當下很實際;至少,把握機會知己知彼很重要。甚至,與不同理念者往來的彈性,也可能是年輕一代的特性與能耐。
臺灣內鬥的政治儀式頑強地不肯落幕,諸如此類的儀式也始終有觀眾,於是臺上的人樂得演戲,臺下的人也樂得串唱,上下一心忘卻只緣身在戲棚中。即使上不了檯面,卻不肯下臺。只是,當守舊的演員們脫下自我膨脹的斗篷,出了自欺欺人的戲棚,也只會發現這世界並不會絕然迴避或天真擁抱民族主義發展下的中國現象。世界各國謹慎但不退縮地與中國交手,是迎向未來的必經現實。臺灣更得知己知彼,既無法信賴有失尊嚴的媚俗,也不能依恃井底窺天的愚勇。我們得儘早走出當前的過渡階段,如果繼續滯留其間,原本的實力累積與反省認識都有可能遁入混沌無解之境,而中國仍會繼續慣行地發展下去,下一代的未來更見真章。
原載於《思想》二七(二○一四),頁二一七─二三二。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