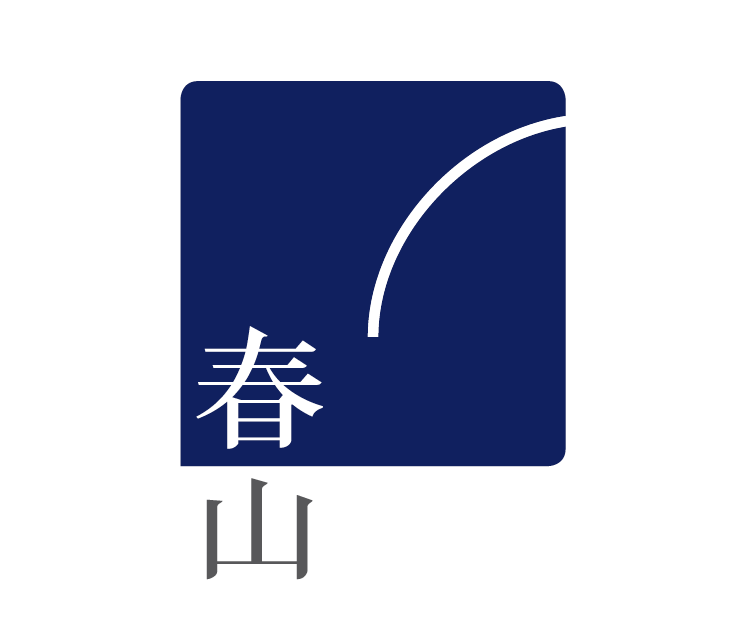
以春山之聲 Voice、春山之巔 Summit、春山文藝 Literati、春山學術 Academic 四個書系,反映時代與世界的變局與問題,同時虛構與非虛構並進,以出版品奠基國民性的文化構造。臉書:春山出版。
《新寶島》書摘:優雅的女士
關於《新寶島》
- 作者 @黃崇凱
- 近期講座:7月3日 20:00,憂鬱的亞熱帶──《新寶島》裡的臺灣圖像(對談馬翊航)
以小說思考臺灣問題,打開臺灣文學的經緯度之作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日,臺灣新任總統宣誓就職,正式開啟史上第一位原住民總統的新紀元。慶典般的氣氛才稍稍褪去,跨入二十一日午夜時分,由於不知名的原因,臺灣與古巴兩座島嶼的住民發生了大交換:兩千三百萬臺灣人在鄰近美國的古巴島上醒來,眼前是陌生的加勒比海。一千一百萬古巴人則來到臺灣島,隔著海峽與中國相望。兩國人民互換到相隔一萬四千五百多公里的陌生島嶼,劇烈擾動國際地緣政治的秩序,也瞬間改變兩個島國的命運。
長年在夾縫下求生存的兩個島國,即使交換地理位置,仍然處在大國陰影下。臺灣第一任原住民總統、也意外成為第一位在國土之外行使職權的總統,他要如何面對前所未有的局勢?無意間形成的臺灣─古巴命運共同體,該如何協調彼此步伐,重新立足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又怎麼在巨變下試圖抓住僅有的日常?
在憂鬱亞熱帶的反覆交涉下,同樣落居北回歸線上的臺灣和古巴,在時間長河中不斷梳理自身的存在。或許未來就是過去,而過去可能是未來的變奏。在時空的層疊開展下,小說多線並置,以訪談、書評、讀書會紀錄、重層虛構等形式複調演繹,消融既定疆界。小說時而從近未來迂迴邁向新世界,時而從新大陸通往繁複存在的可能歷史,也一再叩問當下:臺灣意味著什麼?
優雅的女士
二○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哈瓦那
今天要緬懷一位十年前過世的優雅女士,鄒族名是paicʉ yatauyungana,日本名是矢多喜久子,漢名叫做高菊花。
不過呢,故事要先從一個叫湯尼的男孩說起。
這孩子出生在嘉義,那時他的母親高菊花從臺中師範學校畢業教過兩年書,他的外公高一生則是關押在臺北軍法處看守所裡。他外公在獄中知道自己當外公。湯尼從沒見過外公。這個孩子來得不是時候,沒有得到祝福。在一九五○年代初期,不管他的母親是漢人、美國人或原住民,未婚生子都是讓家族蒙羞的事。他母親只好待在家裡待產,想辦法扛下一家重擔。湯尼在山村的噤聲肅穆中誕生。因為湯尼的父親失去聯繫,他就混在大他幾歲的舅舅、阿姨裡,給外婆帶大。湯尼的皮膚特別白,眼睛特別晶亮深邃,睫毛特別長,家人覺得他可愛親人,開玩笑說,讓湯尼來改良品種,我們鄒族人會更漂亮喔。
湯尼的外公被抓走的三個月後,他們家就沒了外公那份公職薪水當收入來源,原先居住的官舍也被收回,他們搬回給油巴那(Keyupana)的老屋,一家十一口窩在一起生活。湯尼的媽媽以前學生時代就很活潑、很愛玩,跟什麼人都可以交朋友。她在臺中讀師範的時候,常常跟朋友出去跳舞。她的父親,也就是湯尼的外公被捕以後,她下山四處奔走請託父親的朋友幫忙,心情低落,又跟朋友到空軍俱樂部跳舞解悶,才認識了美國海軍軍官保羅。據說就這樣懷了湯尼。保羅跟湯尼的媽媽說,以後會接他們到美國,從此失去聯絡。這樣的故事在當年還非常少見。美軍那時在臺灣有顧問團,駐紮在北中南的基地。一九六○年代中期後,打越戰的美國士官兵放假沒事就全臺趴趴走,其中一個結果就是留下不少混血兒。據說至少有一千個。我們的湯尼算是這些越戰混血兒的先驅。湯尼的媽媽生下湯尼的時候才二十一歲,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一個大學還沒畢業的女生。我們試著從這個女孩子的角度來想像一下:
妳的爸爸被抓,妳的美國人音信全無,妳的媽媽不知如何是好,妳的弟弟妹妹們有的還在讀書,有的還在地上爬,而妳沒結婚還生了個父不詳的孩子,妳該怎麼辦?這還沒說到妳常常被徹夜「約談」,政府的人惡狠狠偵訊妳,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問妳,反覆問一樣的問題,說妳有問題,參加什麼蓬萊組織,說妳有問題,不然怎麼總是看一些日文書、英文書,還想到美國留學。一樣的問題不斷地問,就是想要妳回答他們要的答案。儘管妳盡可能誠實交代,他們就是不滿意。很多個晚上,妳必須要從偵訊所在的奮起湖走回十字路,再從十字路走回達邦家裡。想像在深夜,只有星月的微弱光芒,妳得走幾個小時的路程回家。在路上,妳可能會不停想,忍不住想,為什麼自己要遭受這種折磨。這還不只是針對妳。他們抹黑妳敬愛的多桑(日文とうさん音譯,父親),由妳多桑的縣長好友,向大家宣布,是妳的多桑偷了錢。妳知道多桑是多麼愛惜這裡的山林,多麼盡心盡力為族人的幸福奮鬥,妳知道多桑絕不可能做壞事。但妳被偵訊多了、久了,流言到處在家鄉流傳,族人不敢靠近你們家,彷彿你們一家都是穢氣的惡鬼。真正的惡鬼闖進你們家,尋找什麼「叛亂證據」,撬開天花板,妳弟弟說他們找到的是一頂只剩外殼的鋼盔和平常用來挖筍的生鏽刺刀。暗夜步行時常霧氣濃厚,潮溼朦朧間,妳踩著兩條鐵軌中間的枕木和碎石,竟然有了一絲懷疑,或許多桑真的做了不好的事。妳開始痛恨起自己。為什麼非要生為多桑的女兒。為什麼不能像別人家的女兒,開心跳舞,出國留學。家族的老人家勸妳下山。一方面妳是大姊,得擔起這個多桑留下的家庭重擔,另一方面,或許可以稍微躲避情治單位的騷擾。於是,妳在平地人朋友的介紹下,去了市區的廣播電臺唱歌,唱以前跟多桑聽留聲機的英文鄉村歌曲,唱以前保羅愛聽的一些英文歌,唱著與以前的國家、現在的國家都沒有關係的英文歌。妳唱啊唱的,唱到高雄去,唱到臺中去,唱到臺北去。妳從簡樸的錄音室站到閃亮的舞臺,妳站在舞臺上,灼眼燈光打在妳身上,底下的觀眾對妳只是模糊身影,妳的眼前只有那支麥克風是清晰的,伴奏音樂從耳後傳來,妳準備唱歌,很多很多外語歌。妳唱,例如〈Mañana (Is Soon Enough for Me)〉,歡快輕盈,大家聽了都好開心,妳在臺上左搖右晃,逗得人人跟著搖擺。妳的英文不錯,妳甚至知道mañana是西班牙文,跟英文的tomorrow、日文的あした一樣意思,漢字跟現在的國語寫起來一樣是「明日」。
妳唱著歌,但不能想太多歌詞的意思,只要一想,很多的悲傷就會湧上來。像是〈Mañana〉的歌詞好像可以一一對照妳的處境,妳的口袋裡沒錢,妳的兄弟姊妹沒法工作,妳的卡桑(日文かあさん音譯,母親)很辛苦,妳要到城裡賺錢,妳的多桑真是個大傻瓜。大概是這樣,妳到處唱歌,但又看不起這樣的自己,覺得自己像妓女。妳抽很多菸,妳喝很多酒,妳給自己取了藝名「派娜娜」。這樣妳就可以暫時脫下多桑、卡桑叫妳きくちゃん(小菊)的那個女孩,把自己塞到一件鑲滾邊蕾絲連身洋裝,唱外國歌給外國人聽。
那時候開始有不少人會唱外國歌了,熱門音樂漸漸流行起來。有人在電臺介紹歌曲,書報攤上慢慢有些刊物在介紹美國熱門音樂,妳有時買本叫做《皇冠歌選》的雜誌,上面定期刊登熱門音樂的歌譜。妳在臺北的美軍俱樂部登臺,聽說有個年輕人組成的洛克合唱團,會演不少熱門音樂歌曲,像是白潘的歌,像是貓王的歌,受邀到各個美軍俱樂部表演。後來妳看過他們演出,他們也看過妳唱歌。很多年以後,洛克合唱團的主唱強尼老了,還記得當年有個派娜娜長得很漂亮,很會唱歌。
妳在高雄的歌廳唱歌,下臺後被情治人員帶到旗山偵訊一整晚。歌廳的老闆娘以為妳回不來了,哭了一整晚。妳在高雄唱歌的時候,有個外國人跟美國軍官常常來聽歌,接著又出現一個國軍將領。妳有不祥預感。妳想到山上的老家,家裡的卡桑、弟弟妹妹,還有湯尼。妳幽幽唱著〈Cry〉,聲音搖晃著整間廳室,彷彿所有人都靜止,妳賦予這首男聲原唱一種新的呼吸,每個字詞都在惆悵,妳的天空滿布烏雲,陽光在很遠的地方,妳真的好想放下頭髮,好好哭一哭。
他們要妳去陪那個外國人。山上來的陳副官說,這不是請求,這是命令。他對妳說,山上一切都很好,不過妳不陪的話,可就不保證山上都會很好了。妳會唱英文歌、法文歌、西班牙文歌,妳說流利的日語,但一點用也沒有,妳面對這個滿臉橫肉的男人,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妳只想拿番刀砍斷他的腳。妳被派去陪這個外國人、那個外國人,妳的心情好不起來。妳抽更多菸,喝更多酒,不唱歌的時候話愈來愈少。妳依然常常被訊問,重複的事情一問再問,妳覺得自己只是別人的玩具。妳聽二妹說回到山上的小學教書,時常被欺負。妳聽二弟說,在學校總是有人不想讓他好好讀書。至於三弟,他不說,就是用拳頭反駁。
到歌廳獻殷勤的男人再多,送來的花束再大把,永遠無法填補妳心裡的空缺。妳的多桑永遠不在了,妳的人生一塌糊塗。妳現在國語說得不錯了,但妳還是以日文思考。那個日本男子來聽歌,妳不確定他是什麼背景,他說是來做生意的,妳也只能相信。在那個處處隔絕的年代,妳跟他的語言共通,觀念接近,你們很談得來,雖然他總是話不多。妳以熟練的語言對他說很多很多話。有一次,妳發現妳在講述多桑的故事,妳跟情治人員說過很多次的,妳發現妳是第一次以流暢的語言在說給他聽。妳知道歌廳周圍,住處周圍,總是有人在跟著妳,監視妳,把妳當成籠子裡的鳥。他們會讓妳知道,妳不是安全的,別以為沒事。妳看著家裡被翻找過的痕跡,那些骯髒的平地人連鞋也不脫,就進到妳臺中的住處,翻出所有抽屜、拆出所有信件,把妳家的地板踩得處處鞋印。日本男子跟妳一起收拾,他沒說話,妳也沒說話,默默整理。後來妳又懷了個孩子,這次是女兒。
好,這樣你應該比較能理解湯尼的媽媽、舅舅、阿姨的處境。
我們把故事轉回湯尼身上。
湯尼跟其他山上的族人一樣,年紀到了就上小學,有時媽媽回到家裡陪他幾天,有時媽媽或阿姨或舅舅帶他下山到城裡。湯尼就像家裡最小的小兒子,整天跟著哥哥、姊姊(其實是他的舅舅、阿姨)屁股後面上下學,聽著おばあちゃん(音譯為歐巴醬,祖母或外婆)唱聖詩、哼童謠,看她拿著一本警察講習手冊寫日文字記帳,有時拿出一些舊信件,反覆看,有好幾次他看到おばあちゃん在靜靜流淚。上小學的過程中,湯尼漸漸明白為什麼大家看他的眼神不一樣。他的皮膚非常白,比天上的白雲還要白。他的頭髮顏色比較淺,很像小米結穗時的顏色。他的眼珠是藍鵲尾巴一樣的藍色,他知道有些同學在背後叫他魔鬼。他感覺得出,很多大人不喜歡他們家。那種不喜歡跟討厭不太一樣,好像是在害怕什麼別的事情。他們家常常有佩戴著手槍的軍人在附近走來走去,或者進來問吃飽沒。他去過別的同學家,覺得別人家跟自己家好像沒什麼不一樣,別人信天主,他們家也很多人信天主,他的三舅舅還讀神學院呢。おばあちゃん總是虔誠禱告,週日就上教會做禮拜。可是附近教會的人一樣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的家人。他跟其他同學差不多,都得幫忙家裡,日日來來回回挑水、挑糞,三天兩頭得把米放到石臼裡,雙手握著石杵奮力舂米,再把稻殼剝除乾淨,才能交給おばあちゃん下鍋煮飯。他有時跑到正在插秧的水田中找同學,看他們一家大小都彎著腰,種出一排排秧苗。看他們家的女兒被吸血蟲咬得兩腳紅斑喊痛。他會揹著竹簍到竹林挖筍,在油桐樹下翻樹葉撿油桐子,偶爾遇到蛇,偶爾遇到蜂。他最喜歡一種被他們稱為「小土蜂」的蜂,這種蜂會在泥土裡築巢,只要他發現小土蜂的蹤影,他就會悄悄跟著牠們,找到藏在土洞裡的蜂蜜,用隨手弄來的竹片挖著吃。他也會跟著おばあちゃん、少數還跟他們家來往的族人,到走路兩個小時的深山棕櫚園,採割棕櫚皮。他學著工作的大人熟練拿著砍草刀,砍得虎口痠麻,對著棕櫚樹學習剝皮,每棵樹只能割下三、四片大約一尺寬的棕櫚皮,以免傷到樹。棕櫚皮可以拿來做簑衣、繩子、掃把等等,是那年代重要的原物料。大人整理好以後,再揹下村裡曝曬,等候收購山產的平地人來買。他有時帶著簡易魚叉到溪裡抓魚蝦或抓幾隻yongo(螃蟹)加菜。偶爾遇到好心的大人,說魚抓太多了,竹簍放不下,要借放在他那邊。他不算村裡很會爬樹的小孩,有些大人兩兩一組,一個爬很高很高的樹,一個在樹下撿他們叫skikiya(愛玉)的果實,他看著他們削頭去皮,外翻放在屋外曬乾,再刮下愛玉籽包裝。
湯尼小學畢業,跟打算繼續升學的同學,一起下山到嘉義中學讀初中。他怎樣就是無法適應按表操課的生活。湯尼初一班上的同學升到了初三,湯尼還在讀初一。在舅舅協調下,湯尼轉到優惠原住民讀書的霧社農校。幾個在農校讀書的學生,分別帶幾個新生,徒步走兩個多鐘頭到十字路車站搭火車,搭四個小時車程到嘉義。再從嘉義搭五個小時客運公車到水里,下車轉搭公路局的車子上到埔里霧社。他也遇過下山到了嘉義卻沒接上公車班次,只能到市區的吳鳳招待所大通鋪躺一晚,隔天再上路。
說到吳鳳,他們族人都很不喜歡,偏偏課本一直教。那時嘉義有吳鳳廟、吳鳳中學,市區火車站前還有吳鳳的銅像。湯尼聽二舅說,以前在臺中讀書,有一群山地學生曾在國文課教到「仁聖吳鳳」的時候,集體罷課在外面球場打球。他二舅說,其實他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只是他跟同學窩在宿舍假裝有氣無力,沒他們那麼激烈。湯尼回想,那時候的老師教到吳鳳那一課,跟平常差不多,找幾個同學接力朗讀課文,教教生字,就進入下一課了。老師說,你們這裡叫吳鳳鄉,就是為了紀念這個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偉人。同學要記得,長大要當文明進步的人,不要當野蠻落後的人。湯尼聽不太懂老師的鄉音,其他人好像也不太懂。村裡有老人家說,吳鳳是奸商,他欺負我們老祖先才會被懲罰。他二舅說,你沒機會見到你的おじいさん(音譯為歐吉桑,祖父或外公),不過你可以試試把課文裡吳鳳的名字都改成你おじいさん的名字,可能還不錯喔。他二舅也在當國小老師,邊說邊拿著他的課本,朗讀起來:
他聰明能幹,每天除了自家勤苦工作以外,還教鄰近的高山同胞,播種、插秧和製造工具,所以大家都很敬愛他。後來政府派他做阿里山的鄉長,管理高山同胞。高一生像家長一樣的照顧他們,像老師一樣的教育他們,像朋友一樣的幫助他們。不久,把一個野蠻的地方,治理得有條有理。
二舅說,課文說吳鳳穿紅衣服戴紅帽子被阿里山的高山同胞殺了,這不太可能。我們這裡穿紅色的衣服,通常是peongsi(氏族領袖)、英雄或是偉大的獵人。我們的祖先不會那麼糊塗。課本寫的不一定是對的,一定要記住這一點。湯尼記得,那天在家裡,外面太陽很大,屋子裡的陰影覆蓋在二舅的臉上,二舅的濃眉大眼看起來有點溼溼的。
湯尼到霧社農校報到時,不知哪個同學起頭喊他阿凸仔,他就莫名奇妙變成大家口中的阿凸仔。不只同學這樣叫,本省人的老師、教官私下也都這樣叫。湯尼即使在原住民占大多數的農校,依然是個顯眼的存在。大部分學生皮膚黝黑,而他比身上穿的白色制服上衣還要白。他的藍眼珠,他的高聳鼻梁,他輪廓深邃的線條跟其他原住民同學不同,儘管都理三分頭,他的棕黃髮色在早上晨會升旗的時候,反射得特別耀眼。入學第一年,他長得快,上學期始業式他站在班級隊伍的中間,下學期結業式他已經是班級排頭了。農校籃球隊當然不放過他。教練訓練他打中鋒,整天跟他說克難籃球隊的大中鋒,綽號「大象」的霍劍平如何如何移動,湯尼根本無法想像。請記得,那時候沒有網路影片可以邊看邊學,教練能教會他不要走步,不要兩次運球已經很了不起。湯尼就只是負責在場上盡力跳,盡力卡位搶籃板,傳球給隊友投籃。
農校的男籃跟女籃是同一個教練管的,總是一起訓練。湯尼常常看到女籃的中鋒靈活穿梭籃下,輕鬆摘籃板接著擦板得分,動作順暢得像拿筷子吃飯。這個大他一屆的學姐是學校的風雲人物,長得美,又會跳舞又會打球,收到很多情書。只要訓導處廣播喊出她的名字,球隊同學就會起鬨。這個學姐跟他一樣來自阿里山,不過是隔壁的來吉村。他們練球時會遇到,有幾次也搭上同一班公車或火車回阿里山。學姐有次在家跟姊姊聊到湯尼,姊姊說我們的ak'i(爺爺)的兄弟好像跟他的ak'i以前發生過很不好的事。學姐問,那他怎麼長得那麼像外國人?姊姊說,聽說他媽媽在平地交了美國男朋友,後來就不見了。學姐對湯尼的印象就是安靜,那麼大一個人,老是想把自己隱形起來,但是不可能啊。她在宿舍大澡堂洗澡的時候,總是遮遮掩掩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又乾又瘦的樣子,有時趁大家都洗完澡的時候才溜去洗不怎麼熱的水。她室友跟她說,奇怪妳跳舞、打球從來不畏畏縮縮,怎麼洗個澡卻像小媳婦似的躲躲藏藏。妳有的誰家沒有,這麼害臊真是。妳要是像籃球隊的阿凸仔,聽說那裡的毛的顏色跟他頭髮一樣,那才夠害臊的呢。室友都沒發現她臉紅了。
籃球隊到外地打比賽的時候,對手教練看到湯尼在場上熱身,就要跑去跟裁判要求驗學生證,確認對方是農校學生,哪來這麼個人高馬大的洋將。但只要一跳球,比賽開打,對手的教練就慢慢安心了。這個白中鋒速度不太行,常常跟不上球隊腳步,補位防守會漏,進攻也只能在籃下。唯一優點就是一柱擎天,槓在禁區還是有嚇阻效果。這就是個對籃球沒興趣的孩子。農校女籃的中鋒就不同了。雖然身高只有一六六,但基本動作不錯,禁區殺進殺出的像隻花蝴蝶,渾身運動細胞。教練總是叫湯尼多學學,還吩咐學姐教他兩招。湯尼知道亞東籃球隊的教練特地來看過學姐,她以後說不定會當國手。而且學姐之前跟舞蹈社一起去校外拍電影,有人還問她要不要當明星呢。面對這樣的學姐,湯尼更害羞了,手腳變得更緊繃,連球都拿不穩,練習在籃下背框單打的動作,有時左右搖擺兩下就掉球,不然就是腳步亂成一團。學姐對他說,不要急,慢慢來。有看過kokongʉ(蜥蜴)爬樹吧?牠不會一直動,而是在你一眨眼,突然動了,讓你措手不及。學姐拿球示範,背框拿球,往右瞄一下,肩膀抖一下,突然往左轉身向內鑽,擦板得分。湯尼終究沒能在比賽時成功做出這些動作。
湯尼其實沒有學姐想像的那麼安靜。他放假時會到臺中市區的三阿姨家,他的媽媽,幾個舅舅、阿姨都在,還有他的妹妹。媽媽依然要到處唱歌,深夜醉醺醺回到家,常常開口就是罵人。湯尼覺得奇怪,喝酒不就是為了開心一點,怎麼好像愈喝愈難過。媽媽會抱怨他爸、他外公,還有命運。三舅舅看到就勸她,要相信主,把自己交給祂。媽媽回說,你現在不打架了,那麼會講道理,天主好偉大呢什麼時候讓你當神父啊。湯尼待在臺中的時候,早上會聽到媽媽練嗓子,媽媽練完就會躺回去睡一下,他知道媽媽晚上在歌廳唱歌,非常晚回家,需要補眠。他在臺中家附近時常會看到一些假裝是普通人的守衛,也不時有警察來問話,他以為他們家是二舅舅說的「甲種戶口」,才會跟山上的家一樣。但三阿姨以前就是嫁給警察啊,他怎麼也想不通。湯尼路過隔壁的日式房屋,門口有衛哨,紅漆大門和插著酒瓶碎片的圍牆裡據說住著一位將軍。這幢深綠色日本平房屋頂鋪著魚鱗般的瓦片,最特別的是那根煙囪。媽媽跟他說,以前他們在山上住過跟這個很像的屋子,舅舅補充說,早上還會聽到你おじいさん放曲盤的古典音樂,好像起床號。湯尼想,可是他小時候在山上都是聽おばあちゃん歌頌天主起床的。
湯尼長著一副外國臉,不認識的人看到他都不自覺結巴說起英文。但他的英文也不好,每次一說「我會說國語」,對方就睜大眼睛稱讚他的國語說得很好。他困惑起來,可是在學校,老師一直說我們山地人發音不標準,有山胞腔。他路過向上國中對面的美軍招待所,有些度假的美國大兵跟他打招呼,問他是哪個部隊,他根本搞不清那些越南地名和部隊番號。湯尼靠那張臉,偷偷跑到萬象俱樂部、意文大飯店的歌廳開開眼界。還有幾次他帶著農校同學,跑進像是Sun Star、Blue Angel、OK這些小酒吧,看音樂表演,跟一些大兵、酒吧女在舞池裡搖臀擺手,這麼練出了基本英語會話。湯尼漸漸摸出一些門道,給自己買了便宜的飛行員夾克、牛仔褲、靴子當外出服。他發現,只要這樣穿,就像放假的美國大兵,走在夜晚街上,也沒人會攔你盤查。湯尼看過一次媽媽以「派娜娜」的名字在歌廳登臺。
湯尼坐在吧檯,遠遠看著派娜娜輕聲吟唱,心裡的薄膜好像被一層層細細剝開,聽不懂歌詞,卻覺得有些難受。吧檯的接待boy跟他說,這西班牙語,聽說是有一百年的老歌,派娜娜還會唱法文歌呢。這一帶就是派娜娜會唱最多種歌,什麼語言都難不倒她。喏,你看那邊坐在臺前那一桌的,那是蔣家的人,他常來捧場。那一排吧檯的阿兵哥、吧女聊天吵雜,湯尼望向那個蔣家的人,眼神望著舞臺,頭跟著派娜娜的歌聲輕輕搖晃,他再望向派娜娜,她正唱到一個似有若無的音,左手緩緩舉起,歌廳彷彿在那一秒鐘沒了聲音,接著是一個拖長的尾音,悠緩淡出,湯尼看見一隻鴿子振翅遠走,隱沒在空中成為一顆白點。這是他沒見過的媽媽,這樣的媽媽好悲傷,好美。
學姐畢業後去了臺北,聽說有老師要栽培她當明星。湯尼覺得學姐應該辦得到。上次救國團來學校辦冬令營的晚會,她上臺唱了〈Don’t Forget I Still Love you〉驚豔全場,以他在臺中歌廳聽歌的經驗,確實有出道的實力。後來她果然在臺視的歌唱比賽拿到冠軍,報紙上都是山地姑娘大爆冷門的報導。學姐選上南僑肥皂的快樂公主以後,他們籃球隊還因此獲贈幾箱肥皂,那陣子每個人就連打嗝、放屁都是肥皂味。不用說,學姐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負心的人》,湯尼當然也去看了。他看到大銀幕上那個叫玉芬的女孩,如此熟悉的臉,放大以後卻覺得無比遙遠。湯尼從五年制農校畢業後,暫時待在臺中三阿姨住處等入伍。那段時間他媽媽演出少了,主要在臺北跟朋友合作經營日本料理店。湯尼混跡在五權路一帶的酒吧、俱樂部,做招待boy、當酒保,有時上臺代打唱歌,轉賣一些美軍的二手雜貨,英文溜得不得了。他聽說過一些美國民眾的反戰遊行,也拼湊一些大兵之間的傳聞,猜想美軍在越南的狀況愈來愈糟糕了。湯尼認識一些吧女,交往過兩、三個,總是維持不到幾個月。他會好心奉勸那些女孩,別跟美國人認真,管他是白的黑的都一樣,他聽過太多人的保證、發誓,從沒有一個人回來。他會這麼說:Look at me. I’m the proof.
有些吧女聽了就笑,來不及啦我家的雜種仔放在後頭厝給他自己大。有些吧女點點頭,放在心上,還是陷進去,終究失望了。確實有幾個真的去了美國的吧女,從此失去聯繫。湯尼接到兵單,先回山上看おばあちゃん,她很有元氣地在田裡工作、上教堂做禮拜。他接著到士林看媽媽。媽媽跟他說,打算嫁給一個常來店裡吃飯的客人。對方可以接受她帶著妹妹,對她也很好。他贊成,當晚就跟媽媽、妹妹和對方一起吃飯。
湯尼新兵訓練結束,抽到金馬獎,到金門當了兩年食勤兵。他只記得搭了好久的船,吐了兩次,上岸時整個人軟手軟腳。金門的長官笑他這個阿凸仔中看不中用。他跟著部隊住山洞,躲單打雙不打的炸彈,等到炸彈落地,再跟部隊去挖彈頭,到處回收撿拾附在炸彈尾巴的共匪宣傳單。長官總不懷好意問有沒有偷看宣傳單,他知道要回答報告,規定不能看,所以沒看。長官說,這就對了。別說你知道共匪發射什麼東方紅人造衛星。提都不要提。天清氣朗的時候,對面的廣播聲音順風吹過來,吹掉島上的對匪廣播。他每每聽到「國民黨軍官兵」這樣的詞。當然不敢說,也不需要說。他長得夠顯眼了,不給自己找麻煩。當兵的日子跟著時間、位階很有秩序地前進,其實跟他以前在農校籃球隊按表操課差不了多少。距離退伍還有半年,連上輔導長找他加入國民黨。湯尼說,報告輔導長,我家是甲種戶口,應該不可能。輔導長跟他說,我知道,所以才要幫你。這樣以後出去對你比較好。湯尼說,報告輔導長,我已經跟班上弟兄說好,退伍後跟他一起去跑船。輔導長還是勸他去洗兩張照片,下次交給他去申請辦證。他知道輔導長是好意,但他就是不想入黨。他聽三舅舅說過,以前他想入黨都不核准,直到他當神父才通融讓他加入。他就這樣裝死到退伍回臺灣。
湯尼上岸後見到的媽媽,有些憔悴。那時媽媽最小的兒子還包著尿布,卻不小心在士林的平交道被火車撞死。他只能安慰媽媽。他回到山上陪おばあちゃん,一起下田工作,傍晚待在家門口,靠著牆,對著山,彈吉他唱歌。附近有些小孩會跑來聽他唱歌,湯尼就像他們在電視裡看到的外國人,可是會說他們的話。二舅舅調回家鄉的小學任教,夫妻準備搬回老家住,問他以後有什麼打算。湯尼說,要跟當兵的朋友去跑船,他們家是東部的阿美族,全家的男人都在跑船。二舅舅說,好不容易平安從金門回來,還要出去?可以留下來做茶啊什麼的。湯尼笑回,我想環遊世界。
湯尼那時在練習唱當紅的〈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偶爾想想自己到目前為止的短暫人生。山上的家變得好空,大家都分散在各地工作、生活,只有おばあちゃん一直待在這裡,無止盡重複一樣的日子。他到臺中的三阿姨家,隔壁深綠色大房子的將軍還在,深鎖的大紅門外依然徘徊著便衣特務。三阿姨說,她在市場買過隔壁將軍種的玫瑰,拿來泡茶也不錯喔。湯尼到五權路附近的俱樂部,有些換名字、換老闆,生意非常蕭條,路上看不到外國人,好像灰姑娘的變身時間已經過了那樣冷清。他到北西北撞球部打彈子,聽一個在CCK(清泉崗空軍基地)那邊來的西服店伙計說,現此時生意比兩年前差多了,攏是伊個殺人的美國阿兵哥害的啦。另一個酒吧的酒保說,毋是吧,我聽說是美國欲參阿共仔好,今馬沒那麼多美軍去越南戰爭,伊們亦無補助來臺灣度假囉。湯尼飲著啤酒,腦中不斷回放那首歌的旋律,他猜想著歌詞的意思,有點不太懂,卻又想反覆挖掘:What do you think you'll do then,你想你接著會做什麼,I bet that'll shoot down your plane,我打賭那會打下你的飛機?那又跟黃磚路有什麼關係?他不太明白,但那就像謎語一樣,緊緊黏住他的思緒。
湯尼跟著阿美族的朋友Suming在高雄前鎮搭上了遠洋漁船,開始他的跑船生涯。登船前,他看到朋友家族老老小小三、四十個來港邊送行。他朋友Suming說,因為他的爸爸、叔叔、伯伯、舅舅、表哥什麼的都在跑船,抓魷魚的大概一年可以回來一次,他們這種抓鮪魚的一跑就是兩、三年才能回家。船公司給一般船員每月一千多塊安家費,湯尼想,還不壞,比在山上務農好,抓到的漁獲採分紅制,這樣每月底薪雖然只有幾十塊,有努力就有回報。後來上船發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兩間半教室大、一百四十噸的鮪釣船,所有空間都算得剛剛好,大小依照階級分配,分紅也是。船長拿四份,輪機長拿三份,大副兩份,扣除每趟出海成本,剩下不到一半的收入船員再依照職務位階分紅,最低階的新手船員算起來不過十幾萬。湯尼跟Suming抱怨,每天凌晨四點就要起來輪班綁釣繩,等到揚繩機收線,放繩收繩之間十幾個小時就過去了,說是三班制,實際做起來感覺只有一班做到死。湯尼就算帶手套綁繩索,手掌三不五時就起水泡。老鳥笑說,這白番皮肉真細呢。湯尼山上來的,一開始出航看海好興奮,沒幾天就看得好無聊。海不給看的時候就暈到整隻船都在搖晃。湯尼不大會游泳,適應後在船上意外地穩,他猜不知跟他的美國爸爸是海軍有沒有關。Suming說,啊不然不跑船,就是種田,在都市裡爬鷹架、綁鋼筋,到礦坑挖得面黑黑。湯尼看到那些老鳥,想到自己年紀大一點可能就像他們,整天摸魚賭麻將、牌九、四色牌,用那雙長久拉繩綁索的彎曲手指算牌、記帳、寫信。他想,要能在這種地方生存,只能盡量往上面爬,最好爬上駕駛室,決心下次回臺就去報補習班,先考個無線電報務員的牌照。
湯尼沒待過那麼閉鎖的空間,所有汗味、酒味、機油味、煙囪臭氣味、魚腥味、海風鹹味這些都關在一起,就跟圈養的畜生差不多。很多船員練就一身靠著欄杆拉屎的能耐,屁股亮給海看,偶爾還會吸引魚游過來呢。他窩在住艙輪休,看著狹窄臥鋪旁的小圓窗,船身泡在洋面上上下下,有時看得到遠方隆起物,就像看到熟人那樣興奮起來。船到馬六甲海峽的檳城停泊卸貨、整補,排隊等領港船入港,整船十幾個船員就像準備放假出營的阿兵哥,快快填好報關表格,望著接駁舢舨等上岸。船長扭開電唱機,放了歌仔戲曲盤在聽,海港天空有海鷗盤旋,好像只有他不在乎下不下船。湯尼想起在金門放假也差不多這樣,成群結隊的士官兵等著到八三么,階級差異就在茶室的小房間裡被消化了。湯尼自己在港區街道亂走,隨意找了家酒吧坐進去,要了啤酒喝。滿室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馬來人、在地華人,吧女滿間跑,夾雜幾種語言的歡鬧聲,像他這種白臉孔的不太多。他後來在一家華人雜貨店買了明信片,隨手寫下幾句問候報平安,才猶豫起該寄給誰。最終寫給了おばあちゃん。他想搬回老家的二舅舅可以唸給她聽。
湯尼想像著山坡上的小矮屋,有貓走過窗臺,一個優雅的女士獨自坐在門口前的椅凳,看著眼前的山,哼著據說是她丈夫做的日文歌。湯尼寫下醜醜的漢字:我在馬來西亞的檳城,船上的人說我是新來的,沒暈船很厲害。我們抓到很多鮪魚。下次靠岸就是在南非的開普敦了。
湯尼寫完明信片,在港仔墘福德正神廟附近的路上閒逛。兩旁半空懸吊長串燈籠,周圍來往大都是黑髮黃膚的華人,有說閩南語的,有說廣東話的,感覺像在臺灣的哪個城鎮街上。空中有鴿子低低飛過,他想起媽媽唱的另一首西班牙語歌,也是在說鴿子。他邊走邊哼,遇到不遠處正在東張西望的Suming,想說這個番仔看起來真是孝呆孝呆。
這次故事說得有點太長了,謝謝各位聽眾收聽。我是高再生。
pasola xmnx na mansonsou!
這句鄒語的意思是:願您每回呼吸都順暢!
我們下次再會。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