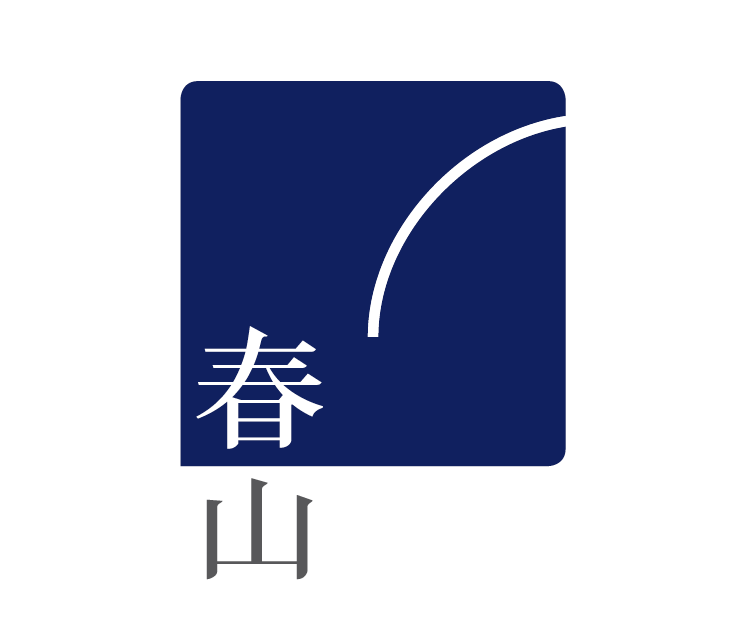
以春山之聲 Voice、春山之巔 Summit、春山文藝 Literati、春山學術 Academic 四個書系,反映時代與世界的變局與問題,同時虛構與非虛構並進,以出版品奠基國民性的文化構造。臉書:春山出版。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永不開花的枯葦(吳俊宏)
◎ 寫於一九九四年春,於妻子陳美虹過世後,二○一二年五月定稿,同年八月二日刊登於《臺灣立報》。二○一二年十二月收錄於《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一輯,國家人權館籌備處。二○二○年七月又收錄於個人作品《綠島歸來文集》,人間出版社。
吳俊宏 (一九四八~) 臺灣雲林北港人。一九七二年就讀於成功大學四年級時,因涉「成大共產黨案」被捕,坐牢十年。 一九八二年出獄後,一九八五年與陳美虹結婚,陳美虹的父親為劉耀廷,因大安印刷廠支部案被捕,一九五四年一月槍決。吳俊宏曾參與組建「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黨」、「左翼聯盟」等左翼團體。目前為「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監察委員會召集人、「左翼聯盟」中央委員,著有《綠島歸來文集》。
陳美虹
夜深了,陳美虹,獨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她燃起一根菸,吸了起來,多年來為了小孩,她已戒了菸,但此刻她已顧不得自己的身體了,她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繚繞的煙霧掩蓋不住她一雙迷惘的眼神。
前年她罹患乳癌,開了刀,兩年後的現在,癌細胞又復發了,今早去看醫生,醫生的態度已很明白地表示,她已無救了。
她今年才三十九歲,小孩才五歲,就此離去,她不但放不下心小孩,更為她這短暫的一生,頗覺無奈。
她拿出一個小藤籃,這是她母親留給她及她的雙生妹妹陳美蜺的遺物。裡面存放著一疊信及兩本相冊,信件是她父親四十年前,從牢裡寄給家人的,以及她母親寄給她父親的。兩本相冊,是父親在牢裡製作給她家人的。
父親的信,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從當時的臺北市西寧南路三十六號(當時稱此處為東本願寺,為保安處看守所)及臺北市青島東路三號,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寄出的。
信已泛黃,但信上父親印蓋的指紋還相當清晰明顯,印泥的顏色也朱紅如昔。信紙上偶爾散布著幾片較大的褐黃色水漬斑痕,陳美虹一直認為它是她父親的眼淚,滴落在信紙上,日久呈現出來的顏色。
父親信總共寄回四十封,以後就再也沒收到了。
相冊是她父親在牢裡,以鋼筆的筆尖當刀片,用粗布紙張、糖果紙等素材製作而成。父親在藝術上有很高的造詣,在兩本相冊的每一頁裡,父親都刻劃著各種山水、花鳥、動物……等圖樣,並題了些字。在這些圖樣及字底下,再襯上各種顏色的糖果紙,使得每一畫面都顯得栩栩如生。這些畫面都表露著她父親內心深處,對自己命運的期許和對家人的寄語。在一九五三年十月製作的第一本相冊的首頁,畫著一尊自由女神像,表露著父親在牢裡對自由的渴望。然而父親似乎也曉得自己來日無多,因此在另一頁上,他題著:「我可愛的小姊妹,美虹!美蜺!自強!!」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製作的第二本相冊的首頁,陳美虹的母親貼上一張很小的日曆紙,上面印刷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就是這一天,她的父親劉耀廷,在白色恐怖的肅殺中,被當局處決,日曆上印著:「為救國家救民族而戰」。父親死時,她兩姊妹僅十一個月大。
陳美虹反覆翻閱著父親的遺物,她不曾和父親晤過面,對父親的認識,除了從親人的轉述外,她只能在父親的遺物中去遐思。父親的死,影響她的一生,當她失意時,她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來。此刻,面對她那行將結束的生命,她腦海裡喟嘆地不斷浮出:「如果父親不死……」的種種幻想。
生父劉耀廷
劉耀廷,一九二五年生,臺灣澎湖人,家境還算富裕,幼時舉家遷至高雄,中學時全家再遷往日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臺灣光復那年,因某種迷信的想法,再遷回高雄。
他個性沉默寡言,生氣起來,良久不說一句話。為人正直,樂於助人,頗具藝術天分。據說在他去世十餘年後,有一位他在日本求學時的音樂老師來臺找他,準備送他一部鋼琴,聽說他已死亡,不勝唏噓,痛惜地說他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天才。從他在牢裡為家人製作的相冊看來,他在美術、書法、工藝等藝術上,的確相當具有天分。
他為什麼捲入這場白色恐怖的肅殺中,而致殞命,其確切原因,他家人全然不知。直至他被處決之前,他家人從沒收到起訴書或判決書,只在他死後收到領屍通知單。
他的詳細案情,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他死後的四十五年,筆者遇到他的一位同案方阿運先生,才取得他的判決書,揭開了掩藏幾近半個世紀的謎底。
他原任職於臺灣省立高雄第一女子中學(現高雄女中),教授英文及美術,一九四九年轉至臺北大安印刷廠工作,擔任經理職務。這個印刷廠,位於現在的臺北市忠孝東路與八德路交接處,當時是中共地下黨的印刷機關,專事暗中印製中共的宣傳刊物,據判決書記載,其所印刷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新聞論文等」。此印刷廠負責人為當時知名作家呂赫若,據說部分資金來自於辜顏碧霞(辜振甫大嫂,辜濂松之母)。
劉耀廷是否因曾與呂赫若相識而被邀參與這個印刷廠的工作,不得而知。他大概於此時投入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列裡,據判決書記載,他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及九月間,兩度參與刊物的印刷,並於同年十月間在劉述生的吸收下,加入中共地下黨「TL支部」。
一九四九年秋中共地下黨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被破獲後,地下黨鑒於形勢危急,即將此印刷廠解散,呂赫若躲入鹿窟山區基地,劉耀廷則回到高雄老家,與相戀多年的施月霞結婚。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深夜,他在高雄家中被捕。其大哥劉耀星,為了營救他,曾四處奔走,找關係說項,不少情治人員也上門來,謊稱有辦法營救其弟,要他拿出金子來打點。親友們皆勸劉耀星不要給,因為那可能是來詐騙的。劉耀星卻說:「不管是不是騙,這些錢是不能不花的,我必須給月霞有個交待,讓她瞭解我們已盡全力在營救耀廷了。」
恩愛夫妻牢裡牢外
劉耀廷被捕後,施月霞正懷著六個月的身孕。他們夫妻原本至為相愛,正當他們期待著那即將出世的愛情結晶時,殘酷的時代黑手,卻強將他們拆散,一位在臺北的黑牢裡,一位在高雄挺著沉重的身孕,他們兩地不僅相思,更彼此背負著椎心的牽掛。然而這一切,似乎也只能在日記裡各自地自我傾訴著:
思念你!思念你! 我心愛的耀廷啊! 以這枝淚水串成的筆寫給你, 待何時 思念的你 才歸來 在這充滿回憶的兩人房間裡 只剩我一人寫著日記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十時半,劉耀廷被捕後的一個月,施月霞在她的日記裡,以日文寫下以上這首詩。
隨後她又寫道:
我夫耀廷,一個月前的今夜,剛好這個時候,正很好吃的樣子地,吃著我用番薯做的點心,吃完後,兩人很快樂地上床,和往常一樣,你右手讓我當枕頭,左手抱著我,很滿足地睡著。 如此幸福夜晚的情境,到底是夢還是現實,如今不堪回想,自此以後,一個月過去了,你已經去那很遠很遠的地方。 月霞這一個月是如何度過的呢? 白天我都在樓下,一面織些編織物給你,一面在腦海裡描繪著你的影像。母親已經去睡午覺了,我才敢較自由地,小聲地叫著你的名字:耀廷!耀廷!我的眼淚也伴著編織的毛線,禁不住地流出來。我想讓母親煩惱是不孝的,所以母親面前一直都忍著眼淚,不敢流出來。 吃飯的時候,看到你的空位,就想著一向偏食的你,在那地方是怎麼吃的啊!但是怕家人煩惱,我擒住了眼淚,同時為了我們最要緊的肚子裡的小孩,我雖沒胃口,也硬吃下了許多。 和以前一樣,我十點就關起房間來,但是一個月以前的房間,是兩人恩愛的房間,現在卻成為月霞一個人孤獨地,流著寂寞的眼淚的房間。那種寂寞,真是太寂寞了,有生以來真正感受到孤獨的痛苦。 蚊帳掛起來後,像往常一樣,向神禱告,並向你說聲晚安。 獨自一個人,鋪上曾經是我們兩人愛用的長長的枕頭,把你已經穿過一個禮拜,還留著你的味道以及油垢味道的襯衫,放在你以前的位置上。一邊叫著:耀廷!耀廷!一邊無意地抱起你的襯衫,哭著,哭著,不知何時竟睡著了。 半夜醒來,如廁時,就披上放在右邊的你的睡衣,獨自一人,走過暗暗的走道,下樓去。過去一向都是你陪我一起去的,但現在只能以你的睡衣來代替了,因為半夜醒來時,我的旁邊已經沒有你,你已經去到很遠很遠見不到的地方呀!叫也聽不到,不能像往常一樣得到你的愛撫。 思慕你呀!思慕你呀!月霞時時哭泣著,哭泣著。然而我的思慕好像愈來愈遠,我真想見到你啊,即使只見一眼也好。真希望你給我一個強烈的擁抱,如果能夠讓你緊緊地抱著,在你的胸懷裡,盡情地哭泣的話,那麼在這瞬間,我們倆人,就這樣脫離痛苦良多的世界而死去也好啊!讓我們就如此緊緊地擁抱著不放,安詳地到天國去吧! 啊,耀廷!我思念的人啊!耀廷!……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雙胞姊妹誕生了,施月霞在這一天的日記裡記載著:
臨產時,我正想著,希望順利生產出正常可愛的小孩,生出來如果是不正常的小孩呢?如果是男,如果是女……,正想間,猛然抬頭看到掛在牆上結婚照裡耀廷的臉,我心頭突然一震,淚水直湧而出,產婆以溫柔安慰的口氣罵著,要我不能哭,要我以堅強的心情,期待小孩生下來。但我的眼淚還是不停地流出來。 溫柔體貼的往事又浮現在我腦際,想起上一次生產時(雙胞胎前,施月霞曾生下一男孩,後不幸夭折),耀廷在我身邊,幫我助力,讓我堅強地生產,孩子生出來時,耀廷輕摸著我的面頰說:很好,很好。但想到如今,我夫卻在很遠很遠見不著的地方,我的眼淚又掉下來。不過,我立刻又想起,哭也沒用,我必須堅強起來,要以堅強的心情,生出我們兩人最愛最要緊的小孩,我在內心裡,對自己叮嚀著,呼喚著。 父親不在,父親的責任,一定由母親承擔,一人盡兩人的責任扶養,使他們成為活潑可愛的小孩,父親回來時,才會感到高興。 看著兩個小孩的臉,我的眼淚又掉下來了。倆人看起來都營養不良,血色不佳,要扶養這兩姊妹,一定要相當費力。月霞!妳要堅強啊!
在施月霞遺留下來的小日記本裡,她以流暢的日文,豐沛的情感,道盡了對丈夫的深情,寫盡了白色恐怖下受難夫妻的淒涼哀怨的詩篇,令人閱之鼻酸落淚。
一九五三年四月間,劉耀廷獲准和家人每週各自通信一封,但為了不讓對方擔心,儘管彼此內心都積抑著無限的思慕和牽掛,卻也不敢在信裡盡情地向對方傾訴著。幾個月的時間裡,他倆都僅僅互報身體健康,望家人放心,以及談論著雙生女兒的種種。
直到九月二十二日中秋節的那天,施月霞終於忍不住地寫著:
耀廷,想不到今夜十五夜下雨,真是想不到,本來等著今夜要與我的耀廷,在同樣的時候,一起看月亮,但是小雨漸漸地落到地上,看不見明月,耀廷,我所知道的八月十五夜都沒下雨,今年怎麼這樣惡天氣,眼睛看著黑暗的天空,心上是想我最愛的耀廷,耀廷,你現在一定立在窗口,很痛苦地看著天空吧!
隨後她又不安地補述著:
耀廷,現在雖是月霞精神上斷腸之苦,但是每天的生活是很幸福的,請你絕對不要掛念。
但是這樣的補述,仍免不了劉耀廷痛苦的指責,他在回信裡寫著:
月霞,你不要時常想我來痛悼憂愁了,月霞!好嗎?決不要!我最掛念是我妻的身體,因為你的一身是很重要的,美虹姊妹全靠了你一人,我不在時假使你也失去了身體的健康時,叫她倆怎麼辦才好呢?
然而,在其後的信裡,他們還是忍不住地吐露著彼此相思之苦。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劉耀廷寄出他的最後一封信,多日後,施月霞收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寄來的領屍通知單,劉耀廷二十九歲的生命,就此終結,這對人間難得尋覓的恩愛夫妻,從此天人永別。
對於劉耀廷的死,陳美虹在雜記上寫著:「父親的苦難結束,我們母女三人的苦難正開始。」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