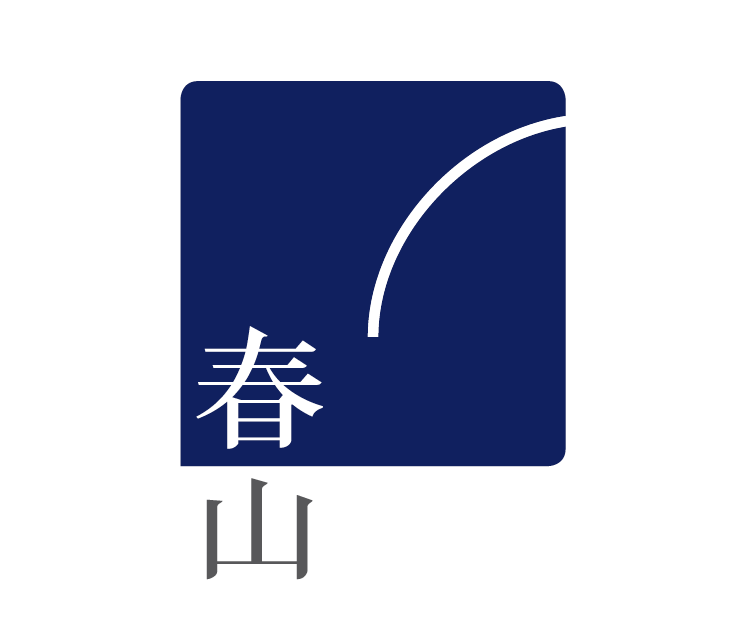
以春山之聲 Voice、春山之巔 Summit、春山文藝 Literati、春山學術 Academic 四個書系,反映時代與世界的變局與問題,同時虛構與非虛構並進,以出版品奠基國民性的文化構造。臉書:春山出版。
傷損的奈米化,我們該如何記起白色恐怖?──《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發表會後記
《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電子書購買連結
因國際書展延期與疫情的關係,《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第一次發表會直到三月十一日才進行,讓各位讀者久等了。這也是第一次,書都已經二刷了,出版社才辦新書講座。很謝謝支持這套選集的所有讀者。第一場發表會由人權館館長陳俊宏主持,兩位主編胡淑雯、童偉格與以〈玉米田之死〉被收錄進選集的小說家平路都到場分享,平路現場朗讀了自己的自傳作品《袒露的心》,回憶那個壓抑肅殺與改變她一生的年代,真摯情感令人動容。
陳俊宏館長一開始就表示,這套書對人權館有兩個重要的意義,大概在兩年前人權館就開始思考以文學做為社會對話與介入的重要方式,讓白色恐怖成為公共記憶的一部分,第二是跟民間出版社合作,希望能更多讀者進行對話。他很謝謝兩位辛苦的主編,花了一年的時間遍讀作品。
主編胡淑雯從這套書的書名開始談起,「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臺灣、白色恐怖與小說,這一套詞語的組合,就面臨了這到底是政治的還是藝術的問題。使用臺灣,是否預設或呼喚了一個政治邊界,有一些創作者覺得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面對白色恐怖,也有人因此拒絕,因為這個詞彙長久以來給人不舒適的感覺。他認為這些拒絕本身是有意義的,因此接受這個拒絕,也去思考,這究竟是政治的還是的藝術的。
胡淑雯強調,白色恐怖這個詞彙至今還是妾身未明,比如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混同,這種不明就理本身也是我們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她解釋,這套書刻意排除單單只談二二八的作品,但卷二納入一些二二八的作品,原因是那些作品是在談論我們如何記憶、遺忘與誤會二二八,以及記憶如何篩選。這套小說選正是渴望去引發討論,這樣重塑性的建構,當代的政治意識如何覆蓋在這個事件上面。
胡淑雯指出,長年以來,臺灣社會有一種深入大眾的說法,讓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臺灣習於讓政治與美學切分。事實上,這種情緒或精神心理,發展出清高的犬儒主義隱隱攜帶著對政權的順從,這可能就是戒嚴體制帶給我們的精神負債(或者是遺產)。閱讀或書寫政治小說,就是在回應這樣的現象,對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的美學回應,才是真正在實踐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胡淑雯說,編選這套書正是要抵抗虛假的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要抵抗的第二重媚俗,則是威權戒嚴體制下透過主義與領袖崇拜,各式各樣的精神獨裁,而這些作品就是在反威權的媚俗。
胡淑雯強調,另外兩個層次的媚俗可能是比較少被討論的。一個是,攀附著國族主義建構的媚俗。她就經常在想,這套書的讀者是因為政治還是藝術的原因而購買。她說,她跟童偉格刻意挑選不服務於主義、國族建構的作品。他們做的不是政治的選擇,而是美學的選擇,依循內在做為創作者的美學立場,成為編選的原則。最後,要抵抗的第四重媚俗是關於英雄與烈士敘事的媚俗。胡淑雯說,媚俗是存在與遺忘的中途站。媚俗像是篩子,是通往遺忘的中途站,因為我們希望它成為什麼樣子,而忽略了雜質。因此英雄與烈士以外,或許讓人不舒服的雜質,才是真正幫我們留存與認識人性的複雜性。
平路則回應說,身為小說作者,覺得小說或許天生就應該處理、面對這些年代的故事。沒有一種文體比小說更適合,因為小說呈現的始終是half truth,這是小說最厲害的事。關於記憶,從來不是whole truth。她說自己寫小說,從來沒有一天感到後悔,因為小說最可貴的是懷疑。當這麼多篇小說湊在一起的時候,正是這些懷疑的部分讓我們看清楚時代的真貌。辯證性是小說最擅長的,小說既重構又解構、建構。小說也特別適合處理雜質,那個時代關於國家暴力、冷戰,到底對每一個個人、家庭,發生了什麼影響?把每一個雜質剖開來,都是人的一生。
平路說,一九八三年寫下的〈玉米田之死〉,如果今天來看,其實是某種預知未來的自傳,當時她在美國公司上班,以為自己會一直這樣下去,但因為那幾年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人生的軌跡。那個敘事的主人翁是一個記者,但那時自己根本跟傳播媒體沒有關聯,後來有機會做《中國時報》海外主筆的工作,因此這篇小說對她非常重要,幾乎是一種預言。
另一共同編者童偉格則說,自己過去讀過一些白色恐怖的小說,因此不確定如果全部讀完,會是什麼感想?這有點像參加一個極限運動。他有一個初步的感覺是,質是不足的。白色恐怖小說書寫長期要面臨一個問題:史的匱乏。因為很多素材創作者是接觸不到的,也因為那個時代對書寫的檢查,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作品都是1970年後由小說家補寫的。這跟臺灣社會史的發展是相符的,學者蕭阿勤就講過1970年代是回歸現實,威權政府開始受到本土化運動的挑戰,體制鬆綁的時候,會有大量現場重構的作品產生。童偉格說,不得不承認一件其實有點悲傷的事,威權的治理對文學的書寫產生很大的傷害。從50年代一路讀下來,直接反應現場的作品幾乎就像是不存在,意思是它被洗乾淨了。這是一個怪異的記號。這像是沒有證物的證明,沒有屍體的死亡。這是他的編序之所以定名〈空白及其景深〉的原因。
童偉格在編選過程也發現到,臺灣文學在70年代在現代主義的影響下開始成熟,這些以現代主義為核心的作品,希望寄存相對普遍化人性的描述,造成詩的壟斷的現象,這些作品在修辭與美學上的一致性,因此通常會選到比較深沉、內省的作品。它會寄存那個時代的身體感受,但一切細節卻像霧中風景一樣。他強調,集體記憶與集體歷史真相是兩回事。集體歷史真相縱然不明,但重新建構的集體記憶仍會反應某種形式的真實,甚至是夾帶面向未來與文學讀者的建議。
因此關於四卷本的架構,做為編者唯一能做的一件虛構的事,是找到一個架構誠實反應這樣的傾向。把全部作品總結在一起,去定義所有這些作品在建議的事情。在現場敘述已經相對薄弱的情況下,能做的是空白以及空白的景深,去探討「白色恐怖將可能是什麼」。童偉格坦言,四卷本的框架其實是冒險,他一直期待讀者問他一個問題,你將不會被認為是白色恐怖的作品也選進來了,照你的詮釋,是不是所有臺灣小說都是白色恐怖小說?對此他自己認為,只有在這個情況下,只有在無法明確定義的白色恐怖這個概念的最大容量,才能讓白色恐怖這個詞不斷被討論。
至於美學與政治的辯論,童偉格說,這兩件事無法簡單分割。就像美國學者厄文.豪(Irving Howe)在評論南非小說家柯慈時,就提到為什麼大家會認為在文學當中排除政治是一種美德呢?他引用班雅明對法西斯政治的見解,說明美學與政治的關係。班雅明認為法西斯是一種浮誇的戲劇,不是話語或辯論的形式。這個政治就是一種美學。這個政權的精神治理要怎麼看到?就在再現民眾與他們自己的方式上,如穿特定的服飾、特定的標語等等。藉由民眾不斷看到自己的形象,確立統治,互為鏡像。因此極致的政治性就是一種極致的美學性,反過來說也是可以。童偉格強調,相對優秀的小說很難將政治性從小說分割,如果把柯慈那些美到不行的小說的政治性拿掉,就像拔掉老虎的牙齒一樣。因為所有內省、孤絕的作者,都不願意放棄對群體連帶的想像,否則所有作品不用這樣費力地被書寫出來,就像現代主義的核心代表郭松棻,把他列在開篇之作是一個故意的選擇,正是因為這是一個索引,最極致的政治性就是最極致的美學性。
童偉格最後說,也許有人會問,正義難道不是要在現實世界尋找嗎?為什麼要在文學?他說明,文學所留存的是複雜的失敗,選集提供的是思考的建議。他也強調,他不認為以白色恐怖命名這些小說,就會傷害這些小說,如果這樣看待是太看輕這些小說。他希望,文學是以自身的複雜度陪伴那個長久沉默、一再被傷損的白色恐怖的事實,這是文學對於一個已經流失的現場,僅僅只剩下索引的名字的基本維護,而如果連白色恐怖都不能提起,甚至認為是貶抑,這是他個人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兩位編者都對所有戒嚴時期的作品是不是都是白色恐怖小說進一步回應,胡淑雯說她很長一段確實是這麼想的。童偉格則說,他確實真誠地這樣覺得,因為所有創作都是白色恐怖成為集體經驗後創作出來的,事實上所有不被記憶的屠殺、傷亡會奈米化,覆著在我們的語言與身體上,沉澱在我們四周。而如果文學負有任何公共義務或責任,那麼就是將一切表達正常化,這套選集僅僅是一個起點。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