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公众号同主页名
双城记23:回归
亲爱的小小刘,
上一封信里,我将自己在英国的流浪地图铺在了你面前。如果按照时间顺序,这封信的标题应该是“牧羊少女奇幻之旅”。

我住进了英格兰乡村一栋600年的老房子里,过上了给羊挤奶给马喂草的田园生活。1.5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后院里,种了一年四季餐桌上的美味,光苹果树就有二十多棵,落在地上的苹果多到我和另一个法国女孩捡了一上午也没捡完。

我在这里做大自然的孩子,向明年就迎来金婚的老夫妇学习如何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隔三差五被英式幽默挠痒痒,视觉和味觉也经常被眼前的食物惊吓、惊艳。

但这封信我决定先不讲这段经历,因为就在过去一周,如我一样计划回国的人经历了情绪的过山车。12月20号英国爆出病毒变种,全国进入严格封锁,24号中国外交部宣布中英之间航线暂停,三天后,中国民航局把停航时间正式定为12月28号到明年1月10日。
我们这群想要归巢的人,有人在打包行李时收到了航班取消的短信,有人握着12月27号的机票颤颤兢兢,有人是29号的飞机,打电话向大使馆、外交部、航空公司确认,结果三方互踢皮球。官方消息和实际操作之间的空隙,寄存了很多人的困惑、绝望和希望。

一个多月前在那栋老房子里,木头在火炉里燃烧,散发出烟草和香草的混合气味。我盘坐在夫妇俩用自家羊身上的羊毛做的地垫上,借助微弱的wifi信号成功订下了一张回国机票。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订机票了。此前几张都因为中国不接受中转以及取消直飞北京航班等政策而“胎死腹中”。
这张机票又像一场赌注,只不过这次我赢了。

一周过去了,那张12月20日的机票还夹在我的护照里。
出发前一晚,英国新闻里都在放首相宣布全国封锁的消息。他的头发依旧像刚被九级大风吹完,只不过这次没人再有心情调侃他的发型了。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刚刚经历了一场龙卷风。
我看着自己一大一小两个行李,感慨从来没有坐飞机这么紧张过。这种紧张不仅是担心下一秒手机就收到携程的短信,更是因为过去的努力把期待的气球吹到经不起一丝摩擦。
我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熟悉英国NHS(全国医疗系统)的预约程序,在“核酸检测”的微信群里,大家分享着几点刷网站能抢到预约号的攻略。11月14日,中国大使馆突然宣布不接受NHS的检测结果。免费且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不被承认,大家只能开始寻找收费昂贵的私人诊所。
双阴性的新要求也同时出台。我没时间去弄明白IgM和IgG抗体到底有什么区别,只知道大使馆只认IgM。和之前找好的诊所确认,对方只能提供IgM快速检测,而非大使馆要求的实验室检测,于是搜寻工作再次启动。

解决了远方抛来的难题,还要应对本地布下的陷阱。
大多数英国私人诊所提供的都是2天出结果的标准服务和第二天出结果的加速服务。大使馆说双阴性结果在两天内测都可以,但是我却不敢选两天拿结果的套餐。我周五检测,正常情况是周日下午6点出报告,而我的飞机是下午1点。因此大使馆的两天和诊所的两天并不能完美对接,导致中国人只能选加急服务,这样就要付双倍的钱。
此外,我选的这家英国私人诊所——也是很多在伦敦的中国人的选择——在检测当天告诉我正常的报告上不包括中国大使馆要求的护照、检测日期、报告日期、医院联系方式等信息,要单独购买医生出具的“适合飞行”证书才行。
“很多中国人都买这个证书,所以我看你的护照才问你是不是需要。”接待我的前台小姐腼腆地笑道。她确保我能顺利登机的关切,让我没犹豫就又交了10英镑。
检测完回到家,我看了一部叫做《race across the word》的真人秀。五组英国人不能坐飞机,没有手机,只给2500英镑,比赛谁能最快从墨西哥的首府墨西哥城到最南端阿根廷的乌斯怀亚,这当然是在疫情发生前拍的。

比赛到了第52天,最先到乌斯怀亚的两组选手在做最后冲刺时,有的把旅行包丢到了街边的酒吧里,有的一边跑一边在路上扔大衣扔书包,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一定要赶上离开地球的末班车一样。
我很能感同身受。检测做完了但还没出结果,不顾一切地跑了那么久,到底能不能拿到大使馆的绿码,那刻的我,不成王则成寇。

第二天醒来,手机里已经收到了两个检测的结果,比规定时间提前了11个小时。按照这样的实际速度,如果我选两天的正常服务,也许也可以顺利登机。但此时,鼓胀的气球里容不下“也许”。
我又对比了检测报告和发给我的飞行证书,下面信息栏的内容一模一样。我摇头轻叹,10英镑够我从超市买一周的菜,但此刻比起五分钟将近人民币3000元的检测费来说,它的损失好像必不可少,又毫无意义。

去机场的那天,正是英国严格封锁开始的第一天,伦敦从第三等级升至第四等级,人们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出门,除了超市药店等必要服务,其他零售一律停业。
来接我的司机kai是孟加拉人,十八年前来英国读书后就留了下来。他上周刚从里斯本回来。
“我不用隔离,因为英国规定只有从某些高发国家回来才需要隔离,里斯本不在那个名单里。”
对kai的说法我不能百分百确认,我关心的更多是中国政府的要求。但上一任房东的儿子不久前从意大利回来,飞机降落在伦敦,却可以回伯明翰的家里隔离。房东也很纳闷,那我儿子从伦敦一路坐火车,真要携带病毒传染给别人怎么办?
所以对于英国的封锁以及隔离,我的感受是,政策和现实是两个平行世界,能否连接起来靠的是自觉。

上车没多久,kai就把一个装着三明治的餐盒递给后座的我,“你吃了没,要不要拿一个?”我九点多叫的车,那时他还没吃早饭,所以只能打包带到车上。
我舔了舔牙齿,确保刚吃过的菠菜没在上面,笑着谢绝了他的好意,但又马上意识到,他根本看不到我的笑,更看不看我牙齿上有什么。
口罩遮蔽了交流的礼仪,却拦不住思维的惯性,我脱口而出,你要是饿的话赶紧吃吧。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kai再没戴过口罩。时而咬一口三明治,时而喝几口咖啡,等红灯时再拨几瓣橘子,每次都不忘问我要不要。
英国人,就算表达善意也和这里的天气一样,湿哒哒的。此时,南亚人的热情像雨后彩虹,虽然明知也许有1%的危险存在,但我仍想让阳光在身上多停留一会。
kai除了对人热情,对他的信仰亦是如此。一路上和我介绍伊斯兰教的历史,为什么它比犹太教好。他总以“你知道吗”开头,又以“你不知道”作为逗号,引出更多观点和解释。
当他沉浸在自己宗教的伟大而错过去机场的高速出口时,我意识到kai不是一个司机,他更像一个布道者,而我也不是收集故事的采诗官,我是一个要追上末日列车的人。
于是我打开手机导航,盯着上面的红点,再没留意kai说了什么。

早上11点不到的希思罗机场,乍一看和15个月前我到英国时没什么不同。但值机台一个个看起来像售票窗口,中间隔着一个玻璃板。飞中国的航班,还要扫中国海关的检疫码填写资料,否则上不了飞机。
有一个阿姨,因为机场wifi信号弱网页打不开,工作人员又忙于应对其他旅客,导致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手机网络填不了表,这样回不去国,你要让我怎么办?!”声音大而不泼,但感受得到声带颤动中的焦急、无助。

安检时,旁边一个中国女孩因为一直在用微信语音告诉朋友机场免税店关了,买不了化妆品,以至于忘记把手机放入安检筐。安检大叔大声地说,你怎么能一直盯着我看呢,连手机都忘了,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让我怎么办?!
他夸张且带点口音的英语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在法国,我站在喷泉前照相,一个跑步路过的大叔直接冲到我身边,大笑着把双手高举过头顶,留下了一张即兴创作。他带来的“笑果”,伴我一路走过梧桐铺就的香榭丽舍大道。
这次的笑声,希望能穿越云霄,带我回到大陆的另一端。

在英国总感觉祖国很远,回国的不确定更让旅程变得如梦似幻,然而吃了两顿饭,看完半本小说后,飞机逐渐和窗外的风景连成了一条水平线,我才相信自己是真的到家了。
只不过这个“家”暂时是上海。

浦东机场的2号航站楼就像为我们开辟的vip通道,除了这个航班的人看不到其他旅客。
到隔离酒店前要经过五关。
首先是检查护照和登机前填的海关健康申报码。桌子连成一长排,被隔成十几个小空间,柱子上贴了中英日韩四国语言标注的提示——“不能拍照”。
一名戴着护目镜、口罩,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他递过一张纸,上面列着一些过去一周是否发烧、是否去过密集场所的检查项。
“你不用填,就顺着告诉我是和否就行。”他拿笔一项项指着问我。
上面的印刷字已经不是很清楚,纸也起了毛边,用手揉成一团松开也许都不会留下痕迹。这张纸不知听过多少人的回答,又逮到过几次“是”。
接着是取抽血用的试管。
我们旁边站的是这架航班的机组人员,其中一个亚洲面孔的空乘懒懒地招呼其他英国人把手机里的二维码拿出来,原来他们也得要这个码。当这些人回国,面对英国机场入境没检查秒过的速度,是要点赞呢还是摇头呢?
拿着装试剂的塑料口袋,我下电梯绕了一圈找到了位于室外的白色板房。
里面是或露着胳膊或仰着头待宰的一只只“羔羊”。这里的环境让我想到小商品批发市场,摊位鳞次栉比,熙攘嘈杂。指派你到哪里去的引导声,护士“张大嘴张大嘴”的指令声,好像她声音越大,你嘴就能张得越大。当然更多是“羔羊”们的呻吟声。
我分到门口的第一个护士,她把棉签伸进我鼻子后出来棉头全是血,我以为这一定是够深够准,谁知旁边一个看起来像主管的老师说,“方向不对,再来一次”。我哭笑不得,赶紧抽出纸巾揉揉鼻子。四天前在英国诊所采集用的棉签更细,刺痛感像轻微电流穿过,而这次电伏则提升了几倍。
主管老师不放心,把着护士的手在我右鼻子上演示,还一边说,“插之前你和她耳根比着,呈90度,这样下去。”
我感觉自己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到了护校的实操课堂,只不过这次我变成了小白鼠。
轮到左鼻子了,护士按照老师的要求在空气中比划,嘴里小声嘀咕,我是这样插下去的呀。老师也许是个急性子,再次亲自示范,免去了我重蹈覆辙的痛苦。
检喉咙时护士让我把嗓子润湿,我要喝水她又不让。我只能在一片干涸中寻找“水源”。
“唾液不能咽下去。”她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好吧,“踮着脚尖”继续求水。
棉签第一次从喉咙里出来时仍是鲜红一片。护士说我痰不多不行。
“我们要的不是唾液,不是鼻涕,是痰!”主管老师的声音敲击着空气中的分子。
她走到我身边看到护士满脸愁容,再次披挂上阵。
“来,多咽几口吐沫。”主管老师说。
悬在嗓子眼的那抹湿润看向一旁的护士,如果它能说话的话,一定是what the f*ck?!
“这里面全是痰啊。”老师重重地刮了几下结束了这场闹剧。
胳膊的血抽了,不是胳膊的血也流了,我抓起书包逃出了这个“实验室”。
最后两关是海关检查和非本地人员分流,在上海没有家的我被告知向右走。
出机场前的大厅里,“疫情不退 我们不退”的蓝底海报和机场蓝色的安全线融为一体,更衬出那个显眼的红色横幅——“青年突击队”。
在我身边来回穿梭的这些人,穿着防护服,远看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更不用说年龄了。就像一路上大多数工作人员,留下的只是一个白色身影。有时他们快走的脚步,轻拍彼此肩膀的动作,也许暗示着层层包裹下是个年轻的灵魂。
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庞大抽象的国家权力和微小具体的无名个体,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正常情况下,你注意不到这些人;非常时期,他们被推到前面,变成了第一道防线。

没人通知我们要去哪里。上了大巴车,司机之后的两排都是空的,且从第三排开始拉了一个白色帘子,我们根本看不到前方的路。
中午的太阳从侧面的窗户照进来,和我并排坐的一对情侣,男的说,好久没看到阳光了。
是呀,在头顶盘踞数月的那片阴云终于散去了。
窗外的景色逐渐从楼宇变成了农家乐,闪过的全是一栋栋二层小楼,不知道这里的小卖部还能不能找到汾湟可乐或者健力宝。
半梦半醒,不知道车开了多久,当我以为自己都快到北京时,它停了下来。
左边窗户下,一个人站在楼门口,像极了我在云南农村小路上偶遇的村民,一身深色西服,里面是一件v领毛衣,边走边抽烟,好像身后就是自家的客厅。
一直被帘子挡着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中门进入了我们这个“毒气室”。他全副武装,上来就宣布,“各位同学,我是当地民警,现在代表有关部门给大家宣读注意事项……”。原来一路上我们是由民警保驾护航的。
填表、交钱、加微信,一系列动作之后我拿到了一张写有1112的便利贴。工作人员手一指,我看到了那个离大厅最近的房间,门还半开着。
我下意识担心,离门口这么近会不会吵啊,但又一想,连门都不让出,谁吵你。

房间里的电视在放一部没看过的国产谍战剧。不知道是为了迎接我特意开的,还是在等我们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聚在这里打发时间。

这是一间普通的大床房。但它留有很多空白:厕所洗手台上空空如也,超大的双人床上只有一个枕头,桌上没有酒店通常配的额外服务收费表。
有的是几个白色塑料袋,其中一个里面放了洗漱用品,牙膏牙刷套装加起来正好14个,到隔离期结束。拖鞋手纸和纸巾打包在另一个口袋里。还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酒精棉、可溶性泡腾消毒片、体温计和黄色医用塑料袋。

床头多了几张打印纸,是隔离期间的告知书。一行字特意用黑体突出:
“每天晚餐时送一次快递。不接受外卖、需冷藏或容易腐烂的食品。”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接下来的14天里,“快递”是我们和外面世界产生物理连接的唯一方式。
稍微习惯了这间房,又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它如亚洲女性的年龄,带着一丝神秘。
这间房看起来很新,像我入住前一秒刚整修好。原木色的地板看不到一丝划痕,桌上一擦也没土。
但房间的棕红色大门上能看到“装修”留下的粉尘,厕所的门上也浮现细小的白色颗粒。走廊里铺的灰色薄地毯,上面也像撒了一层白灰。大堂的前台——如果能称为前台的话——全用黑色白色的塑料布罩了起来,连吊灯也不例外。
难道是像方舱医院一样拔地而起的“方舱酒店”?

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传到网上,手机自动获取的地理位置写着:崇明岛。
“荒岛”生存开始了。
但其实这里更像疗养院。
一天三顿饭有人准时来送。有时是按门铃或敲门,有时则顺着走廊一路喊“送饭了送饭了”,有时静悄悄但到点一开门,饭就在凳子上放着,还很热乎。
这些细微差别也许说明轮班送饭的至少有三个人?但每个进入这栋楼的人看起来都像一个人。

开门拿饭,看到工作人员还在走廊里,我会下意识说声“谢谢”,但往往没有回应。我猜是因为防护服把耳朵都遮了起来,再加上不是面对面这样的距离,导致这些感激只能留在听不见的时空里。
房间不会有人来打扫,我们的生活垃圾一律扔到自己的房门口。工作人员会在送三餐的时候清理。有时扔出去的垃圾上面出现了一层“水珠”,有时则是垃圾不见了,留下湿漉漉的一圈。
我恍然大悟,原来屋里屋外那些白色粉末不是灰尘,而是消毒水在一个地方多次喷洒后的结晶。
隔离的一天被分为上午八点、中午十一点半、下午两点以及晚上四点半。因为这时会有人来“探监”——送饭或者量体温。
当然不仅有人,有时还能招来意外惊喜。

我用一包榨菜首先俘获了棕猫的心,不久它又带来了黄猫。
黄猫明显更馋,或者说更矫健,竟然蹿到台阶上。但它从窗户跳不进来,因为这扇窗最多能开到四个手指伸平那么宽。为了保持“社交距离”,我用筷子扎了吃的送出去。

就这样,每天又多了两个来探监的“人”。有时候它们吃完就蹲坐在我窗前,不叫,也不离开。

住一层的另一个好处是“隔离”感不是那么强烈。向远处望去,如果忽略中间的窗户,我好像就站在篮球场旁边。

上下班的工作人员也会三三两两从窗前经过。虽然他们都戴着口罩,但相比走廊里的“宇航员”,此时是我离正常世界最近的时候。
这里面会不会有每天给我送饭的人?会不会有冬至那天给我们包饺子的人?会不会有每次都把素菜单独打包装盒,再把“1112 吃素(鱼可以吃)”的便利贴订在送餐口袋上的人?会不会有寒流来袭,在微信里面温馨提示我们的人?……

在疗养院的第一晚,我裹着厚被,忍着时差带来的头疼,看完了飞机上看的那本小说。这是我最爱作家的最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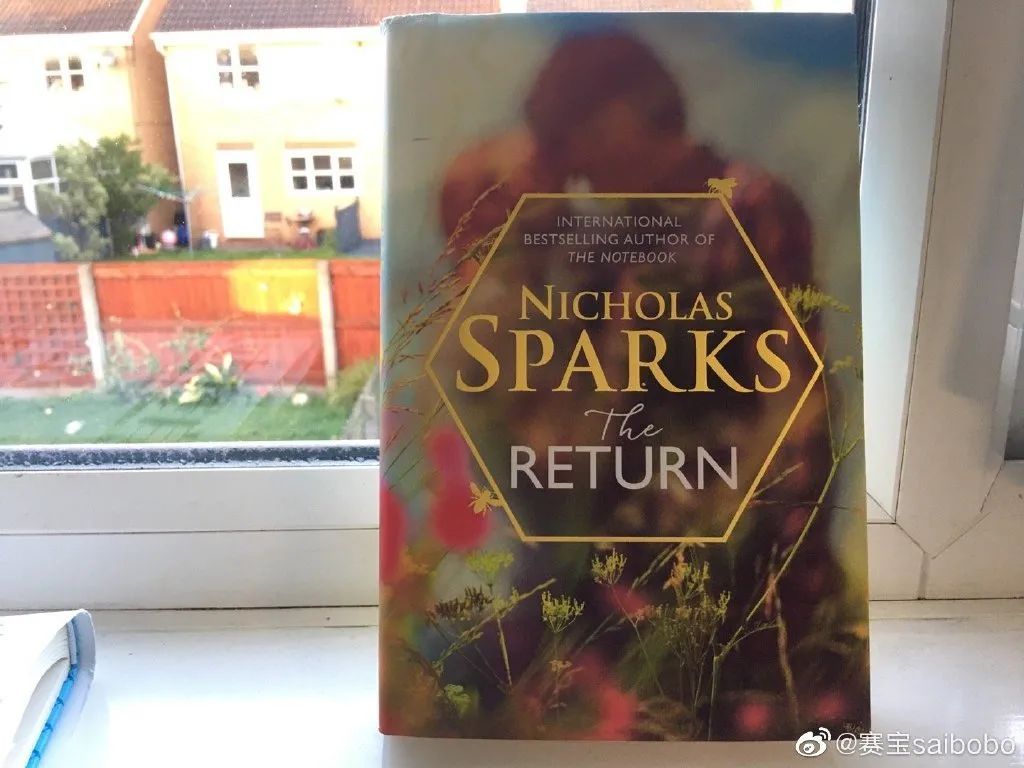
在英国伯明翰下午四点却如半夜的寂暗中我翻开第一页,在云霄上对准微弱的头灯穿越到了故事里美国东海岸的小木屋,现在在宽敞到能打滚儿的大床上合上了最后一页。
窗外仍是一片寂夜。
The Return(回归),正如书名一样,我也经历了一段离开再回来的旅程。回到最熟悉的土地,带着孩子扑向母亲的亲昵,又怀揣着像新冠下不知道要不要伸出去握手的谨慎。
这片土地,孕育着一幕幕令人激动和感动的欢愉,又暗藏着一次次被消音、被禁闭的伤痛。
黑与白,冷与热,强大和卑微,赞许和失望,都最大化地存在于这片土地之上。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我声称的是要充分活出我所在时代的矛盾(What I claim is to live to the full the contradiction of my time)。
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我想这正是这次回归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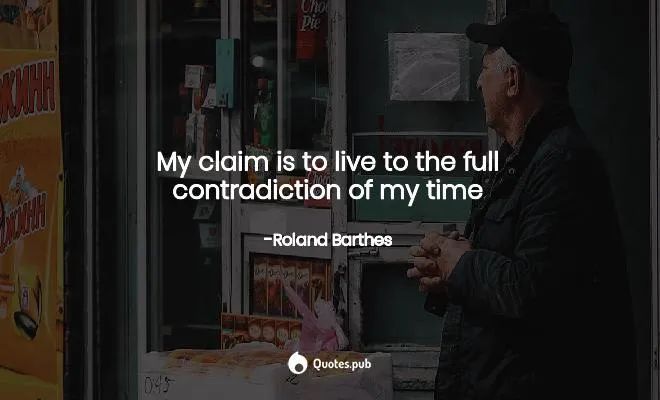
---------------------------------------- 回信 -----------------------------------------
亲爱的大赛,
此时此刻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了。
由于英国疫情病毒变异、又有之前几次航班取消的阴影,一直为你这次飞行担心,好在有惊无险、按时起飞,也算是赶上了最后来自英国飞机,这次的确受到了神的眷顾。否则的话,简直不可想象,真是后怕。
之前在农场的各种体验,我觉得挺好的,虽然有些累,但对你这个城市里长的的孩子来说是难得的体验机会,各种第一次,还有两位有知识又风趣幽默的老夫妇…
你主要给我们讲述了下飞机后的各种检测、到酒店后的隔离生活,虽然有些地方还做得不够好,但我希望你还是多一点理解、多一些包容
你的隔离生活被你调侃成疗养院生活,的确,在你这个年龄的人,要不是疫情隔离需要,难得会有这样理所当然的、有吃有喝、还有猫的清净生活,看书、学习、写作,很是惬意…
再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闻到熟悉的气息,一定感受颇深,在这安静的环境中,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往后的人生道路…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